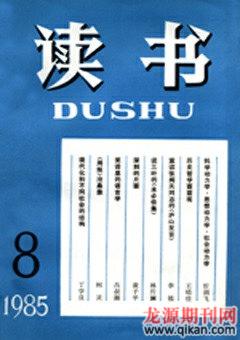歷史哲學面面觀
王晴佳
在歷史學家看來,歷史學是有關事實的學問,何用哲學?哲學家則認為:哲學本來是無所不包的,何必要加一個限定詞?自從伏爾泰第一次使用“歷史哲學”以來,這樣的疑問、爭議、斥責在西方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以這樣說,沒有一門學科象歷史哲學那樣,有著如此激烈、如此長久的爭論其本身存在價值的歷史。
上海兩家出版社近幾年出版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以下簡稱為《文選》)和《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以下簡稱為《文集》)兩本書,為我們展現了這一歷史中分外復雜、卻又興味無窮的一段。
克萊奧——科學還是文學?
歷史女神克萊奧,原是古希臘九位文藝女神中的一位。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在西方史學發展史上,即使在科學君臨一切的十九世紀,對于歷史學是科學還是文學的爭論仍然沒有停止。十九世紀末,英國史學家約翰·布瑞為鞏固歷史學的科學地位,曾發出“歷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學”的斷言。然而時隔不久,他的同胞喬治·特里維廉在一九○三年便發表了《克萊奧,一位繆司》的反駁論文。如果說布瑞的文章中洋溢的是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熱情,那么,特里維廉則帶著對此不屑一顧的態度開啟了二十世紀多元歷史學的大門。難怪二十世紀的哲學大師伯特蘭·羅素、卡爾·波普爾都贊同或者傾向于特里維廉的觀點。然而,在時間上對文化的發展作絕對的區分畢竟是片面的,思想意識的發展是緩慢的積累的過程。正象現代西方美術有它的塞尚那樣,現代西方歷史哲學也有其先驅。被稱為“德國現代哲學之父”、在《文選》中名列第一位的威廉·狄爾泰,便是這樣的一位先驅者。在《夢》一文中,狄爾泰運用幻想和離奇的文筆,描繪了兩個虛幻的夢境,體現了自己的哲學觀和歷史觀。狄爾泰認為,無論是企圖尋找規律的唯物主義、實證主義,還是滿足于對“人性中神意”探討的唯心主義,都“是建筑在有限的認識力和宇宙之間的關系上的。這樣一來,每種世界觀都在它自己的范圍內反映了宇宙的某一方面。就這一意義來說,每種世界觀都是正確的。然而無論如何,每一種世界觀卻又都是有其片面性的”(《文選》第7頁)。在這里,我們觸摸到了跳動在現代西方文化中的脈搏。狄爾泰較早地表述了歷史觀的多元性和認識論的相對性思想。作為一個反實證主義哲學家,狄爾泰還區分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他稱之為“精神科學”)的界限。自然科學有其因果規律,在精神科學中,一切都是相對的、個別的。歷史學家的任務是“理解”過去,深入體會個別歷史現象的精神,而不能企圖作什么規律性的概括。《夢》便是他對作為精神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認識。現代西方史學盡管在方法上吸取了大量自然科學的成果,在歷史觀上卻再也找不到十九世紀那種以尋求規律性為己任的精神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狄爾泰開辟了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先河。
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亨利希·李凱爾特發展了狄爾泰的歷史理論,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歷史哲學。李凱爾特著重從方法論上把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作了區別。他認為,自然科學家所面對的是一般的概念,而歷史學家則是對個別的、不再重復的歷史現象作研究。這種個別的、不可分的歷史現象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是因為它們與某種現實的價值相聯系。這種價值并非人們常用的好與壞、高與低等的價值觀念,而是歷史學家選擇史料時的判斷標準或取舍標準。于是,在李凱爾特看來,歷史是現實科學(《文集》第37頁)。他用“價值”這一觀念補充了狄爾泰提出的歷史相對性思想。然而,就李凱爾特的本意而言,他是力圖運用此番論證來維護他心目中的歷史科學的。這就說明,二十世紀初期的狄爾泰、李凱爾特等人盡管強調了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但仍然不想把歷史學劃出科學的界限以外。他們是反實證主義的哲學家,然而卻只能在實證主義總的精神下進行反叛。這種文化的“滯后”現象提醒人們:思想家的智慧和思辨不管多么復雜、多么深邃,與復雜的歷史現象相比,卻常常是幼稚的、近視的。
整整半個世紀以后,在當代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歷史作為一種藝術》的講演中,人們已很難找到李凱爾特等人的模棱兩可了。羅素以一個過于謙遜的開場白開始他的講話,卻表達了直率的思想:歷史何必要成為科學,作為藝術它也同樣有、而且將來也還會有著自己的存在價值。請聽他的議論:“歷史必須不僅使那些由于某種特殊原因而希望知道某些系統的歷史事實的人感興趣,而且使那些以讀詩歌或讀好的小說的態度去讀歷史的人,都感到興趣。這就首先要求歷史學家對他所敘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應該懷有感情。……從這個意義上說的不偏不倚的歷史學家,將是一個枯燥無味的作家。”(《文集》第137頁)從這些思想出發,羅素已經不僅丟掉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和歷史學家(盡管他不能算是歷史學家)的科學態度,而且拒絕了對歷史真相的追求。他援吉本為例,認為吉本作為一名杰出的歷史學家,盡管把他筆下的人物都涂上了十八世紀的色彩,卻仍然能給人以一種“非常逼真的感覺”。羅素的歷史哲學反映出當代西方文化在經過一次大戰前后的動蕩和不安之后,已經徹底擺脫了十九世紀實證主義哲學家把任何學科都納入科學殿堂的企圖,尋找到了新的立足點。那就是,任何個人、任何學科都有其本身的存在價值,這種存在價值沒有外部的、單一的標準,而在于其內在的合理性或者合意性。一句話,主觀的東西非但不用服從客觀真理(許多人也不再承認有客觀真理),而且正因為是主觀的,才是屬于人的、現實的。
了解了羅素從一個歷史“消費者”的身份對歷史學的議論之后,再回過頭來看一下特里維廉的文章,或許會有新的感受。特里維廉缺少羅素的幽默和熱情,但也無愧于作為馬考萊的侄孫。在我們看來,顯然,羅素、特里維廉以及狄爾泰、李凱爾特等人的論點難于全予首肯的。馬克思主義引導我們的歷史學走上了科學的道路,它也將引導我們從五光十色的西方歷史哲學中,找出它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并且在堅持發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同時,吸取西方歷史哲學中的合理成分,不斷更新自己的歷史理論,拋棄那些陳腐的說教和教條,換之以活生生的、有說服力的歷史內容。
歷史的規律
用“歷史的規律”這樣一個我們十分熟稔,而在現代西方頗多歧義的概念來繼續我們的評述,有些困難。在我們看來,歷史存在客觀規律,我們運用科學方法揭示這種規律,是歷史學的科學基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現代西方文化中,已經很難找到此種信念。象歷史決定論這樣的字眼,西方思想家幾乎無人能夠接受。英國哲學家,當代西方歷史哲學最有代表性的雜志《歷史與理論》編委埃西亞·伯林斷然說,如果承認決定論,那么人們“想些什么,感覺什么,談論什么,以及如何想、如何感覺、如何談論,這從心理上說,幾乎已不可能,就如同(比如說)假設我們生活在一個空間、時間或通常意義下的數已不復存在的世界中那樣,是行不通的。”(《文集》第195頁)不管我們對此如何評價,從中顯然可以看到現代西方思想家對十九世紀實證主義深惡痛絕的態度。的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沖擊的現代西方文化意識已經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代大不相同了。在十九世紀,先是黑格爾,后是孔德,都把人類歷史看成是一個有規律的向前發展的過程,而他們自身所處的時代是其完美的最高階段。同時,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特別是牛頓、拉普拉斯的科學假設,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強了此種信心。時隔數十年,世界大戰的爆發、特別是物理學的嶄新突破,導致決定論作為經典自然科學的理論表現的破滅。這一系列事件使得他們不得不從美好的遐想中驚醒,面對嚴峻的現實。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所說的:“如果連所謂精密科學都失去了決定論的嚴格準則,那么它們在那些永遠不能求得精密性的科學中又怎能保存呢?”(馬夏爾:《科學方法和經濟學》)于是,一切以往的確定的、一元的概念都被拋棄,余下的則是存在多種發展趨勢的世界與人生。從這一背景下來認識西方歷史哲學家對歷史規律的態度,就比較易于理解了。
阿倫·尼文斯的《歷史和教條主義者》一文,反對歷史的必然性,強調“運氣和意外在歷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以為對于歷史的進程而言,“不測的疾病、氣候的改變、一封文件的喪失、一個男人或女人突然間所產生的一個狂念——這些都曾經改變過歷史的面貌。”(《文選》第282頁)作為一個實踐著的歷史學家,尼文斯寫作了不下十二本傳記,來論述那些“驚天動地的人物”。他贊賞的是這樣一句話:“否認英雄的重要性要比夸張他的重要性更容易犯錯誤”(同上,第283頁)。尼文斯的理論和實踐,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美國現代史學的一種趨向,企圖以對歷史人物的各種分析(主要是心理的和精神的)來展現歷史內容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與尼文斯的坦率相比,哲學家雷蒙·阿隆和卡爾·波普爾以一種溫文爾雅的方式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阿隆認為,在理論上或者原則上,可以承認有一種規律存在,因為可以承認事件之間有其連續性。然而,這種規律不能應用于歷史,更無法推演到未來。他說:“我們越是要求歷史性,合法性也就越是趨向于消滅。因為歸根到底,唯一的、不可逆轉的變化,根據定義是不容許有規律的。”(《文集》第65頁)顯然,所謂“唯一的、不可逆轉的變化”,就是指歷史的發展。再進一步,阿隆又反復強調人們認識的相對性和局限性。在他看來,要想通過認識“一個局部演化的規律來進而求得貫穿全部的時間或一種總體的演化過程”(同上,第72頁),近于玄想。用一句話作為阿隆歷史哲學的總結:所謂歷史規律只是片面的、局部的,要想發現總的規律,唯有碰運氣、或依賴宿命論。
在阿隆的文章中,已經流露出探討歷史規律毫無意義的論點,而卡爾·波普爾尤為明確。依波普爾之見,歷史學家不用企圖象自然科學家那樣進行普遍的認識和一般的概括。歷史學是為了說明特殊事件的科學。令人稍覺詫異的是,波普爾把這種理論看作是對以往歷史學的總結,仿佛歷史學誕生以來只是為了說明特殊事件,這就未免武斷了。
最后,讓我們再來看一下現代西方歷史哲學大師科林伍德的有關論點。作為一名克羅齊的信徒,科林伍德的歷史哲學對現代西方影響很大,而且因其觀點新穎而獨成一說。他對歷史哲學有著自己的理解,然而卻是以犧牲歷史規律性為基點的。他認為,對歷史的規律性認識不是歷史哲學,歷史無法作出這樣的概括。“歷史是一場戲,但這是一場即席演出的戲,是由它自己的演員互相協作即席演出的”(《文集》第152頁)。這是他的名言。因為歷史是一場戲,所以便有整體性,然而演員是即興演出,每一個部分又都是具體的、不可預測的。正是以此為出發點,科林伍德提出歷史學家唯有沉湎于歷史中,重新體驗歷史人物的思想,才能獲取歷史的真義。
事實上,對于歷史規律的承認與否,取決于如何認識歷史的規律性。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如何辯證地認識歷史規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歷史發展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歷史的客觀性和相對性
本尼戴托·克羅齊有一個有名的論斷:“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含義是,歷史學家只能從現實出發研究歷史,而在研究過程中又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無法得知真正的歷史過程,尋不到歷史事實真相。這種歷史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體現了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主要面貌,同時也是整個現代西方文化在歷史學中的反映。美國的L.J.賓克萊在《理想的沖突》一書中曾用相對主義來概括當今的西方世界,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詩句作了這樣的描繪:
“全看你在什么地點,
全看你在什么時間。
全看你感覺到什么,
全看你感覺如何。……
今日為是,明日為非,
法國之樂,英國之悲。……
一切就得看情況,一切就得看情況……”
在現代西方文化中,不僅歷史觀,而且道德觀、價值觀都是以相對主義為特征的。于是,絕大部分西方歷史哲學家都無可避免地丟棄和嘲笑了利奧波德·馮·朗克所倡導的“客觀主義”史學思想和“如實直書”的史學編纂原則。卡爾·波普爾明確說:“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的歷史,只能有各種歷史的解釋,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因此每一代人有權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釋。”(《文選》第155頁)這種說法抹煞了歷史的客觀性,把歷史全部歸結為依賴人的主觀解釋的產物,這是一種明顯的歷史相對主義。然而,比波普爾還要走向極端的還有卡爾·貝克爾。他提出不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而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依貝克爾之見,歷史事件一旦發生之后,便永遠消逝了,人們只是從回憶中來求得其歷史。因此,歷史無異于歷史知識,“歷史便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歷史便無法擺脫主觀性。再往下推論,既然歷史憑藉回憶而存在,那么每個普通人都要回憶,每個人也就是自己的歷史學家。貝克爾正是通過這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論述來展開和證明他自己的觀點。他曾和另一位美國著名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一起,在三十年代的美國史學界掀起了一場實用主義、相對主義的“反叛”。就目前來說,他們當時的“努力”盡管沒有得到多數人的首肯,影響卻仍是巨大的。除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一文以外,貝克爾還有《什么是歷史事實》等文章。他從三個方面論證:所謂歷史事實,也是主觀與客觀結合的產物,歷史事實與其說是某個具體事件,毋寧說是某種象征(見《文集》第227頁)。
一般人常說,美國人除了實用主義以外,沒有哲學傳統,不擅長理論概括,這話說對了大半。就拿貝克爾、比爾德的歷史相對主義來說,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來自歐洲大陸,德國思想家曼海姆就是其中之一。曼海姆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已經提出了“相對主義”、“相關主義”的概念,并且強調: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其嶄新的探索和獨特的見解,并因此而用一種新的角度去觀察‘同一個對象。”(《文集》第49頁)除了說明認識有其“角度”之外,曼海姆還討論了認識中的能動因素和真理的范圍問題。這些都是貝克爾和比爾德理論的直接“觸媒”。不過,三十年代之后,美國擁有了一大批從歐洲逃亡過去的哲學家,這使得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不僅可以與歐洲并駕齊驅,而且在新學說、新方法的提出和運用上,超過了當今的歐洲學術界。
除了歷史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以外,我們還可以在施本格勒和湯因比的著作中發現另一種文化發展的相對主義思想。施本格勒和湯因比都主張人類各個文明的發展有著自己的生長和衰亡的過程,而從整個地球生物史的角度著眼,“一切所謂文明類型的社會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時代性的。”(《文選》第119頁)于是,每個文明的歷史都是相對的,沒有統一的一線發展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施本格勒和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是以相對主義為主要特征的。這是他們的共同點。然而,他們又各自帶有自己時代的烙印。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炮火洗劫的施本格勒,帶著當時許多人所具有的恐懼和不安心理,用一種悲觀主義的態度發出了對西方文明衰落的感喟。與施本格勒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相反,湯因比除了“在這位德國人的先驗論留下空白的地方,讓我們試一試用英國的經驗論來加以填補”(同上)之外,還以“菊殘猶有傲霜枝”的樂觀態度指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創造性活力和神奇光彩。從施本格勒到湯因比,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人生觀和歷史觀。當然,這也是西方文化在經過動蕩、變遷之后逐步得到調整,重新建立起立足點的過程。
湯因比曾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國際上的智者”。他的文明發展四階段、挑戰與應戰等理論,也曾風行一時。但湯因比的歷史思想并非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的主流。他的那種視野宏闊、結構龐大的理論體系,與當代西方側重分析、探求人的主觀認識奧秘的時代趨向并不合拍。因此,有人把湯因比看作是繼承黑格爾哲學傳統的最后一位大師,不無道理。
總之,現代西方歷史哲學家強調人的主觀性、認識能力的有限和主體與客體的相互聯系,否定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直至否定歷史真理的存在,流于歷史相對主義。毫無疑問,克羅齊是較早接受和宣揚歷史相對主義的思想家,但比他更早的還有德國的狄爾泰、文德爾班等人。克羅齊之所以比他的德國前輩有著更為巨大的影響,我們可以引E.H.卡爾的一段話作為參證:“這也許不是因為克羅齊跟德國的前輩比起來,是個更為精明的思想家,或者是個更富于文采的學者,而是因為在第一次大戰以后,事實向我們投過來的笑臉沒有1914年以1前那么慈祥了,因而我們便容易接受一種有意貶低事實的威望的哲學了。”(《歷史是什么?》)這一現象再次體現出文化背景對思想家的巨大制約作用。
歷史的意義
在了解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家貶低歷史學的科學性,摒棄歷史規律性的反實證主義、非理性主義傾向以后,再來看一看他們對待歷史的意義的論述,本身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所謂歷史的意義至少包含兩層意思,正象W.H.沃爾什所說的那樣:“在歷史中尋找意義是一回事,追索歷史的意義卻是另一回事。”(《文集》第216頁)實際上,歷史的意義既包括歷史本身的意義,同時又含有對歷史學的性質、功用等問題的探討。
W.H.沃爾什是當代西方“分析”歷史哲學的倡導者之一,他的名著《歷史哲學導論》既有對歷史事實和真理、歷史的客觀性、歷史的解釋等問題的探究,也有對黑格爾等人思辨歷史哲學的批判。在他看來,黑格爾、孔德等人只是臆想出一個歷史發展的模式,用來強加給歷史,而“事實的海洋是那么廣闊,不管一種見解是多么荒謬絕倫,要想釣取幾個事實或其它東西證明它有理,無論何時都是可以辦到的。”(同上,第220頁)沃爾什批判了思辨哲學家是形而上學地尋找歷史的意義的方法,自己卻沒有對歷史的意義作明確的解答,只是含混地表明,歷史學家的工作(對歷史事件的說明)本身就表明歷史有其意義。
事實上,不承認歷史發展有其因果聯系和規律性,也就是否認歷史有意義。然而,饒有興味的是,大部分西方歷史哲學家并不屑于去追尋此種歷史意義。波普爾就明確說,要是這樣去做,歷史便沒有意義。但是,他進而說道:“歷史雖然沒有目的,但我們能把這些目的加在歷史上面;歷史雖然沒有意義,但我們能給它一種意義。”(《文選》第166頁)由此,我們能找到西方近代和現代歷史哲學的重大差異。嚴格說來,西方歷史哲學誕生于近代,其主要動因是為了探索歷史的規律性,即歷史的意義。然而,到了現代,在認識了人的有限的認識能力和歷史的無限發展之間的矛盾之后,西方歷史理論家不再希圖去揭示普遍的歷史意義,而專注于對局部歷史現象的說明,并認為這就是歷史的意義。于是,歷史哲學的重點也就從歷史本身轉到了歷史學的性質、作用等上面。這是所謂“分析”歷史哲學的主要特征,也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主要趨向。
請看歷史相對主義者貝克爾的“慷慨陳詞”:“把歷史看作已過去的現實的一種緊縮而不完備的表述,一種經過重新設計、新加染色來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記得的事情的不穩定型式,并不一定會損害歷史的價值和尊嚴。我們歷史學家的辛勤,也不因為我們任務的局限性,及我們的貢獻只有一時而偶然的重要性而貶低價值。”(《文選》第276頁)無論是波普爾的“給予意義”還是貝克爾的“重新設計”,都說明,歷史的意義在西方已變得如此具體、如此實用。
由此,我們便容易理解克萊奧女神為什么在經歷了本世紀初期的危機之后,能再度登場,重新抖擻其綽約風姿的道理了。她已經失去了那種冷峻、嚴肅,昭示人類未來的面孔,而代之以和善可愛、服務于人類現實的笑臉了。于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可以把歷史看作是解答人生奧秘,進行自我認識的重要手段,歷史的意義在他看來就在于“教導我們要從人的最崇高的潛力和不朽的創造力來看待人。”(《文選》第36頁)湯因比研究歷史則是為了解救西方文明,“希望在許多不同的文明中把西方文明繼續保留下去。”(同上,第138頁)克羅齊進而認為,只有對歷史和哲學加以綜合,才是真正的哲學,即歷史的哲學。處于冷戰時期的美國現在主義史學家C·李德直接地把歷史看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維護美國的理想和標準(《文集》第253頁)。李德以一個美國人的直率,把他心目中的歷史實用性表達得淋漓盡致。但是,從實用的角度研究歷史,發掘歷史的意義,在現代歐洲和美國都是共同的。
從追索歷史進展的意義到放棄這種企圖,再到賦予歷史以某種意義,西方歷史哲學經歷了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過程。如果說,近代西方哲學是一元的,現代則是多元的;近代是單線發展的,現代則是多中心的;近代是獨斷的,絕對的,現代則是多樣的,相對的;近代是客觀的確定,現代卻是主觀的假設。歷史哲學是如此,西方文化亦是如此。兩者既相互統一,又相互作用。
了解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要了解其文化背景。但這還不夠,還要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與成果。在這方面,西方歷史理論家對于歷史認識論的探究,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另外,我們還可發現,大多數西方的史學理論都反映了并且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目前,我國的歷史學正面臨一場挑戰,原有的信條和方法顯得陳舊,新的卻尚未確立,這與我們當前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時代要求不太相稱。時代要求對以往的歷史作出深沉總結,對現今的改革和未來的道路作出抉擇,這首先是歷史學家、歷史理論家的任務。因此,惟有用馬克思主義深入研究我國的歷史、深入認識我國的文化土壤,并以此為基礎來面對現實、正視未來,才能繁榮歷史學,推進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大業,也許,歷史的意義就在于此吧。
(《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田汝康、金重遠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1.15元;《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張文杰等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