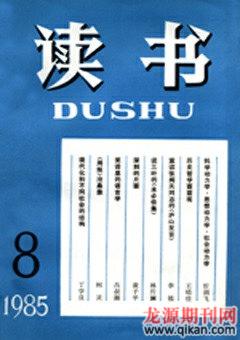科學動力學·思想動力學·社會動力學
忻劍飛
1
哲學與科學——人類智慧的產兒,常常象《舊約全書》中以撒和列伯加的孿生子:以掃和雅各,為爭奪長子權而兄弟鬩墻。當近代科學還在襁褓中的時候,哲學就以君臨一切的姿態,裹挾了科學;而當科學開始以精密的態度審視以往種種哲學猜想時,它一方面正確地摒棄了舊的自然哲學,另一方面卻又開始拒斥哲學……,這種現象時起時伏,綿延至今,并未絕跡,不少杰出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在這里留下了令人遺憾的敗績,如黑格爾,如牛頓。
但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西方哲學中出現的科學主義潮流,客觀上卻證實著恩格斯的論斷:“各門科學在十八世紀已經具有了科學形式,因此它從此便一方面和哲學,一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馬恩全集》第三卷第666—667頁)而科學哲學的興盛則為哲學與科學的聯盟搭起了現實的橋。不管這座橋還有多少不盡完美之處,但它在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等方面體現出的社會功能卻愈益顯著,越來越惹人注目。
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出了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在理論上把生產力劃分為兩種不同的形態:一種是直接形態,即直接生產力;一種是一般形態,即一般生產力,科學就在一般生產力的意義上被包括在生產力之內。而科學又可以分為兩種知識形態:一種是作為科學研究成果的科學知識,無疑它的物化就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直接生產力;另一種是作為科學知識的結晶的科學方法,它涉及到科學成就的評價和選擇,科學發現或發明的結構,因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將更為深遠。研究科學方法必須把重點放在科學知識的動態發展上,這就是科學動力學。所謂科學動力學,無非是以科學史和科學思維為對象,進行多層次多側面的哲學思考。當然,這種哲學思考不僅在研究內容和對象上,而且在思維形式和特征上,都離不開科學。科學與哲學的這種互相交融、緊密結合,產生了一門主要是屬于我們這個世紀的學科——科學哲學。
如此看來,說科學哲學不僅是科學動力學,而且也是一種社會動力學,并不虛妄。正是在尋求社會發展動力和推動社會發展的問題上,科學動力學與社會動力學共有著一個出發點和歸宿。
研究科學動力學,努力使之轉化為社會動力學,這個任務對于中國人來說似乎更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人們都說,中國政治化倫理化的哲學傳統曾經阻礙了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達,然而,一旦門戶打開,這種哲學特性卻也鼓舞了人們從新近輸入的近代科學思想中尋找社會動力學的熱情。例如,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曾被人們認作最新的社會動力學。但事實很快證明,問題遠非那么簡單,于是而有了中國哲學界六十多年以前的那場關于“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情況復雜,以往總習慣于把它簡單地視為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們之間的內部爭斗,近來又有人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者在論戰中的作用,于是又把它作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我倒覺得,不如把它主要地看作當時人們對哲學與科學關系的一場大討論,是人們尋求科學的社會動力學的一種表現,不過,那時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已開始大規模傳播,這場討論卻置此不顧,加之中國并無發達的科學,世界上也還并無發達的科學哲學,所以就難免不了了之。半個世紀以后,由于教條地或者是歪曲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觀造成的惡果,由于新的事實和理論大量涌現,更由于人們尋求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現代化歷程的需要和熱情,許多中國人又重新思考社會歷史觀的問題,希望在理論和實踐的活動中構建新的科學的社會動力學,除了對歷史和現實中的大量現象進行再研究(如:重開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問題的討論,重建社會學等等),在理論上,人們大體上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審核我們以往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發掘馬克思思想中更富有預見力、生命力的東西,在新的闡釋學的基礎上,實現“馬克思還原”;二是借鑒現代歷史哲學,湯因比、克羅齊、結構主義等都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三是再一次與自然科學結盟,這次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結合,又引進了當代科學哲學,自然今非昔比。
所以,今天當我們聽到有人尖銳地發問:“我們能否貢獻一個愛因斯坦?”并知道這個問題引起震動和反響的時候,我們無疑感受到了時代的要求。
在這種背景下,讀到邱仁宗著《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一書,首先便在腦際浮現出“社會動力學”這個詞,引出了上面關于哲學與科學分分合合的歷史的感想。以下則試圖從該書對科學哲學的闡述中獲得對社會動力學的新的啟示。
也許這并非出于主觀臆想,因為作者在書的“序”中已明白地說明了科學哲學對于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意義,批評了屬于社會上層建筑領域中尚存在的重大弊病:“我們畢竟與外界隔離太久,對他們的了解很差。更重要的是現在哲學界有些人仍然喜歡作‘語錄式批判。人家說些什么都沒有搞清楚,甚至人家的主要著作都沒有看,就根據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中摘出的幾句話來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地加以‘批判。而有的雜志也樂意刊登這種未經研究的‘哲學研究文章。”開放地汲取外來文化,科學地開展學術研究,大膽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本身也屬于社會動力學的問題。
當然,任何重大的社會現象總是世界性的。自從邏輯經驗主義在新的科學水準上開始了科學與哲學的聯姻(盡管,其中有些杰出人物主觀上還在籠統地拒斥哲學,如賴欣巴哈),幾十年來,科學哲學中一些最著名的代表,如Popper(波普爾),Kuhn(庫恩),Lakatos(拉卡托斯)和Feyerabend(費耶阿本德)等無不喜歡同時談談哲學認識論,方法論,談談社會學、歷史學甚至馬克恩主義,表現出強烈地參與社會動力學的傾向。以致,一九七九年在第十六屆世界哲學會議上,A·帕里加洛夫(Polikarov)專文闡述“支持哲學與科學相關聯的十個論證”,并對未來作了這樣的展望:“科學的現狀將在數十年或更長時期內加以概括總結。在歷史的歸納或重建的基礎上(顯然,這還是較不重視科學與社會相聯系的邏輯經驗主義的提法——引者注),許多現在遮蓋著這個基本過程的東西將作為細節或之字形的東西而得以減少,基本的觀念、傾向、方法和結果將會出現,他們的方法論的和哲學的特點將會更為清楚地突出出來。”(《第十六屆世界哲學會議論文集》第355頁)
看來,科學與哲學的聯盟還會加強,科學動力學的社會功能也還會加強。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下,其表現和特色是不同的罷了。
2
我認為,科學哲學對于人們思維方式的啟示是最值得重視的,尤其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在提倡科學與民主,建設現代化的時代。
試擇其要者,略述一二:
“人可以比大自然喊得更響”——切勿拘泥于經驗沒有一門科學可以完全脫離經驗,然而,也沒有一門科學是拘泥于經驗事實的。拉卡托斯關于人比大自然強的口號,既是對科學家們創造性思維的禮贊也表現了科學哲學家們的共性。對哥白尼革命的紛紜眾說,是最明顯不過的例子:歸納主義者認為哥白尼革命就在于發現了新事實并從事實中作出了正確概括;概率主義者則把它解釋為相對于當時全部可得到的證據而言的結論;否證主義又用否證和判決性實驗的觀點看待它;約定論則認為哥白尼理論比托勒密體系更簡單(第159—160頁)。所有這些解釋,都有其局限性,但人類正是在自己的創造性思維過程中推進了對事實的了解,增長了知識,甚至創造了新的理論、新的學科。當然,這不是提倡“唯我論”,“唯意志論”,而恰恰是基于對作為認識對象的經驗事實的深刻了解。如所周知,現代量子物理學已告訴我們“對任何系統的狀態的觀察,都必須考慮到對這個系統的擾動”(《無數學的物理》),用費耶阿本德的話來說,“證據受污染”是難以避免的。所以,要想使認識有所前進,除了盡可能多地掌握客觀材料之外,更關鍵的恐怕還在于發揮能動性,提出更有前途的假說來。這個問題頗有現實意義,盡管在前些年里,我們較多地看到了唯意志主義、教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大施淫威的惡果,但我們千萬不要忽視歷史表象背后的東西,正是幾千年封建主義禁錮下,小生產的狹隘經驗論的思維方式襯托了某些“超人”的權力意志。另外,從社會科學研究上來看,忽視理論必須要有材料之外的結論,并用這種結論去組織材料,從新角度去分析材料,正是當前社會科學落后的癥結之一,因為,照杜恒(Duhem)的說法,一些最深刻的科學理論具有“糾正事實”的作用(第128頁)。所以,波普爾的口號應當時時記取:“大膽假說,嚴格檢驗”(第61頁)。
“反對科學沙文主義”——追求多樣化思維費耶阿本德的這一意見也與其他科學哲學家基本一致。如果說,強調創造性思維是對人作為認識主體的謳歌,那么強調多樣化思維則是把人的主體性認識特點貫徹到底——誰都有權發揮思想的主體性,但誰也不能壟斷它。在哲學史和科學史上,沙文主義的現象屢見不鮮。但是,一部科學哲學史大體上卻是愈來愈堅決地反對科學沙文主義的。從“現代歷史學派的鼻祖”惠威爾(Whewell)的關于科學發展的支流—江河模式,到邏輯實證主義的歸化論的累積主義,都反對了科學沙文主義的理論永恒性。波普爾的“不斷革命論”,庫恩的常態和革命的雙相觀,都否定了科學沙文主義的權威的絕對性。而拉卡托斯關于各種理論競爭和并存(包括對已退化的理論的寬容)的研究綱領,和費耶阿本德的無固定模式的“科學的無政府主義”,則連科學沙文主義暫時的棲息之地也剝奪了。當然,他們(主要是歷史主義一派)的科學發展觀多少有些相對主義的缺陷,然而,近年新起的夏皮爾(P.Shapere)和薩普(F.Suppe)的科學實在論(這一派邱著未曾涉及,不免是一個缺憾),盡管在積極糾正歷史主義一派的相對主義,但同樣與科學沙文主義格格不入(江天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多樣化思維在今天中國社會的極端必要性,似乎無須多加論證了。值得一提的倒是這樣一個令人汗顏的事實:費耶阿本德在諷刺只允許一種模式的傳統的科學教育時,竟以中國女人的小腳為喻。“三寸金蓮”早成了歷史陳跡,但大一統的僵硬性會不會再成為新的歷史笑柄呢?
“逆規則”——來一點反向思維所謂“逆規則”,即要求我們采用和闡發與已被充分確證的理論和充分證實的事實相矛盾的假說,也就是要我們按反歸納法行事。這合理嗎?費耶阿本德對此作了回答(第178—179頁)。逆規則包括兩條:關于提出與公認的、高度確證的理論不一致的假說的逆規則,是建筑于這樣一個重要論點之上的——只有借助于另一個不相容的理論,才能發掘出反駁一個理論的證據(這是否有點象我們今天所說的“先立后破”呢?)。另一條是關于提出與觀察、事實和實驗結果不一致的假說的逆規則,其根據是:沒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是與在它周圍內的所有已知事實一致的(這與我們前面提到的證據受污染相似)。很明顯,就思維方式而言,“逆規則”啟示我們要來一點反向思維,這里有兩個意思:一是要有一點懷疑常識(包括理論和事實)的勇氣,二是要懂得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我們知道常識往往蒙蔽人,如最近看到《新民晚報》一篇短文,說世界上本無狐貍,只有分別叫狐和貍的動物,可見我們的許多常識是大可懷疑的。而中國畫與西洋畫截然相反的透視法也只不過是無數相反相成事物之一例。盡管如此,種種惰性和慣性畢竟太強大,以致我們必得常常提醒自己和別人:來一下“反彈琵琶”,如何?
“格式塔轉換”——調整思維的目標哲學史和科學史上充滿了調整思維目標的事例。人們今天對休謨和康德的重視,從某種角度講,也在于他們倆人一個從消極的意義上(懷疑主義,提出歸納問題),另一個從積極的意義上(反躬自問,提出人的認識能力問題),轉換了傳統哲學和科學思維的問題。科學哲學史表明,這種轉換常常是革命性的,開拓性的。如果說,休謨的懷疑主義對弗·培根(F.Bacon)以來的證明主義是一個格式塔式轉換的預兆,那么波普爾的否證主義,把對理論的證明問題轉向理論的發現問題,則是科學哲學史中的重要一舉。顯然,它比卡爾納普(Carnap)等的新證明主義更高明些,因為它拓寬了思維空間,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而后者盡管也有可觀的成就,如對概率問題的研究,但由于走的是原來的思維道路,因而路子變窄了。意味深長的是庫恩把科學發展與格式塔心理學與皮亞杰(J.Piaget)發生認識論聯系起來,從而增加了這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我們今天不也常常面臨這種狀況嗎?一些或者只具有常識意義的命題,或者毫無現實感的命題充斥于學術研究的象牙之塔,對于這種學術研究,誰都有正當理由去懷疑它的信息量和意義,不過,我們還是不要過多地去理會和指責為好,庫恩認為對舊范型、舊的心理定勢的執拗是科學革命中的正常現象,關鍵是對于那些具有創新能力的人,尤其是青年理論工作者,應當鞭策和激勵他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與問題有關的真理才與科學有關”——正確引入價值觀價值論在科學哲學中占有相當地位,科學哲學中討論的分界問題、意義問題,研究科學成就的評價和選擇問題,都與價值論有關。波普爾把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作為科學追求的目標,而摒棄“所有的桌子都是桌子”、“1+1=2”這樣的真理(我想,也包括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象牙之塔中的理論),這種價值觀是積極的。更為難得的是這種價值觀還體現了思維方法中的寬容原則,即對一些看來屬于片面的、極端的但畢竟是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的思維方式的寬容。被稱為“科學哲學界的怪杰”的費耶阿本德就是一個善于獨辟蹊徑,啟迪思路的人,但他又的的確確是有不少片面性和極端性的。如果沒有寬容,沒有愛因斯坦那樣的把提出問題看作是一種極大的價值的觀念,費耶阿本德就一定會陷入劈頭蓋腦的“大批判”之中。問題的現實性還在于,在中國這樣一個提倡了幾千年“中庸”之道的國度,宣傳波普關于理論的可否證度與邏輯概率的反比關系的見解,并使之深入人們的思維方式之中,將有極大的意義。否則,可以想象,面對著“明天這里天下雨”與“明天這里天下雨或不下雨”這樣兩個陳述(第50頁),中庸思想熏陶下的人們一定會選擇后者,盡管這種模棱兩可的“預言”,信息量只等于零(可否證度也等于零),而邏輯概率卻等于1(因而是百分之百地正確的)。襄王枕上原無夢,莫看陽臺一片云!
3
愛因斯坦十分推崇新方法,但他更重視人類精神的作用,他說過,在一切方法背后,如果沒有一種生氣勃勃的精神,它們到頭來不過是笨拙的工具而已。
所以,這里還想談談科學動力學及其創造者們的精神。主要是:批判和開拓精神;追求科學知識一體化的精神。因為,這兩種精神對我們今天探求科學的社會動力學關系甚大。
批判和開拓同屬于人類最本質的精神的系列。波普有一個著名的論題:“從阿米巴到Einstein只是一步。”說它是一個論題,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句表明人類根本特性的格言式的話,而且是以新的生物進化理論為依據,又以人類的偉大實踐為證明的。波普認為,作為單細胞原生動物的阿米巴和愛因斯坦所差的一步在于:雖然兩者都在進行排除錯誤的“自然選擇”,但阿米巴不是理性的,“不喜歡犯錯誤,不喜歡承認錯誤,結果它與錯誤一起死亡”(第61頁)。而愛因斯坦則不然,他提出相對論時,就聲明了在什么條件下他的理論就可被證明是錯誤的,并準備放棄它。所以,波普所認為的批判精神實際上是一種既批判別人,也批判自己,又接受別人批判的科學精神,是一種徹底的批判精神。而這種批判精神又必然導致開拓精神,開拓精神也與新的生物進化論相聯系,同樣為人類實踐所驗證。波普認為,宇宙或宇宙的進化是有創造性的,而隨著人的出現,宇宙的創造性變得明顯了,最有力的證據是人類已創造出一個新的客觀世界——人類精神產物的世界,波普名之曰“世界3”。
對于批判精神和開拓精神的提法,我們并不陌生。問題在于我們需要科學動力學的幫助,以便將這種精神與科學,也與哲學聯系起來,并付諸實踐。在此,波普的理論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說明。問題還在于人類并沒有都達到了愛因斯坦的境界,一個大活人卻只擁有阿米巴的進化能力的情況還并不罕見。所以,波普聲明,他所引證的都是在“英雄意義”上的科學史的創造者,“他們的生活是由大膽的思想組成的”(第67頁)。
追求科學知識一體化的精神乃是當代科學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時下,人們很喜歡談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統一的問題,并嘗試著做一些互相介紹和引進的工作,或者客串另一領域遨游一番,留下一些新鮮的足跡。科學哲學家們也不乏這樣的興趣。波普兼有歷史哲學家的身份,他用他的“猜測一試錯”法否定了歷史規律陳述的可驗證性;庫恩將他的“科學革命”與政治革命作比較,得出兩者大體相同的結論;拉卡托斯用他的“科學研究綱領”的退化階段來解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問題;費耶阿本德甚至直接引用列寧在《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關于實踐比理論、方法更豐富的話來證明他的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當然,這些嘗試性的工作總不免帶有局限性,甚至明顯的荒謬性。所以,我覺得,更值得注意的倒是科學哲學為知識一體化的基礎所提供的獨特的證明。說它獨特,是因為科學動力學中關于知識一體化的傾向,常常是從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對自然科學的影響這一面體現出來的,這恰好彌補了當前人們往往只從另一相反方向來談論知識一體化問題的不足。比如:波普關于科學始于神話的觀點,費耶阿本德關于科學始于非理性的“激情”或“愛好”的觀點,可以看作知識發生學意義上的證明。庫恩關于社會的某種需要引起常規科學的危機,關于世界觀決定對范型的選擇的觀點,則是知識發展觀意義上的證明。而科學哲學中的主流派——歷史主義,顯然在方法論上與社會科學意義上的歷史主義具有共通性。此外,科學哲學注重討論認識論,引入價值觀,都可以從知識一體化的意義上來理解。的確,知識一體化是一種雙向的趨勢,列寧就呼吁過,不要讓幻想為詩人們獨占了。
在《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一書中,作者專辟兩節,敘述了“理論動力學”和“思想社會學”(第88頁,第94頁)對于庫恩科學哲學觀的影響,隨之,作者又說明庫恩的理論又著著實實地構成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對諸多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沖擊波”。可見,在科學動力學與社會動力學之間,思想動力學是極重要的媒介。本文旨在發掘科學動力學對社會動力學的影響,然卻把主要筆墨化在科學動力學對哲學、對人類的思維方法,對人類精神等思想動力學的影響上,其源蓋出于此。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現代科學哲學概述》,邱仁宗編著,知識出版社(滬)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