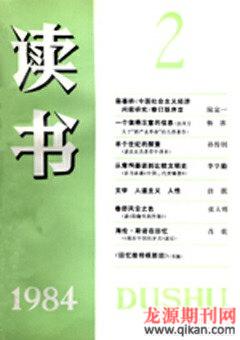讀《李商隱研究》
高海夫
在唐代詩壇上,李商隱的詩雖不能和光滿人寰、衣被后世的李、杜相比,但它迥不猶人的藝術個性,卻宛如一顆明星,也放射出耀眼的光輝,博得不少人對它的皎潔、高遠、幽邃,以至帶有幾分神秘的氣象,賞玩、嘆美不已,甚而為之陶醉。
由于義山詩長于隸事用典,巧于比興寄托,詩風有如“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其綽約妙姿,只是仿佛可見,因而遠在古昔,博雅如元遺山、王漁洋,即已發出過箋釋匪易、解人難得之嘆。于是,見仁見智,聚訟紛紜,贊毀皆有,贊與毀俱未得其當者亦有之。解放以后,雖然還有斥義山為唯美主義、反現實主義,或予以涂抹附會,譽之為法家詩人這樣失之淺率偏頗的意見,但總地說來,由于有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對義山詩的研究與評價,在前人的基礎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成績是很顯著的。只是新的論著,大抵言之,或者側重一面,令人有只見一斑、未識全豹之憾;或者總論其人、其詩,又多嫌簡略,未能給讀者以慊心快意之感。體大慮周,蹊徑獨辟,索隱探微,有如《李商隱研究》(以下簡稱《研究》)者,似屬首見。因而在我看來,如許吳先生為義山詩的“解人”,庶幾近之。
《研究》對李商隱的生平、思想、審美觀、政治詩、愛情詩、詩歌的藝術特色、風格的形成和發展,乃至其詩的淵源、影響,以及前人對它的評價諸方面,均加以細致的論列探討。書中的論述并非舊說的綜輯排比,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多年潛研精思,多所深化與拓展。如對李商隱江鄉之游的考辯,作者不取馮浩時在開成五年說,而取其地在江鄉與劉
《研究》之于義山詩,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方可察其隱微,洞其奧秘,故能知之;出乎其外,方可立足今天,居高臨下,故能評之。因而讀《研究》,既能知義山之為義山,又對鑒古知今,古為今用不無裨補。紀昀在評述其時“世之習義山詩者”時,曾說過幾句感慨的話:“夫深山大澤,有龍虎焉,不見其噓而成云,嘯而生風,而執其敗鱗殘革以詫人,以為龍虎如是。人見其敗鱗殘革也,亦以為龍虎不過如是而鄙之,以為不足奇,可謂之知龍虎哉!”(《玉
《研究》不僅以一整章的篇幅,深入分析了義山政治詩的思想意義,在其他章節,還時有論及。第三章于結合牛李黨爭辨析了義山的政治立場與態度后,首論其早期的鴻篇《行次西郊》,次及其對腐朽事物的抨擊與嘲諷諸作,再次,對正面人物與理想抱負的詠嘆,末殿以回顧生平失意、感慨理想破滅的《錦瑟》詩,既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義山詩思想內容方面發展變化的軌跡,同時也揭示了他在這方面所達到的不算太低的高度及其缺陷與不足。他指出“他憂心國事的政治思想相當深摯”(87頁),但又指出:“由于他和人民的聯系不密切,他的忠君憂國思想就不能同愛民思想更深地結合,他的忠君憂國也必然局限于政局的風云變化,而對政局的關心,有時又難免牽連著個人的升沉得失。正因為這樣,他的詩歌題材較難反映波瀾壯闊的歷史時代,也就更說不上‘詩史了。”又說:“若說李商隱的詩歌完全沒有反映時代風貌,這自然不對;但如果說他唱出了時代的強音,卻也是錯誤的。”(235頁)對義山的愛情詩也是如此。不僅批判了那些耽吟香艷、風流自賞之類庸俗的艷體詩,即使對那些真純優美、廣為傳誦的愛情詩,也既看到它“閃射出百折不渝的高潔理想的光輝,給讀者以美感的享受”(139頁),從而給以足夠的肯定;同時又指出其中時時流露的哀婉、悵惘、低沉的情調,以及過分追求詞藻,不免窒塞內容等,則是不足取的。其他如對義山特有的審美情趣,詩歌的藝術特色,以至他對前人藝術的借鑒、所給予后世的影響等,也都有所剖析,對其得失利弊的指陳也較為允當。
詩歌屬于藝術美,是人們審美活動的重要對象之一。它雖然來自現實美,是現實美的反映,但它卻不同于鑒之于容,形之于影,而是詩人創造性勞動的產物。現實美的存在形態是無限豐富多樣的,而詩人的審美趣味、審美能力、審美理想等又是千差萬別的。這樣就必然會形成詩人們審美意識的千差萬別,互不相復,形成其各具面目的個性差異。這個性差異,乃詩人創作個性、藝術風格的基礎。因而要分析、探討、認識一個詩人詩歌創作的貢獻與特有的審美價值,無論是他對現實特有的敏感與把握,還是他藝術構思與表達的特色,不由其審美觀入手,都是頗難原始要終、探本窮源的。而這一點卻恰恰是目前古典文學研究中相當薄弱的環節。《研究》之于義山詩,綜合文學史、古代文論與美學,冶三者于一爐,特別是從審美觀的高度,予以剖析探討,以義山的審美情趣、觀念、理想統攝全書,這是它尤為顯著的特色。
古人論義山詩,雖多有憑私而決、主觀臆斷之處,然亦不乏精當入微的審美見解,只是多三言兩語,欠系統而難捉摸。吳先生充分利用了這些傳統的美學思想資料,加以深入而又明晰的闡述,以我國自有的詩論傳統論義山詩,從而使《研究》帶有濃郁的中國風味與鮮明的民族氣派:兼重論析與鑒賞,揣摩作品的意境、韻味,描摹作者的氣質豐神。
《研究》旨在論義山詩,然又不拘拘于義山,而是把它放在我國詩歌發展的長河中,放在與其同時代的眾多的詩人、流派里,亦即放在縱與橫兩方面的比照考察中加以鑒賞論析。就總體說,對李詩不唯論其成就,明其個性,而且溯其淵源,察其因革,是如此;就部分看,也是這樣。如對義山的詠史詩,經過對班固質木無文的《詠史》,以迄唐代許多詩人同類作品的比較考察,然后得出了他的創作個性之所在:不用賦體,多用比興;不用敘事,多用抒情,追古涵今,濃縮凝煉,更多地把感時與論史結合起來,具有更為突出的美刺諷諭、顯忠斥佞的特點。對他的優美的愛情詩,也經由同樣的途徑,指出它的特色在于:在朦朧的意境和悲劇的氣氛中,著意創造苦于愛情的折磨而又執著于愛情,創造
上述諸端,不難看出,都無不著意于美學的探索,又無不統攝于義山的審美觀。《研究》于首章論列了李商隱的生平和思想以后,接著即專章剖析其審美觀,這是提綱摯領之舉。李商隱并非美學家,他的審美觀點絕少直截的理論表述,大都滲透在他的詩文創作中。作者經過細心的鉤稽,高度的綜合,揭示出它的基本特點:審美情趣側重于優美,但這情趣中卻蘊藏著理性觀念和道德內涵,包含著耿介的風骨和柔韌不屈的意志,決不是一味溫柔,更未流于輕浮。它既無龍吟虎嘯,也不雄姿俊發,但卻不曾與壯美絕緣。此其一。他也懷念、景仰崇高美,但他經常體驗與探索的卻總是這種美的消沉與幻滅,和此刻他悵惘感傷的心靈,而缺乏巨大的力量和氣魄,因而他所探索的美的境界,總是迢遙恍惚,可望而不可及的。此其二。他的美的理想火焰,并未曾在寂寞暗淡中熄滅,而是始終在燃燒,只不過是在寂寞中燃燒。此其三。在論述中,作者對義山《初食筍呈座中》、《北禽》、《夕陽樓》、《初起》、《蟬》等詩的分析,既有理論的說服力,又有形象的可感性,給研讀義山詩啟示良多。
西方“趣味無爭辯”的諺語,顯然是一偏之見,并不符合客觀事實。實際上,詩人的審美觀并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純主觀的不可究詰的東西,它無不受著特定的時代、個人的世界觀、生活經歷、學習素養、心理氣質等因素的制約。李商隱當然也并非例外。《研究》的首章即揭示了形成義山上述特有的審美觀的諸因素:他所處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代,唐王朝的大廈將傾,已非一木可支;他“年方就縛,家難旋臻”,“生人窮困,聞見所無”的早年生活對他抑郁感傷情懷的影響;早歲江南旖旋風光的感受見聞,以及后來受知于以駢文盛負時譽的令狐楚的機遇對他“百寶流蘇”詩風的孕育;中年的仕途坎坷、黨爭夾縫中間的苦悶,“風朝露夜陰晴里,萬戶千門開閉時”的遭際,回天無力、理想破滅時的心情況味的體驗等等。
正是基于這樣形成的審美觀,所以他早年雖曾汲取了杜甫“詩史”的精神,寫出了《行次西郊》那樣的鴻篇巨制,勾畫了一幅唐王朝崩潰前夕的鳥瞰圖,波瀾壯闊,大氣磅礴,但終不免孤篇獨耀,后難為繼。之后,常見的是纏綿悱惻、感傷哀怨的情調,而慷慨激越、雷霆震發之音就很少了。至于義山詩的藝術特色,如深情婉約,意境曲折;如脈絡細密,詩律暢適;如鏤物精細,用典工切;以至對詠史、無題詩的愛好、發展、創造等,亦無不導源于他的審美觀,是他對現實美獨特的感受在構思與表達方式上的反映。在第六章中,吳先生借用義山《嫩筍》、《流鶯》、《錦瑟》三詩的畫面形象,闡述了義山詩早中晚三期風格的異同特征,并兼及五七言古近體各體的消長變化。在細致的分析中,雖顯示了由于各種因素的湊泊,別調間見,但仍不失其沉博絕麗的本調,仍未違離其審美觀的制約。第七章論義山詩的淵源,論列了屈原、六朝詩人特別是徐庾,以及杜甫、李賀等家對義山的影響,闡述了義山重視兼材,轉益多師,廣泛學習遺產,汲取滋養,但仍可看出,他終還是取其性之所近,博采眾花,釀成佳蜜,更充實、突現了他的審美個性,和以此為根基的藝術風格。
(《李商隱研究》,吳調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0.8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