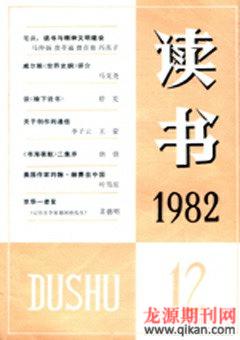《書(shū)海夜航》二集序
唐 弢
初讀《書(shū)海夜航》,我就十分吃驚于作者外國(guó)文學(xué)知識(shí)的淹博,信手拈來(lái),信口開(kāi)講,沒(méi)有規(guī)矩而自成方圓。尤其難得的是,這不是一般的讀書(shū)記,而是掌故史乘的漫談,談的是成書(shū)的經(jīng)過(guò),版本的優(yōu)劣,插圖的變易,觀點(diǎn)的沿革,作者的遭遇,……一句話,不限于書(shū)里的故事,多的是書(shū)外的見(jiàn)聞。這樣,屬于知識(shí)范圍的縱筆所之的放談不必說(shuō)了,便是就書(shū)論書(shū),也要有獨(dú)具的識(shí)見(jiàn),精當(dāng)?shù)牟牧希蔷屯耆揽孔髡咂饺盏男摒B(yǎng)和積累,不是可以僥幸取得、一蹴即就的了。
我以為這是《書(shū)海夜航》的一個(gè)最大的特色。
北京有句贊揚(yáng)京劇表演家的話,叫做:臺(tái)上幾分鐘,臺(tái)下幾年功。藝術(shù)修養(yǎng)在京劇、音樂(lè)、美術(shù)乃至文學(xué)方面,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所以這一句話,同樣可以移贈(zèng)《書(shū)海夜航》的作者。他的文章,即使不是全部,也很有清淡娓娓、言之有物的妙處,顯示了一個(gè)書(shū)話作者的深厚的功力。
這是難得的,但決非偶然。作者精通外文,熱愛(ài)圖書(shū),如他自己所說(shuō),他的秘密在于沒(méi)有秘密:每天晚上,“從八點(diǎn)到深夜兩點(diǎn)”,“老老實(shí)實(shí)一句句地看書(shū)”,“十年如一日”,駕扁舟航行于書(shū)的海洋中。如今積儲(chǔ)在手頭的,寫(xiě)入在書(shū)里的,正是他多年來(lái)從海上不斷漁獵、不斷網(wǎng)罟而得的珠貝。《書(shū)海夜航》是一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名稱。
據(jù)作者說(shuō),這是他的摯友嚴(yán)慶澍(筆名唐人)代為命名的,現(xiàn)在,《書(shū)海夜航二集》又將出版,寫(xiě)法稍有變動(dòng),特點(diǎn)卻還清楚地保存著。至于書(shū)名,只添上“二集”兩字,一來(lái)說(shuō)明作者自己的愛(ài)好,二則表示對(duì)亡友的紀(jì)念,這樣就多了一層意義,不知不覺(jué)中,終于默默地加重了書(shū)的感情的分量了。
我不知道這些內(nèi)幕,只覺(jué)得《書(shū)海夜航》的名稱很不錯(cuò)。當(dāng)初一看書(shū)名,首先想到的是明朝張宗子(岱)的《夜航船》,我有這書(shū),版本雖然粗陋,內(nèi)容卻很別致;其次是阿英的由《夜航船》而命名的《夜航集》,一九三五年三月列為“良友文庫(kù)之二”出版,收入的是讀書(shū)小品、考訂隨筆,讀來(lái)也頗有趣;從書(shū)的性質(zhì)出發(fā),我把《書(shū)海夜航》和這兩本聯(lián)起來(lái),看作是第三代,那就不是毫無(wú)根據(jù)的了。這回很想將《夜航船》找出,重讀一過(guò),幾經(jīng)遷徒,又遭變亂,苦思冥想,翻箱倒篋,還是連影蹤都沒(méi)有。不過(guò)序文收入《近代散文抄》,不算難找,我拿來(lái)和阿英的《夜航小引》閱讀,倒也很有啟發(fā)。
《書(shū)海夜航》、《夜航集》、《夜航船》有一個(gè)共同含義,暗示作者都是在夜闌人靜、萬(wàn)籟俱寂的時(shí)候,開(kāi)始其讀書(shū)寫(xiě)字的生活的。三本書(shū)的序文都談到了這一點(diǎn)。不過(guò)張宗子另有自己的閱歷和見(jiàn)解,值得我們注意。他說(shuō)天下學(xué)問(wèn),唯夜航船中最難對(duì)付。余姚風(fēng)俗,后生小子,無(wú)不讀書(shū),二十歲后學(xué)為手藝,所以百工雜技,偶有問(wèn)訊,舉凡“瀛洲十八學(xué)士,云臺(tái)二十八將”,逐一報(bào)名,對(duì)答如流,活象一口“兩腳書(shū)櫥”。這種問(wèn)答常在夜航船中進(jìn)行。本來(lái),偶然失記姓名,無(wú)害學(xué)問(wèn)文理。但在百工雜技眼里,認(rèn)為有損博學(xué)之名,往往傳為笑柄。他還講了一個(gè)很有風(fēng)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拳足而寢。僧聽(tīng)其語(yǔ)有破綻,乃曰:請(qǐng)問(wèn)相公,澹臺(tái)滅明是一個(gè)人兩個(gè)人?士子曰:是兩個(gè)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gè)人兩個(gè)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gè)人!僧乃笑曰:這等說(shuō)起來(lái),且待小僧伸伸腳。”
這個(gè)故事很有意思。張宗子勸我們“聊且記取”,“勿使僧人伸腳則可已矣”。我有點(diǎn)不同的看法。象我們這樣以搖筆桿為業(yè)的人,有時(shí)總不免要談這談那,既然談這談那,總不免會(huì)出現(xiàn)破綻,既然出現(xiàn)破綻,總希望有人能夠駁難更正,居士和尚,一概歡迎。何況拳足而寢,時(shí)間一久,兩腿便要發(fā)麻,為什么不許和尚轉(zhuǎn)個(gè)身、“伸伸腳”呢?
誰(shuí)都知道,航船的艙身實(shí)在是很小,很小的呵!
約定為《書(shū)海夜航二集》寫(xiě)篇序,話卻說(shuō)遠(yuǎn)了,作者一定會(huì)原諒的吧。我從“夜航”拉扯到“夜航船”,又因先前寫(xiě)過(guò)書(shū)話,竟將自己的一點(diǎn)心意和盤(pán)托出了。我沒(méi)有《書(shū)海夜航》作者的博識(shí),如果重理舊業(yè),提起筆來(lái),即使不至于將堯舜說(shuō)成一個(gè)人,將春秋魯國(guó)的澹臺(tái)滅明說(shuō)成兩個(gè)人,但差池一定難免的,有朝一日,在夜航船里答問(wèn),正當(dāng)興高采烈之際,船艙角落,忽然傳出一聲低低的訕笑,說(shuō)道:
“這等說(shuō)起來(lái),且待小僧伸伸腳。”
誠(chéng)然,對(duì)自己,我會(huì)覺(jué)得慚愧的。但對(duì)這個(gè)發(fā)笑的人,不管居士和尚,我都竭誠(chéng)歡迎,歡迎他伸伸腳,再伸伸腳!如果天下和尚,從此都說(shuō):“且待小僧伸伸腳。”到那時(shí)候,看來(lái)也就不會(huì)再有認(rèn)堯舜是一個(gè)人、澹臺(tái)滅明是兩個(gè)人,而又“高談闊論”、盛氣凌人的“相公”了,這將是文化界和知識(shí)界的莫大的幸運(yùn)。
話已經(jīng)說(shuō)得不少了,又都是個(gè)人的意見(jiàn)。質(zhì)之《書(shū)海夜航二集》的作者,不知以為何如?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夜于北京
(《書(shū)海夜航二集》,杜漸著,三聯(lián)書(shū)店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