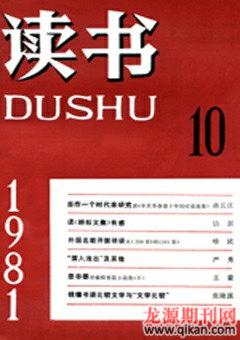漫話盧那察爾斯基論《愛與死的搏斗》
李健吾
羅曼·羅蘭在《愛與死的搏斗》原序中告訴我們,他從一九○○年起就一直想把《愛與死的搏斗》寫出來,醞釀了將近二十五年,才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寫出。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導(dǎo)演是格萊米耶(Grémies),劇場是法蘭西國家劇場“高亭”(Odéon,“高亭”的譯法是照過去唱片的譯法譯的)。后來又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五日,為了紀(jì)念法蘭西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蘭西喜劇院才又安排了一次演出的。
一九二四年正好是我在師大附中做學(xué)生會主席的時候,這時我已經(jīng)不演戲了,學(xué)著寫戲,頭一個見不得人的獨幕劇就發(fā)表在北京《晨報》的《文學(xué)附刊》上。一九二八年,我已經(jīng)考上了清華大學(xué),害肺疾,擔(dān)了個清華戲劇社社長的虛名。一九四○年,于伶同志和幾位同仁擴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把我從暨南大學(xué)找出來,為了使話劇打入法租界,籌備演《愛與死的搏斗》。我們只想著為“孤島”時期的話劇運動填補空白,一點也沒有想到要紀(jì)念法蘭西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一百五十周年。那時演出戲,磕頭求奶奶的,有多困難啊!巴金兄從內(nèi)地回了一趟上海,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把《愛與死的搏斗》劇本印出來,又匆匆去了內(nèi)地,好象演戲、出書都是為了紀(jì)念法蘭西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一百五十周年似的。
現(xiàn)在解放了,日子好過多了,臨到一九七八年,我以十分喜悅和感謝的心情讀到蔣路同志送我的一本書,書的名字是《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xué)》。我仔細讀了一遍,發(fā)現(xiàn)里面有一篇論文談《愛與死的搏斗》,還發(fā)現(xiàn)譯文引用的第九場是經(jīng)我校改過的譯文。什么時候我為譯者校改過的?我完全想不起來。這就是老年人的苦處,忘性大,眼前就是有書,也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是徐成時老弟作成我校改的?什么時候?一定是在十年浩劫之前了。十年浩劫!可憐徐成時老弟還白坐了一趟牢,而我已然老態(tài)龍鍾了。
但是,能讀到《論文學(xué)》我還是十分高興的。我?guī)е兄x的心情讀完了他這篇論文,得到的印象卻很不愉快。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理解錯了還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來想去,怎么也弄不明白。盧那察爾斯基當(dāng)時為什么那么不給羅曼·羅蘭留有余地呢?
首先,他的擔(dān)心是多余的,他怕這個獨幕劇太長。他說:“這出大戲是一個發(fā)生在同一地點的連續(xù)性的故事,換句話說,事實上沒有空當(dāng)和閑隙來落下幕布。要一氣聽完全劇,在觀眾相當(dāng)困難。”因而他認為“這里所顯示的藝術(shù)是否太多一點,這可能給實際演出造成困難。”上海劇藝社當(dāng)時的演出盛況就否定了他這種多余的擔(dān)心。觀眾始終是聚精會神地在看戲。后來我們還卻不過觀眾的盛情,又加演了兩場。而且演出用的是原裝,和中國觀眾有些距離。盡管我在翻譯上給觀眾留下不小的困難,可是這擋不住觀眾進戲。王統(tǒng)照先生有一首熱情洋溢的詩就是證明。觀眾深深被戲打動了,也許因為在生死問題上,我們的演出對當(dāng)時的“孤島”處境和全國抗戰(zhàn)氣氛有很大的作用。貪生,還是不怕死?這是引起觀眾共鳴的一個根本原因。
盧那察爾斯基在后文透露當(dāng)時“在法國以外有五十七個劇場立刻著手上演這個劇本,它們的觀眾會受到感動。”我們的演出是一九四○年,和原劇已經(jīng)相隔十六年了。但是一九四○年“孤島”的觀眾卻是依然還“受到感動”。我們承認觀眾當(dāng)時大部分都是小資產(chǎn)階級小知識分子,然而就當(dāng)時而論,除去漢奸之流暗中使壞以外,又有哪個觀眾不被戲所感動呢?
這是題外的話。不過,我還要老實不客氣地問一句,蔣路同志,你在說明引文來龍去脈之后指出:“一九三九年法國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紀(jì)念時,羅蘭將本劇第九場略加增補。但全劇基調(diào)既錯,修補也無濟于事了。”(538頁注2)這個注證明你完全是站在盧那察爾斯基一邊的。你說“基調(diào)既錯”,什么是這出戲的“基調(diào)”呢?還說“修補也無濟于事了”。你大概是沒有看過上海劇藝社的演出才說這番話的。我們的演出確實根據(jù)的是“修補”的第九場演出的。可是“基調(diào)”是什么,我想了再想,始終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一出戲的基調(diào)呢?是指無產(chǎn)階級立場?我還很少聽人用“基調(diào)”這種模棱兩可的字眼來說明一場戲或者一出戲的。其實,戲?qū)懙氖菤v史,反映的是歷史真實,而作者又是小資產(chǎn)者。蔣路同志何苦把調(diào)子提的那么玄而又玄呢?
這算題外話之二吧。
盧那察爾斯基在評論文章一開頭,就用堂吉訶德來形容羅曼·羅蘭,說什么“我覺得,用堂吉訶德的特點來形容這個同革命實際發(fā)生沖突的現(xiàn)代理想主義者,是確切的。”看到這里我又糊涂了。“革命”是戲里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還是戲外的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管是哪一種,“發(fā)生沖突”就似乎嚴(yán)重了些。這位“現(xiàn)代理想主義者”從來沒有發(fā)表宣言反對過列寧領(lǐng)導(dǎo)的蘇聯(lián)革命。如果指的是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那發(fā)生“沖突”又有什么壞處呢?文章寫到后來,盧那察爾斯基又把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再作一番宣傳,說什么“在某種程度上促使那些原先被它忽視了的讀者去注意注意它,因為最近它在歐洲也頗有影響。目前它在柏林一家大劇院上演四十多場,經(jīng)常滿座。”(522頁)我們知道有“五十七個劇場”要演羅曼·羅蘭這出戲,是盧那察爾斯基告訴我的,羅曼·羅蘭在“序”中一句也沒有提到他有過這種光榮。可是拿自己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和《愛與死的搏斗》相提并論,我們卻是從盧那察爾斯基自己的論文里才知道的。這意味著什么呢?難道一位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還不及一位資產(chǎn)階級“敵人”(看下文)?這種對比讓我有些替作者面紅耳赤。這算題外話之三吧。
現(xiàn)在還是看第二部分,因為很可能在這里找到“基調(diào)”,雖然“全劇基調(diào)既錯”,我們還是以尋找一下為是。
十八世紀(jì)法蘭西大革命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我們方才已經(jīng)稍稍點到了這一點,當(dāng)領(lǐng)袖的大部分是小資產(chǎn)者。他們把同事一個又一個地先后送上了斷頭臺。人心渙散了,果實讓有野心的拿破侖搶了去。怎么好混淆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列寧領(lǐng)導(dǎo)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呢?當(dāng)時工人階級還在萌芽階段,參加革命最多的也不過是些手工業(yè)者、農(nóng)民和知識分子,不是律師,就是教師、科學(xué)家、文學(xué)家或者百科全書派。說到底,無非是小資產(chǎn)者。農(nóng)民靠不住,在旺代省(Vendèe)三番兩次跟著反動的教士跑,與革命為敵。他們中間的情形是極為復(fù)雜的。讀盧那察爾斯基這篇文章,表面上頭頭是道,分析很細致。可是仔細一想,象盧那察爾斯基那樣一位無產(chǎn)者戰(zhàn)士,怎么好忽略歷史的真實性,會缺乏歷史唯物主義呢?歷史到底不是現(xiàn)實呀!“全劇基調(diào)既錯”,“基調(diào)”是不是就是被盧那察爾斯基弄“錯”了的歷史唯物主義?
權(quán)且把這作為問題之一吧。因為不細琢磨,是不容易體會出來這個錯誤的“基調(diào)”的。
其次,羅曼·羅蘭到底是一位資產(chǎn)階級進步作家,怎么能拿無產(chǎn)階級的黨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他呢?他既然是進步分子,就已經(jīng)不錯了,只能等著他的發(fā)展,而不能指責(zé)、漫罵、攻擊。法國到現(xiàn)在還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王國”,盡管歷史上有許多粉身碎骨的人物、許多可歌可泣的政治變故,這卻是鐵板釘釘般的事實。就連共產(chǎn)黨員阿拉貢(Aragon),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在我這個耳目蔽塞之人看來,他也不過是一大群小資產(chǎn)階級進步分子中的一員。盧那察爾斯基盡管在蘇聯(lián)掌著教育文化之權(quán),也不能把一個外國人說得那樣不堪。盧那察爾斯基未免忽略現(xiàn)時的實際,沒有考慮起碼的策略。
其三,他指責(zé)羅曼·羅蘭和他創(chuàng)作的虛構(gòu)人物科學(xué)家是“道地的庸人思想家”,而羅曼·羅蘭的論調(diào)是十足的庸人之見。劇中人物與劇作者既然已經(jīng)合而為一地戴上“庸人”的王冠,劇作者顯然無辭以應(yīng),只能俯首聽命了。劇中主人公被指責(zé)為“正在于他被流血嚇破了膽,又沒有卡爾諾那份道德力量。于是,據(jù)說似乎是為了科學(xué)的緣故(我們知道這套科學(xué)!),他連進步的觀念本身也放棄了。”(542頁)這里的兩個他顯然指的都是顧爾茹瓦希耶,①可這種指責(zé),卻把我們讀者嚇壞了。這“顧爾茹瓦希耶是偉大的科學(xué)家、百科全書派,由于熱烈同情革命,他加入山岳黨。”(528頁)可是不分青紅皂白,他變成了“庸人”。而劇中唯一不成其為“庸人”的,似乎就是有“道德力量”的卡爾諾。可是這種道德力量是哪個階級的,他就“王顧左右而不言”了。人性相通,不過對于盧那察爾斯基說來,到底也談明白了它是上層建筑物,那就是說,“卡爾諾那份道德力量”當(dāng)然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上層建筑了。說顧爾茹瓦希耶“為了科學(xué)的緣故(我們知道這套科學(xué)!),他連進步的觀念本身也放棄了。”多可怕的罪名!作者連“科學(xué)”也蔑視起來了。第一,科學(xué)是資產(chǎn)階級與無產(chǎn)階級共有的,它不過是個服務(wù)的東西罷了,誰拿在手里,誰就可以稱雄稱霸。第二,盧那察爾斯基蔑視的“這套科學(xué)”是些什么東西呢,顧爾茹瓦希耶是來自兩位科學(xué)家的,一位是著明的數(shù)學(xué)家貢道爾塞(Condorcet,1743-1794),是科學(xué)院的終身秘書,寫過一本書,他不但不“退步”,而且連題目也有“進步”的字樣,他的題目是:《人類精神進步的歷史前景的概要》(Enguirredun tableau historigue de pregrès de lesprithumain),而且“進步”在原文還是多數(shù)。他是服毒自盡的。另一位是著名的化學(xué)家和物理學(xué)家拉茹瓦錫耶(Lavoisier,1743-1794),他在化學(xué)方面第一個發(fā)現(xiàn)了氧氣,還第一個發(fā)表了“原子質(zhì)量守衡定律”,單這兩項對全人類的貢獻就有多大!他可以說是今天二十世紀(jì)的火箭發(fā)明者的祖師,由于他的身份是包稅人,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唯成分論者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和一批包稅人全都送上了斷頭臺。戲是假的,把這兩位著名的科學(xué)家合成一個典型都是假的:顧爾茹瓦希耶的原型也是盧那察爾斯基自己在文章里告訴中國讀者知道的,不然,中國讀者真還不知道呢,盡管羅曼·羅蘭在法文序里也說起了,可是有幾個人懂得法文呀?你明明知道兩位科學(xué)家的貢獻那么偉大,為什么還那么看不起他們?還來了一句“(我們知道這套科學(xué)!)”。難道蘇聯(lián)今天不要“進步”,不要“火箭”?當(dāng)然你不知道事情發(fā)展之速出乎你的意外,可是他們都是百科全書派,這該知道吧?為什么還要左一句“庸人”,右一句“庸人”,還加上一句“懦夫”?我實在想不通。
其四,盧那察爾斯基在“永生”上做文章,說什么“對于卡爾諾,整個生活是一座苦心營造起來的建筑物。卡爾諾確實是永生的,顧爾茹瓦希耶確實只有一時半刻的生命而已。”(543頁)卡爾諾(Carnot,1753—1823)也是一位數(shù)學(xué)家,在戲里所起的作用是送護照,給顧爾茹瓦希耶一個逃走的可能,在朋友的情分上,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難道這就是他“永生”的根據(jù)?而另一位科學(xué)家,在盧那察爾斯基看來,也“只有一時半刻的生命而已”。我不怪罪卡爾諾,他后來組織軍隊,支持了搖搖欲墜的法蘭西,還用大炮無意中幫拿破侖贏得了稱雄歐洲的“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創(chuàng)建帝國的機會,而拿破侖忘恩負義,卻敬而遠之疏闊了他。卡爾諾“整個生活”很不幸,也是樂其所樂的復(fù)辟王朝最后讓這位正人君子死在國外。不過他頂多也只能說是個資產(chǎn)階級中的佼佼者,和“永生”怎么能聯(lián)系在一起呢?而戲里另一位科學(xué)家,只因為服毒自盡,就被說成了“也只有一時半刻的生命而已”。一位科學(xué)家的“永生”是盧那察爾斯基給的,另一位科學(xué)家的短促生命又“確實”是歷史上羅伯斯比爾給的。怎么好拿戲中人和戲外人相比呢?兩個人原來一樣是戲中人呀。最后,又把人道主義歸罪于劇作者和他所創(chuàng)造的顧爾茹瓦希耶。我們還是不談這個人道主義吧,我們只能把人道主義歸罪于時代,別的話也就不必多說了。
而其五,也就是最后一點,盧那察爾斯基指責(zé)劇作家虛構(gòu)的一個資產(chǎn)階級婦女索菲(即女主人公、顧爾茹瓦希耶夫人)遵守婦道。難道要她學(xué)習(xí)無產(chǎn)階級婦女的榜樣嗎?她是一個歷史上的虛構(gòu)人物,怎么能向二十世紀(jì)剛剛解放了的蘇聯(lián)婦女學(xué)習(xí)呢?能如盧那察爾斯基希望的那樣,當(dāng)著丈夫的面跟一個真正的“懦夫”公開淫奔,即使她曾經(jīng)愛過他,難道這樣才算什么“勇敢”地和世俗決裂嗎?別說是虛構(gòu)的資產(chǎn)階級婦女,就是現(xiàn)實生活中任何一位婦女,誰心甘情愿,跟著一個真正的讓“流血嚇破了膽”的罪犯潛逃呢?因為真正的膽小鬼是她的舊情人,而不是她也曾經(jīng)愛過、并在科學(xué)事業(yè)上勤勤懇懇地從事工作、視死如歸的丈夫。
在這些“左”的思想支配下,于是,羅曼·羅蘭犯下了滔天大罪,跟托爾斯泰一樣,“給他那博學(xué)的羊羔顧爾茹瓦希耶披上種種英雄主義和殉道者精神的宗教外衣,從而在宣傳真正的人的理想和現(xiàn)實理想的真正道路這一偉大事業(yè)中成了我們的敵人。”(548頁)一下子就把羅曼·羅蘭說成了我們的敵人,在現(xiàn)實政治斗爭和策略中,“確實”是失策。
一九三二年,羅曼·羅蘭接受了莫斯科科學(xué)院的名譽院士的稱號,并不是“我們的敵人”。盧那察爾斯基的批評寫在一九二六年,又在一九三三年去了世,一九三五年羅曼·羅蘭終于去了蘇聯(lián),受到高爾基的熱情款待,總算“我們的敵人”變成了同路人,沒有讓當(dāng)時過頭的批評“嚇破了膽”。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附言:《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xué)》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承蔣路同志送我一本,我十分感激。我這里就《愛與死的搏斗》一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傷害了蔣路同志一句,我想他是不會怪罪我的。凡加引號的地方全見于譯文。
①此處譯名系從法文譯出,與《論文學(xué)》中的俄文譯名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