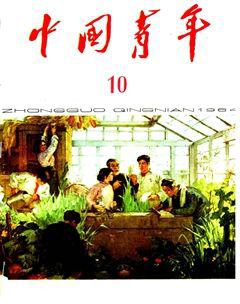理想的種子要種在現實的泥土中
楊緒昌
亦群同志提出的理想問題,我頗有感觸。理想,這個閃閃發光的字眼,多么吸引人啊!特別是我們青年人,都愛用幻想的畫筆,給它描上絢麗的色彩。我在中學時曾想過將來當一個工程師,隨著自己圖紙的繪成,龐大的水電站便像雨后春筍般地誕生,給工廠輸送力量,給居民以光明。
可是,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又抱著將來當一個詩人或文學家的理想回到了家鄉。我想用溶化天地萬物的熱情,盡情謳歌我們偉大的時代,我想寫出鴻篇巨作,來贊揚我們壯麗的事業……但是,兩年來,我感到家鄉所給我的并不是我想像的那種詩情畫意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消逝,我的理想色彩漸漸淡了。
鄉親們的輿論,母親對我沒考上大學的失望,更使我不安。一個同學又積極叢恿我和他一起到內蒙或新疆去。那里有“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風光,有萬紫千紅的花果園……于是,我的個人主義溫度升高了。去年秋天的一個拂曉,我偷偷地離開家鄉,坐上了西去的火車,穿過了崇山峻嶺之后,一望無際的戈壁灘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又涼了半截,新疆,這能是我理想中的新疆?我帶著失意的心情踏上歸途。但一想,回家怎么有臉去見父母和鄉親們呢?于是我轉向南陽市,找我舅父去。我想,他是個老干部,
總能給我找個工作干干吧。不料舅父嚴肅地批評了我,說我連和平的勞動都不想干,若趕上從前炮火連天的時候,很可能當逃兵。接著他就談起了他自己年青時想當個農民都不成,如何為地主所迫,走上了革命的戎馬生涯。他指著我說:“老一輩人給你們開辟了道路,難道你還想叫我們這樣幾十歲的老頭子,把你背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嗎?”舅父語重心長的批評使我猛省過來。我明白了,與時代背道而馳的個人主義的理想,無論你怎樣粉飾,怎樣苦心奮斗,早晚是要破滅的。有志氣的青年人,必須樹立革命的理想,而革命的理想,必須以革命的現實作基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正是革命現實的需要,自己的理想就應該從這個現實出發。于是,我又回到了家鄉,拿起了鋤頭。
最近,我看了魯迅先生的《論第三種人》一文,很有感觸。文章雖然是對三十多年前的文藝狀況而說的,但目前對我來說,還是不無作用的。他說:“……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斗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又說“……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將來會有意義。”是啊!去年的出走,不就像是用自己的手拔自己頭發的可笑的行動嗎?先生的話更加堅定了我在農村的決心。現在我已在農村安下心了。生活的磨煉使我丟掉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學會了一步一個窩地走路。我深信,只要把自己的理想的種子,種在現實的土壤中,勤耕耘,常鋤草,在黨的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是一定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