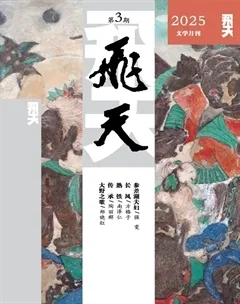巴閘天空的飛機
郭喬,本名王秀琴。魯迅文學院第44屆高研班學員。作品見于《民族文學》《清明》《飛天》《天津文學》《朔方》等刊。曾獲朔方文學“新人獎”。
“坐在上面平穩嗎?會不會像暈船一樣暈機?”鄉鄰老賈羞澀地撓撓鼻頭,感覺自己的問題有些愚蠢,肖大鵬卻表揚了老賈,夸他問得地道。在又一次呷下一口茶水后,肖大鵬給出了答案:“很平穩,跟坐在家里的沙發上一樣。別人坐飛機都暈機,我沒有。空姐都特高特好看,看到她們也暈,但不是暈車的那種暈。”大家一陣哄笑。
遠處,黃河樓在逐漸黯淡的光線中,變幻了幾次顏色,從黃昏時的磚瓦紅,變成了此刻的鴿灰青。功夫茶盤上泥黑色的圓肚紫砂壺與描花小茶杯,也快要被逐漸降臨的夜色吞沒,大家的興致卻并未減損。自從鄉鄰們知道肖大鵬坐過飛機,并且坐到了遠在天邊的吉隆坡后,就有人三三兩兩地伙起來,晚飯后來到肖大鵬家的院子里,圍著他的木質小圓桌,聽他聊坐飛機的事。
每一次,肖大鵬都像是第一遍講,從飛機起飛時的滑翔,到升空后俯瞰的感覺,甚至連航站樓的內部設施,都細致地給大家伙講了。在他的描述中,巴閘鎮的鄉親們,像是跟著肖大鵬親自坐了一回飛機。大家對飛機的想象,變得具體可感了,不像從電視上看到的,只是一個單薄的掠影。
從市里南郊的飛機場破土動工的那天起,巴閘鎮的老少們,就期待著能親眼看回飛機,甚至坐上一回。現在,新機場就要建成了,鄉親們商量著一定要在開通那天,去看真正的飛機。在看之前,聽肖大鵬講講,也算是提前過回癮吧。
半年前,肖大鵬被鄭州的電子廠優化裁員了,說是優化,其實是被辭退。這些年,他輾轉在成都、西安、深圳等大城市打工,美好的年華在流水線上一點點流逝,直到年近四十,失去了和年輕人拼眼速和手速的競爭力,才決定告老還鄉。在故鄉的街巷里,肖大鵬的再次出現,并沒有迎來鄉鄰們多么熱情的歡迎。或許是大家伙從他的穿戴上,沒有看到多少衣錦還鄉的意思吧。直到一天傍晚,肖大鵬站在街邊的一棵臭椿樹下,和開肉鋪的李兵聊了一會兒天。李兵問他坐沒坐過飛機,感覺如何?肖大鵬告訴李兵,就那么回事,跟走大路一樣。那些日子,鄉鄰們只要聊天,話題一定是新建的飛機場,以及和坐飛機有關的事。肖大鵬還告訴李兵,他去得最遠的地方是吉隆坡,光飛機就坐了大半天。“雞籠坡?哪是個啥地方?”顯而易見,李兵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地名。“馬來西亞的首都啊。”肖大鵬很隨意地答道。李兵的舌頭似乎短了半截,表情訕訕的,含著羞澀與羨慕,喃喃嘆道:“咱這輩子啥時候才能坐回飛機啊,別說坐了,就是見一回也行啊!”肖大鵬立即安慰李兵:“快了!新機場馬上就要建成了。”
肖大鵬去過吉隆坡的消息,很快就在巴閘鎮傳開。再從街巷里走過時,鄉鄰們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沒坐過飛機很正常啊,在咱們國家,有十億人沒坐過飛機,十二億人沒出過國,這是大數據統計出來的,沒有錯……”這幾句話是今天肖大鵬演講里新補充的內容,目的是安慰在座的鄉鄰們。果然,大家開始議論紛紛,這種議論很治愈,作為龐大數目中的一員,不應該為沒坐過飛機而羞愧。一邊講,一邊留意著對門的庭院,肖大鵬注意到,那個低著頭在菜圃里忙活的女人,聽到這幾句話時,又向這邊望了一眼。
肖大鵬有些緊張,再說話時,聲音就顯得有些干巴。他怕她聽出什么端倪來。那是個城里女人,雖然落魄了,暫居在這鄉下,保不齊她坐過飛機。轉念又一想,這幾句話又不是自己瞎編的,是網上的大數據調查出來的,怕啥,再將目光投向那女人時,肖大鵬就顯得有底氣多了。
這段日子以來,每每給鄉親們講解的時候,肖大鵬都會時不時地瞥一眼對面院里的情況。那個女人若在院子里,他說話的時候,就會小心翼翼。為了防止自己說錯話,肖大鵬總是會緩緩端起茶壺,滿滿倒上一杯,然后悠悠喝上一口。喝茶的工夫,他心里組織著要說的話,一句一句過一遍,盡量做到準確無誤。他怕自己哪句說錯了,被那女人聽出問題來。
肖大鵬真想過去問問女人,有沒有坐過飛機,沒坐過,就好好聽他講;坐過了,就回屋里去,不要總待在院里,豎著耳朵偷聽。肖大鵬最煩女人的表情,間或投過去一眼,總會看到女人臉上掛著耐人尋味的笑。兩人目光或有相撞時,女人眼里也是令人如芒在背的質疑,甚或是嘲弄。
肖大鵬很喜歡晚飯后的這段時光,被眾人圍著,享受著眾人欽羨的目光,這種感覺是他從未體驗過的,感覺自己是個人物了。……從吉隆坡轉機到仙本那,那邊的太陽和雨,都毒辣得嚇人……”“對,光是機票錢就萬把塊。我一共花費了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元……”肖大鵬越講越自信,在他嘴里,吉隆坡儼然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唯一讓他感到不適的,就是對門的那個女人。
肖大鵬和那個女人,幾乎錯前錯后地在巴閘鎮定居了下來。也就是他剛回來沒幾天,對門的庭院里就搬來了那個女人。女人還帶著個一瘸一拐的老娘,和一條活蹦亂竄的小狗。肖大鵬十分納罕,施翠芬哪去了,她的房子里怎么住進了這么個陌生女人?納罕歸納罕,看到對門住進了這樣一個風吹柳條般的女人,肖大鵬心里掀起的浪頭,頓時讓他把施翠芬拋到了腦后。
那個女人進進出出地收拾著隨身帶來的家具和器物,肖大鵬也進進出出地在自己的庭院里踱步,捎帶用眼風窺伺著對面。在女人費勁兒地把一只三角柜往屋里挪時,肖大鵬終于逮到了機會,他很自然地上去幫她,兩人合力把那只柜子抬進了屋里。建交始于此。在肖大鵬又幫著女人抬動了幾件家具后,基本上也就摸清了女人的情況。這房子算是好姐妹施翠芬租借給女人的。女人的老娘才做了膝蓋換置手術,需要這樣一個院落來練習行走康復。“再說了,在城里住久了,真的很想住在一個這樣的院落里,可以種種花種種菜,晚上還可以看月亮看星星。”女人邊把一瓶水遞給肖大鵬,邊笑意盈盈地回答。額頭上的汗珠和眼睛里的星星都亮晶晶的,刺激著肖大鵬的眼和心,一種崇拜和自卑的感覺,在他心里同時升起,這是個有文化的女人啊!自己差人家,不是一星半點。他對女人的態度,除了過分的殷勤外,立馬多了幾分尊敬。女人回報他的,也是熱乎乎的態度,哥長哥短地叫著。空氣里蕩漾著甜絲絲的氣氛。這是起初的日子。然而,好景并不長,一切都緣于流言傳播的速度。
肖大鵬把從街頭巷尾聽到的議論,拼湊起來,關于女人的來路,大致也就清晰了。一個離了婚的女人,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房子被賭鬼前夫輸掉了,手頭緊得在城里租不起房,只好到鄉下來撿便宜。而這個女人,還能鎮定自若地告訴別人,她只是喜歡農村的新鮮空氣。真是個撒謊精啊!女人的形象,迅速在肖大鵬的心里打了折扣。再看見女人時,肖大鵬的態度變得矜持了些,熱情里帶了很多克制的成分;女人本已把花兒般完全綻放的笑臉,擺在了臉上,看到肖大鵬的神色有異,那笑臉也就僵住了,慢慢地收回,最后變成淺淺的一抹。
及至聽說女人還有一個上職高的兒子時,肖大鵬的心,才算是徹底涼了下來。理智告訴他,這樣的女人招惹不得,一旦被纏上,麻煩就大了。自己可不想做大冤種,替別人養兒子,最后還被吃干榨盡。自己的女兒跟著前妻,這些年生活費他都不一定能按時奉上。嘿嘿!替別人養兒子,除非他腦門子讓驢踢了。這種事情利弊非常明顯,根本不需要權衡,肖大鵬對女人的態度又冷了幾分,他再也不主動到對門的院里去,有事沒事地搭訕女人。有時候,隔著街巷,女人主動向對門院里招呼時,肖大鵬也是不冷不熱地回應,感覺很不自然,尷尬的氣氛,在兩人之間逐漸形成。
然而,還有一些不可控的東西,不是肖大鵬靠理智完全掌控的。一個四十才出頭的男人,體內分泌的雄性荷爾蒙,以及動物本能的東西,讓他時時有一種大腦控制不了行為的沖動。畢竟女人長著那樣嬌俏的一張臉,說話的聲音,像是才從地里拔出的嫩蘿卜一樣,好不脆生生水靈靈。尤其當女人扶著老娘,在院里做康復訓練時,或者半低著頭,伏在案上做她的燙花手工時,周身散發出來的那種溫潤迷人的氣息,都讓肖大鵬有一種挪不開眼的失控。偶爾,女人也會向對門瞥來一眼,目光相撞時,再也沒有了當初的內容,審慎刻在眼底,那目光看上去冷冷的,嘴角卻掛著一抹似笑非笑的笑。那一刻,肖大鵬才明白,女人有多聰明,他所有的小心思,都沒逃過她的眼睛。
女人雖然一直配合著他,根據他態度的變化,來變化自己的態度,實際在心里,女人早把他看扁了。洞察到了這一點,肖大鵬對女人的態度又熱絡了起來,這種熱絡卻是排除了性別因素的,是一個人靠著冷漠,從另一個人那里贏得的尊重。女人卻徹底冷卻下來,一副愛招不理的樣子。肖大鵬也很快死灰了,他心想,不就是個女人么,憑老子的條件,哪里找不到。就這樣,他們的關系,經過了一番沒有擺在明面上的較量,產生了心電圖似的變化。兩個多月后,似乎又回到了建交前的陌生人狀態,稍有不同的是,比建交前多了嫌隙與隔閡。
“余伯,喝茶啊!”肖大鵬給鄉鄰余伯倒上。余伯佝著背,嘴上叼著根熄滅的煙,一直眼含笑意地默默聽著。大家伙便慫恿余伯也問個問題。六十多歲了,一回飛機都沒坐過,心里一定想得很。
“您老也問一個唄,老肖又不收費。”大家伙調侃著。
“問一個?”余伯憨厚地笑著,顯得越發靦腆。
“問,問!”眾口齊聲。
“問一個就問一個。”余伯皺眉思索著,少頃,說道,“飛機的肚子里真能盛下一百個人?”
大家伙被逗樂了,哈哈哈,這算什么問題。沒等肖大鵬開口,鄉鄰小錢就搶著回答了,“別說一百個,就是五百個也能盛得下,看您坐多大的飛機。”
余伯也笑了起來。那張黑紅臉在黯淡的光線下,也能看出來變得愈發黑紅。
“余伯,等飛機場建成了,讓余明拉上我們一起去看飛機。”小錢趁機提議。余明是余伯的二兒子,自己有一輛中巴車,在縣城跑專線。
“那沒問題!”余伯笑著說,挪挪身子,窘迫很快得到了緩解。
“到時候,讓老肖給我們當向導。”
“得給老肖留個前排的座。”
“可以,可以!”
……
夜色在大家伙的說笑中,又深了一層。對面敞著的院門,像個洞開的大嘴,在這將黑未黑的時刻,把大地殘留的光影,盡數納入口中,看上去有些親切,又有些隔膜。院子正中仿古的鋁合金涼亭,亭子邊上的核桃樹和美人蕉,南墻上的爬山虎……都變成了隱隱綽綽、迷迷蒙蒙的一團,和白天的景致完全不同,作為院子主人喜愛的器物,好像它們從來就沒有彼此分開過。
有人喊了一聲“撤”,緊跟著是三五聲的“撤”,一陣桌椅板凳挪動的聲音后,院子里空寂了下來。對面的大門,不知何時關上了。肖大鵬也閉了門。一天結束了。
肖大鵬睡到第二天晌午才起床。昨晚,他熬夜看球賽,過了點,睡著時已是后半夜。回鄉后,肖大鵬的生活,就是這么隨性,要么喝酒,要么釣魚,怎么舒服怎么來。有時候,他真想一直這么悠閑地過下去,可存折上的數目,只能讓他嘆口氣,再混個一兩年吧,實在扛不住了,再出去打工。其實,也可以走另外一條路,最近肖大鵬整天都在思謀這個事。
魏紅麗對肖大鵬釋放的信號,已經由隱約變得顯明。肖大鵬感覺自己再這么繃下去,沒準這事就黃了,他得快點決定了。說到底,他還是不中意魏紅麗的相貌,上學的時候,魏紅麗就不受看。
那天,肖大鵬去鎮中心閑逛,打過幾圈臺球后,有些口渴,就出了臺球室,信步走進旁邊的一家商店。拿了一瓶冰紅茶,去柜臺付賬時,肖大鵬才覺察到,女老板一直在盯著自己看,他就把目光迎上去,感覺這個長著盆子臉的女人,有幾分熟悉。還沒等肖大鵬在腦海里搜索,對面的女人已經叫出了聲:“肖大鵬,你是肖大鵬吧?”肖大鵬也即刻認出了魏紅麗,那小眼睛里放出的熾熱又癡態的光芒,讓他一下子想起了初中時的同桌,那個連留兩級被安排跟他坐的女同學魏紅麗。
魏紅麗依舊熱情,攀住肖大鵬敘了好一會兒舊,臨走,還給肖大鵬裝了一袋免費零食。之后,肖大鵬又去了幾次“紅麗”商店購物。魏紅麗的熱情,一次比一次高漲,看肖大鵬的眼神,也一次比一次火辣。肖大鵬知道魏紅麗的心思。上學的時候,魏紅麗就給肖大鵬寫過小紙條,他看都不想看。她想和他搞對象,門都沒有。看來,十幾年過去了,魏紅麗對肖大鵬,依然賊心不死。別的事,肖大鵬不敢保證,就魏紅麗看上自己,他還是蠻有把握的。當年,他就有個“巴閘吳奇隆”的稱號,二十多年過去了,他的身形依然板正挺拔,鷹鉤鼻依然高聳尖峭,深眼窩依然目光炯炯。
之后,魏紅麗又主動邀約了肖大鵬兩次,不是在商店里,而是在魏紅麗的家里,好酒好菜款待著,話也說得越來越露骨,感覺就差那句“我嫁給你吧”。肖大鵬在心里把算盤打了一遍又一遍,理智與感覺的天平,越來越傾斜,這主要緣于魏紅麗的經濟實力。
前兩年煤礦塌方,魏紅麗的丈夫被埋到了地下,給她和唯一的女兒換來了一筆巨額賠償金,數目大得讓人當時聽了就牙根酸痛;而那家商店,看起來營業額也不錯,供給一家日常的吃穿用度應該沒問題。在鎮子上的公共活動中心瞎混時,肖大鵬除掌握了這些信息,他還聽到一些光棍漢們閑諞,“娶了魏紅麗這老娘們,以后就只剩躺著吃了,還用得著苦哈哈地跑到工地上搬磚?”這些,都讓肖大鵬動搖。
其實,肖大鵬從心底是排斥吃軟飯這種行為的,但正像光棍漢們私下議論的,清高當不了飯吃,老來有個安樂窩,才是最重要的。辛苦漂泊了大半輩子,肖大鵬真想安定下來了。何況,魏紅麗對他又那樣好,她對他的熱情加迷戀,讓他心里很熨帖,不像對面那個女人,現在看見他,眉毛不是眉毛眼睛不是眼睛的。
近距離地接觸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肖大鵬再看魏紅麗的大包子臉和小瞇瞇眼,沒有當初那么丑了;現在看上去,怎么說呢,感覺還有點親切,有點踏實。對,應該是踏實,肖大鵬一遍一遍在心里強化著這種感受。
早飯和中飯合在一起吃了后,閑著無事可干,肖大鵬就打算到魏紅麗那里轉轉。這次是他主動,心里難免又有一些糾結,但也只是轉瞬,想象著那個光明安逸的未來,一切的問題,似乎都不是問題了。
對面的女人已經坐在涼亭里開始燙花,這是肖大鵬每天清晨打開自家的院門時,定會看到的景致。燙花是一種傳統工藝,先要描花,然后用一種叫作燙鏝的金屬球體燙花,待最后一道工序粘花完成后,一束比真花還要好看的燙花,也就做成了。這是剛建交沒多久,他倆的關系還處在“蜜月期”時,女人邊制作邊給他講解的。女人還告訴他,燙花就是她的收入來源,網上有很多人訂購呢。
此刻,女人正輕捻一朵花瓣,將它舉高,就著日光觀察顏色的濃淡,那專注的樣子,真是迷人啊!這娘兒們哪像三十六歲,說她是個姑娘,都有人相信,肖大鵬心想,眼睛又有些挪不開了。然而意識深處的自覺,又使他立刻低頭,走出自家的大門。轉身、鎖門,鑰匙還沒從鎖眼里拔出,對面院里就竄出了那條白色的板凳狗。那狗呲著亮牙,閃電一樣鉆到了肖大鵬腳下,不知道是示愛還是示威,卻把人嚇得不輕。出于本能,肖大鵬一腳飛出去,把狗踢出老遠。狗汪汪叫著,哀哀地啼鳴,趴在巷道里,半天起不了身。狗主人聞聲色變,扔下她的花兒,飄飛出了院落,那張粉白的小圓臉,瞬間變成了通紅的長條臉,杏核眼里迸出的火星子,看起來立刻就能將整個人引燃。
肖大鵬自覺剛才那一腳踢得太重,新買的方頭牛皮鞋,鞋頭硬得像石頭,自己穿都硌腳,卻踢在那么個小家伙身上。還沒等對面的女人口吐芬芳,肖大鵬立馬雙手作揖賠罪:“踢得重了,不是故意的啊,剛才被嚇了一跳。”
女人想說什么,肖大鵬只是連連地抱拳作揖。怒色從女人的臉上漸漸褪去,只用一雙含有怨氣的眼睛,幽幽地盯著肖大鵬。眼神里的內容,肖大鵬明白,是“有什么你盡管沖我來,對一只小狗下手,不覺得下作嗎?”肖大鵬也用眼神回答:“沒有啥,剛才真不是故意的。”這一段時間,他和女人盡用眼神交流了。交流越多,肖大鵬越覺得,這不是個簡單女人。女人身上有一股狠勁兒。
好在女人也沒多做糾纏,抱起狗,頭也不回地進了院。肖大鵬鎖好門,騎了電摩,急匆匆地逃離了。
一溜電摩,肖大鵬就到了魏紅麗的家里。為了迎接肖大鵬的到來,魏紅麗把才開張的店門關閉了,并掛上了“歇業一天”的牌子。回到鎮子東邊富平園小區二樓的家里后,魏紅麗又麻溜地整出一桌好菜,酒就不用說了,是店里最高檔的一款。
肖大鵬和魏紅麗吃著菜,喝著酒,一晃一下午就過去了。從魏紅麗家里出來時,日頭已經偏西。肖大鵬因為喝了酒,不便騎電動車,就步行著回家了。進了街巷,還沒到家門口,就聽到對門的院里,傳出新聞聯播開始的前奏音。女人和她的老娘,正坐在樹陰下吃晚飯。新聞聯播和之后的天氣預報,是她老娘每晚必看的節目。一臺小電視從早到晚,都擺在老娘面前的方桌上,陪著老娘度過了大半個夏季。因為早晨的事,肖大鵬有些過意不去,就主動跟母女倆打了個招呼:“姨,看新聞聯播呢啊!”女人只是抬起眼皮子,向這邊瞟了一眼,就繼續低頭吃她的飯了。那老娘倒是仁義,熱情地回應著肖大鵬,還招手讓他過去吃飯。肖大鵬答聲已經吃過了,就轉身進了自家的門。直到進了屋,心里的不快都沒有消失,這婆娘,氣性太大了,那條狗整天叫個不停,一見人就猛撲過來,那娘兒們倒像占了多大理似的。都怪自己面情軟,剛才就不應該主動跟她們打招呼的,顯得自己更沒理了。
上了床,手機沒看幾分鐘,肖大鵬就在酒精的催發下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對面又傳來了一陣綿密的狗吠聲,接著是鐵門劃著水泥地的聲音,是對門的女人在關院門,每晚九點是女人關院門的固定時間,這標志著一天又結束了,巴閘鎮正式進入了夜晚。肖大鵬想起了自家的院門好像也還開著半扇,便不顧頭暈爬起來關門,自然和那個女人又迎了個臉對臉。兩人都不拿正眼看對方,插了門銷,各自回了屋。
第二天下午,一個爆炸性的新聞,突然在巴閘鎮傳開了:魏紅麗被人殺了,兇手是肖大鵬。在市公安局的審訊室里,肖大鵬嚇得癱軟在審訊椅上,臉黃得就像是被硫磺熏過。公安每問他一個問題,他的心都會驚一下,回答的時候,語句磕巴得就像是才學說話的娃娃,“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肖大鵬翻來覆去只有這一句。“不是你干的,魏紅麗的身體里怎么會有你的體液?”公安隊長把一張檢查單,甩在肖大鵬面前。肖大鵬的臉色,頓時由黃變紅。他明白公安隊長的意思,他們在魏紅麗的身體里,檢查出了男人的體液,和肖大鵬的相似度高達99%。
昨天半夜,他們把肖大鵬抓到公安局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采集肖大鵬的體液。拈著尿杯往衛生間走的時候,肖大鵬心里還想著,這是干嘛。當時,他并不知道魏紅麗已經被害了,兇手宰了魏紅麗,她平時戴的那兩個沉甸甸的大金鐲子和四個克數不小的戒指,連同脖子里的大金鏈子、耳朵上的金耳環,都不見了。第一嫌疑人自然是肖大鵬。
肖大鵬把一切都交代了,就是沒有提他碰了對方的事情。他敢說當時他不是主動的,魏紅麗一直勸他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她去了趟臥室,出來的時候,身上換了件紅色真絲低胸睡裙。她的臉也紅撲撲的,嘴上也是油乎乎的紅。她目光灼人,身上佩戴的那些金飾,更是閃得他眼暈。當魏紅麗移步到沙發跟前,又一步一步挨著肖大鵬坐下時,他的眼里只有一片火一樣的紅,紅艷中跳躍著兩座雪白肥碩的山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把她推倒在沙發上……他們又從沙發上,滾落到了地上。完事后,肖大鵬心里的感覺很復雜,有些后悔,又有些得意,仔細想想,又覺得踏實。
他怎么好意思把這個事講給公安嘛。話說回來,他要是知道這關系到一樁命案,打死他都不會隱瞞。
肖大鵬只得給公安反復解釋,他是和魏紅麗做了那事,完了以后,魏紅麗接了個電話,說她女兒要回來了。她女兒在省城打工,幾個月才回來一次。肖大鵬只得先行告退。“魏紅麗其實是想讓我見她女兒一面的,是我覺得剛喝了酒,狀態不好,還是下次吧。”肖大鵬只得把什么都招了,連公安沒有問到的細節,他都一五一十地講了。他怕得要命,怎么都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樁命案扯上關系。
審訊他的兩個人,對了個眼色。公安隊長又問他,是什么時間離開魏紅麗家的。“大概六點鐘左右,”肖大鵬想了想說,“我家到魏紅麗家是五公里的路程,騎電摩十五分鐘左右。我喝了酒,她不放心讓我騎,我就步行回來了。如果走大路,大概得一個半小時。我是從沿河的林陰小道回來的,涼快還省時間。我到家時正好是七點。”
“你在路上有沒有遇到什么人,有誰能給你做證?”公安隊長的眼神像電鉆,鉆得肖大鵬沒做賊都感到心虛。他才意識到,自己沒走大道有多愚蠢,起碼有監控,可能還能遇到很多熟人。他走的那條道,那個時間段靜悄悄的,只有黃河水緩緩的流動聲,和樹林里蟲鳴鳥叫的聲音。拐到鎮子后的水泥硬化道上時,他才碰到了一個熟人,還是他們鎮的半腦殼老漢楊四孩,那個迷糊了一輩子的傻呆呆,正撅著屁股,趴在一只垃圾箱上,搜騰什么。肖大鵬自然是懶得打招呼。
“沒有……遇到什么人。”冷汗加熱汗順著肖大鵬的額頭往下流,他恨不得哭出聲,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兩眼放光地喊道,“有,我有證人!”他想起了對門,那個女人和她的老娘,當時正在看新聞聯播。
那個女人被帶到了隔壁的審訊室。肖大鵬不知道她是啥時候來的,又是啥時候走的。等待的那幾個小時,他心里一直想著,要是女人告訴公安,他是七點鐘到家的,他應該就沒啥事了。公安一準會放了他,說不定還會為誤抓他,向他賠禮道歉呢。結果卻超乎了他的想象。公安告訴他,那個女人說沒注意他是不是七點回來的,當時她正低著頭吃飯呢。聽到這樣的結果,他只覺得頭頂的吸頂燈,晃了幾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和他一起,落入了水中。
作為最重要的嫌疑人,肖大鵬暫時被收押了。審訊的間隙,肖大鵬一直在想,魏紅麗到底是被誰殺的。應該是他沒走多久,魏紅麗就遇害了。怎么就那么巧,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就在那個時候?他真是太倒霉了。怪不得公安會懷疑他。還有那個女人,為啥不說實話呢,她就那么恨他?肖大鵬縮在鐵柵欄后的椅凳上,有時候淚流滿面,有時候又雙眼噴火。
在看守所捱到第三天的時候,肖大鵬突然記起了一件事,當天應該是飛機場開通的日子。八月十號,沒有錯!這個日子在巴閘鎮,反復被提及,已經深深刻在每個巴閘居民的心里,大家約好了那天一起看飛機。肖大鵬想起了余伯的許諾,要給他留個前排的位置。他要給他們做向導啊,這是這段日子以來,他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可是現在……他真想插上翅膀飛出去,他使勁兒拍打著鐵柵欄,一遍一遍高喊著,人不是他殺的,迎來的卻是幾聲斷喝。
第七天的下午,拘押肖大鵬的那個單間的門,又被打開了。肖大鵬記不起這是今天的第幾次,他習慣性地伸出胳膊,讓公安人員押著他往審訊室走。他面色烏黑,胡子拉碴,才一個禮拜,他的精神就近乎渙散。進來的卻是公安隊長,“你沒事了,可以回家了。”肖大鵬一時沒明白過來,他盯著公安隊長的嘴,希望他再說一遍。對方果然又重復了兩遍,他才仿若從大夢中醒來,抱住公安隊長,又是跳又是笑,眼淚把對方的臉頰,都沾濕了。
還沒從電梯口出來,肖大鵬就聽到有女人嚷嚷,聲音細中帶脆,很像對面那個女人。“讓我進去跟隊長說清楚,肖大鵬是七點回家的,當時新聞聯播剛開,他還和我們打了招呼……”兩個保安擋在女人的前面,不讓她往里沖。隊長嘴里嘀咕著:“這個女人怎么又來了,還嫌被關得不夠?”肖大鵬懵了,他不知道女人唱的哪一出。但是,看見女人的那一刻,他本能地沖了上去,和他腦海里想象了無數遍的一樣,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公安們撲上去,很快把他制服了。隊長說:“肖大鵬,你是非得殺個人才過癮嗎?”女人被她掐得漲紅了臉,邊咳嗽,邊用惡狠狠的目光盯著他,里面還有一絲洋洋得意,雪白脖頸上留下了一個八字形的紅印。
隊長命令一同審訊肖大鵬的兩名公安小趙和小李,把他和女人送回巴閘去。“一路再給老肖把這案子說道說道,讓他明明心。”隊長說。肖大鵬和女人坐在警車的后排,怒火四濺的目光,在聽了一段前排兩個公安對案情的講述后,慢慢變了內容。殺害魏紅麗的兇手,也是巴閘鎮人,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放出來才半年,就捅了這么個大婁子。
那天,肖大鵬要走,魏紅麗把他送出了門。想到肖大鵬來的時候,沒有把電摩放在指定地點,而是隨意停在了單元門口,她就跟著肖大鵬出去,安頓他把電摩停在小區東側的公共充電區域,以方便明天來取。因為住在二樓,魏紅麗圖方便就沒鎖家門,就下來一兩分鐘,犯不著再拿鑰匙開門。
這件命案,就出在那道虛掩的防盜門上。那個勞改犯放出來以后,因為找不到其他工作,就做了送水工。那會兒,他從五樓一家送完水,返回途中經過二樓時,看門是虛掩的,就起了賊心。賊人知道那是魏紅麗的家,清楚開商店的人,家里每天肯定放著萬把塊的流動資金。平時送水路過魏紅麗家時,那門都是反鎖著的,今天可是逮著好機會了。于是,賊人把嘴上戴的那個防曬面罩,往上拉了拉,又摸了摸工裝褲口袋里那把常備折疊匕首,便大模大樣地進了屋。他是這樣想的,如果屋里有人,他就說送水走錯了門;如果沒人,事情正好讓他干成。
返身回來后的魏紅麗,在賊人的脅迫下,獻上了所有的財物,卻依然被殺害了。原因是,在賊人費勁兒取魏紅麗那日漸增粗的手腕和手指上的金飾時,她認出了賊人。那個坐了八年牢才被放出來的勞改犯,那個經常到魏紅麗的商店購物和轉悠的熟人,在露出了真面目后,本能反應是快逃,剛到門口,又折返了回來——逃出這個門,卻逃不掉再吃牢飯的結局。賊人不想再坐牢了,所以只有一條路。賊人回過頭來,舉起匕首,在魏紅麗肥膩的脖子上劃了一刀。魏紅麗倒地的那一刻,兩手捂著脖子,她那閃著金光的腕子和手指,再次刺激著賊人的眼和心。賊人心想,就是因為這幾個東西,他才殺的人。不能就這么走了。于是,賊人又用匕首,去割魏紅麗的手指和手腕,太費勁了,才想起去廚房取切菜刀……
賊人離開沒多久,魏紅麗的女兒就回來了。
這個案子之所以一周內能破,要歸功于肖大鵬既膽怯又堅定的陳述。公安們越審訊越覺得肖大鵬不像個殺人的,就他那■樣,殺個雞,估計都手抖。再說,他也沒有殺人的動機。于是公安們又把尸首和現場細細檢查了一遍,果然在魏紅麗的兩根斷指中,找到了線索。那涂了紅色指甲油的指甲縫里,藏著一些粉紅色的東西,是人體組織,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據賊人交代,他從魏紅麗的手上取戒指時,魏紅麗疼得受不住了,除了大聲喊叫外,還用另一只手去阻止他。魏紅麗的指甲很長,又想使勁兒推開那只手,就抓破了賊人的手背。
“案子就是靠這幾縷組織破的。拿到省里的公安機關,進行了DNA檢測。又和全國所有在庫犯人的DNA,進行了比對。終于將犯人緝拿歸案。”小趙說。
“這樣啊!我以為是我見天找你們,你們相信了我的證詞。”女人說。
“和你的證詞,沒多大關系。審訊你,只是走正常流程。”小李說。
“就案子發生的那個時間,誰做證都沒用,我們需要更確鑿的證據。老肖,你說說是不是這個理。”小李補充道,他的意思很明確,肖大鵬根本沒必要恨女人。
“那你們憑什么關我兩天?”女人嚷嚷道。
“關你兩天算是少的,誰讓你拿證詞當兒戲。”小趙說。
送走了兩位公安。肖大鵬和女人站在街巷里,兩人都有一種失重感,像是從遙遠的時空穿越而來,才落地。
遠處巴閘河的水緩緩流淌著,到了韋橋的夾岸處,河水迂回曲折,打著旋兒,又往前流去。沉默了許久,肖大鵬終于開口了:“剛開始你為啥不說實話,是因為我踢了你的狗嗎?還是因為……我不和你搞對象?”
“都不是!”女人淡淡地說,眼神從遠處的風景中,回落到肖大鵬的目光中時,顯得很復雜。午后的陽光依然熾烈,肖大鵬卻生出了一種起風后的蕭瑟。
“那到底為什么?”
“為什么?你心里沒數嗎?你隔幾天就坐在對面,邊喝茶邊給那些大老粗講你坐飛機的事情,那個張狂樣啊,看得真讓人牙根癢癢。就你坐過飛機是嗎?我們這些沒坐過飛機的人,只能當你的觀眾,看你表演嗎?我還就告訴你,我就沒坐過飛機,我娘也沒坐過。她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就是坐飛機去趟北京,去天安門廣場轉轉。可是她的腿腳卻不行了……”
說到后面,女人的聲音有點哽咽了。肖大鵬怔住了。良久,他才醒轉過來,咽了口唾沫,說:“可是,我也沒坐過飛機。去吉隆坡的事,都是我編的。”
“什么?”女人瞪大了眼睛。驚異過后,爆發出一陣高亢的笑聲。笑聲清脆尖利,從街巷中升起,直沖云霄。
夏日的尾巴,在肖大鵬閉門不出的日子里,一點一點縮短;秋季在刮了幾次風,下了幾場雨后,也逐漸走向深處。
肖大鵬關了屋門,一待就是一天。有時候,他也踱到院子里,坐在屋檐下的馬扎上,看青色的天空中,流云聚攏成團又消散如煙。哀傷也在他的心里攏攏聚聚,凝結成團,卻怎么都無法隨風消散。
肖大鵬千想萬想,怎么都想不通,自己怎么會和這么一樁事情扯上關系。活了大半輩子,他自忖自己不是一個幸運的人,但也談不上倒霉。然而這次,他卻像是被一雙無形的大手,輕輕地舉起來,又重重地摔下去,摔得筋斷骨折,幾個月過去了,他都緩不過勁兒來。他總感覺自那天走進魏紅麗的屋里起,就有一雙眼睛在暗處盯著他,不然為什么他前腳剛走,魏紅麗就被害了。他又反過來想,如果他那天不主動約魏紅麗,對她給他釋放的信號視而不見,她是不是就會躲過這一劫。說來說去,都是他的錯,是他害了魏紅麗。如果不是因為貪心,他就不會接受魏紅麗,事情說不定就不會發生了。都罵那個殺人犯財迷了心竅,仔細想想,他的行為和那個殺人犯的,又有什么區別?這樣一想,肖大鵬又是冷汗涔涔。
還有對門女人的那場笑,當時就像幾個清脆的耳光扇在了他臉上,扇得他滿臉通紅,幾個月過去了,那紅暈都沒有消失。他越想越覺得自己可笑,干嗎要吹那么個牛呢。他都能想象得出,他坐在院子里吹牛,女人得有多反感。
之前,對于自己編造的謊言,肖大鵬不是沒生出過后悔之意。自己不該撒謊的。的確,撒一個謊要用無數的謊去圓。那天,他就不應該對李兵說自己去過吉隆坡。當時他只是隨口一說,至于吉隆坡這個地名,也是他腦子里隨即迸出來的,他也搞不清楚他從哪里知道的這個地名。過了幾日,當他在街巷里閑轉時,就有街坊迎上來和他搭訕,問的就是有關吉隆坡的事情。他只能現場編謊,敷衍了幾句,就借故有事離開了,邊走心里邊嘀咕,孫子才去過吉隆坡。別說沒去過,就是飛機,老子也一次沒坐過啊。不是買不起那張機票,這些年,在外面打工,多多少少他還是積攢下了些,可他和一般的打工人一樣,沒有享受的心態。他的長途遠行,通常都是綠皮火車,一張硬座票,從南坐到北,也有坐臥鋪的時候,在他來說,算是頂奢侈享受的了。
為了避免其他人追問吉隆坡的事情,肖大鵬早早回了家。那一天,他一直抱著手機不停地查閱,去吉隆坡的機票需要多少錢,吉隆坡有哪些著名的景點,吉隆坡人的吃喝穿戴、交通工具等等,他恨不得拿個本本記下來。為了不穿幫,他還挖空心思地編了幾件自己在吉隆坡的趣事和糗事。沒想到當天晚飯后就用上了,有幾個鄉鄰來到他的院子里,圍著他讓他講講。剛開始他還有點緊張,舌頭打著顫,講著講著就順溜了。
沒想到,女人真以為他去過吉隆坡。可能他的樣子真太討厭了,才使女人那么憎惡。那天,他其實也問過女人改口的原因。女人說,她很少說假話,做偽證的確是因為看他不順眼。出了公安局的門就后悔了,她覺得自己會良心不安的。聽了這話,肖大鵬當時就怔住了。這些日子,躺在屋子里,他一直都在琢磨這幾句話,越琢磨越覺得羞愧難當。曾經他還看不上女人,現在看來,他給人提鞋都不配。
肖大鵬躺在屋子里,鉆了牛角尖一樣地想著這些問題,想得腦殼發沉,有些想明白了,有些仍然懵懵懂懂。痛苦和煎熬纏繞著他,使他的身體與精神,越來越沉重,從未有過的沉重。
窗外的一隅天空,隨著季節的變換,也變換著不同色調,從清晨到黃昏,一日比一日冷;秋風也時緊時歇,狂風大作時,刮得門窗跟上“哐當哐當”地響,在肖大鵬的耳畔,反復震蕩著,使他憂傷的心里,又加入了一些不一樣的內容。
那一日卻是好天氣,隔著窗玻璃,他都能感覺到天空的響晴。推開門,卻是徹骨的寒冷。這股冷,侵襲的速度很快,立刻在他裸露的皮膚上,形成了一股鮮明的沖擊,然后迅速蔓延至周身,直達內里,使他虛乏的身體,為之一振,似乎獲得了一種久違的力量。肖大鵬開了院門,打算把積了一窗臺底的垃圾,清理出去。
對面的院門照樣大敞著。女人正在院子中央的菜圃里忙活,經了幾場秋霜秋雨后,原本濃綠葳蕤的菜棵變得憔悴枯黃,被幾場大風吹過后,枯枝敗葉到處飄飛。女人拔了那豆角桿,整整齊齊地放在墻角下。肖大鵬才有了時間過得真快的感覺,初夏女人插桿的情景還如在眼前。這段日子,他過得煎熬,總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女人的老娘蓋著個毯子,坐在南墻根下曬太陽,那只狗臥在她腳下,打著瞌睡。
許時門栓劃地的聲音太刺耳,那狗警覺地豎起了耳朵,女人和老娘也轉過頭來朝肖大鵬這邊瞧,待看清楚了門口的人時,臉上就都露出了驚異的神情,仿佛看到的是一個陌生人,狗也對著他“汪汪”叫了起來。肖大鵬有些緊張,他依然害怕見到人,尤其是對面的女人。女人的老娘主動招呼他:“小肖,出門了啊?”他嘴里“嗯嗯”著,目光卻瞟向女人,女人也正盯著他看呢,眼神里沒有了之前的鄙薄加譏誚,看上去很平靜。老娘又說:“小肖啊,你瘦了,瘦太多了。”肖大鵬已經好久沒照鏡子了,他不知道自己現在看上去清瘦憔悴、神情憂郁,像換了個人似的。他嘴里依然“嗯嗯”著,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便端著簸箕朝巷底的垃圾桶走去。
遠方的轟鳴聲越來越近,一架飛機從南郊飛來,離地面不是很遠。這些日子,肖大鵬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一次都沒出來看過飛機。這還是他第一次近距離地觀察,不是以前看到的玩具樣的劃著兩條細長白線的小飛機,也不是從電視或者手機上看到的圖片或者視頻,是真正的飛機,昂貴金屬制成的巨型大鳥,氣勢非凡,英姿颯爽。他的腳蹤跟隨著飛機,進到了自家的院子,目光跟隨著飛機飛了很遠,直到再也看不見。對門的女人和她的老娘,也正無限神往地看著遠去的飛機。
“你說那么大個鐵疙瘩,是怎么飛到天空中去的。”老娘像是提問,又像是自言自語。“我的娘哎,這個問題你都問了八百遍了,不是給你說了嘛,科學原理。飛機本身的設計是一個方面,還靠滑行,靠氣流的托舉。”女人的這個回答,肖大鵬再熟悉不過,這是百度百科上的回答,之前他也準備過,只是從未有鄉鄰問過他,可能是覺得幼稚吧。老娘果然一副害羞的樣子,訕訕地說:“我一看見那東西飛過,就忍不住想問。”女人就笑了,再跟老娘解釋時,顯得耐心了很多。
“等明年開春,您的腿腳好了,我們就坐飛機去北京,到天安門廣場去。”女人對老娘說。聽著母女倆的對話,肖大鵬感覺有一股熱流劃過自己的胸腔,他被女人說話的勁頭感染了,有些振奮。他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明天他就出門打工,他要攢夠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元,明年他一定要坐飛機,到吉隆坡去看看。
責任編輯 晨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