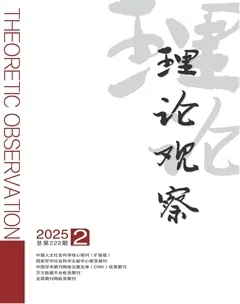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反思與方法論啟示
摘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引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力爭實現國與國之間、個體與個人之間合作共贏的發展格局。這一思想推動“沖突對抗”向“命運與共”精進,“二元對立”向“多元一體”轉化,“主觀意志”向“實踐思維”轉進,“普世價值”向“共同價值”嬗變,破除了對立競爭的僵化思維定勢,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思維陷阱,體現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從歷史到邏輯,從反思到實踐,以及二者的相互統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更為曠闊的視角來構建全人類的發展愿景,必將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引領世界歷史進步、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方法論遵循。
關鍵詞:唯物史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反思;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5)02 — 0016 — 08
在邁入21世紀的最初二十年,全球形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面對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不禁要問:世界歷史發展將呈現什么樣的趨勢?國際秩序會朝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能否向世界展示大國擔當?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通過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對人類發展價值的理性批判,實現了從沖突、對立、抽象、封閉,轉向與共、多元、實踐、開放的價值轉型,破除了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定勢,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思維陷阱,著眼于全人類命運與共的整體性,突出全人類利益的一致性,真正站在世界各國互惠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礎上,實現發展成果由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展現出深刻的理論反思與價值重塑。
一、“沖突對抗”向“命運與共”轉變
近現代以來,世界歷史先后經歷了500余年的殖民主義時代、200余年的帝國主義時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70余年的霸權主義時代。先是歐洲殖民,再是美蘇爭霸,而后則是美國超霸、獨霸。蘇聯解體后,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占據霸主地位,為了維持其霸權、強權不擇手段地打壓、壓榨其他國家,特別是打壓相對落后國家已成劣習;對于或意識形態不同、或政治制度不同、或經濟體制不同、或不追隨美國的國家,動輒制裁、圍堵,策劃煽動“顏色革命”,以推翻其合法政府,扶持美國和西方的傀儡和代理人。美國的獨霸、窮兵黷武成為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亂、敘利亞戰亂的根源。世界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和勢力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回顧歷史進程,人類不斷經歷沖突戰亂、動亂,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沖突與對抗的根源,時刻會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霸權主義規定了一種帶有內部差異的相互滲透的方式,呈現出多種多樣的矛盾性、分離性。”[1]無論哪個時代,只要存在霸權主義,人類就避免不了深陷沖突和對抗的泥潭。
自現代化進程推進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抓住了三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先進的科學技術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助推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成為世界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抓住遠離戰爭腹地的機遇,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綜合實力顯著增強,遠遠超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頭號強國。冷戰結束后,美國躍升為世界的一極,成為名副其實的“權力中心”。人類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卻拋出“文明沖突論”,未能脫離“沖突對抗”的理論框架。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世界話語體系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翻版。“文明沖突論”處處表現出西方學者對美國是否能繼續保持和維護“世界中心”地位的懷疑和擔憂。一批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的巨大恐慌。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威脅和挑戰,重新拋出“修昔底德陷阱”論,鼓吹強國必霸的錯誤言論,企圖藉此遏制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提出的大國競爭的命題,認為兩國之間對立和沖突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2]“修昔底德陷阱”蘊含的理論邏輯是,新興國家一旦崛起后,必然要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進而對守成大國的權力、利益和主導地位構成威脅,造成心理恐慌,為維護其權益對新興國家進行遏制打壓,甚至孤注一擲發動戰爭。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總體趨勢來看,通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逐步實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達至自然性與社會性、物質性與精神性、個體性與整體性、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完整統一。從“命運與共”→“命運分殊”→“命運共同體”,這種歷史邏輯與價值趨向體現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而資本主義社會因資本作祟奉行的是“沖突對抗”的價值選擇,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趨向截然相悖。“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3]人類總是在實踐中逐步接近、認識、掌握必然規律的,這種按照必然規律來構造即“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實踐過程,既是一個“實然”的又是一個“應然”的過程。但具體勞動過程具有“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現實性、可能性,即便是在“異化”勞動中人民群眾也在自覺與不自覺地“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但是,當社會主體的勞動者被剝削殆盡、兩極殊分、民不聊生、環境惡化之時,便會產生矛盾糾紛、沖突對抗,以致勞動階層通過反抗、斗爭打破舊的平衡而構建新的平衡。當今時代,面對愈加錯綜復雜的矛盾,面對霸權紛爭的角逐,面對環境惡化的困境,人類不斷反思、改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熱衷的“沖突對抗”的價值選擇,代之以“命運共同體”的科學價值目標引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力爭實現國與國之間、個體與個人之間合作共贏的發展格局。
21世紀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延續零和博弈和叢林法則等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與后發國家的關系問題。現有的這種國際關系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適者生存,將叢林法則搬挪到國際社會,將“修昔底德陷阱”重新搬到世界政治舞臺,想盡一些辦法壓制、欺凌廣大后發國家,嚴重破壞國際關系良性發展。霸權主義所秉承的邏輯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論,而“國強必霸、霸則必戰”成為西方國家認識和處理國際關系的霸權邏輯。他們秉承“修昔底德陷阱”論,其目的在于維護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延續數百年的權益和地位,千方百計地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辯護,不擇手段地遏制和打壓后發國家的發展勢頭。當前,由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快速崛起,使美國深深地擔憂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戰,棄國際準則和貿易規則于不顧,不斷挑戰中美互利共贏的和平局面。美國不僅用“修昔底德陷阱”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中美關系,而且致力于構建一套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話語體系,為美國污蔑、打壓中國崛起編織理論依據、輿論氛圍和強勢話語,以“中國威脅論”的種種謊言污蔑中國,掩蓋其卑劣伎倆和強盜行徑的霸權主義實質。
根深蒂固的“國強必霸”思維,是西方現代化發展邏輯的高度概括和典型思維。從西方工業革命開始,西方就用霸權來衡量和宰制世界的版圖,從這一邏輯出發,西方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判斷必然帶有偏見,必然以陳舊、對抗的邏輯審視他國的發展。從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英法等資本主義老牌勁旅以“文明中心”自居,將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程度最高的社會,將非西方國家視為文明程度底下的野蠻社會,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西方模式為標準的現代化唯一途徑的思維定勢。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崛起,生動證明了現代化發展模式并不是要依靠壓迫和霸權。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權邏輯受到了質疑和挑戰。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拒絕承認這一事實,反而拋出“中國威脅論”的歪曲言論來維護霸權邏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危機頻發,各種“主義”盛行,如果仍按照西方老套的思維和邏輯來建構世界秩序,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堅定地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實現各國的互利共贏,與西方“沖突對抗”的思維邏輯存在本質上的差異。西方的發展模式和思維定勢,總是從零和博弈、二元對立的方式處理國際問題、對待后發國家的發展,是不利于世界和平與進步的。西方的發展模式不是將全人類都作為“命運與共”的主體成員,不是為了滿足所有主體成員的需要,也不是為了促進所有主體成員的全面發展,而是為了滿足一些擁有資本和霸權的少數成員的利己需要與欲望。
當今世界的主題依然是和平與發展,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都與修昔底德所處的時代相去甚遠。全球化編織了世界的地球村網絡,不同國家、民族經濟和文化的普遍聯系不斷增強,偌大的世界凝結為一個有機整體,各國利益休戚相關。中美關系是大國關系中最為棘手的一對雙邊關系,不斷崛起的新興中國和傳統守成大國美國之間,能否找到實現兩國合作共贏的一條道路,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偏見,對中美兩個大國的可持續發展,乃至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都至關重要。有西方學者清醒地指出,“美國和中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取得了超級大國地位。中國的發展未沿襲軍事成功的老路……中國崛起不是敵人慘敗的結果,不是在任何意義上建立帝國的嘗試。”[4]不僅如此,中國為避免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在理論上、行動上做出了各方面努力。中國反復聲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無意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中美兩國在許多領域擁有共同利益,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具有現實可能性。一方面,中美兩國應攜手應對世界面臨一系列共同挑戰。例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屢禁不止的問題;多方面的環境保護問題;遺傳學操縱和其他科技技術發展——只服從于利益與權力,而不是服從于人類的福利的控制問題;國際犯罪率上升的問題;網絡病毒蔓延的問題;減少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移民問題等等”。[5]這些都是中美需要而且可以深度合作的領域。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在貿易、科技、人文、醫療、教育等領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間。中美雙邊貿易的不斷擴大,兩國經濟深度交融,不僅使雙方獲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促進了亞太地區的共同發展。中國探索了一條改革開放、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發展之路,沒有搞對外擴張、沒有搞武裝侵略,依靠艱苦奮斗和辛勤勞動實現了快速發展,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6]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國際上,中國一直奉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展示負責任大國形象,營造共同發展的良好環境和輿論氛圍。文明的、負責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的崛起,向世界人民詮釋著一條與西方大國截然不同的強盛之路。這條道路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合理關切他國利益,將中華民族的利益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主張大國應該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充分肯定國家應當承擔的歷史角色,包容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資源稟賦、發展水平各異,強調應當把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放置于自身力量的基點上,堅持自己的事情必須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從自己的國情和實際出發自主選擇本國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作為日常話語的一種建構,國家是集體實體,存在于民,借力于民。國家不分歷史長短、人數多少、力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這也是不同國家政黨和社會組織開展交往的基礎。國與國之間要堅持以寬廣胸懷尊重不同國家對全人類共同價值內涵的認識和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己私利搞“雙重標準”,反對把一個國家的發展建立在損害別國利益之上。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的背景下,世界各國都應當肩負起為本國和世界人民謀發展的歷史責任,攜手應對共同的時代挑戰。從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連的藍圖設計,到“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設立、絲路基金的設立、世界政黨大會及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勝利召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不懈追求以及開創性實踐。習近平主席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呼吁,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引領21世紀的世界迎來“合作共贏”時代,在這一時代,和平備受推崇而戰爭遭人唾棄,合作帶來發展而對抗損人害己,共贏受到普遍歡迎而零和博弈終遭冷落,和平、進步、發展是人類社會無法抗拒的時代主流和永恒主題。共贏時代展現出公正性、平等性、包容性、和諧性、可持續性、穩定性,是對舊的利己主義價值觀的超越,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先進理念和實踐范式。
二、“二元對立”向“多元一體”轉化
從哲學上講,形而上學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執此一端,非此即彼,看不到事物內部、事物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二元對立”就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長期以來,由于不同文明之間在民族傳統、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差異,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或對抗、或聯合的不穩定關系,西方社會秉承“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來處理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亨廷頓曾指出:“在這個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的沖突。”[7]西方的歷史話語和認知框架恪守著“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無論歷史境遇發生何種變化、社會歷史發生了何種變遷,西方的價值評判方式、評判標準依然沒有改變。從歐洲殖民擴張開始,西方中心主義開始形成,西方眾多戴著有色眼鏡的人一直俯視、貶低非西方,這種主觀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的偏見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里根深蒂固。
啟蒙運動時期,西歐率先實現了思想革新和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贏得了對于中世紀封建思想、封建領主和教會神權的勝利,便將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絕對化、神圣化,視為文明的終結形態。這種狹隘的西方民族主義,鄙視不發達國家和民族,認為西方是文明社會,而東方是蠻夷之地、南方是愚昧貧瘠之地。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的主要民族國家,從原先被兩極格局所分化、壓抑的地區爭端與民族沖突中紛紛釋放出來,大力發展民族經濟,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西方被迫創新其話語體系,以拉攏曾經是對方陣營的民族國家,其實質依舊是“零和博弈”“叢林法則”面對新態勢的一種重構。但這種重構仍然沒有擺脫西方固有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和思維模式,并以此作為價值標準來評判是非、綁架人類的認知體系。
不少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深刻批判西方國家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取向。如哈貝馬斯深刻批判了這種價值評價模式,他強調,“將政治割裂成愚蠢的、代價高昂的非戰即和的二元對立,對世界是無益的”“單單意識到我們具有共同的政治命運和共同的未來就可以讓少數派不去阻礙多數派的意愿。從根本上說,一個民族的公民必須將另一個民族的公民視為‘我們中的一員’。這方面的缺失引出了如下問題——這也是不少懷疑論者的反應——是否存在這樣的歷史經驗、傳統和成就,它們對歐洲公民而言,可以建構起對于同舟共濟的政治命運的意識?對未來歐洲的誘人的、不遺余力的‘愿景’并不會從天而降,今天,它只能從走投無路的不安感中誕生出來。在這樣的窘境中,歐洲人可以喚起那種愿景,但它必須在一個眾聲喧嘩的公共領域中進行表達。如果這一主題至今還沒有列入議事日程的話,我們知識分子就失敗了。”[8]哈貝馬斯的論述深刻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緊密相連,任何一種文明和文化不可能絕對勝出,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不可能絕對凌駕于其他民族和國家之上。全球化的文化交融需要不同質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交流、整合、重構、創新,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價值評價體系。各民族國家之間應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思想聚合點,不斷拓展交往和外延,豐富交往內涵,創新交往方式,完善全方位、立體化、多層次、寬領域的交往格局,增強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信任和理解。
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發展,世界范圍內的分工和協作日益加深。“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9]一個重要的特征是中國等東方大國成功地進行改革開放,變革了舊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融入并改變了國際體系,呈現出不同于二元對立價值體系的一些特征,“二元對立”的價值評價日漸與歷史潮流和現實邏輯不符,如若不消除“二元對立”的價值評價方式,將會導致出現一個毫無意義、缺失正確價值標準的世界。毋庸諱言,極端的“二元對立”評價體系式微,多元一體的價值評價體系正為世人所接受,“命運共同體”意識正是人類在應對諸如環境、病毒等共同危機的反映,多元存在且“歸一”的一體化進程逐步加速。當然,此“歸一”不是西方強權語境下“一統天下”西方化的一體化,而是在共同的利益觀、命運觀和合作觀指引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為原則,謀求和諧共生、共克時艱,尋找人類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既不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又不委過于人推卸共同責任。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共同性與文化的多樣性并存,人類利益的整體性與規范的可協調性并存,倡導多元價值評價體系,順應世界歷史發展的需求,摒棄并超越舊的“非我同類即為異類”的思維模式,使價值評價標準從“非黑即白”的絕對對立,轉向相互交融的“多元一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之所以為世界人民所接受,經實踐證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以人類整體利益為最高利益,統籌兼顧了“部分—整體”“普遍—特殊”等代表部分的多元利益方,面對世界民族發展的各種不平衡問題,以新的更加積極的運作方式,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實現向“多元一體”共同發展的價值標準轉向。
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優勢就是科學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無疑,這二者的統一占據了“科學立足點”和“道德制高點”。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歷史事實、世界潮流為依據,科學把握全球化、命運一體化的客觀規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性認識;它重視國際利益與國際義務相統一、整體利益與部分利益相統一、發達國家權益與發展中國家權益相統一,實現了權力、利益、倫理(責任)三者的有機統一,進而有效緩解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性與包容性的矛盾,成為利益多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科學指導與價值引領;在多元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國際政治與合作的行動邏輯將發生轉變,國際合作的整體性、協調性、包容性可以有效擺脫舊的價值評價體系、方式對人類整體的割裂,進而轉向注重人類價值的共同性和文化的多樣性。因此,多元一體的國際合作成為國與國之間最能接受的合作理念,通過價值評價體系、方式的轉變,為人類整體利益做加法和乘法。
三、“主觀意志”向“實踐思維”轉進
人類是一種“類”存在,追求“類”實現和“類”價值。馬克思站在“類”本質上思考人類發展的未來命運,從橫向上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進行考察,從縱向上對人類社會過去、現在、未來去向何處開展思考。馬克思對人的“類”本質規定,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地區、時間、空間的局限。比如,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本質是“絕對精神”,類派生個體,千差萬別的個體是類本質的外化和異化的表現,而個體存在的根本在于具有類本質“觀念”,如此,觀念成了主體,而現實的鮮活的個體卻被理解為觀念內在想象活動的結果。類存在不是自身的存在,而是外在于個體本身的異己的存在,世界歷史是“絕對精神”的外化。[10]馬克思對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類概念進行了批判,認為觀念、精神的思辨本質應該從現實的個人中去尋找,從而賦予其現實基礎。費爾巴哈則從直觀體驗來規定人的“類”本質。他只看到認識自然的存在,而沒有把人看作自由的有意識的實踐存在。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感性的人”的基礎上提出了“現實的歷史的人”的概念。他指出,在“類”本質意義上思考人,不是要思考人的肉體、情感、感性,而是要思考人的實踐、物質生產、社會關系。因此,人的“類”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實踐活動,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內在統一的關系,“類”特性的實現就是超越“直觀體驗”“絕對精神”,轉向“現實的歷史的人”。
當今,世界歷史前進步伐不斷加快,社會歷史與現實條件已與馬克思時代迥然有別,但人類社會發展依然在馬克思所設想的道路上前進。世界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依然是生產力,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生產方式的變革,由此形成了人類社會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交往。這一進程不是黑格爾自我意識的抽象行動,而是人類實踐推動的,可以為經驗所證明的。事實勝于雄辯,人的行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并不是所謂的某種虛幻的、神秘的“抽象思維”,而是指向和回歸現實世界的極具確定性的“人的實踐”,惟有以“實踐思維”指導人類的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才能推動世界歷史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實踐的思維觀點從抽象的人以及與人分離的神或觀念世界,轉向關注現實中的人及其與現實世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客觀物質關系。回顧歷史,由“抽象思維”出發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規則總是試圖掩飾不平等世界的本質,設置服務于統治階層的規則和社會觀念。而指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思維”則意在改造現實世界,倡導人類社會對平等、正義等共同價值理念的追求,力避用功利思維、零和博弈看待、解決共同關切問題的風險和陷阱,調整實踐活動和社會關系達到科學性、價值性的統一,構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抵制抽象思維的唯意志論和意志自由論。
一方面,“實踐思維”打破現有國際關系中人設的壁壘,強調世界各國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聯系之網中,主張打通人類實踐的阻隔加強互聯互通。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事實背后總有其共性的、普遍的發展規律,那些鼓吹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僅僅維護特定國家利益集團和群體利益,而撕裂人類社會、人類共同利益和整體性聯系的唯意志論的霸權主義思維,終將被人類社會所摒棄,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基于“實踐思維”的人類實踐,關注全人類平等的實踐主體,關注供全人類發展進步所需的物質客體,以及超越國界的爭取人類共同利益的實踐方式和手段,即實現實踐主體、客體、介體等實踐要素的有機聯動與統一。這種實踐是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發展實踐,是符合人類本質的普遍聯系與互動。
另一方面,“實踐思維”可以根據既有的成功經驗,正確認識、規劃未來并創造性地改變現實。正是基于對社會主體的歷史地位和責任擔當認識的提升,馬克思認為,從“抽象思維”走向“實踐思維”,代表著人類作為社會實踐的主體,對待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態度實現了黑格爾所說的“實踐的和理論的”統一。人類創造理想的價值客體的基本前提是正確認識當下的客觀存在,并在正確的合規律的“實踐觀念”指導下創造出這個曾經在頭腦中觀念地存在著的價值客體,充分凸顯出人類實踐活動的客觀現實性、自覺能動性與社會歷史性。這就要求人類面對全球化的復雜難題發揮歷史創造主體的作用并擔負起時代責任。當今時代,在這個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不充分,文化傳播多樣化的時空壓縮膠囊里,社會進步帶來人類普遍福利改善的同時,在實踐中戰勝面臨的危機,克服來自社會、自然界和內心世界的挑戰顯得尤為重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實踐思維”轉向,讓人類保持樂觀謹慎地對待社會發展進步,積極勇敢地應對動蕩與危機,以更具主體意識的創造性行動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不能依靠“絕對精神”“孤立的個人”或“宗教情感”來眷顧、垂憐,而只能依靠全人類的社會實踐,百折不撓地去拼搏、去構建。
唯物史觀解釋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科學回答了世界歷史發展演變的動力和基本走向問題,體現出鮮明的實踐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表達了對人類命運美好的愿景,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從實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邁向應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11]“應然”的共同體必然包含邁向這一形式的實踐過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深刻回答了人類困境的解決方案,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前瞻性和科學性。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的理論邏輯,突出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將人的發展納入世界歷史進程中去思考和謀劃,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延續了這一理論邏輯,強調人的“類”本質及其功能的凸顯。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現時代對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理論的實踐繼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推動世界歷史朝著“真正共同體”不斷邁進。
四、“普世價值”向“共同價值”嬗變
價值反映的是主體的需要與客體滿足主體需要,及其滿足程度之間的相互關系,能夠滿足主體需要的物質、精神以及人(個人、群體和國家)皆可納入客體的范疇。價值反映客體和主體的相互作用關系,價值不能脫離主客體,直接表現為抽象的存在。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加快,人類相互聯系和彼此交往加深,交集越來越多、越來越廣,產生了共同的價值需求。這種需求同孤立隔絕狀態下個人自我需求決然不同。它不是超歷史的、抽象的、虛幻的、固化的,而是歷史的、實踐的、具體的、變化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需求。由于各國之間共同交集的領域增多、共同利益加深,世界歷史催生了基于相同需求和利益取向的價值共識。
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將個人從具體的社會關系中抽離出來,探索人的共性,提出以“自由、平等、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其實質是從“抽象的個體”中得出“抽象的共性”,由抽象的人組成抽象的社會。爾后基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需要,“普世價值”的內涵進一步擴展,包含多重含義,既指代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等,也指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如私有化、自由主義、三權分立等,還包含由此衍生的國際準則,如“華盛頓共識”、霸權主義、“中心—邊緣”的政治格局等,形成了以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的話語體系。西方推崇和宣傳“普世價值”,不是旨在宣揚人類的共同價值理念,而是以抽象的價值理念為偽善的面紗,以人類道德制高點自居,強力推行其基本制度、體制,維護西方的權威話語體系,并由此衍生出西方的所謂“國際標準”和評價體系。在特定場域條件下具有部分合理性的價值觀念,被西方資產階級詮釋、扭曲為意識形態的話語工具,其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資產階級意志的本質要求,必然與自身吹捧的普世價值產生矛盾,進而成為名副其實的謊言。
一些發展中國家被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好的辭藻和謊言所蒙騙,未能認清西方“普世價值”的本質與危害,未能抵御西方意識形態的侵蝕,淪為西方經濟政治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附庸。早期全球化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擴張之上的,資本主義國家用堅船利炮轟開了落后國家的大門,用武力建立并維護世界殖民體系。冷戰結束后,發達國家找到了更具蒙蔽性、欺騙性的武器,使西方國家的武力威脅和武裝干涉打上“正義的旗號”。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2]普世價值是沒有硝煙的武器,企圖將之滲透到全世界,其主體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在理論的構建過程和實際操作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往往把資產階級不可告人的政治、經濟企圖“遮蔽”,把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未能實現的、人類所向往的美好的價值觀念,宣揚成為拯救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發展道路和自身國情的民族國家的靈丹妙藥和普世模式。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傳播手段與亂世法則。基辛格指出:“美國的對外交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而是傳播價值觀的工程。它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13]
顯而易見,“普世價值”之所以能夠影響民族國家的發展,是因為它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一,“普世價值”具有抽象性,遠離人的實踐性。馬克思認為,任何價值觀念,都是發展的、變化的,不是絕對的、永恒的。“普世價值”把理性當做現存一切事物的裁判者,先驗地存在于個體和社會之中,是跨越現實因素的抽象價值。而作為反映人與人社會關系的價值,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發揮作用,離開社會實踐討論價值只能是“空中樓閣”。顯然,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人類一切價值觀念都不能擺脫生產力、社會關系客觀條件的制約,根本不存在什么超現實的“普世價值”。其二,“普世價值”有超越思想觀念本身的政治圖謀和欲望。由于是基于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制度之上的價值觀念體系,“普世價值”本然地為西方話語體系“代言”。西方表面上看似在宣傳人類普遍的價值觀念,實際上是憑借所謂超越民族、國家、階級,超越文明、宗教、信仰差異的抽象共性,將自身的制度模式強加予他國,使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政治的附庸,以利于它們繼續攫取霸權邏輯和強權政治的紅利。其三,“普世價值”實質上是資本控制世界的意識形態工具。“普世價值”這種抽象的價值理念生成并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資本披著外衣攫取私利時尋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反映。
事實上,“普世價值”與具有天生不平等性的資本相結合,產生的只能是形式和抽象的平等與自由。資本所帶來的不斷擴大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導致“平等”“自由”等“普世價值”掩蓋之下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正如米歇爾·羅卡德、多米尼克·布爾格在《世界報》的聯合署名文章《人類物種,已經陷入危險之中》中指出,“在啟蒙運動時代,在培根、笛卡爾或者甚是黑格爾所生活的時期,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的生活水平超過最貧困地區的兩倍。社會不平等應該讓現代工程的發明者們感到羞愧。”[14]這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困境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國家不遺余力地在世界范圍內宣揚“普世價值”,以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為誘餌,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納入西方軌道,進而控制發展中國家。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加深,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國家大流行,讓“普世價值”似乎失靈了。西方“普世價值”及其衍生的經濟政治弊端日漸凸顯,“逆全球化”浪潮不斷涌現,資本主義世界霸權體系矛盾重重,無法實現自救。國際社會需要新型全球化,人類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和新的理念。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共同價值”理念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客觀需求的價值理念。
人的生存發展離不開所處的共同體,家庭、村社、社群、民族、政黨、國家都是共同體的形式。在不同層次和不同形式的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形成客觀的聯系與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共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如共同的物質生產、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乃至共同的價值觀念。“共同價值”是內生性的,是構成人類社會的每個民族、每個國家因客觀存在的“共同需求”而生成的觀念。它與共同體相互促進,共同價值維系著共同體的秩序,是將該共同體的成員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人類“共同價值”是在充分尊重各國特殊道路、制度、國情的基礎上,符合人民價值期待的根本性價值,是國家、地區和群體之間平等對話基礎上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價值追求。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真誠呼吁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15]這既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要求的反映,也是對世界各國共同愿望的表達。
一方面,“共同價值”的內涵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是多樣性的而非單一性的,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共同價值”是對人類社會共同問題、共同需要的認知和反映。正因為世界上存在霸權主義,恃強凌弱問題嚴峻,平等才成為人們的價值共識;正因為世界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貧富分化問題嚴重,公平才成為人們的價值共識;正因為人類仍然處于資本——貨幣異化邏輯之下的社會關系中,受到不合理的必然性的束縛,自由才成為人們的價值共識。當前人類面臨諸多共同的威脅和挑戰,在許多領域危及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欲滿足人類社會發展要求,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形成價值共識,方能解除這些威脅和挑戰。而“共同價值”從哪里來呢?它既非來自天才大腦的臆想,又非來自天國的神諭,而是來自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交往的客觀實踐,實踐中因共同需求形成了共同價值。各國人民在相互交流、傳播、學習、互鑒的過程中,形成了普遍性的價值認同、價值追求。由此看來,“共同價值”的提出具有歷史必然性、社會現實性、客觀實踐性,必然是對以“普世價值”為根本的世界話語體系的否定。
另一方面,“共同價值”是人類在相互交流、交往、交融過程中形成的。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區在歷史實踐中形成了共同價值的具體表現形態,并結合各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選擇適合自身的實踐形式。共同價值在尊重差異性的基礎上實現了共性和個性的辯證統一。全球化時代,人類共同價值有助于推動形成全球化發展新格局。人類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將人類緊緊聯系在一起,傳統的霸權思維和模式無法提供解決危機的有效手段。人類只有在共同價值的引領下,在國際范圍內尋求對全人類共同面臨重大問題上的價值共識,在“求同存異、共謀發展”中才能實現雙贏、多贏和共贏,才能有效化解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建立在共同價值基礎上的全球化發展不是為某個國家服務的,而是為世界各國和全人類服務的。“一帶一路”的生動實踐表明,人類共同價值尊重每個國家、民族的制度模式、意識形態、文化理念的多樣性,在謀求本國發展的同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由此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具有科學的理論淵源和科學的現實基礎,它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選擇、價值目標和價值主體。人類共同價值觀蘊含了生存價值觀、社會價值觀和政治價值觀三個方面的內容,具有包容性、共享性、開放性,對于構建新型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秩序、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話語權、提高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共同價值理念引領下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將取代西方固定思維模式之下全球化“舊思維”“舊模式”。中國正在以實際行動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正在以共同價值為指引,為全球經濟發展舉旗定向,注入共同價值內涵和發展動能。
〔參 考 文 獻〕
[1][美]阿爾君·阿帕杜萊.全球化[M].韓許高,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238.
[2][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9.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4][英]馬丁·阿爾布勞.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領導力理論[M].嚴忠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67-68.
[5][美]雅克·布道.建構世界共同體:全球化與共同善[M].萬俊人,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33-34.
[6]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64.
[7][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6.
[8][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分裂的西方[M].郁喆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46-48.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1.
[10]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81-82.
[11]汪信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真意涵[J].社會科學輯刊,2018(6).
[12]鄧小平文選: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13][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05-306.
[14][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M].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16.
[15]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5-56.
〔責任編輯:秋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