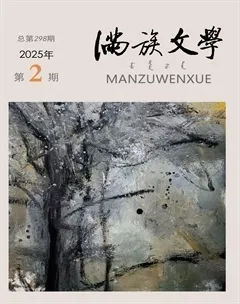正午
上到半山腰,望著兩邊密密叢叢的森林,聽著古怪的鳥叫,我瞬間有些恐懼了。再也不想去看什么飛瀑流影、歐陸風情了,更不想到熱帶植物園里去瞧什么龍血樹、豬籠草、蛋黃果樹了。時值七月的正午,云夢公園里一個人都沒有,在這個南方城市里,想必只有我這個北方人,才頂著攝氏四十度的高溫逛公園。云夢公園,不只是因為它的名字好,這兒還曾是我跟初戀男友第一次到這個城市逛過的第一個景點。本來走公園正門,進門上幾層臺階,就是著名的景點飛瀑流影(平臺上有一個圓形的水池,隨著音樂,里面噴泉飛濺,形成不同造型),我們就是坐在水池邊,望著腳下繪著玫瑰、蘭花的五彩臺階,他輕輕吻了我一下,然后說了年輕男人愛說、少女們迷醉的情語。更何況這個年輕男人個子高挑,眼神清亮,還愛詩,專用一些新鮮得像水果般的語言,撩撥得年輕女孩兒紛紛為他失眠。我們談了三年,最終他莫名其妙地娶了一個相貌平平的女孩為妻。
為什么走后門,是當地朋友的建議。她要陪我,我堅決回絕了,說有些地方適合一個人慢慢地走,晚飯我們一起吃。她意味深長地打量了我半天,說離我住的賓館不到兩公里就是公園的后門。我想,天實在太熱,抄個近路上山,一路都是風景,養眼,剛好還可以慢慢回味往事,年輕時光總是讓三十多歲的人留戀不已。當了別人丈夫的男友,隨著歲月的沉淀,在我心里只留下了美好。在該城只有半天時間,我要把這珍貴的時光用來緬懷青春。一個城市,有朋友有回憶,這個城市就是天堂。上午剛開完詩歌研討會,我心中仍詩意盎然。
穿過一條長滿棕櫚樹的鄉間小徑,我來到公園后門。一扇鏤空的小鐵門微閉,無人驗票,入口的小房間里,一臺電風扇在窗內不停地呼呼吹著,白色蚊帳里也沒有一人。反正我是軍人,不用買票。我大步邁進園里,這個依山而建的公園,跟前門一樣,也是一層層的臺階,一眼望不到頭,兩邊密密叢叢的樹木掩映得臺階更加局促窄小。好在頭頂樹蔭濃密,人不至于站在烈日下暴曬。
樹木花草大多我都沒見過,七彩陽光從綠色植物中穿透出來,好像電影里令我著迷的鏡頭,還有一股股香氣,襲得我心情大好。也顧不得熱了,又是拍照,又是打開手機軟件一一認識花花草草,不覺間就上到了半山腰。
心情緊張,先是由一些蛩聲引起的。接著我看到一棵棵樹木好像要倒下來,一些不知名的小鳥在不停地古怪地尖叫著,林間某個地方忽然呼啦一下,再呼啦一下,驚得樹葉一陣亂響,我的心像根橡皮筋,或緊或松。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呼哧呼哧地喘氣,又聽到樹杈咔嚓一聲裂開,嘩啦一聲倒下來,玻璃似的物體碰得當當作響。總之,就在那一刻,我腿發虛,心發緊,感覺此時像極了影視片中一些壞事即將到來的場景。
干脆還是原路返回吧,百度顯示我已走了八公里,離正門還有十幾公里。望著一層層望不盡的臺階,上面還有什么,不得而知。
就在這時,一團紅影從山頂高高的臺階慢慢移來,我一陣欣喜。終于有人了,我放心地抹了把臉上的汗珠,絕對不是因為熱,我想是正午的靜寂嚇出的虛汗。
那么是繼續上山呢,還是下山?正猶豫間,我發現那紅影越來越近,這是一個男人,肉色的身子在陽光下明晃晃地越來越近。在一個人都沒有的半山腰,又是大中午的,一個光著上身的男人忽然出現,我比先前更緊張了。
原來有人也非好事。
我立即決定,下山!一個個窄而陡的臺階,根本走不快,而他離我越來越近了,有二十多歲,赤著上身,身上卻背著一個黑色的雙肩包,手上提著一件紅色的T恤,不,是掄著,邊走,邊掄,急急地奔了下來。他的速度很快,那步子騰騰的,像陣鼓點,咚咚地敲在我心上。我很不合時宜地想到了一句詩:漁陽鼙鼓動地來。
可能因為想到了詩,我冷靜多了,心想,我又沒錢,也不年輕了,三十多歲的女人。再說,這兒可是城市中心的公園,又在光天化日之下。此念頭只是一閃,我又想起前幾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則消息,一個女孩子在公園晨跑時遇到一個從獄中放出來的男人,被先奸后殺。
這么一想,我腿軟心跳,頭上的汗又浮出了一層。回頭再看那人,臉黑黑的,個子足有一米八五。怎么辦?他越來越近了,跑不過,那么只有智斗。咱無論怎么說,是一個讀過書的大學生,不,嚴格意義上講,還拿到了碩士研究生文憑,學校也是響當當的名牌大學,知識可不只教咱寫幾篇文章換點稿費,還教會了咱如何做人,運用知識改變了命運,從農村走到城里,又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現在我得用學到的知識保護自己。這么一想,我步子就慢了,掏出手機,想報警。又一思忖,萬一是自己神經過敏,啥事也沒有,你報的哪門子警。思來想去,還是查到了公園管理處電話,怎么也打不進去。給朋友打電話,手機沒人接,我立即留語音,小聲說,后山人少,我遇到一個男人,有些害怕。然后假裝通了一會兒電話,心想,朋友即便馬上看到,她也不可能很快趕來。我只是想讓對方知道,我已告知了人,他們隨時有可能上山,他若存壞心,趁此趕緊滅火。
我假裝拍照,把手機調到振動狀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想著讓他過去,他在前面,我在后面,相對安全些。
他離我近了,我才發現他其實不到二十歲,好瘦,身上一道道肋骨極其明顯,左眼角附近還有一道拇指長的疤使他顯得滄桑了些。這樣我心里踏實了些,無論怎么說,年輕,總是經驗少些,好對付。還有他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這讓我心里更踏實了。讀書人,想必不會干壞事。
他越來越近,已在我手機鏡頭里出現了,我拍照的手晃得里面的密林也是模糊的,心跳得按捺不住。
我仍擎著手機邊走邊盼著他快點下去,沒想到他竟然走到我跟前,把手中的衣服系在了腰上,說,你想拍照,我幫你吧。
不用,不用。
我說完,怕惹惱了他,又補充道,謝謝。
他不走,卻一屁股坐到旁邊的臺階上,拿衣服扇著涼瞧了我一眼問,你也是一個人逛公園?
朋友馬上就來了。
怎么不上了?
天太熱。
他仍沒有要走的意思,我取下肩上背的小包,里面有兩瓶礦泉水,有幾本書,我想萬一遇到危險,這個包可以當武器。因為緊張,踩到了腳邊的太陽傘上,心想,真是,都嚇糊涂了,這是多好的防身武器呀。
天真熱,他又說。
是的,熱得讓人實在受不了,所以我讓朋友來接我回去,他很快就到了。我背上包,撐開傘,盡量讓自己的聲音不要那么顫抖。
他看著我,我低頭朝山下瞧,除了一眼望不到邊的層層臺階,啥也看不到。后面,更是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好后悔,上大學時,老師教過我們軍體拳,可是我早忘記了。不,好像有一招,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可以踢對方的要命處。對,男人的要命處。可是臺階這么密,別說踢人,就是兩人并排走,也易掉下去。更何況他比我高半頭。
朝對方的雙眼扔土,可是臺階光光的,啥也沒有。
我的武器只有一把傘,可是密密的臺階,跑不動呀。這個招不行。算了算了,靜觀其變。我繼續下山。
他抹了抹臉上的汗,又說,天真熱。跟我并排走。
眼神又一次瞟過來,我看著他干而發白的嘴唇,忽然想,硬斗不過,還是軟一些。男人都是憐弱者,你要是對他好,他豈能害你?這是去世的媽常說的話。我當兵走時,第一次坐長途汽車,她送我到車站的路上,給我說了一路的注意事項,其中就有這么一條:如果遇到壞人,不能逼對方,要盡力軟化他。十幾年了,雖然沒有遇到壞人,但我堅信此法一定有效。這么一想,我從包里掏出一瓶水,遞給他。
他顯然愣了一下,半天才明白過來,說,不要,不要。說著,擺擺手。
喝吧,我沒打開過,里面也沒有毒。
他接過水,顯然太渴了,一下子喝去大半瓶。我瞧了他一眼,問,這么熱的天,你也出來逛。聽你口音好像是陜西人。
是,額是陜西人,今上午工地沒電,出來逛逛,沒想到他媽的老天爺這么不給面子,把人往死里曬。我轉了一圈,上面山上一個人也沒有,也沒啥可轉的,除了樹,還是樹,還不如回去睡覺。他說著,又看了我一眼。
我心跳得更厲害了,心想,穩住,一定要穩住。便說,就是天太熱了,南方就這點不好,啊,聽你口音,咱們是老鄉呀。其實我只在陜西當過三年兵,又上了四年大學,也算是半個陜西人了,陜西話說得還是挺不錯的。我想跟對方拉近關系,這叫感情投資。
他興奮了,呵,我在南方兩年了,還真沒遇到陜西人。說著,伸出了手,我先嚇了一跳,看他不像干壞事的樣子,就輕輕握了一下。手掌粗糙,一個打工的小子,能壞到哪兒,我心態放松了,你家陜西哪里的?
長武的。
那是西蘭公路必經地呀,可是好地方。
你還知道長武?我們那可是個小地方,黃土高原。
我當兵時,班長是長武的。我說的是實話,謝謝班長這時救了我,我記得他說過,家鄉縣城有個昭仁寺,還有塊唐碑,是淺水塬大戰后李世民為犧牲的將士立的,于是我邊想邊編。誰都是戀家鄉的,挑起他的鄉情,他歪心思就淡了。
你們班長是長武哪搭的?他現在也當干部了?
他家好像是在縣城,三年后退伍了。對了,他說長武人常說,一碗白蒸饃泡血條湯,給知縣都不做。
他咧嘴笑了,一口白牙,挺齊整。對呀,聽說其他地方都沒有。血條湯你知道是咋做的不?
我搖了搖頭。
他興致勃勃地說,把豬血做成面條蒸熟,這就叫血條。湯呢,把水燒開后,放肉臊子、豆腐條、海帶絲,湯開后,把血條放進去煮熟,出鍋時,打只雞蛋,再撒幾片香菜,特別好吃。我聽我媽說過去逢年過節才能吃上,現在想吃,隨時做。
你說得我都想吃了。
我們長武的秦冠蘋果也特甜。他笑了,臉上的傷疤好像也不像我起初看時那么猙獰了,甚至讓人有點憐惜。我不禁又說,聽班長說,長武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就是柳毅傳書的地方,講的是一個愛……我說到這里,忽然意識到自己話題又危險了,趕緊調轉方向,對了,你家里還有弟弟妹妹嗎?
他搖了搖頭,說,上面還有兩個哥哥。我考上大學了,爸死得早,媽一個人帶著我們兄弟仨,剛給大哥蓋了房,娶了媳婦,二哥也二十五了,日子還是挺緊張的,我沒錢上學,才出來打工的。
一聽媳婦,我又緊張了,想了一下,馬上現編故事,說,我家也是農村的,有個哥哥和弟弟,哥哥對我可好了,出去打工回來,給我買表,給我買雨鞋,我當兵時,還送我到車站。哥哥結婚后跟我們分家了,現在我可想我弟了,這次出差回去,我要回家看看他。對了,你跟我弟弟個頭差不多,幫我參謀一下,我給他送什么禮物好呢?我想,我一定要轉移他的注意力,讓他隨著我的故事走,這樣拖延時間。我已給朋友發短信了,讓她趕緊跟公園管理處聯系,最好上來兩三個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剛才我裝看時間時,朋友回短信了,說我的定位已收到,她已在來的路上,讓我盡量周旋,只走大路,不要把對方逼急了,他要啥給啥,只要不傷人命。
他抹了一下眼睛,說,有姐真好。
我想給我弟弟買件衣服,可又怕大小不合適,想給他買把像城里男人一樣的刮胡刀,或者一條漂亮的領帶,你說好不好?
不好,不好。他認真地說。
那買什么呢?我仍沒有放慢腳步,舉著傘,好讓他不要太靠近我,與他保持著一米的距離。
你給你弟在城里找個工作多好。你不是軍官嗎?給你弟弟找一個不用打工的工作,讓他有時間看書,看電影,讓他穿著漂漂亮亮的衣服去找個好女孩,好好過日子,這才是你真正幫他。
我沒想到他這樣回答,一時有些發怔,說,我怕沒這本事。說著,一步跨下兩個臺階,差點兒摔倒。
他也加快了步速,跨了三個臺階,嘴上仍說,你是大學生呀,又在城里工作,又是軍官,你只要把這事放到心上,肯定就能給你弟找到工作,也不是要找多么好的,就是不要拖欠工錢的,閑時看書工頭不拳打腳踢的,不要十幾個人睡一間屋子,隨地吐痰不洗腳,能讓人瞧得起的工作就可以了。他說到這里,鼻子抽動了一下。
我弟只上過初中,他到城里能干什么?
他可以給人送水,送快遞,或者收發報紙什么的。實在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帶他到城里來玩玩,讓他看看這么美麗的公園。
這個可以辦到。
你是個好姐姐。
你要是有弟弟妹妹,一定也是個好哥哥。
我想會的。他說著,望了望四周,捏了下鼻子,我喜歡這個公園,喜歡漂亮的花草,喜歡城市,可是這個城市不是我們這些打工人的。
你不要那么想,我剛開始當兵時,也那么想,后來我上了大學,有了工作,我就覺得只要自己干得好,別人也會瞧得起咱們農村孩子的。我說咱們時,語氣重了些。
我望望后面,還是沒有來人。前面,公園門口的白房子隱約能看見了,我的心稍稍踏實了一些,忽聽到他說,你看,森林里多好看呀,那些樹,那些花,在咱們北方根本就見不到,你看那棵像啤酒的樹,長得多有意思。還有那棵樹,竟然叫面包樹。還有那棵樹枝上,怎么長了那么密密的草。對了,你進去我給你照張相吧,你到南方,又不是經常來,來了就照張相,我照相水平還是可以的,你不信可以看看我手機里這些照片,都是我平時拍的。有街景,有人群,還有天上的云彩和小鳥。
我當然沒有看,但嘴上贊嘆了幾聲,又擦了擦臉上的汗水。
他仍在興致勃勃地講。我拍的這些紅紅綠綠的花,我問過別人了,紅的叫三角梅,開白色碎花的樹叫香樟樹。你拍了照片可以給你弟弟發過去,以后你有時間了,帶你弟弟到南方來多好呀,即便冬天,這兒也四處都有花,花市花更多了,蝴蝶蘭、金桔、水仙、繡球、山茶,開得可漂亮了,要不,這個城怎么叫花城呢?我在宿舍養了一盆花,叫令箭荷花,它屬于仙人掌科,有刺,開著粉紅色的花,特別像荷花。對了,就像下面那種花,咱們下去,看看!
我剛一說好,馬上就后悔了。心想,他莫不是要騙著我到密林里,趁機干壞事?我沒了手機,不就跟外界斷了聯系?這么一想,我便笑著說,天太熱,還是算了,一動渾身都是汗。我說著,下山的步子加快了。
他卻停下說,那你幫我拍張吧,我們工地很忙,難得出來。雖然天熱,風景還是不錯的。
我看了他一眼,發現從他臉色上看,好像沒有做壞事的樣子,可是那臉上的傷疤好像又猙獰了。我急中生智,忙說,剛才我看到路邊寫了一行字,樹林里蛇多,不要隨意進去。
他朝四周看了看,是真的嗎?
你不信,可以在手機百度上查,南方密林蛇易出動。我說著,打開手機,飛快地看了一下與朋友的共享實時位置,朋友離我越來越近,他們繞的是小路,不到幾分鐘,他們就會從我右后一條小徑悄悄穿過來。小伙子當然一點兒也沒有察覺到,嘆息了一聲,說,那就算了。
一看到他的表情,我又心軟了,說,要不,這樣,你站到臺階上,我給你拍照。這臺階、密林,還有天上的云彩,也很好看。
他笑了,手指劃開,梳了幾下頭發,舌頭伸出,潤潤嘴唇,雙手垂直,站得端端正正。
我說穿上衣服,光著背不好看。他這才發現自己身上沒穿上衣,害羞地說,南方太熱了,我們老家,現在早晚還蓋被子呢。他穿好衣服,又整了整黑而密的頭發,挺起了胸。我說你不要緊張,放松些。他仍然站得筆直,雙手貼到褲縫邊,咧大了嘴。我按下了手機。他的手機實在太破,屏幕還粘著透明膠帶,也上不了網。一股憐愛之情涌上我心頭。
你的理想是什么?
等我掙到錢,就上大學,上中山大學化學系,本來我都考上了,要是有錢,我現在都大二了。我想了,我要走讀,大學畢業,我還要到北京去,看看我夢想中的北京大學。
你到了北京給我打電話。
他說真的嗎?我說當然,他把電話告訴我,我記了下來,卻沒有回撥。又感覺對不起他似的,說,要不你到密林里我給你照一張?反正朋友他們離我不遠了。
他說算了,我怕蛇。
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蛇,再說一照馬上就出來。我心虛地說。
算了,以后再找時間吧。他一屁股坐到了臺階上,閉上了眼睛。
我回頭一瞧,看到朋友和兩個保安從左后方的小道上穿了過來,他們越來越近,我又是給他們揮手,又是用眼神制止,我希望他們裝作路人,我跟他道個別,與朋友高高興興出去,聊聊天,然后回京。
可事非預想。就在小伙拿著礦泉水正要喝時,兩個保安干凈利落地把他的胳膊扭到了身后。半瓶水,全灑在了地上,瓶子順著臺階一路滾了下去。
朋友戴著墨鏡,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大聲問,他沒把你怎么樣吧?
沒有呀。
小伙一雙眼睛緊張地看著我們,說,你們這是干什么?說著,冷冷地瞧著我。
他什么也沒干,你們放開他。我也急了。
兩個保安也不理我,一人一胳膊架著小伙,往山下小徑走,還不時你踢一腳,他踢一腳。小伙子著急地說,你們為什么打人,我好好的,什么也沒干。真的,什么也沒干。哎,這位——這位姐姐,你說話呀。咱們一路不是談得挺好嘛,你叫這么多人干嗎?
他真的沒干啥事。我越急,越結結巴巴。
干了就晚了!你是怎么進來的?胖保安厲聲問小伙。
當然買票進來的。
票呢?
扔了,都進來了還要票干啥?
胡說,胖保安一巴掌抽到小伙子臉上的傷痕,瞬間血就流了出來。瘦保安看了一下,說,不要打人嘛,讓他慢慢交代。
我急著說,他真的什么也沒干,他人挺好的,我們一直聊天呢。你們要相信我。我說著掏出我的軍官證,急著對兩個保安說。胖保安也不理我,對瘦保安說,閉嘴。瘦保安吐了下舌頭,就再也不說話了。朋友瞪著我,小聲道,你真是個傻子。
胖保安又朝小伙子瘦瘦的屁股踢了一腳,小伙子沒有防備(另一個保安此時正點煙,松開了小伙),一下子倒在地上,眼鏡隨即落地,他沒看到,踩了一腳。我拾起眼鏡給他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要戴眼鏡,才發現一只腿斷了,他就一只手拿著眼鏡,一只手握著斷掉的眼鏡腿,被倆人架著拖到小路上停著的云夢公園的電瓶車上了。
我跟朋友也坐到他對面。我不敢看小伙子那張血臉,只不停地說你們放開他!他真的什么也沒有干。相信我,我以軍人的榮譽向你們擔保。我說著,又掏出軍官證。
兩個保安誰也沒理我,小伙子說大哥,我真的什么也沒有干呀,我真的沒有干,你們要拉我到哪里去呀,我下午還要上班呢。
別說話,胖保安說著,一把扯下他的雙肩包,就要打開。
別動我的包!小伙急了。
胖保安也不理,邊打開包的拉鏈邊說,我敢肯定,你進公園沒買票。
買了!小伙子很堅定地說。當時是一個女孩在賣票,你可以問她,十塊錢一張票。
票呢?
我說過了,我進來后以為沒用就扔了。
滿口謊話,小流氓。
你才是流氓!你搜人包是違法的。
違你媽屁,還法,你懂什么?小流氓。胖保安說著,從包里取出一包東西,一本《化學》書,一包吸了一支的雙貓煙。還有一把系著三把鑰匙的紅柄水果刀。
為什么帶兇器?
你長眼睛沒,那是水果刀。小伙大聲喊著,臉都氣得變紫了。
轉過臉去!胖保安說著,抽了小伙一巴掌,他細白的臉瞬間紅了。另一個保安更緊地抓著小伙子的胳膊,小伙子憤怒地朝車上唾了一口唾沫,背過臉去,瘦瘦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可能哭了。
他真的沒干什么事,你們放開他。你們要相信我。當時只是害怕,我才給朋友打的電話。曉萌,你得替我說話呀。
朋友卻一聲不吭。戴著墨鏡看起來好是陌生。我摔開了她拉著我的手。
胖保安冷笑一聲,說,女士,干了啥就晚了。
我還要說話,朋友又一把拉住我的手,說,準備下車。這時電瓶車停了,已經到了公園后門。瘦保安站在旁邊,又吸了口煙,胖保安罵道,你他媽是不是不想干了,還在公園里吸煙?
瘦保安忙把煙扔到地上,狠狠地把火踩滅,看到胖保安還瞪著他,又把一團散了的煙蒂抓起來,燙著了似的,嘴咧了咧,扔進了垃圾箱。然后很不情愿地抓住小伙的胳膊。
兩個保安把小伙子架進了公園門口的小房里,小伙子再也沒有看我一眼。我要跟進去,朋友把墨鏡往眼睛上推了下,拽著我說,快走!要是讓這些小流氓記住模樣,可就慘了,我還在這城市生活呢。
你也進來,把他如何調戲你的經過寫下。胖保安說著,朝我招手。
什么都沒有,寫什么。給你們添麻煩了,真的,什么都沒有。求求你們,放了他。我錯了。我還要說,朋友把我拉出門拽上車,說,你這人,就是心太軟,男朋友都變心了,還老給我說他如何對你好,那是假的,要是他對你好,怎么跟別人好了。還來緬懷,也不長個記性。那個小流氓,差點就要動手了,還幫著他說情。真是待在部隊把人都待傻了。
他不是小流氓!我,不,是你們警惕過度了。
你看他臉上的傷,一看就是讓人打的。還有身上帶著刀子。要不是我們來,誰知道會發生什么事?
他說是工頭打的。他還考上了大學,是中山大學,學的是化學專業,這個系可是最難考的。因為家里沒錢念書,才出來打工的。他到這個城市來,就是想到校園圓夢。他為什么要選擇中山大學,只因為這個城市一年四季都有花,這是他親口說的。他知道魯迅曾在中山大學教過學,擔任過文學系主任,還知道中山大學化學專業在全國都很牛。你也看到了,他是近視眼,證明學習很用功的,是一個上進的小伙子。他給我講他家鄉的美食,講他的哥哥。他那么愛花,感情那么豐富,怎么可能會對我一個無辜者下毒手呢。還說他媽做的血條特別好吃。還說他媽會灌血腸。他家殺了豬后,把豬的腸子洗干凈,里面灌上用血、面和各種調料做成的料,把口系緊,蒸熟后,切成片,放到碟子里,特別好看,白的皮,紅的肉,比賣的還好吃。你給保安打個電話,他們相信你,把小伙子放了,他打工不容易。我越說越急。
朋友開著車,目視前方,冷笑一聲,說,你呀,就是太單純,愛輕信人。記得大學里咱們玩的殺人游戲吧?你每次無論手里拿的牌是警察還是法官,反正最終的結果都是殺人犯獲勝。別人一句動情的狡辯,你馬上就信了。要是我們來得晚些,現在你怕是哭都來不及。
我不理朋友的武斷,仍不停地解釋,他才多大,他竟然還知道是魯迅把木刻這個繪畫形式引進到中國的。
朋友說,這些東西上網一查遍地都是。他們也要與時俱進嘛。你以為人家一見你,馬上就跑上來,脫你衣服,姐妹,清醒清醒,現在是智能時代了。
我越聽越刺耳,沒好氣地說,我也是農村來的,我也是騙子!你離我遠些。
朋友愣了一下,拍拍我的肩說,對不起。
車外,陽光更毒了,芭蕉葉都曬得有氣無力地耷拉到地面了。
一路上,我跟朋友講了我跟小伙子在山上說的每一句話,說到傷心處,我還落了淚,可是我不明白,我們交往了十年的朋友,卻沒有聽進去我的話。
我讓朋友打電話跟保安說明,他是無辜的。我說你再不打電話,我就下車自己走了。
朋友最后說,好吧,好吧。一會兒下車我就打。神態充滿了不耐煩。
我們可曾是大學四年住一間宿舍的朋友呀,我不知道她為什么那么不相信我。看來世界上最讓人難過的事就是你把對方當朋友,可她卻不信任你。不,她可能還一直在骨子里輕視你。
原計劃我要跟她一起吃晚飯,在此之前,我有許多話要對她說。我是晚上九點的飛機,可我須臾間沒了情緒,借口有急事要返回,謝謝她大中午的來救我。
女友把我送到賓館門口,幫我整了整散亂的頭發,再一次叮囑我,以后不要輕信于人。
我一個人百無聊賴地躺在沙發上,望著窗外這個潮濕而悶熱的城市,懷想公園前門那個我沒有到達的飛瀑流影,想背出男友背給我的那些讓我終生迷醉的詩句。上山前還記得的詩句,此時一個詞都想不起來了。
后來我給云夢公園打電話,公園的負責人說他會過問此事。至于結果如何,再也沒有了消息。我打小伙留給我的電話,電話起初傳出的是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最后就是:沒有這個號碼,請你查對后再撥。我知道,我冤枉了他,他恨我。我很想對他說聲對不起,卻不知他在哪里他叫啥,只知道他的家在陜西長武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