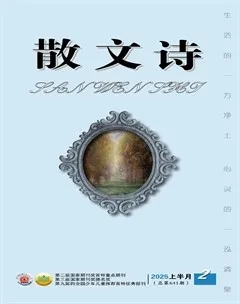太白山組章
文公石碑
五月,平原炙熱的季節,在石頭壘起的文公廟前,一株草或者一只鳥,都在觀望一座石碑。
石碑朝南,云海的末端能夠隱約看到石碑身上,被山風扯斷的紅綾,北岸無風。
重量是冰川紀之鳥在空中綻放,那些億萬年前摩擦生熱的火種,在南北之際燃燒。
一座孤立的房屋,通天大火熊熊燃燒著,彼時星辰璀璨的東方,孕育著何種日升。
當午夜的星辰停止轉動,一抹在紫色霧瘴中搏殺而出的光輝,才從無數翻轉灰塵的初生中,將光影置于文公石碑的側面。
石碑初日升。
大爺海
一座通往海的扶梯下,是萬丈冰川,連接寒武紀散落在海岸的碎石。碎石有光,一整個夏季的夜晚,螢火蟲劃過星空,海岸線之上會燃起綠色和藍色的螢火。
此時,站在冰雪覆蓋的扶梯上,緩緩向上攀登,氧氣與寒風一樣,都是清醒者的武器。
大爺海,一片藏在海拔三千六百米之上的海域,能向太平洋祈求些什么?
無非是冰封之際,那些穿越洲際的暖流,和大雪之際,一片藍色的冰封之眼。
雨雪之路
危巖,踩著青色石塊的骨架上山,看一株被霧氣打濕的草,在縫隙中攀爬。
古道,還是那個可以橫絕峨眉巔的古道;不過又多了一群穿五彩雨衣前行的背包客,行走。踩著淅淅瀝瀝的雨水,連古道中石板的表面也泛起青黃,漸漸霧氣升騰。
烏云覆滅的速度,遠快于背包客行走的速度,于是我們看到:在路的左側,在你的身旁,云雨飄過只是一瞬,在那些觸手可及的天空中,破裂又重組。
返程之路,風刮得更緊了,雨雪夾雜著冰雹的烏云向你襲來,側身聽風的同時,被風緊緊地抓住,在山腰的鐵亭。
拔仙臺
陸地之上,昆侖之下,是秦嶺蜿蜒曲折的脊背,細數那些突出如馬鞍的骨頭,讓無數棧道流淚。
冰雪是你一年四季的常客,像一種回望,回望冰川古老年輪所昭示的飲冰者。那是億萬年的燃燒與血液,是脊梁的抬升與忍痛割裂,是東方大地一次沉默嬗變。
你抬頭,看見自己的攀登者在一片深藍的海域停留,片刻之后,向你的肩脊發起沖鋒。
拔仙臺,一個將神話故事刻在自己背面的石峰,總有一群朝圣者要登頂,在頂上朝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