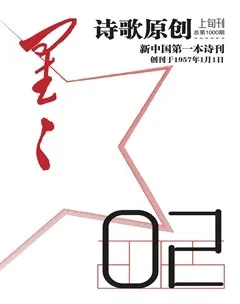海濱行(組詩)
黑衣客
群樹婆娑,懸崖變得溫柔,
死,已如此溫柔,
萬千之星,我愁苦的喬木夠不到你,
關節里的痛像漏下的沙。
那年,一樹繁花被黑暗收走,
但每當你回眸,
它們總會在你的笑容里重現。
而落葉是被驅散的日子,踩著它們,
像驚動了歲月前頭的響動。
石階的盡頭,比喻結束,
在那里,無數事物已死于被愛,
接骨木枯干在藤蔓中,
烏桕、側柏,則避開了近在咫尺的危險,
它們,從預感里向上長,最后,
長成了高大預言的樣子。
“不,我沒有死,
愛是纏繞,也是個不斷膨脹的漩渦,
在它內部,我是灼炭般
收緊了疼痛的黑衣客。”
平 原
路徑消隱,
河灘上盡是亂蓬蓬的影子,
多么無辜呀,記憶的枯樹和熾烈的麥苗,
一個冬天,
重新從大地里提取出了火。
群鳥掠過頭頂,
它們的心,因耽于低飛而無法冷卻。
庭院里,有人在給舊桌椅釘釘子,要把
積攢無數苦難才能得到的一小點鐵,
釘到老家具體內去。
海濱行
有人垂釣,有人發呆,
有人在古槐下問道,波濤在他心中遠去。
有人則在山上蓋房子,
要把大海接引到
掠過窗口的一陣微風里。
我們拾級而上,看見石欄邊的一只流浪貓。
小西蹲下來向它說:對不起。仿佛
她沒帶食物給它是有罪的。
復又下山驅車前行,王華問:
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呢?
她不知道,大海正攜帶著蒼茫
穿過她的問題。
突然聽到有人喊:看,夕陽!
我們抬頭。那是即將落回人間的夕陽,
在山頂上散發著柔和的光。
我們的車子向它奔去,仿佛
要不顧一切闖入它的世界。
其實,再過一會兒天就會黑下來,夕陽
將落到山的那一邊,
——那是
我們從未到過的另一邊。而我們的奔赴,
仍將停在這一側,停在漸漸
被暮色統治的大海邊。
廢棄的巷道
黑暗中的挖掘如同虛構。
黑暗中的挖掘變成了不斷地
挖掘黑暗。
一邊挖,一邊用木頭
把挖出的空間支撐起來。
支撐亦如虛構。但我們
已從語言之外來到了它的內部,
并熟練地掌握了對空洞的敘述。
幾點礦燈閃爍,
如同幻視,如同
只能用來自救的碎詞。
而永不停歇的轟鳴
從盡頭傳來。最后,
是對岑寂的處理:當木頭被抽走,
整個大地帶著它的重量
緩緩壓下來如同
一個腸胃空空的老社會在一次性
解除它的饑餓。
臺風過后的雨
已是無害的雨,
落在安然無恙的屋頂上,
落在折斷的大樹上。若它
小溪一樣從瓦壟里滑下,
你將得到懷念;
若它斜著滑過高鐵的窗玻璃,
你將離開那懷念。
雨落著,像這天地間仍有
某種不明的需要
要給那些剩下的人,令我想起
昨夜的我在被擊打中
恐懼,孤獨,就要解體了,卻又
那么興奮,像在
大自然的瘋人院里獲取了
咔嚓一聲把自己折斷的勇氣。
最后的島
我羨慕那些住在島上的人,
他們因為周圍都是茫茫海水
而像擁有了整個大海。而且,
因為他們住在島上,
比那些只擁有大海的人,
擁有的似乎更多了一點。
有次在一個島上散步,
想象著那些想像我這樣生活的人
多么辛苦,正乘著船從遠方趕來。
還有一次,海上風暴大作,
朋友們擔心會被困在島上。
而我卻心里輕松,因為我知道,
想長久地待在島上,
這想法本身就是一場風暴。
有些島上沒有人,
那些游玩的人到了島上轉一轉
就回去了,讓那些島繼續
獨自呆在海上。
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乘著船,
越過最后的島向大洋駛去。
我羨慕他們,想象自己也站在
他們中間,并一起回頭,
望著海島和島上的我,越來越小,
直至從他們的視線里消失。
海 灘
我看見海浪印上沙灘,
它卷著,仿佛在從自身里抓取什么,
然后,撲倒在沙灘上。
想起小時候去集市,有一次,
看見一個好看的女孩子。
我想過去和她靠近一點,
但母親拽著我,消失在人海中。
所以不如沉默,當我們坐在這大海邊。
現在,如果我說我愛你,
我也會在瞬間碎去。
我們聽著濤聲,一聲又一聲,
既然它能撫慰心靈,它就不是愛。而我,
只能像這卷起的海浪,
用一個虛構的自我,才能再次
把我和你聯系在一起。
車 站
來,從我手里取走你的疲倦,
來,取走你的軀體這超重的行李。
來吧,鋼軌上的巨獸,
你面無表情,但呼吸灼熱,
你進站又離開,只偶爾送來窺探的一瞥。
一瞥,就夠了:所有車站,
都還不曾學會祝福的方式。
要忍住長久的焦灼之后,
背影們才能學會排隊。
當那隊裂開,如同一塊
沒結構好的固體的分崩離析。此為
不同時刻提供的人間;目的地
提供了不同目的的人間。
但列車時刻表像早已忘了人間,
它把自己固定在
一個個不確定的臨界點上。
而車輪,要小到一只拉桿箱的輪子
那么小時,才能用來承載生活,
一邊滾動,一邊用吱嘎
不停的噪音拖走了,
散落在大廳和鐵軌上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