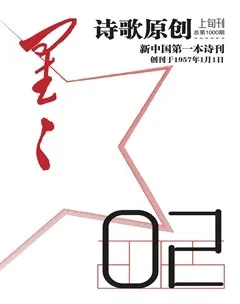活在語言里(組詩)
2025-03-04 00:00:00袁永蘋
星星·詩歌原創 2025年2期
心 鳥
她們在爭吵后急切地表達愛,
血液上涌,她們都哭了,
嘶吼,但這之后她們中的一個
率先冷靜下來
她們都不能沒有對方,
她們從表達憎恨轉為表達愛。
窗外秋季已經完全消失,
冬季的雪在最柔軟的地方
變為一條白色棉毯,
但在最堅硬的地方結冰——她們累了,
該時候表達她們的愛了……
不應該鋪開傷害的毯子。
畢竟她們真的愛著彼此,
即使她們生氣說:“我要離開家!”
但她們并不會真的走,這是
她們的窩,除此之外再沒有
別的了。而我想問:
你是否細心觀察過那些?
我說的是鳥巢,在房檐上的那些
用泥土和干草做成的鳥窩?
它們的顆粒質地就像淤泥的淚滴,
哦,我不應當提起這個……
在暴風雨到來之前,它們低旋
徘徊但總是朝著一個方向……
現在的問題是,當她們爭吵的時候
她們內部有一個膨脹的氣球,
隨時可能爆炸,誰又會注意到雷霆?
還有閃電中,它們的心鳥,
那作為醫生的痛苦收集?
午間風景
我端坐在一把陽傘下面,
就像愛德華·霍珀的畫中人一樣。
我捋你的頭發,它們柔滑如
你愛吃的巧克力,
我撫摸著那些頭發,就像
我從未撫摸過任何頭發。
我把眼前的事物分解,
如立體派繪畫……
魚
的確,知識永遠學不完。
如果學完了,人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她站在岸邊看冰封的江面上垂釣者在垂釣,
他們在江心端坐,用粗糙的老手鉗住魚鉤,
像母親在燈下引線,不能抖動,
要“定住”自己:
眼睛先于針尖鉆入針孔。
“鰲花 鳊花 鯽花……”他不斷向我闡明
這些魚巨大的區別,
而我看來都一樣啊!
銀白色的冰之光在他的手指尖跳躍,
他說著“魚魚魚”,
我聽到的是“詩詩詩”。
奧維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濱
托米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