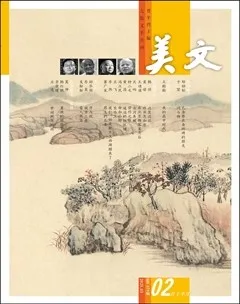遙遠的鐵匠鋪
一把鐵鉗在我家放了三十年,銹跡斑斑,每當拿起它,我就能聽到“篤篤,篤篤,篤篤”的打鐵聲傳來。
離開故鄉已經好多年了,尤其是在微熹的黎明,斜陽如血的黃昏,鐵匠鋪浸在一片玫瑰色水彩中,那幅油畫至今都嵌在我的腦海里無法忘懷。小城的北二道巷有個王家大院,它與我家是鄰居。王家大院有個鐵匠鋪特別出名,在巷道上就能看到它。那是一間破破爛爛的正房,房子里擺滿了各種各樣打制的農具,極像一個散亂的農具博物館。屋外有一個鐵匠爐,被炭火燒得通紅,一只破風箱被徒弟拉得呼呼直響,高高的火苗舔著鐵塊,直到把鐵塊通體燒成紅色。鐵鉗是鐵匠鋪重要的工具,它不但要抓熱鐵,還要調整鐵塊位置和角度。王師傅用鐵鉗把燒紅的鐵放到鐵砧上時,十斤重的鐵錘就砸在了紅鐵上,此時的鐵就像一塊紅泥,由鐵鉗夾著在鐵砧上移動,用錘打完后,鐵塊又被鐵鉗送進炭火中。風箱拉得混響,藍色的火苗一次一次升騰,燒紅的時候就用錘打它 。一塊鐵把它打制成農具,全靠一把好鐵鉗來把方向。錘打它是為了把它重塑,一塊亳無生氣的廢鐵,被鐵匠多次鍛打成形,鐵匠心里自有圖案,那是犁、是鋤、是刀、是劍、是希望、是成就。徒弟只顧鍛打,王師傅成為方向的把握者。我突然想起羅丹是從大理石中解救出天使,鐵匠是借助鐵鉗把廢鐵鍛打成了藝術。
鐵匠鋪的掌柜王鐵匠,是古鎮方圓幾十里有名的鐵匠。他是一個大個子,有一米八高,濃眉大眼,瘦臉帶點黑、高高的顴骨,走起路來有點駝背,這與他常年站著打鐵有很大關系。他是十分幽默的人,他打鐵的時候駝著背,腰上拴著一個藍圍裙,只要他站在那里,圍觀的人就特別多,許多人是來看他打鐵的,也有人是看紅火來的。王鐵匠有個習慣,從看打鐵的年輕人中挑選徒弟,就在這輕松的氣氛中,他還真找到了一些愛學鐵匠的徒弟。他挑的徒弟都很機靈,身體一般都比較好,無論是拉風箱,還是掄鐵錘,都是呱呱叫的人。可是這些徒弟沒有一個是大個子,一個高個子和一個低個子站在一起打鐵,還真有點不搭套。他最不滿意的是徒弟的個子,常常譏笑他們,他說自己命里就沒有大個子徒弟,為什么跟他學藝的人都是小個子,他直到死都沒弄明白這個問題。當然他也挑選上幾個大個子徒弟,可是,不是徒弟不想學鐵匠,就是家里人不同意。他就這樣不搭調地打了一輩子鐵,一高一低成為他們絕版的師徒組合。他還是一個愛講古朝的人。一般情況講古朝,他總是在黃昏以后,一邊紅爐炭火,一邊打鐵,一邊講著笑話,一邊嘮著古朝。黃昏落進院里,鐵匠爐冉冉升起,“篤篤,篤篤,篤篤”的打鐵聲,從巷尾傳來灌滿了整個童年。凡是經他鍛打過的鐵器,切菜刀、刀子、鏟子、耙子、大鋤、小鋤、犁、剪刀等,不但好用,還特別鋒利,他的鐵器是謎一樣的存在。
王鐵匠打制的鐵器十分暢銷,每天都有來鐵匠鋪買鐵器的人,尤其遇到趕集,鐵匠鋪常常圍著一群人,那是北二道巷特別紅火熱鬧的地方。讓我印象最深的是罩在夜色里的鐵匠鋪,那時候巷子里沒有路燈,少年的我與伙伴們玩耍完,老遠就能看到鐵匠鋪閃閃的火花,射向深黑的巷子,那絲光亮是多么醒目,它驅散了黑暗,讓我不再恐懼、害怕,那躍動在夜色里的火花,是少年的希望之光。每次晚上回家,看到燦爛的火光,聽到打鐵的“篤篤,篤篤”之聲,我就感到特別溫暖。我們幾個小伙伴總是纏著王鐵匠嘮古朝,經不住我們的糾纏,徒弟的勸說,“半升麻子倒婆姨,張丑子鋸木鋸子把老師掉在死窟窿,說岳全傳,隋唐演義,楊家將,西游記,水滸傳……”開講了。直講得天昏地黑,眉飛色舞,唾沫飛濺,哪管它夜深月出,驚動夜里飛動的鳥雀。一個鐵匠鋪變成了一個動人的夜故事場,不知不覺就坐了好多人,講得我少年心性開始狂野,我知道大山那邊,古鎮的外面真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它遙遠、迷人、陌生,是我所不知道的。并不是每天晚上都能聽到鐵匠的古朝,我們總是要等上好長時間,才能聽到他講的故事。王鐵匠雖然打得好鐵,但他也是個十分會過日子的人,他總是集中幾天打下許多鐵器,就得休息幾天,看看書,睡個懶覺,每天早晨還要喝半斤牛奶,過得也十分逍遙。為這個習慣,鄰居們常在背后風言風語。據說他讀過不少書,后因家道敗落,為了生計,不得不學了個鐵匠,他學什么都十分了得。今天我才真正懂得王鐵匠是深得做人的精髓,不為生活所累,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做不到的,于是在人們眼中他又成了另類。
當鳥鳴敲破曙色的黎明,“篤篤,篤篤,篤篤”的打鐵聲傳來,像一聲聲起床的小號。在兩個院落里,這聲音此起彼伏,極像一曲美妙的音樂,穿墻而過,它常常伴我入眠,督促著我在晨風中醒來。由于起床早,我要先在鐵匠鋪看一會打鐵,然后才去上學。徒弟將風箱拉得呼呼作響,鐵匠爐里串起藍色的火焰,熱烈的火苗舔著那塊廢鐵,鐵被燒透了,紅紅的臉膛,一把鐵鉗夾住鐵塊放在鐵砧上,王鐵匠自然是掌鋪的人,那個徒弟忙得不可開交。一會兒拉風箱,一會兒掄起鐵錘打鐵。篤篤,篤篤,篤篤,火花四濺,鐵匠鋪的四周都是鐵的碎屑。我仔細數了一下,一個鐵器從廢鐵到成品,要在火中回爐三次,每一次鐵錘都要敲打幾十次,一件成品得打二三百次,直到師傅說停才能停下來,否則徒弟再累也得掄起那大錘。廢鐵變成鐵器,有火紅的溫度,鐵鉗夾住放入水槽,槽里的水滋滋直響,不斷冒煙,不斷沸騰,那是生命的一次淬煉。把熱鐵塊放入水中,這就是鐵匠的淬火,淬火時,鐵器已經鍛打成型,淬火后鋼鐵就有了硬度,浴火重生,鳳凰涅槃。這是生命之錘,還是生活之錘,這掄錘子之人,在熊熊的火光中,汗水不停地在黝黑的胸膛滑落,你能看到那雙胳膊肌肉的力量之美,青筋暴突,凹凸有致,展示出生命特有的光輝。做一個夾鐵之人,他是鐵匠鋪里能掌握命運的人,但夾鐵的師傅也是從掄大錘開始的,他最初也是徒弟,徒弟變成師傅需要生活的磨礪,沒有一個人從一開始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打鐵還需自身硬。一件鐵器打成了,王鐵匠催促著我快去上學,那是一條通往學堂的路,也是一條未來的路。
王鐵匠的打鐵手藝得到了許多群眾的認可,經他打制的農具不但有硬度,而且還非常好用,他是古鎮周邊最有名氣的鐵匠。我爺爺曾給我說:“王家幾代都是大戶,到了他父親這代家道敗落,他父親學了鐵匠,把手藝傳給了他。他家打鐵有絕活,在一定的火候上,要在刀刃上加上鋼水淬煉,經幾次冷卻打磨,才能出成品,每一件成品把關都十分嚴格。”王鐵匠不愁沒有徒弟,要跟他打鐵的年輕人很多,他的徒弟換得很快,不是徒弟不跟他,而是最關鍵的絕技他不傳,這讓徒弟們很是絕望,跟上一個階段學不到真傳,就離開了。從始至終他是想把這絕技傳給兒子,可是偏偏兒子就是不學鐵匠的手藝,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把絕技傳給了最后一個徒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鐵匠手藝是技術活,是一份殷實的職業,王鐵匠自然是過得日子比較好的這類人。他有一個特別好的習慣,每年他都抽一段時間到農村去,一邊收廢鐵一邊打鐵,住在農家吃在農家,并經常征求農戶對農具使用過程中的意見,這使得他不斷地著手進行改進,深得農民的歡迎。吃百家飯,拉百家話,是手藝人的生活特征。我清楚地記著,他家養著一頭毛驢,就是為了跑農村,我經常騎那毛驢,它特別溫順,從不踢我。每當他從農村回來,一進大門就高聲大叫,我回來了。那陣勢真的是特別威風,整個車子上裝滿了許多東西,凡農村有的東西車里都有,有瓜果、玉米、大豆、豌豆、紅薯,還有各種蔬菜,那真是一個聚寶盆。我總能在車子里找到好吃的東西,他看著我們拿走東西,笑哈哈的顯得特別高興,徒弟在收拾東西的時候,他常常手背在后面,哼著小調向家走去。
少年的我經常混跡于鐵匠鋪,看打鐵成為我童年里最有趣的事。為了看打鐵,其實更多的是為了聽王鐵匠講故事。那些陌生、新奇的人和事,曾給少年的我帶來了激動、幻想和希望。因為經常在鐵匠鋪,所以幫忙是少不了的,主要是徒弟不在的時候,給拉風箱,一箱一箱的風源源不斷地吹向紅紅的鐵塊,那淡藍色的火苗就是勇敢的火舌,讓堅硬的鐵變成一個原初的材料,經回爐、重塑、打制,成為一個新的物件。鐵匠在廢鐵中雕成了一個新農具,變成了豐饒大地的一個得力幫手,這是多么有意義的一件事。時光將王鐵匠打磨成了一個巧匠。看得多了,我也成為王鐵匠的一個編外徒弟,我曾試著舉起十多斤的鐵錘打鐵,卻堅持不了幾分鐘,最讓我受不了的是,經受不了火焰的炙烤,真實的體驗讓我懂得,打鐵是特別辛苦的一件事,只有好好學習,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實我離當鐵匠僅一步之遙,父親看到我特別喜歡打鐵,學習不怎么上進,而且還因此遲到過幾次,就對王鐵匠說:“讀書也成不了氣候,把他帶上打鐵吧。”王鐵匠并沒有答應帶我,后來他送給我一把鐵鉗。也許我并不是他中意的徒弟,入不了他的法眼,也許他更期待我能好好讀書,不要走一板一眼能看到底的人生。其實內心我是喜歡打鐵的,但我更喜歡他講的古朝和那個陌生的世界。我十分害怕父親讓我當鐵匠,那意味著一生將與鐵為伴,好長一段時間我再沒有去鐵匠鋪,專心于學習,從此父親再沒有提起這事。我雖然沒有成為王鐵匠的徒弟,沒有當成一名鐵匠,但那把鐵鉗我一直藏著,每次搬家我都把它帶上,舍不得丟棄它,它已成為我的一個時代。
我是一個熱愛大自然的人,少年時的我特別癡迷于故鄉的山水,由于貪玩經常受老師批評,小學時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太好。每天癡迷于鐵匠鋪,險些被父親送去當了鐵匠。如果當時真的跟了王鐵匠,我會成為一個有名的鐵匠嗎,不管有名與否,一生將依靠手藝吃飯,只不過手藝的好壞,將會決定生活的好壞。我會為自己親手打制的農具而高興和自豪,也會產生一種榮譽感,那將是另一種人生。其實不管哪一種人生,勞動是最光榮的,也是最美麗的。在鐵匠鋪打鐵時,我總是看見王鐵匠的一條胳膊不對勁,時間長了我也沒好意思問他。終于父親有一次給我說了實情。文化大革命時期,王鐵匠因為單干自己沒進鐵業社,又經常出入農村售賣農具掙錢,而給了人口實,紅衛兵把他作為黑五類分子批斗過,并把他的一條胳膊致殘了,他整整被關進黑房子折磨了半年。令人特別傷心的是,就在他被禁閉期間,他母親生病去世了,但他們并沒有放他出來處理母親的后事,是親戚朋友幫他盡孝的。那個生命中至暗的時刻,他連處理母親后事的權利也沒有,身體的傷殘和屈辱,讓他想到了自殺,但他最終還是挺了過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讓一個底層的手工藝者王鐵匠,徹底獲得了新生。他又可以去農村了,那是一個廣闊的天地,他打制的鐵器受到了村民的追捧,連著兩三個月他都回不了家,他終于從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一個人的價值。不管你一生做什么,你一定要感受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所在,這才是最重要的。
“ 篤篤,篤篤,篤篤”的打鐵聲,像一串音符長久地飄蕩在故鄉的夜空。那火光中有我少年的希望和憧憬,有我夢想中的詩和遠方。而今小城里已經見不到鐵匠鋪了,縣城里也沒有了,沒有火光,沒有煙霧,沒有藍色的火苗,音樂的敲打,還有那風箱,時光是多么寂寥。尤其是我看到兒子的童年,是沒有火光的,我特別的沮喪。我為兒子惋惜,也為這代人惋惜。那片光是可以給人指引方向的。打鐵需要自身硬。打鐵需要淬火,打鐵的每個過程,都能給人生以成長啟示。王鐵匠去世的那年,我曾回過一次老家,鐵匠鋪依然破破爛爛地立在那里,那一間瓦房的頂部已經塌陷,地上還能看到一層碎鐵屑的痕跡,那是一頁時光書,讓我們來不及翻看,就消失了。最近我又回了趟老家,鐵匠鋪徹底地消失了,那塊地方被新修的幾間蓋板房覆蓋,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路徑了。只聽到風箱呼啦啦地響,那閃閃的火光照亮了夜的眼睛。鐵匠走了,他沒有帶走鐵匠鋪,也沒有帶走一件鐵器,甚至他那間放鐵器的房子也倒塌了,用他農具的人也一個個走了,我的內心充滿了一種悲哀。故鄉給了他名聲,給了他房產,最后都一一地收回了。再也看不到鐵匠鋪了,手工打制的農具也消失了,我看到的全是精美的不銹鋼器件,從一個車間,一個模子生產出來,沒有汗水,也沒有情感的滲透。只要有時間,我就拿起王鐵匠送給我的那把鐵鉗,仔細地端詳,這把鉗子不只能鍛打鐵,也能鍛打生活,經過鍛打的日子,才有火光,才能找到生命的希望。這樣的時刻,我就常常想起故鄉鐵匠鋪里的火光,它一直照耀著我靈魂里跋涉的路途。
篤篤,篤篤,篤篤的打鐵聲,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