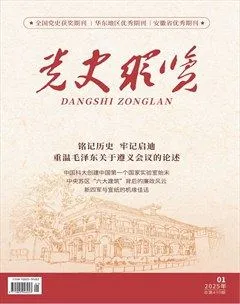從皖江到淮河:紅色文化在安徽的傳承路徑
具有地域特色的安徽紅色文化,是中國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安徽呈現的文化形態。如果將紅色文化置于安徽的歷史地理,皖江、淮河則是無可置疑的載體和符號。那么,安徽紅色文化起自何處,又向何處延伸,最終歸于何處?這些,顯然是重要而有意思的話題。學術界對紅色文化與長江、淮河的關聯以及在地理上的延展路線并未論及。本文擬在對馬克思主義在安徽由思想理論到革命實踐的發展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對紅色文化的傳承路徑試作闡釋,以彌補相關研究的不足,并以此推動省域內紅色文化傳承與發展問題的討論。
萌發于皖江之畔
紅色文化是指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先進文化。此處取其狹義,特指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以紅色基因為精神內核的文化形態。“它的上限,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的那一歷史時刻”,為了究其根源,還要回溯至1910年代前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和活動,其下限至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在1910年代末的中國社會落地生根,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盛行于各地的新文化運動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思想文化背景,得風氣之先的大城市以及沿江沿海的口岸城市則是這種外來新生事物最早的登陸點。馬克思主義在安徽傳播的兩個重要的地理坐標就是長江之畔的安慶和蕪湖,從文化源頭而言,是源自安慶,盛于蕪湖,蕪湖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而成為新思想的主流,從而成為安徽紅色文化的源頭的。
安慶作為安徽的省城,必然是新文化新思潮的中心。但是,當時的省城又是舊勢力舊體制最為頑固、對動搖當局統治的革命思潮最為排斥的地方。因此,清末民初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在安慶表現出極為慘烈的形態,如1907年光復會會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失敗后被殘忍處置。然而,歷史的邏輯往往是新舊斗爭在所難免,新舊更替則是歷史大勢,而思想文化領域的更新更是成為社會革命的先導。在徐錫麟被害的同一年,后來在蕪湖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高語罕就來到安慶從事秘密反清活動。他“與朱蘊山、易白沙佐助革命黨人韓衍創辦《安徽通俗公報》《安徽船》《青年軍報》《血報》等激進報紙……這些報刊連同1904年陳獨秀等人創辦的《安徽俗話報》一起成為安徽乃至全國新文化運動的先聲”。
因安慶是舊勢力猖獗之地,安徽文化革新的主場便轉到蕪湖。這一轉場以陳獨秀和他的同鄉房秩五、吳守一等人在安慶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蕪湖的發行為開端。近代的蕪湖作為皖江之畔開埠最早的城市,不僅是省內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在西風東漸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相對開放寬松的社會文化氛圍,成為近代安徽反帝反封建和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在當時的蕪湖,宣揚新思想新文化直至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有以科學圖書社為“據點”的陳獨秀、汪孟鄒等人,后有以安徽省立第五中學為活動中心的高語罕、劉希平等人。這些知識精英“大都與清末民國間的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學者、革命者和教育者集于一身,正是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的共性”。
位于蕪湖“中長街二十號”的科學圖書社是績溪人汪孟鄒于1903年開辦的新式書店。蕪湖及科學圖書社在社會革命和傳播新文化中的作用,正如1922年高語罕所指出的那樣:“安徽近二十年,所謂種族革命、政治戰爭、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蕪湖實居重要地位,而長街之中,方丈危樓、門前冷落之科學圖書社,實與之有密切關系!”陳獨秀來蕪湖的直接動因就是投奔他的摯友汪孟鄒,而科學圖書社則成為其在蕪湖的落腳點。
陳獨秀在蕪湖的活動只有短短的3年,但是他主辦《安徽俗話報》、創建“岳王會”以及在安徽公學和皖江中學任教等活動,為馬克思主義在蕪湖的傳播進行了必不可少的鋪墊。而接續這一使命的則是在省立五中任教的劉希平、高語罕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據朱蘊山回憶,陳獨秀離開蕪湖后,“在某種意義上說,劉希平實際上是陳獨秀在安徽的代表”,“安徽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從蕪湖第五中學開始的”。曾在五中就讀的石原皋也指出:“新文化的種子是在五中撒播的,民族民主思想是在五中發芽生根的。而這些,是與劉希平、高語罕兩位老師分不開的。”
1916年,同盟會早期會員劉希平受聘于省立五中(1920年被推舉為校長)后,向學校推薦了其同鄉兼好友高語罕到該校任教并兼任學監。高語罕與陳獨秀是至交,也是陳獨秀的追隨者,此前就在上海參加新文化運動,“是早期《新青年》雜志的主要作者和宣傳者”。學校聚集了一批具有新知識、接受新思想的青年人,其中包括蔣光慈、錢杏邨(阿英)、李克農、尹寬等許多優秀的青年學生。劉希平和高語罕引導學生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書刊,依托學校成立了無政府主義團體“安社”,編輯出版《自由之花》。在他們二人的大力倡導下,青年學生積極以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專科學校(簡稱“二農”)、省立五中為依托,在科學圖書社的助力之下,掀起新文化運動的熱潮。五四運動的消息傳來,高語罕立刻組織蔣光慈(時被推舉為蕪湖學生聯合會副會長)等學生骨干到其他學校進行聯絡。他本人和劉希平則親自聯絡蕪湖的教員。
五四運動后,經高語罕、劉希平等人的引導,蕪湖便成為馬克思主義在安徽傳播的大本營。1921年初,汪孟鄒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高語罕授課講義《白話書信》,“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是安徽最早最系統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課本,后竟出至39版,在安徽以致全國都有較大影響”。安慶也同時興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熱潮。當時“傳入安慶、蕪湖等地的書刊有《新青年》《湘江評論》《每周評論》《赤都心史》和《星期評論》《創造周刊》等不下數十種之多”。必須指出,安慶是陳獨秀的故鄉,而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這昭示了安徽紅色文化基因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民主義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陳獨秀早年在安慶和蕪湖的民主革命活動以及后來在思想文化界和建黨上的巨大影響,促使紅色文化基因在安徽迅速蔓延。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共中央加大了對各地黨團活動的組織和指導。馬克思主義也因此在安徽得到進一步傳播,“到1923年,安慶、蕪湖、合肥等地都先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氏研究會’和‘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編輯出版了一大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刊、書籍。工會、黨團組織也隨之在安慶、蕪湖等地陸續建立。至此,馬克思主義在風云際會的時代浪潮中,以一種近乎“純文化”的形態在皖江之畔播撒紅色文化的種子。革命知識分子還深入工廠、學校,組織推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積累革命斗爭的經驗,為紅色文化的生長積聚能量。
植根于淮河流域
從表面上看,早期馬克思主義在安徽的傳播主要是在以安慶、蕪湖為中心的皖江沿線展開的,與淮河流域似無關聯。事實并非如此。劉希平、高語罕這兩位安徽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均來自淮河流域。劉希平是六安人,高語罕是壽縣人。一大批來自淮河流域的年輕人南下蕪湖求學,或受教于他們門下,或受他們影響,如生長于皖西革命中心地帶金寨縣白塔畈鎮(時屬霍邱縣)的蔣光慈,曾先后在蕪湖工讀學校、蕪湖公立職工學校就讀并擔任學生會主席和馬克思主義讀書會負責人,來自壽縣的曹淵以及下文提及的曾在蕪湖接受革命教育、后回大別山從事革命運動的眾多革命者。這批來自淮河流域的知識青年和家鄉故土聯系密切,帶動當地的思想革新和革命運動,成為紅色基因從皖江到淮河的傳承紐帶。
體現長江、淮河紅色基因傳承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壽縣。五四運動爆發后,壽縣“在蕪湖二農學校和工讀學校讀書的學生胡萍舟、孟靖、陶淮、陶久仿等同志都參加了集會,示威游行,散發傳單,積極投入了反帝反封建運動,并與家鄉的教育界、知識界聯系,給他們寄宣傳材料”。反帝反封建的進步思想開始由蕪湖傳入壽縣。此后,這種“反哺”式的“輸送”持續進行,“從1919年到1923年之間,壽縣在蕪湖讀書的薛卓漢、曹淵、王培吾、徐夢秋、曹廣化、方運熾等十余名學生……同家鄉的進步青年知識分子聯系,寄回馬列主義的書籍《唯物史觀》《社會進化史》和革命刊物《新青年》《向導》等給他們閱讀。薛卓漢、曹淵、曹廣化等人還利用寒暑假返回家鄉,以串親、訪友的形式,宣傳馬列主義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他們在蕪湖中學畢業后,有的回到家鄉,分在學校里以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另一部分學生,如薛卓漢、曹蘊真、方運熾、徐夢秋等人轉入我黨領導的上海大學讀書……這些學生從多方面影響了家鄉的進步青年,致使壽縣的革命氣息愈顯濃厚”。在此基礎上,“1923年秋,共產黨員薛卓漢、曹蘊真、方運熾等根據黨的指示,接受了在壽縣發展黨組織的任務,從上海返回壽縣家鄉……首先發展了瓦埠小學校長方運初入黨,接著又發展了小甸集小學校長曹練白和教師陳允常等人入黨。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多、革命隊伍的壯大,在壽縣地區建立黨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這時根據黨中央的指示,1923年12月于壽縣小甸集召開黨員會議,成立了壽縣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壽縣小甸集特別支部”。
類似情形也出現在霍邱縣,“1926年,在上海東吳大學就讀的共產黨員樊逸仙,受黨組織委托回鄉建黨,在霍邱縣成立了第一個黨組織:中共烏龍廟特別支部,并組織了烏龍農協小組,吸納進步青年加入黨組織。1927年10月,烏龍廟特別支部改為中共霍邱特支,這為日后的白塔畈暴動集聚了力量”。正是這些來自淮河流域、在長江沿岸接受革命熏陶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篳路藍縷,才使馬克思主義從長江之濱的革命理論轉變為大別山間、淮河南岸的革命狂飆。
長江之濱和淮河流域的紅色基因聯結從詹谷堂和他學生的革命經歷中也可窺一斑。詹谷堂是豫東南黨組織創建者,是立夏節起義(又稱“商南起義”)的領導者之一,早年在家鄉金寨開私塾教書,1918—1924年應聘到河南省固始縣志誠小學任教,在該校組織讀書會,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一批受教于詹谷堂的孩童之后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蔣光慈、袁漢銘、王明等。蔣光慈11歲時“到故鄉五十里外的志誠小學讀書,當時具有進步思想的國文教員詹谷堂對蔣光慈影響甚大。蔣光慈參加了詹谷堂組織的讀書會,閱讀了大量進步書刊”。年幼的蔣光慈是“受詹谷堂教育、啟蒙、開始成長的”。學界雖然對蔣光慈介紹詹谷堂入黨以及蔣回鄉建黨等史事有所爭論,但蔣光慈此后在蕪湖、上海,后來去蘇聯的革命經歷以及在革命文學創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未嘗不是與包括他老師在內的革命者在皖西革命活動的一種呼應。
在志誠小學接受詹谷堂思想啟蒙的另一位學生袁漢銘,1920年考入董必武、陳潭秋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在那里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1921年秋天,袁漢銘“曾帶領詹谷堂同志去武漢與董必武同志會晤。之后,詹谷堂多次去武漢向董必武同志領取文件、材料,接受革命任務”。后來袁漢銘被黨組織派回家鄉建黨和從事革命工作,與他的老師詹谷堂并肩戰斗,1924年在筆架山農校創立了皖西地區第一個黨組織。正是這批革命師生共同領導了1929年著名的立夏節起義,開創了皖西革命的新局面。
皖江與淮河在紅色文化生長過程中所體現的這種路徑上的關聯,還可以從皖西革命根據地創始者的革命經歷中找到更多的例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皖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舒傳賢。舒傳賢是霍山人。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正在省城第一甲種工業學校就讀的舒傳賢參加了安慶學界聲援北京學生的示威游行,1921年10月,他在安慶籌建了安徽省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參加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爭,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八七會議后,舒傳賢被派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他利用串親交友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立以‘交換知識,聯絡感情,砥礪學術,主張公道’為主要內容的學術研究會,發展共產黨員”。在此基礎上,舒傳賢建立黨組織,領導發動六霍起義,走上了創建皖西革命根據地的道路。與舒傳賢并肩作戰,被譽為“創建皖西蘇區的杰出領導者”的周狷之早年也在安慶參加反帝反封建運動,后受黨組織派遣回家鄉開展革命事業。
在六安河西(淠河以西)地區點燃革命火種的毛正初也有類似的經歷。毛正初是六安人。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毛正初在六安參加了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1921—1924年,毛正初先后在蕪湖“二農”、私立求是中學和省立五中學習。在校期間,毛正初由于在五卅運動的“三罷”斗爭中表現“突出”而被校方開除,被迫離開蕪湖,“是年秋,在朱蘊山的幫助下,轉入安慶建華中學”,不久加入共青團。1926年,黨組織選派毛正初去黃埔軍校第六期學習,并接納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6月,毛正初“接受黨的派遣,回到家鄉開展農民運動,以徐家集國民小學教師的合法身份為掩護,秘密組織農民協會,領導農民開展抗糧、抗債、抗稅斗爭”,直至建立黨的組織和武裝,進而領導河西暴動,建立河西革命根據地。
雖然現有資料不足以清晰地繪制出皖西紅色革命發動者的社會關系網絡和革命活動軌跡,但以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這些革命者大多出身于本地,早年在家鄉接受思想啟蒙,稍長,則到長江之畔接受革命教育,走上革命道路。他們與家鄉保持聯系和互動,有的直接回到家鄉創建黨組織,領導革命暴動。誠然,從大的歷史背景看,這種地理上的來源和互動應當是多元的,但他們絕大多數都在長江沿岸城市接受革命洗禮和鍛造,既有從安慶、蕪湖回到家鄉的,也有從上海、武漢回來的,或是先在安慶、蕪湖就學,后轉到上海、武漢歷練,再回轉家鄉的。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安慶、蕪湖是大多數人的革命起點,在皖西革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如主要領導者舒傳賢、周狷之、毛正初等人。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經由他們從皖江之畔帶回到淮河流域,由革命理論變為革命實踐。長江沿岸的革命火種在大別山間熊熊燃燒之日,就是紅色文化植根于淮河流域之時。
化成于江淮大地
提到皖西革命、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大別山,很少有人將其與淮河相聯系。事實上,大別山是長江淮河的分水嶺,其北部屬于淮河流域,南部屬于長江流域。而皖西革命的中心在大別山北麓即淮河流域,包括壽縣、霍邱、六安、霍山等地,鄂豫皖蘇區更是囊括了淮河的上游和中游。皖西革命的興起和發展、皖西蘇區的建立,標志著紅色文化開始在安徽淮河流域生根發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安徽的發展軌跡看,安徽紅色文化的形塑經過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的鍛造和洗禮,呈現出從皖西向東向南擴展,最終化成于江淮大地的傳承路徑。
1929年六霍起義后,“以六霍為中心的皖西各地的工農武裝割據斗爭,以燎原之勢發展到六安、霍山、霍邱、英山、潛山等縣相毗連的廣闊區域”。這個紅色區域范圍已囊括安徽淮河流域的大部,南部直抵皖江流域。1930年6月,鄂豫皖蘇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標志著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從此,皖西融入中國工農武裝割據的大潮中,在反“圍剿”、蘇區建設的斗爭實踐中凝練革命文化的精神內核。
安徽紅色文化的精神品格與學界同仁熱衷探討的“蘇區精神”“大別山精神”是一體的。這也是安徽紅色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精神譜系中的地位之所在。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將蘇區精神概括為“星火燎原,信念堅定;反對‘本本’,開拓進取;執政為民,爭創第一;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無私奉獻,不怕犧牲”。他特別指出:“這個內涵盡管是以中央蘇區的歷史為背景做的概括,但它涵蓋了包括金寨·鄂豫皖蘇區在內的全國各蘇區軍民用鮮血和生命所凝聚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正是有這種偉大精神力量的支撐,蘇區人民既打造出了過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又不惜前仆后繼、承受一切犧牲,為新中國的誕生進行奠基。”這充分說明了皖西蘇區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
“大別山精神”也是學術界探討的一個熱點問題。“大別山精神”的形成還包括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錘煉,但這不影響我們對其精神內涵的理解。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大別山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前仆后繼的奮斗和犧牲,創造了“28年紅旗不倒”的革命傳奇;皖西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僅金寨縣為革命犧牲的在冊烈士就有1萬多人。關于“大別山精神”的內涵,這里仍然引用石仲泉的表述,歸納為“堅守信念、對黨忠誠,"胸懷全局、甘于奉獻,"依靠群眾、團結奮斗,"不畏艱苦、勇當前鋒”。從“蘇區精神”和“大別山精神”的角度理解安徽紅色文化的精神內涵是理所應當的。但就安徽紅色基因的生成而言,還應將其置于新四軍在華中的展開、解放大軍馳騁江淮以及百萬雄師過大江等歷史現場來加以考察。
七七事變爆發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除瓊崖游擊隊外)被改編為新四軍。安徽是新四軍的集中地、東進抗日的出發地,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華中抗戰領導中心所在地,也是新四軍堅持八年抗戰的主戰場之一。新四軍軍部所在的涇縣云嶺也處于皖江流域的腹地。在皖南完成整編的新四軍第一至三支隊隨即開赴安徽、江蘇長江兩岸的抗日前線。皖西大別山地區的紅二十八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這支成建制的紅軍隊伍的保留就是堅守信念、不怕犧牲革命精神的體現。隨后第四支隊東進抗日,在江淮之間與日偽展開激烈的戰斗。在第四支隊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四軍第二師,開創了縱貫津浦路的淮南抗日根據地。新四軍還在安徽創建了皖江、淮南和淮北抗日根據地。皖江、淮河流域是新四軍在安徽活動的中心區域,革命文化以民族解放戰爭的形式在江淮大地上繼續深耕、綻放。新四軍精神是對革命文化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新四軍在華中的經營為解放戰爭中人民軍隊突入中原、重建大別山根據地創造了基礎和條件。
江淮大地上紅色文化的獨特魅力在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得到充分展現。安徽是淮海戰役指揮中心、總前委所在地和主戰場。包括安徽在內的解放區人民對淮海戰役的支援是全方位的,“在這約3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從后方到前方,從鄉村到城鎮,男女老幼齊上陣,家家戶戶忙支前。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支援什么,解放軍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成了千百萬人民的自覺行動。廣大共產黨員、干部、勞模帶頭支前,父子、兄弟爭上前線,許多青年自動推遲婚期,丈夫奮勇去支前,妻子積極忙生產,保證支前、生產兩不誤,各地的模范人物及事跡層出不窮。人人都在為爭取這次決戰的勝利,努力多做貢獻,展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宏偉圖景”。群眾路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法寶之一,“依靠人民”是淮海戰役精神的重要方面。有學者指出:“無論過去、現在、將來,淮海戰役精神都具有永恒的魅力和深遠的影響,"是我們取之不竭的精神動力和紅色養分。”淮海戰役精神是對紅色文化基因的傳承和發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走向成熟的標志。
渡江戰役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決勝之戰。安徽是渡江戰役的指揮中心、練兵場和出發地,八百里皖江更是百萬雄師千里競渡的主戰場。繁昌縣夏家湖(今屬蕪湖市弋江區)是當年“渡江第一船”登陸點。“偉大的渡江戰役鑄就了偉大的渡江精神。安徽是渡江精神的主要孕育和鍛造之地。”江淮大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支前運動,皖南軍民采取各種行動策應大軍渡江,廣大民眾的無私支援和奉獻是戰役取勝的重要因素。陳毅曾經指出:“在沿江人民支援我軍渡江方面,表現積極熱烈……在合肥、巢、無方面,人民出糧供應亦很積極,船工亦聽調參加演習。”劉伯承曾這樣評價:“六安、合肥到安慶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前送軍糧,沿江居民省出自己的糧食給軍隊吃,他們貢獻極大,感人極深。”渡江戰役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走向勝利的標志,也是紅色文化化成于江淮大地的高光時刻。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由理論到實踐在安徽的發展歷程看,紅色文化基因由皖江之畔播遷到淮河流域,最后化成于江淮大地的傳承路徑是相當清晰的。這一路徑轉換賦予安徽紅色文化以鮮明的底色,簡言之就是先進性、鄉土性和人民性。先進性體現在一批革命知識分子站在時代的潮頭浪尖,讓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成為皖江之畔的最強音;鄉土性體現在淮河流域孕育了安徽早期的革命者,他們與故土聯系密切,又扎根故土點燃革命之火;人民性體現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過程中,江淮兒女始終是革命的依靠對象,他們的犧牲和奉獻是安徽紅色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責任編輯:胡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