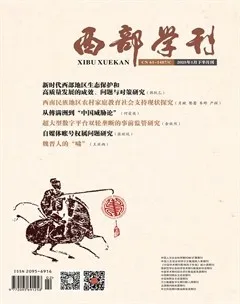“兩個結(jié)合”與家族宗法性國家的特色關(guān)系研究
摘要:中國由于數(shù)千年的歷史文化傳承而形成了特定的國情,中華民族的具體實際立足于家族宗法性社會的基礎(chǔ),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是立足于家族宗法性傳承的精神追求,如家風(fēng)與家學(xué)、宗法與民族、信仰與國家,并且形成了宗法性國家的管理體系,這種以宗法性家族為上層,以郡縣為主要單位從上到下的運行體系,伴以大一統(tǒng)儒家意識形態(tài)和集體主義觀念,使得中國社會長期保持了穩(wěn)固。中華復(fù)興需要“兩個結(jié)合”,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jié)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又要深入挖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特質(zhì),進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文化是社會長期發(fā)展的基石,要完善自身文化的話語體系與社會人文結(jié)構(gòu),提高思想道德建設(shè)水平,使中國走向“文化上多樣,結(jié)構(gòu)上恰當(dāng),道德上合理,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明之路。
關(guān)鍵詞:“兩個結(jié)合”;宗法性國家;家族;民族與信仰;制度與文化
中圖分類號:A81;D61;G122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2-0144-0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Family Patriarchal Country
Dong Ning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China’s unique national context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millennia-ol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inherently tied to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at forms the basi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essenc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lso grounded in this patriarchal clan-based inheritance, encompassing aspects such as family ethos and scholarship, clan laws and ethnicity, and beliefs and nationhood. This has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inherently patriarchal, with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led by clan-based families and organized primarily around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is system, coupled with a unified Confucian ideology and collectivist value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Chinese society.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lls for the “two combinations”: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rounding in the realities of China while delving into the excellent qual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e can thu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e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ety’s long-term development. To perfect our own 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structur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China must embark on a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is culturally diverse, structurally appropriate, morally sound, and institutionally complete, following a Chinese-style path to civilization.
Keywords: two combinations; the patriarchal country; patriarchal clan; ethnicity and belief;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化與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chǔ)上開辟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是必由之路。”[1]從辯證的角度而言,不同國家或者民族應(yīng)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需要對其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做出具體不同分析,在結(jié)合實際的基礎(chǔ)上,進而形成最合理的決策。中華民族由于數(shù)千年的歷史文化傳承而形成的特定國情,特別是宗法性社會的家庭基礎(chǔ)、教育、信仰等國家特性,始終影響了制度化的建設(shè)進程。
一、中華民族的具體實際:立足于家族宗法性社會的基礎(chǔ)
中華民族,是由“各種血緣關(guān)系的眾多家族”為主導(dǎo)組成的“宗法性社會”[2]群體,其中少數(shù)民族等群體的不斷融合,也提升了華夏子孫的團結(jié)性與凝聚力。因而,中國是一個極具包容性與融合性,而民族、信仰與文化具有多樣性的國家。
對于宗法性社會的存在歷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例如,先秦的《儀禮》等文獻中即有相關(guān)記載。古代中國以血緣關(guān)系管理氏族、宗族的制度,是維持政治、經(jīng)濟及其他社會秩序運轉(zhuǎn)的主要方式。這種制度所涉及的階層以士卿、大夫、周天子及其分封的諸侯國國君為主,而多數(shù)的這些諸侯國,則由姬姓家族及有功的臣子家族及附屬組成。這種家族性的王朝統(tǒng)治,由于長期中國農(nóng)業(yè)文明的基礎(chǔ),在經(jīng)歷了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與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以及數(shù)千年來的各種社會變革后,最終走向了以工業(yè)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現(xiàn)代文明世界。但是,人類家族的血緣性,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宗法性社會強調(diào)家族性、集體性、民族性的固有特點,伴隨著社會的需要,會長期持續(xù)留存,并形成特有的國情。
時至今日,人們的思想隨著生活的改善、社會的進步,以及時代、科技等變化而變化。但是,大至國家建設(shè),小至家族村落——這種集體性的觀念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得到了歷朝歷代的重視,并形成了當(dāng)下優(yōu)秀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并傳承不息。中國長期以一姓一氏的門閥家族為管理中心,同時周圍圍繞著各個家族,他們的思想由官僚體系影響,延伸至整個社會與國家。這種情況,在魏晉時期達(dá)到了高峰,成為以門閥氏族聯(lián)合管理國家的特定政權(quán)形式。無論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出于穩(wěn)固社會、建設(shè)國家等因素,嬴劉李趙朱等帝王家族一直到愛新覺羅氏,期間經(jīng)歷了“分封制、郡縣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三省六部制”等形式,以此引發(fā)出了關(guān)于家族教育、官僚體系、王朝周期更替的內(nèi)容,特別是在“上下階層關(guān)系如何進行辨證處理”的問題上——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對此進行了深入交談,黃說道:“我生六十多年……一人,一家……乃至一國……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毛澤東答曰,“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fù)責(zé),才不會人亡政息。”[3]可以看出,無論是黃炎培還是毛澤東,都對此有著各自深刻的理解。
近代的中國,發(fā)揮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所形成的集體性智慧。人民群眾在各種困難面前,團結(jié)一致、萬眾一心,為當(dāng)家作主而英勇奮斗。在經(jīng)歷了不斷的變革后,中國一步一步地從農(nóng)業(yè)文明踏入了工業(yè)文明的世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一代又一代領(lǐng)導(dǎo)集體的正確引領(lǐng)下,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商業(yè)社會的發(fā)達(dá),帶來了全球貿(mào)易與分工,經(jīng)濟基礎(chǔ)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使得社會關(guān)系與上層建筑發(fā)生了變化,中國與全球的聯(lián)系也越發(fā)頻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廣大人民群眾做出艱辛的努力和付出,終于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總結(jié)我國發(fā)展的歷史進程時,就已經(jīng)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建立于中華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基礎(chǔ)之上。這一基礎(chǔ)是中國發(fā)展到當(dāng)下的幾千年文明史的經(jīng)驗所組成的。因此,“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nèi)涵與獨特優(yōu)勢。”[4]只有把握好“兩個結(jié)合”,才能讓社會得以穩(wěn)定、獲得長足的發(fā)展,才能把握好新時代的特征,從而更快地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水平。
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立足于家族宗法性傳承的精神追求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基與文脈,是豐富理論思想的源頭,也是立足于家族傳承的精神追求。這些都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長足發(fā)展提供了思維與方向,無論在治國理政、經(jīng)濟發(fā)展、家族傳承、道德修養(yǎng)乃至思想水平的建設(shè)方面。
(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家風(fēng)與家學(xué)、宗法與民族、信仰與國家
《大學(xué)》之中“修身、齊家以能夠治國、平天下”的身國共治觀念,時刻影響著國人的內(nèi)心價值與共同目標(biāo)。
特別是在漢魏家族的教育中,“這些大族普遍重視宗族內(nèi)的儒學(xué)教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定的‘家風(fēng)’和‘家學(xué)’,以維持他們的地位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墜”[5]。這些家族的子弟們普遍具備高于普通人的文化學(xué)識與道德修養(yǎng),并且他們之間還相互關(guān)聯(lián)與照應(yīng)。他們的影響代代相傳,以至于這種情況延續(xù)至今,并使得現(xiàn)代的族譜修繕行為日益繁盛。同時,這也反映出了家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體現(xiàn)出了對于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使得炎黃子孫形成了“尋根問祖”的良好風(fēng)氣。
與“西方家國關(guān)系在王權(quán)與宗教體系上所建立的社會、群體與私人范疇”不同,中國文化中的“家國同構(gòu)”持久而深入影響了家庭傳統(tǒng)教育的特征[6]。這種與人倫、宗法關(guān)系密切相連的性質(zhì),尤其是《孝經(jīng)》的影響,更是強化了集體和國家,而形成了國家主義。如著名的王氏、謝氏家族,他們家族的家風(fēng)、家學(xué)即體現(xiàn)于家族子弟“為學(xué)為仕、修身齊家”的思想行為之中,并且身國共治與世代傳承。某種意義上而言,“經(jīng)學(xué)研習(xí)與傳承的家族化,使得以官學(xué)方式存在的經(jīng)學(xué)傳授得以延續(xù)”[7]。門閥士族希望家族子弟,包括父兄表親在家教、仕途等,都能做到敬老愛幼、顧及同胞,并文史皆通、聲名遠(yuǎn)播。“此兩種希望,并合成為當(dāng)時共同之家教,最終成為了‘家風(fēng)’與‘家學(xué)’。”[8]這種由經(jīng)學(xué)沿襲產(chǎn)生的家風(fēng)、家學(xué),由魏晉延續(xù)到宋明時期,最終由下至上帶來了真正的“國風(fēng)、國學(xué)”,形成以家庭傳遞為基礎(chǔ)的國家思想持續(xù)影響到了近現(xiàn)代。
在信仰與習(xí)俗之中,宗法性的傳統(tǒng)宗教,則以祖先與天神的崇拜為主流,以自然崇拜為輔助、其他崇拜為補充而出現(xiàn)的“郊社、宗廟與祭祀制度”,成為中國宗法等級社會禮俗的主要內(nèi)容——這也是維護整個社會秩序、家族體系、國家精神的力量與保證。中華民族的宗法性文化、信仰與傳承特征,也使得外來宗教融合于本土之中。例如,瑯琊王氏家族所呈現(xiàn)出的思想變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王戎等人受玄學(xué)影響而成為玄學(xué)人物;佛道流行時,王導(dǎo)尊崇佛教,而王羲之信仰道教;三教融合時,王褒則尊孔并均學(xué)習(xí)之。
中國是一個民族、信仰、宗教都充滿多樣性的大國,它們在差異、交流、互動中走向了融合與發(fā)展。無論是儒釋道或基督教等方面的跨文化、跨地域傳播,都存在受眾共同的興趣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共通之處,并能產(chǎn)生情感共鳴,拉近彼此的距離。從而,建構(gòu)了符合受眾群體的話語方式與文化故事,達(dá)到不同群體性認(rèn)同的效果。這些都豐富了華夏民族的文化內(nèi)涵,在家風(fēng)、國風(fēng)、文化、信仰的共同影響下,促進了中華人民的大團結(jié)。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文明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道德與信仰的重要傳承,是文化、思想、精神融合的巨大成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離不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離不開整個社會的積極參與。
(二)宗法性國家的管理體系:個體與民族、制度與文化
從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之后,分封制與郡縣制最終在秦漢得以成型,并隨著朝代的更替而長期并存。這種以宗法性家族作為上層建筑,以郡縣為主要單位而從上到下的運行體系,使得農(nóng)業(yè)社會的發(fā)展得以較長時期的穩(wěn)固。尤其是以帝王、宰相搭配的形式所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度,成為古代相對完善的管理體系,成就了兩千年來中國特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
作為民族性國家,由漢代先哲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西漢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漢武帝乾綱獨攬。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被扼殺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在內(nèi)外政策上進行一系列變古創(chuàng)制、更化鼎新。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學(xué)說為基礎(chǔ),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建立起一個具有神學(xué)傾向的新儒學(xué)思想體系。理論,使得“大一統(tǒng)”思維令中國的國家凝聚力越發(fā)提升,也讓國家越發(fā)穩(wěn)定與團結(jié)。同時,這種思想也影響到了歷朝歷代的各個階層。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話語體系。以二十五史為代表的持續(xù)性敘事的記載情況,伴隨著各個家族在時代的風(fēng)云變幻,與包容萬象、百花齊放的人文精神,更充分體現(xiàn)出中華文明的各個階段的特色歷史經(jīng)驗。
唐宋以來,科舉制度的千年盛行形成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君臣父子”[9]各居其位的思想,形成了秩序性的現(xiàn)象。這種情況如《舊唐書》中,“使各專其業(yè)。凡習(xí)學(xué)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nóng),巧作器用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10]這些共同的價值觀,使得各個階層的思想形成了一個整體。因而,科舉所創(chuàng)造出的制度性地位,使得官僚階層將共同的價值觀進一步帶給了地方社會群體,從而完成國家與社會的價值聯(lián)結(jié)[11]。自魏晉時期繁盛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使得漢代以來那些世家大族最終發(fā)展成了門閥士族,而皇室只是門閥士族中的第一家族。這種情況經(jīng)歷魏晉南北朝,而延續(xù)至隋唐時期。在唐末及宋元至明清的階段,地方的鄉(xiāng)紳貴族、宗族家長等基層的力量更加強大,并且他們通過以聯(lián)姻、結(jié)拜、依附等方式在幾乎所有的行政范圍內(nèi),直接擁有了政治、經(jīng)濟、社會等權(quán)力。
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中國,科舉在唐、宋、元、明之時,形成了千年來固有的制度性特征。這種情況可見于《明史》的選舉志部分,無論是包括經(jīng)義、詩賦、策論還是其他的科考內(nèi)容,都“沿唐宋之舊”[12]。這些傳統(tǒng)特色的官方行為,使得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的思想走向了一致性。因此,制度性的選拔導(dǎo)致了“任何觀念上的偏見,都會傾向于將世界構(gòu)建成某種特定形態(tài)”[13]。
中華文明從夏商周,從秦漢至明清,積累了數(shù)千年的集體性文明傳承經(jīng)驗,并使得絕大多數(shù)人具有集體觀。“中國古代文明十分強調(diào)集體性,尤以王朝國家的強化為目標(biāo)。”[14]這些特征,也是王朝周期率的誕生原因。隨著農(nóng)業(yè)文明進入到工業(yè)文明的時代,由于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形式的紛爭,在中華大地上曾經(jīng)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局面。19世紀(jì)中期以來,東西方的頻繁接觸伴隨著思想與經(jīng)濟矛盾、各種戰(zhàn)爭等,使得王朝模式遭受了沖擊,并帶來了國人的激烈情緒與奮勇爭斗。在多重復(fù)雜的心態(tài)下,這些運動最終促使中國駛離了舊有形式的軌道,而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15]。人類文明的新形態(tài),是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shè)中生成的,也是與中國具體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情況,以及中華民族的社會理想結(jié)合起來的結(jié)果。
因而,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相互結(jié)合,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基于中國文化的固有特點,更是中國走向成熟世界的根本需要。
三、結(jié)論:中華復(fù)興需要與“兩個結(jié)合”形成特色關(guān)系
“兩個結(jié)合”的出現(xiàn),對中國國情下的社會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伴隨著傳統(tǒng)文化的深入影響,中華民族在不斷地實踐探索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隨之“兩個結(jié)合”的應(yīng)用,顯得更為極其迫切與需要。
(一)中華民族發(fā)展至今,更需要注重“家國情懷”的教育。社會在實踐層面中需要避免形式化,以深刻領(lǐng)會“兩個結(jié)合”的真正要義——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jié)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強調(diào)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fā)展過程中,既要立足中國實際,又要深入挖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特征,進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
(二)兩千多年來,以血緣親疏與上下秩序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家族宗法性社會的國情,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在“家風(fēng)與國風(fēng)、制度與文化、民族與信仰以及人類共同價值觀”的作用下,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內(nèi)在凝聚力,維護了社會的團結(jié)與穩(wěn)定,產(chǎn)生了長遠(yuǎn)深刻的影響。在“兩個結(jié)合”的引領(lǐng)下,完善自身文化的話語體系與社會人文結(jié)構(gòu),提高思想道德建設(shè)水平,能夠使中國走向“文化上多樣,結(jié)構(gòu)上恰當(dāng),道德上合理,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式文明之路。
(三)文化是社會長期發(fā)展的基石,尤其是在家族宗法性傳承的國家之中,體現(xiàn)出了相當(dāng)?shù)闹匾浴?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在當(dāng)代更加應(yīng)該發(fā)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中華的復(fù)興,需要以“兩個結(jié)合”為指南,開闊視野與胸懷,增強自信。并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動力,科學(xué)把握好國家與社會的努力方向,制定符合國情的戰(zhàn)略與政策,進一步實現(xiàn)民族的繁榮昌盛。
參考文獻:
[1]王偉光.實現(xiàn)“兩個結(jié)合”是開辟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J].理論導(dǎo)報,2023(9):4-8.
[2]彭新武,周瑞春.傳統(tǒng)社會治理規(guī)范的現(xiàn)代審視[J].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1(1):20-27.
[3]池軼.說說“窯洞對”[N].人民政協(xié)報,2021-05-31(9).
[4]習(xí)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3(17):4-7.
[5]王永平.漢魏六朝時期江東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變遷[J].揚州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0(4):59-66.
[6]戴紅宇,成若彤.我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私人性與公共性[J].集美大學(xué)學(xué)報,2022(3):52-59.
[7]孫杰.經(jīng)學(xué)傳承與家風(fēng)養(yǎng)成:以魏晉南北朝為中心的考察[J].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教育科學(xué)版),2023(6):14-21.
[8]錢穆.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論叢:第3冊[M].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9:178-179.
[9]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128.
[10]舊唐書:卷43[M].北京:中華書局,1975:1825.
[11]李磊.官僚類型變遷:科舉制與傳統(tǒng)中國的治理模式[J].文化縱橫,2021(6):118-127.
[12]明史:卷70[M].北京:中華書局,1974:1693.
[13]尼爾·波茲曼.技術(shù)壟斷:文明向技術(shù)投降[M].蔡金棟,梁薇,譯.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3:11.
[14]尾形勇.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M].張鶴泉,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1-62.
[15]陶東風(fēng).社會轉(zhuǎn)型與當(dāng)代知識分子[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6-10.
作者簡介:董寧(1989—),男,漢族,浙江金華人,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為中西哲學(xué)。
(責(zé)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