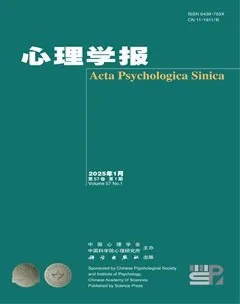“摸魚(yú)”如何帶來(lái)創(chuàng)新?恢復(fù)體驗(yàn)曲線中介效應(yīng)的情景實(shí)驗(yàn)與調(diào)查證據(jù)












摘 "要""基于資源保存理論, 文章探索了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過(guò)猶不及效應(yīng), 分析其如何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影響, 以及正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通過(guò)對(duì)情景回顧實(shí)驗(yàn)的182份樣本和三輪問(wèn)卷調(diào)研的503份領(lǐng)導(dǎo)?員工配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檢驗(yàn), 結(jié)果發(fā)現(xiàn):(1)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 并進(jìn)一步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影響; (2)正念調(diào)節(jié)了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 即員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時(shí)間竊取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以及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作用越強(qiáng)。文章發(fā)現(xiàn)時(shí)間竊取可以作為一種工作內(nèi)恢復(fù)形式影響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和創(chuàng)新行為, 這一觀點(diǎn)豐富了時(shí)間竊取相關(guān)文獻(xiàn), 拓展了工作內(nèi)恢復(fù)的效果和機(jī)制研究, 同時(shí)也為管理員工“摸魚(yú)”提供了實(shí)踐啟示。
關(guān)鍵詞""時(shí)間竊取, 恢復(fù)體驗(yàn), 正念, 創(chuàng)新行為
分類號(hào)""B849: C93
1 "前言
在當(dāng)今競(jìng)爭(zhēng)激烈和快節(jié)奏的工作環(huán)境中, 員工常常面臨著工作事務(wù)蔓延到非工作時(shí)間、工作時(shí)間延長(zhǎng)、工作與生活邊界日益模糊等壓力(Steffensen et al., 2022; Xu et al., 2023)。在這樣的背景下, 越來(lái)越多的員工選擇在工作時(shí)間進(jìn)行“摸魚(yú)”, 比如閑聊、休息時(shí)間過(guò)長(zhǎng)等(Brock et al., 2013; Martin et al., 2010)。特別是,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和通訊技術(shù)的發(fā)展, 員工的“摸魚(yú)”行為變得更加復(fù)雜和多樣化, 頻次也越來(lái)越高, 這對(duì)企業(yè)管理實(shí)踐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也引起了管理者和學(xué)者們的廣泛關(guān)注(Brock et al., 2013; Hu et al., 2023; Xu et al., 2023)。
“摸魚(yú)”一詞源自“渾水摸魚(yú)”, 原意為趁形勢(shì)混亂私自攫取利益, 后引申為不認(rèn)真工作的表現(xiàn)。學(xué)者們通常使用時(shí)間竊取這一概念來(lái)指代員工的職場(chǎng)“摸魚(yú)”行為, 即“員工在工作時(shí)間從事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活動(dòng)” (Martin et al., 2010)。正如“摸魚(yú)”常隱含貶義, 以往大多數(shù)研究將時(shí)間竊取視為一種有意傷害組織的偏差行為(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 認(rèn)為從事該行為本身會(huì)消耗可用資源, 并削弱員工隨后從事積極行為的能力(Harold et al., 2022)。但也有學(xué)者提出, 時(shí)間竊取不一定是故意傷害組織的行為(Brock et al., 2013), 也可能是一種應(yīng)對(duì)壓力的自我保護(hù)行為(Xu et al., 2023)。例如, 有研究發(fā)現(xiàn), 員工在經(jīng)歷情感和認(rèn)知資源消耗后, 為避免進(jìn)一步資源損失而進(jìn)行時(shí)間竊取(Harold et al., 2022; Xu et al., 2023), 甚至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獲取新的資源(Methot et al., 2021)。這些研究表明:從事時(shí)間竊取既可能獲取資源, 也可能損失資源。但目前關(guān)于時(shí)間竊取何時(shí)帶來(lái)資源收益、何時(shí)帶來(lái)資源損失的研究仍然很少, 無(wú)法解釋以往研究發(fā)現(xiàn)的矛盾機(jī)制。本研究認(rèn)為, 員工在從事不同程度的時(shí)間竊取時(shí)所獲得的體驗(yàn)可能有所差異。具體來(lái)說(shuō), 適量的時(shí)間竊取不易被人察覺(jué), 能幫助員工獲得更多積極體驗(yàn)和資源, 促使員工更好地從工作應(yīng)激中恢復(fù); 而過(guò)量的時(shí)間竊取易被發(fā)現(xiàn)與懲罰, 并引發(fā)更多消極體驗(yàn), 阻礙員工資源的恢復(fù)與重建。因此, 本文的第一個(gè)研究目的是探索時(shí)間竊取的這種“過(guò)猶不及”效應(yīng), 并依據(jù)資源保存理論提出時(shí)間竊取和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可能存在倒U形關(guān)系。
本文的第二個(gè)研究目的是檢驗(yàn)正念是否為時(shí)間竊取影響恢復(fù)體驗(yàn)的重要邊界條件。依據(jù)恢復(fù)體驗(yàn)的相關(guān)研究和理論, 員工的意識(shí)和注意力從工作任務(wù)中脫離是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的關(guān)鍵前提(Chong et"al., 2020; Sonnentag amp; Fritz, 2015)。正念作為一種管控當(dāng)下注意力和下意識(shí)行為的有效特質(zhì)(鄭曉明, 倪丹, 2018), 能夠通過(guò)關(guān)注當(dāng)下的方式, 幫助員工在工作任務(wù)和非工作活動(dòng)之間靈活地切換和控制意識(shí)和注意力(Chong et al., 2020)。因此, 我們推測(cè), 利用時(shí)間竊取所獲得的恢復(fù)體驗(yàn)可能因人而異, 高正念水平的員工在從事時(shí)間竊取時(shí), 能更迅速地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并聚焦到非工作活動(dòng)上, 更敏銳地感知到時(shí)間竊取所帶來(lái)的恢復(fù)體驗(yàn)。
此外, 為揭示時(shí)間竊取的深層次影響, 本文提出第三個(gè)研究目的:探討員工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獲得的恢復(fù)體驗(yàn)如何影響其后續(xù)的創(chuàng)新行為。創(chuàng)新行為不僅能反映員工的工作表現(xiàn), 更是企業(yè)持續(xù)獲得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關(guān)鍵因素(Babalola et al., 2021)。盡管研究表明, 工作外的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有一定的促進(jìn)作用(Eschleman et al., 2014), 但鮮有研究探討工作內(nèi)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之間的關(guān)系。我們認(rèn)為, 適量的時(shí)間竊取能夠幫助員工即時(shí)修復(fù)和重建工作中所消耗的資源(無(wú)需等待下班和休息日), 這種即時(shí)的恢復(fù)體驗(yàn)可能會(huì)進(jìn)一步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更直接的正面影響。
綜上, 基于資源保存理論, 本研究構(gòu)建了一個(gè)有調(diào)節(jié)的間接效應(yīng)模型(如圖1), 并擬從三個(gè)方面做出理論貢獻(xiàn):首先, 本研究提出了一個(gè)新穎的視角, 即時(shí)間竊取于組織而言并不總是有害的, 也存在一定的積極效應(yīng), 并探索了時(shí)間竊取如何作為一種工作內(nèi)恢復(fù)形式促進(jìn)員工的創(chuàng)新行為。這一觀點(diǎn)挑戰(zhàn)了以往將時(shí)間竊取視為生產(chǎn)偏差行為的傳統(tǒng)看法(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 增加了我們對(duì)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認(rèn)識(shí)。其次, 本研究揭示了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 以及其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這不僅解釋了時(shí)間竊取是如何過(guò)猶不及的, 還豐富和拓展了時(shí)間竊取的后效研究。最后, 本研究探討了正念在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及創(chuàng)新行為之間關(guān)系時(shí)的雙重作用, 展現(xiàn)了其在不同程度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中所帶來(lái)的積極效應(yīng)與潛在成本, 為時(shí)間竊取對(duì)員工產(chǎn)生差異化影響提供了理論解釋。
1.1""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曲線關(guān)系
恢復(fù)體驗(yàn)是指員工從工作應(yīng)激中恢復(fù)的心理過(guò)程, 包括與資源保護(hù)有關(guān)的心理脫離(不再思考工作事務(wù))和放松體驗(yàn)(低應(yīng)激水平)、與資源獲取有關(guān)的掌握體驗(yàn)(克服新挑戰(zhàn)或?qū)W習(xí)新技能)和控制體驗(yàn)(自主決定時(shí)間分配和活動(dòng)安排) (Bennett et al., 2018; Sonnentag amp; Fritz, 2007; 吳偉炯"等, 2012)。根據(jù)資源保存理論, 個(gè)體有動(dòng)力保護(hù)現(xiàn)有資源, 并通過(guò)資源投資活動(dòng)獲取新的資源, 實(shí)現(xiàn)資源重建, 進(jìn)一步恢復(fù)損失的資源(Hobfoll, 1989)。而時(shí)間竊取向員工提供了暫時(shí)從工作需求中脫離出來(lái)的機(jī)會(huì), 停止現(xiàn)有資源損耗, 并且允許員工在工作時(shí)間“即時(shí)”補(bǔ)充所消耗的個(gè)人資源以及建立新資源(Xu et al., 2023; Zhu et al., 2019)。因此, 有理由認(rèn)為時(shí)間竊取可以作為一種壓力應(yīng)對(duì)手段, 影響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然而, 鑒于時(shí)間竊取具有可隱蔽性和未經(jīng)批準(zhǔn)性特點(diǎn)(Lorinkova amp; Perry, 2017), 這種影響是復(fù)雜的, 不是簡(jiǎn)單的線性關(guān)系。
一方面, 通過(guò)適量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 員工可以暫時(shí)從工作需求中解脫出來(lái), 避免持續(xù)消耗資源(Bakker et al., 2013; Sonnentag amp; Fritz, 2007), 從而減少工作帶來(lái)的疲勞并改善情緒(Zhu et al., 2019)。這時(shí), 員工可以暫時(shí)不用去思考與工作有關(guān)的事, 降低了自身應(yīng)激水平, 實(shí)現(xiàn)心理脫離并獲得放松體驗(yàn)。而且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具有隱蔽性(Lorinkova amp; Perry, 2017), 不易被領(lǐng)導(dǎo)和同事察覺(jué), 員工可以決定自己做什么, 從中獲得一種控制體驗(yàn)。另外, 時(shí)間竊取也為員工提供了接受挑戰(zhàn)性體驗(yàn)的機(jī)會(huì), 例如上班時(shí)間玩解謎游戲。這時(shí)員工可以暫時(shí)擺脫工作角色的限制, 探索個(gè)人興趣, 并從應(yīng)對(duì)挑戰(zhàn)中感受到能力感與成就感, 獲得掌握體驗(yàn)(Sonnentag amp; Fritz, 2007)。因此, 在時(shí)間竊取處于中低水平時(shí), 隨著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增加, 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會(huì)提升。
另一方面, 時(shí)間竊取并非越多越好, 因?yàn)樗俏唇?jīng)組織批準(zhǔn)的, 會(huì)給員工招致批評(píng)與懲罰。盡管短期內(nèi)具有隱蔽性, 但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超過(guò)一定水平時(shí), 很可能會(huì)被察覺(jué), 導(dǎo)致同事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不公平感(Ketchen et al., 2008), 甚至可能會(huì)激怒領(lǐng)導(dǎo)和同事。為了不被排斥和懲罰, 員工會(huì)更加小心翼翼, 甚至采取各種手段包裝時(shí)間竊取行為(Baskin et al., 2017), 這反而會(huì)消耗個(gè)體的內(nèi)部資源, 提升員工的應(yīng)激水平, 降低放松體驗(yàn)。同時(shí), 這也降低了員工在決定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內(nèi)容、時(shí)間和頻率方面的靈活性, 削弱了員工的控制體驗(yàn)。另外, 員工從事的時(shí)間竊取越多, 其可隱蔽性優(yōu)勢(shì)越少, 預(yù)期的風(fēng)險(xiǎn)與懲罰強(qiáng)度越大, 消極體驗(yàn)越多。這些消極體驗(yàn)不僅會(huì)引發(fā)員工的焦慮和對(duì)工作的消極反芻(Hunter amp; Wu, 2016), 阻礙員工的心理脫離, 也增加了員工在上班時(shí)間獲得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挑戰(zhàn)應(yīng)對(duì)經(jīng)驗(yàn)和學(xué)習(xí)新技能的難度, 降低獲得掌握體驗(yàn)的可能。也就是說(shuō),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超過(guò)一定水平時(shí), 反而會(huì)給員工帶來(lái)資源損失。根據(jù)資源保存理論的損失優(yōu)先原則, 相比于資源獲得, 資源損失對(duì)個(gè)體的影響更快, 持續(xù)時(shí)間也更長(zhǎng)(Hobfoll et al., 2018)。因此, 在時(shí)間竊取處于中高水平時(shí), 隨著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增加, 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反而會(huì)降低。綜上所述, 本研究假設(shè):
H1: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
1.2""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
創(chuàng)新行為是指員工在工作過(guò)程中產(chǎn)生創(chuàng)新性想法和解決方案, 并努力付諸于實(shí)踐的行為表現(xiàn)(Scott amp; Bruce, 1994)。從事創(chuàng)新行為需要員工投入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 并承擔(dān)高風(fēng)險(xiǎn)和不確定性(Anderson et al., 2014; Yuan amp; Woodman, 2021), 這會(huì)損耗創(chuàng)新主體的情感、認(rèn)知等資源。根據(jù)資源保存理論, 個(gè)體會(huì)積極地獲得、保護(hù)和建設(shè)資源, 擁有較多資源的個(gè)體更有能力和動(dòng)力從事資源投資活動(dòng), 以獲取新資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因此, 本研究認(rèn)為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獲得的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員工創(chuàng)新行為有積極影響, 因?yàn)檫@種恢復(fù)體驗(yàn)意味著即時(shí)的資源補(bǔ)充與重建。具體來(lái)說(shuō), 恢復(fù)體驗(yàn)主要包括放松、心理脫離、掌握和控制(Sonnentag amp; Fritz, 2007)。首先, 放松體驗(yàn)可以降低員工的應(yīng)激水平, 心理脫離允許員工在精神上脫離工作, 這可以避免進(jìn)一步資源損失, 還有助于形成積極情緒(Zhang et al., 2023)。積極情緒往往更容易帶來(lái)有趣的、廣泛的、發(fā)散的思維和新的想法(Vahle-Hinz et"al., 2017), 促進(jìn)創(chuàng)新行為。其次, 掌握體驗(yàn)為員工提供了接受挑戰(zhàn)和學(xué)習(xí)新技能的機(jī)會(huì), 能給員工帶來(lái)技能、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等內(nèi)部資源(Eschleman et"al., 2014)。而創(chuàng)新行為恰恰需要運(yùn)用和開(kāi)發(fā)特定領(lǐng)域的知識(shí)、技能和能力(Anderson et"al., 2014; 尹奎"等, 2022)并需要自我效能感作為激勵(lì)因素(Mao et al., 2021; Ng et al., 2022; 姜平"等, 2020)。最后, 研究表明, 創(chuàng)新行為往往是非常規(guī)的, 需要一定的行動(dòng)自由度來(lái)積極尋求與落實(shí)新的想法(van Knippenberg amp; Hirst, 2020), 而控制體驗(yàn)——能夠決定如何分配工作時(shí)間以及安排非工作活動(dòng)——恰能滿足這一條件。綜合以上分析, 本研究假設(shè):
H2: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如上文所述, 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可以幫助員工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 保護(hù)他們剩余的資源并即時(shí)恢復(fù)已損耗的資源。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 員工可以重新補(bǔ)充他們?cè)诠ぷ髌陂g已經(jīng)耗盡的資源。一旦資源得到即時(shí)補(bǔ)充, 員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 更有意愿和能力去從事創(chuàng)新行為。然而, 當(dāng)從事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時(shí), 員工更容易感到焦慮并對(duì)工作產(chǎn)生消極反芻(Methot et al., 2021), 這時(shí)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反而會(huì)降低, 這意味著更少的資源補(bǔ)充。而創(chuàng)新行為作為一種具有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為(Scott amp; Bruce, 1994; 秦許寧"等, 2022), 不僅要承擔(dān)不確定性風(fēng)險(xiǎn), 還會(huì)額外消耗員工大量的資源(朱金強(qiáng)"等, 2020)。根據(jù)資源保存理論, 個(gè)體的資源是有限的, 如果個(gè)體不能獲得足夠資源, 則會(huì)傾向于保存現(xiàn)有資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也就是說(shuō), 當(dāng)員工恢復(fù)體驗(yàn)不足時(shí), 他們往往不會(huì)將資源與精力花費(fèi)在耗時(shí)且高風(fēng)險(xiǎn)的創(chuàng)新行為上, 進(jìn)而會(huì)減少創(chuàng)新行為(宋孜宇, 高中華, 2020; Vahle?"Hinz et al., 2017; 朱金強(qiáng)"等, 2020)。基于以上推理, 本研究假設(shè):
H3: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間接影響創(chuàng)新行為。
1.3 "正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正念是一種有意識(shí)地聚焦于當(dāng)下體驗(yàn)而不對(duì)過(guò)去和未來(lái)加以批判的心理特征(Brown amp; Ryan, 2003)。它可以幫助個(gè)體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意識(shí)與注意力(Bergin amp; Pakenham, 2016; Fisher et al., 2019; 倪丹"等, 2021), 并提高個(gè)體對(duì)周?chē)榫熬€索的敏感度(Kao et al., 2021)。因此, 高正念的員工在從事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時(shí), 能夠迅速靈活地將注意力從工作中轉(zhuǎn)移出來(lái), 使因工作激活的生理和心理系統(tǒng)得以恢復(fù)(Bakker et al., 2013; Sonnentag amp; Fritz, 2007)。并且高正念的員工還能專注于當(dāng)前所從事的非工作活動(dòng), 持續(xù)地穩(wěn)定他們的注意力, 以便在他們分心時(shí)將注意力帶回這些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活動(dòng)(Good et al., 2016; 張靜"等, 2017), 從而獲得更好的恢復(fù)體驗(yàn)。但當(dāng)從事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時(shí), 隨著行為隱蔽性的降低, 高正念的員工更容易察覺(jué)到周?chē)那榫熬€索(如同事的不滿), 意識(shí)到行為的不妥, 并感受到更多來(lái)自組織規(guī)范和道德標(biāo)準(zhǔn)的壓力(Hülsheger et al., 2021)。這種壓力感知可能增加他們的負(fù)面情緒如內(nèi)疚(Hülsheger et al., 2021), 進(jìn)而削弱他們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這種違規(guī)行為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的能力。
相比之下, 低正念的員工不太關(guān)注當(dāng)下體驗(yàn)。當(dāng)從事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時(shí), 他們往往繼續(xù)思考與工作有關(guān)的問(wèn)題, 難以專注于時(shí)間竊取帶來(lái)的恢復(fù)體驗(yàn)(Brown amp; Ryan, 2003)。換句話說(shuō), 在參與適量的休息、閑聊等非工作活動(dòng)時(shí), 他們的思緒隨時(shí)可能會(huì)跳躍到對(duì)工作的考慮與擔(dān)憂上(Chong et al., 2020; Smallwood amp; Schooler, 2015), 這減緩了身心系統(tǒng)的恢復(fù)。同樣地, 在從事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時(shí), 由于缺乏對(duì)情景線索的敏感度(Kao et al., 2021), 低正念的員工往往難以察覺(jué)到自己的處境和潛在的風(fēng)險(xiǎn)與懲罰, 從而減少了自身的應(yīng)激與焦慮。這種無(wú)意識(shí)狀態(tài)使得低正念員工不易受到當(dāng)前環(huán)境壓力的影響, 從而降低了從過(guò)量時(shí)間竊取中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的難度。因此, 對(duì)于低正念水平的員工而言, 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形關(guān)系將不那么明顯。綜上, 我們假設(shè):
H4:正念會(huì)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相比于低正念員工, 高正念員工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更強(qiáng)。
基于假設(shè)3和假設(shè)4, 我們認(rèn)為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呈現(xiàn)間接曲線關(guān)系, 而正念調(diào)節(jié)了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曲線關(guān)系。因此我們推測(cè), 正念對(duì)時(shí)間竊取與創(chuàng)新行為之間的間接曲線效應(yīng)也具有調(diào)節(jié)作用, 具體而言, 這種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的間接曲線效應(yīng)在正念水平高的員工中更為顯著。因此, 我們假設(shè):
H5:正念調(diào)節(jié)了時(shí)間竊取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員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影響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越強(qiáng), 反之越弱。
1.4""研究概覽
本研究旨在考察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和邊界條件, 以及對(duì)后續(xù)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為了檢驗(yàn)上述假設(shè)模型, 我們采用實(shí)驗(yàn)研究和實(shí)地研究相結(jié)合的方式, 以建立內(nèi)外部效度。研究1采用情景回顧實(shí)驗(yàn)設(shè)計(jì), 通過(guò)操縱時(shí)間竊取來(lái)檢驗(yàn)?zāi)P偷那鞍攵危?即時(shí)間竊取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以及正念特質(zhì)的調(diào)節(jié)作用。研究2采用分時(shí)點(diǎn)的領(lǐng)導(dǎo)?員工配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全模型的檢驗(yàn), 進(jìn)一步驗(yàn)證并拓展了研究1的結(jié)論, 從而提高整體模型的可靠性。
2 "研究1:情景回顧實(shí)驗(yàn)
2.1 "樣本和程序
本研究使用G*Power (Faul et al., 2009)計(jì)算實(shí)驗(yàn)所需的樣本量, 設(shè)定中等效應(yīng)量f"= 0.25, 顯著性水平α = 0.05, 要達(dá)到1 ? β"= 0.80的檢驗(yàn)效能, 至少需要158名被試參與實(shí)驗(yàn)。我們借助問(wèn)卷星平臺(tái)招募被試, 并進(jìn)行了一項(xiàng)預(yù)篩選調(diào)查, 共有182名符合條件的被試自愿進(jìn)入到正式實(shí)驗(yàn)階段。篩選條件包括:符合在職員工身份, 且經(jīng)歷過(guò)三種不同強(qiáng)度的時(shí)間竊取體驗(yàn)(從事過(guò)低時(shí)間竊取行為、中時(shí)間竊取行為和高時(shí)間竊取行為)。此外, 為確保被試認(rèn)真填答, 本研究在實(shí)驗(yàn)問(wèn)卷中設(shè)置了注意力檢測(cè)題, 填答通過(guò)的被試能獲得一定的報(bào)酬。最終, 我們收到了182名被試的實(shí)驗(yàn)結(jié)果。其中, 男性83名, 占比45.60%, 平均年齡為33歲(SD"= 5.58), 90.10%接受過(guò)本科及以上教育, 平均工作年限為7.22年(SD"= 4.67)。
實(shí)驗(yàn)采用單因素3水平被試間設(shè)計(jì), 所有被試被隨機(jī)分配到“低時(shí)間竊取” (N = 61)、“中時(shí)間竊取” (N = 61)和“高時(shí)間竊取” (N = 60)三組。首先, 每組被試測(cè)量自身的正念特質(zhì)并匯報(bào)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信息。然后, 被試按照指導(dǎo)語(yǔ)回憶最近在上班時(shí)間完全沒(méi)有摸魚(yú)/適量摸魚(yú)/大量摸魚(yú)的一天, 要求被試仔細(xì)回想那天具體做了哪些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事情, 并盡可能詳細(xì)地描述那一天的經(jīng)歷, 不少于100字。完成情景回顧后, 被試填寫(xiě)操縱檢驗(yàn)測(cè)量題項(xiàng), 并根據(jù)自己所回憶的真實(shí)感受, 填寫(xiě)恢復(fù)體驗(yàn)測(cè)量題項(xiàng)。這種回憶范式的方法, 已被證明與直接操縱一樣有效, 可以引起被試的特定反應(yīng)(Li et al., 2023; 滕玥"等, 2024)。另外, 中時(shí)間竊取組和高時(shí)間竊取組被試在完成操縱檢驗(yàn)測(cè)試后需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那天, 我的摸魚(yú)行為是很容易被領(lǐng)導(dǎo)和同事發(fā)現(xiàn)的”, 以測(cè)量時(shí)間竊取的可隱蔽性。
2.2""測(cè)量工具
操縱檢驗(yàn)工具。采用Harold等人(2022)所開(kāi)發(fā)的時(shí)間竊取五維度量表, 其中, 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休息、在上班時(shí)間從事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行為以及在工作場(chǎng)所與他人過(guò)度社交這三個(gè)維度強(qiáng)調(diào)在工作時(shí)間內(nèi)從事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活動(dòng); 偽造工作時(shí)間與操縱自己的工作速度這兩個(gè)維度強(qiáng)調(diào)故意不客觀報(bào)告自己的工作時(shí)間或工作效率(Harold et al., 2022)。本研究關(guān)注員工在工作時(shí)間如何通過(guò)一些非工作活動(dòng)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 因此選擇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休息、在上班時(shí)間從事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行為以及在工作場(chǎng)所與他人過(guò)度社交這三個(gè)維度進(jìn)行測(cè)量和研究。同時(shí), 借鑒Hu等人(2023)的做法, 將這三個(gè)維度簡(jiǎn)化為3個(gè)題目, 對(duì)被試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進(jìn)行操縱檢驗(yàn), 典型題目如“那天, 我把應(yīng)該工作的時(shí)間花在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事情上”。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4。
恢復(fù)體驗(yàn)。采用Sonnentag和Fritz (2007)開(kāi)發(fā)的量表, 共16道題, 典型題目如“面對(duì)工作要求, 那時(shí)候我得到了一絲喘息”。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9。
正念。采用Brown和Ryan (2003)開(kāi)發(fā)的量表, 共15道題, 均為反向計(jì)分, 典型題目如“我會(huì)由于走神或粗心大意把事情搞砸”。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9。
以上測(cè)量均采用Likert 7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從“1 = 完全不同意”到“7 = 完全同意”。
2.3 "操縱檢驗(yàn)
單因素方差分析的結(jié)果表明:三組被試對(duì)從事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感知有顯著差異(F(2, 179) = 150.27, p"lt; 0.001), 低時(shí)間竊取組(M低"= 1.72, SD"= 0.72)比中時(shí)間竊取組(M中"= 4.25, SD"= 1.16)顯著低, 高時(shí)間竊取組(M高"= 4.76, SD"= 1.16)比中時(shí)間竊取組顯著高, 說(shuō)明實(shí)驗(yàn)操縱有效。此外, 我們對(duì)比分析了中時(shí)間竊取組和高時(shí)間竊取組的可隱蔽性得分, 結(jié)果顯示, 中時(shí)間竊取組的“摸魚(yú)”行為(M中"= 4.31, SD"= 1.56)比高時(shí)間竊取組的“摸魚(yú)”行為(M高"= 5.58, SD"= 1.48)更不容易被領(lǐng)導(dǎo)和同事察覺(jué)(t (119) = ?4.61, p"lt; 0.001), 符合假設(shè)中對(duì)可隱蔽性這一特征的闡述。
2.4""研究結(jié)果
首先, 本研究對(duì)被試的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以及時(shí)間竊取、恢復(fù)體驗(yàn)和正念等研究變量進(jìn)行了描述性分析和Pearson相關(guān)分析。結(jié)果顯示(見(jiàn)表1), 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顯著正相關(guān)(r"= 0.62, p"lt; 0.001)。根據(jù)假設(shè)1, 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因此, 在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正相關(guān)的基礎(chǔ)上, 我們進(jìn)行了單因素方差分析。結(jié)果表明, 3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低組"= 1, 中組"= 2, 高組"= 3)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具有顯著的二次效應(yīng)(F (1, 179) = 105.94, p"lt; 0.001)和顯著的線性效應(yīng)(F (1, 179) = 172.58, p"lt; 0.001)。進(jìn)一步對(duì)比分析表明, 中時(shí)間竊取組(M中"= 5.14, SD"= 0.63)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顯著高于低時(shí)間竊取組(M低"= 3.17, SD"= 0.88, t (120) = 14.24, p"lt; 0.001)和高時(shí)間竊取組(M高"= 4.84, SD"= 0.55, t (119) =2.76, p"= 0.007)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初步支持了假設(shè)1。
其次, 假設(shè)4提出, 正念會(huì)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為驗(yàn)證這一假設(shè), 本研究以恢復(fù)體驗(yàn)為因變量, 并借鑒現(xiàn)有研究經(jīng)驗(yàn)(曾慧"等, 2024), 以中位數(shù)(M中位數(shù)"= 4.91)為分組依據(jù)將正念特質(zhì)連續(xù)變量轉(zhuǎn)變?yōu)榉诸愖兞浚?進(jìn)行3 (時(shí)間竊取:低"vs."中"vs. 高) × 2 (正念:低"vs. 高)的方差分析。結(jié)果顯示, 時(shí)間竊取與正念的交互效應(yīng)顯著, F(2, 176) = 6.76, p"= 0.001, 假設(shè)4得到初步驗(yàn)證。進(jìn)一步簡(jiǎn)單效應(yīng)分析發(fā)現(xiàn)(如圖2所示), 在低正念水平下, 中時(shí)間竊取組(M中"= 5.06, SD"= 0.69)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顯著高于低時(shí)間竊取組(M低"= 3.43, SD"= 0.86, t (62) = 8.31, p"lt; 0.001), 而與高時(shí)間竊取組(M高"= 4.95, SD"= 0.62, t(53) = 1.89, p"= 0.063)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無(wú)顯著差異; 在高正念水平下, 中時(shí)間竊取組(M中"= 5.22, SD"= 0.56)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顯著高于低時(shí)間竊取組(M低"= 2.84, SD"= 0.82, t (56) = 13.12, p"lt; 0.001)和高時(shí)間竊取組(M高"= 4.71, SD"= 0.41, t (64) = 2.25, p"= 0.029)被試的恢復(fù)體驗(yàn)得分。
最后, 為進(jìn)一步驗(yàn)證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和正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我們借助拔靴法來(lái)檢驗(yàn)研究假設(shè)。為了降低多重共線性的影響, 我們?cè)跇?gòu)建平方項(xiàng)和交互項(xiàng)之前, 先將時(shí)間竊取和正念進(jìn)行中心化處理。結(jié)果顯示(見(jiàn)表2), 時(shí)間竊取一次項(xiàng)系數(shù)為正且顯著(β"= 0.63, 95% CI [0.56, 0.70]), 時(shí)間竊取二次項(xiàng)系數(shù)為負(fù)且顯著(β"= ?0.31, 95% CI [?0.39, ?0.24]), 且隨著時(shí)間竊取水平由低(?2 SD和?1 SD)、中(0 SD)轉(zhuǎn)為高(+1 SD和+2"SD), 簡(jiǎn)單斜率也由正轉(zhuǎn)為負(fù)(分別為1.45、0.93、0.42、?0.09、?0.61), 說(shuō)明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 假設(shè)1得到驗(yàn)證。同時(shí), 時(shí)間竊取的平方與正念的交互項(xiàng)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顯著且系數(shù)為負(fù)(β = ?0.21, 95% CI [?0.34, ?0.05])。為了更加直觀地表示正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我們計(jì)算了簡(jiǎn)單斜率并繪
制了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圖(見(jiàn)圖3)。結(jié)果表明,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處于低水平和高水平時(shí), 相比于低正念, 高正念條件下的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的關(guān)系顯著且更強(qiáng)(?2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50, 95% CI [0.18, 0.83]; ?1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90, 95% CI [0.30, 1.48]; +1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30, 95% CI [?0.56, ?0.004]; +2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70, 95% CI [?1.21, ?0.12]);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處于中水平時(shí), 正念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不存在顯著差異(0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10, 95% CI [?0.004, 0.21])。綜上, 正念對(duì)這一倒U型關(guān)系起到調(diào)節(jié)作用, 假設(shè)4得到驗(yàn)證。
3 "研究2:多時(shí)點(diǎn)多來(lái)源問(wèn)卷調(diào)查
3.1""樣本與程序
本研究選取位于北京、上海、新疆的17家企業(yè)中的員工作為正式調(diào)查的研究對(duì)象, 主要涉及金融、咨詢、互聯(lián)網(wǎng)、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行業(yè)。研究者向調(diào)研對(duì)象及其領(lǐng)導(dǎo)說(shuō)明調(diào)查內(nèi)容與目的, 并強(qiáng)調(diào)數(shù)據(jù)僅用于學(xué)術(shù)研究且會(huì)嚴(yán)格保密。在征求調(diào)研對(duì)象同意后, 獲取了員工及其領(lǐng)導(dǎo)的名單, 并進(jìn)行編號(hào)和配對(duì)。所有參與調(diào)查的員工均為自愿參加, 通過(guò)線上方式填寫(xiě)問(wèn)卷。
為避免數(shù)據(jù)同源偏差的影響, 數(shù)據(jù)采集分三個(gè)時(shí)間點(diǎn)進(jìn)行, 每次間隔1個(gè)月。第一階段, 收集了員工的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數(shù)據(jù), 并讓員工評(píng)價(jià)自身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正念和工間微休息, 該階段共發(fā)放633份問(wèn)卷, 回收606份問(wèn)卷。第二階段, 讓員工評(píng)價(jià)自身的恢復(fù)體驗(yàn), 該階段共發(fā)放606份問(wèn)卷, 回收569份問(wèn)卷。第三階段, 由直屬領(lǐng)導(dǎo)評(píng)價(jià)員工的創(chuàng)新行為, 該階段共邀請(qǐng)到120名領(lǐng)導(dǎo)參與調(diào)研。三輪調(diào)查完成后, 采用編號(hào)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配對(duì), 剔除缺失重要變量和明顯填答不規(guī)范的樣本后, 最終獲得503份有效領(lǐng)導(dǎo)?員工配對(duì)問(wèn)卷, 問(wèn)卷有效率為79.46%。在所有被調(diào)查的員工中, 男性占比58.10%;年齡分布在22~58歲之間, 其中, 22~30歲占比33.80%, 31~40歲占比43.70%, 41~50歲占比18.50%, 51~58歲占比4.00%; 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下占比15.70%, 本科占比62.60%, 研究生及以上占比21.70%; 在本單位的平均工作時(shí)間為6.71年(SD"= 7.28), 在本崗位的平均工作時(shí)間為6.61年(SD"= 6.63)。
3.2 "測(cè)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國(guó)內(nèi)外權(quán)威期刊公開(kāi)發(fā)表的成熟量表, 并對(duì)時(shí)間竊取行為、正念、恢復(fù)體驗(yàn)、工間微休息的英文量表進(jìn)行了翻譯與回譯, 以保證問(wèn)卷翻譯的準(zhǔn)確性; 創(chuàng)新行為直接采用國(guó)內(nèi)學(xué)者使用過(guò)的中文量表。
時(shí)間竊取行為。同研究1, 根據(jù)本文研究范圍, 采用Harold等人(2022)所開(kāi)發(fā)量表中的在上班時(shí)間從事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行為、未經(jīng)批準(zhǔn)的休息、在工作場(chǎng)所與他人過(guò)度社交三個(gè)維度進(jìn)行測(cè)量, 每個(gè)維度3道題, 共9道題, 典型題目如“工作期間, 我參與與工作無(wú)關(guān)的活動(dòng)”、“我休息的時(shí)間比單位允許我休息的時(shí)間長(zhǎng)”。采用Likert 7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其中“1”表示“從無(wú)”, “7”表示“總是”。在本研究中, 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92。
正念。采用Brown和Ryan (2003)開(kāi)發(fā)的量表, 共15道題, 均為反向計(jì)分, 典型題目如“我會(huì)由于走神或粗心大意把事情搞砸”。采用Likert 5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 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8。
恢復(fù)體驗(yàn)。采用Sonnentag和Fritz (2007)開(kāi)發(fā)的量表, 共16道題, 典型題目如在工作時(shí)間參與諸如休息、聊天、上網(wǎng)等非工作活動(dòng)期間, “我忘記了工作”、“我放松一下”。采用Likert 5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 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7。
創(chuàng)新行為。采用Scott和Bruce (1994)所開(kāi)發(fā)的、王甜等人(2019)所使用的中文版量表進(jìn)行測(cè)量, 將“我”改編為“該下屬”, 共6道題, 典型題目如“該下屬經(jīng)常會(huì)產(chǎn)生一些有創(chuàng)意的想法或點(diǎn)子”、“該下屬會(huì)為實(shí)施創(chuàng)意制定合理的計(jì)劃與流程”。采用Likert 5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其中“1”表示“從不”, “5”表示“總是”。在本研究中, 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95。
控制變量。根據(jù)以往研究, 本文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時(shí)間等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同時(shí), 根據(jù)恢復(fù)體驗(yàn)相關(guān)文獻(xiàn), 工間微休息能夠?qū)T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Kim et al., 2017), 因此本文將工間微休息納入控制變量, 并采用Kim等人(2018)開(kāi)發(fā)的量表測(cè)量員工的工間微休息行為。量表列舉了一些典型休息活動(dòng), 如“伸懶腰、在辦公室散步或短暫地放松”, 共9道題。采用Likert 7點(diǎn)量表計(jì)分方式, 其中“1”表示“從無(wú)”, “7”表示“總是”。在本研究中, 內(nèi)部一致性系數(shù)為0.86。
3.3 "研究結(jié)果
3.3.1 "研究變量的區(qū)分效度檢驗(yàn)與共同方法偏差檢驗(yàn)
為檢驗(yàn)時(shí)間竊取、正念、恢復(fù)體驗(yàn)、創(chuàng)新行為這4個(gè)變量的區(qū)分效度, 且考慮到創(chuàng)新行為的數(shù)據(jù)結(jié)構(gòu)具有嵌套性問(wèn)題, 本研究通過(guò)Mplus 8.5將創(chuàng)新行為設(shè)置為多水平、其他變量設(shè)置為個(gè)體水平進(jìn)行了跨層驗(yàn)證性因子分析。由于本研究模型變量與對(duì)應(yīng)的測(cè)量題目較多, 因此對(duì)時(shí)間竊取、正念、恢復(fù)體驗(yàn)的測(cè)量題目采用平衡法進(jìn)行打包(吳艷, 溫忠麟, 2011), 每個(gè)變量的題目均打?yàn)槿齻€(gè)包。結(jié)果顯示(參見(jiàn)表3), 相比于其他競(jìng)爭(zhēng)性模型(單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 本研究所使用的四因子模型的擬合效果更優(yōu)(χ2/df"= 2.41, CFI = 0.97, TLI = 0.97, RMSEA = 0.05, SRMRbetween"= 0.04, SRMRwithin"= 0.03), 對(duì)不同的構(gòu)念有更好的區(qū)分效度, 可進(jìn)行下一步分析。
盡管本研究采取多時(shí)點(diǎn)、多來(lái)源的調(diào)研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同源偏差的影響, 但由于數(shù)據(jù)均由問(wèn)卷調(diào)查的方法獲得, 仍然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數(shù)據(jù)分析前, 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素法對(duì)共同方法偏差問(wèn)題進(jìn)行檢驗(yàn), 結(jié)果顯示未經(jīng)旋轉(zhuǎn)的第一個(gè)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34.41%, 小于40%的臨界值。另外, 進(jìn)行共同方法潛因子模型檢驗(yàn), 結(jié)果顯示, 當(dāng)將共同潛因子納入模型后, 模型擬合指標(biāo)分別為:χ2/df = 2.54, CFI = 0.97, TLI =0.96, RMSEA = 0.06, SRMRbetween"= 0.06, SRMRwithin"= 0.04。相比于控制前的模型, χ2/df提升0.13, TLI降低0.01, RMSEA提升了0.01, SRMRbetween提升0.02, SRMRwithin提升0.01, 所有擬合指標(biāo)變化程度均不超過(guò)0.13, 說(shuō)明加入共同方法潛因子后模型的擬合度未得到顯著改善。綜上判定, 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問(wèn)題。
3.3.2""描述性統(tǒng)計(jì)與相關(guān)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9.0對(duì)樣本的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變量、控制變量工間微休息、研究變量時(shí)間竊取、恢復(fù)體驗(yàn)、正念、創(chuàng)新行為進(jìn)行描述性分析和Pearson相關(guān)分析。各變量的均值、標(biāo)準(zhǔn)差和相關(guān)系數(shù)如表4所示, 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顯著正相關(guān)(r"= 0.21, p"lt; 0.001), 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r"= 0.18, p"lt; 0.001), 時(shí)間竊取與創(chuàng)新行為顯著正相關(guān)(r"= 0.11, p"= 0.012)。這一結(jié)果為后續(xù)研究假設(shè)論證提供了初步依據(jù)。另外,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時(shí)間、工間微休息等控制變量也與恢復(fù)體驗(yàn)、創(chuàng)新行為等主要變量存在不同程度的關(guān)聯(lián), 說(shuō)明有必要在分析中加以控制。
3.3.3""假設(shè)檢驗(yàn)
由于本研究的數(shù)據(jù)結(jié)構(gòu)是嵌套型數(shù)據(jù)(創(chuàng)新行為由一位領(lǐng)導(dǎo)評(píng)價(jià)多名下屬, ICC1 = 0.35, p"lt; 0.001), 因此使用Mplus 8.5進(jìn)行多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分析。此外, 因抽樣設(shè)計(jì)導(dǎo)致數(shù)據(jù)還存在其他層次的嵌套(員工分布在不同企業(yè)中), 我們借鑒張偉雄和王暢(2018)處理這種樣本誤差非獨(dú)立性的經(jīng)驗(yàn), 在Mplus中加入COMPLEX語(yǔ)句進(jìn)行分析, 并在放入回歸模型前, 將時(shí)間竊取、正念等核心變量進(jìn)行了總均值中心化處理, 以降低多重共線性影響。
主效應(yīng)與間接效應(yīng)檢驗(yàn)。首先, 假設(shè)1提出, 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從表5的模型3可以看出, 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平方項(xiàng)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顯著且系數(shù)為負(fù)(β"= ?0.15, p"= 0.001), 并且隨著時(shí)間竊取水平由低(?2 SD和?1 SD)、中(0 SD)轉(zhuǎn)為高(+1 SD和+2 SD), 簡(jiǎn)單斜率也由正轉(zhuǎn)為負(fù)(分別為0.25、0.14、0.03、?0.08、?0.19), 符合倒U型曲線趨勢(shì)(如圖4所示), 說(shuō)明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的倒U型關(guān)系成立, 假設(shè)1得到驗(yàn)證。
其次, 假設(shè)2提出, 恢復(fù)體驗(yàn)與創(chuàng)新行為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從表5的模型6中可以看出, 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14, p"= 0.002), 假設(shè)2得到驗(yàn)證。假設(shè)3進(jìn)一步提出, 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間接影響創(chuàng)新行為。表5的模型7顯示, 同時(shí)加入時(shí)間竊取、時(shí)間竊取的平方項(xiàng)和恢復(fù)體驗(yàn)之后, 時(shí)間竊取的平方項(xiàng)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β"= 0.03, p"gt; 0.05), 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依舊顯著(β"= 0.14, p"= 0.002), 初步判斷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間接影響。
最后, 由于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非線性的倒U型關(guān)系, 中介變量M隨自變量X的變化而非線性變化, 因變量Y也隨M的非線性變化而變化, 不存在一個(gè)單一的間接效應(yīng)來(lái)表征X通過(guò)M對(duì)Y的間接影響。因此, 本研究借鑒以往研究的經(jīng)驗(yàn)(Hu et al., 2019; 劉智強(qiáng)"等, 2023), 使用Hayes和Preacher (2010)提出的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檢驗(yàn)方法, 估計(jì)在低(?2 SD和?1 SD)、中(0 SD)和高(+1 SD和+2 SD)水平下, 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 并使用Preacher和Selig (2012)推薦的Monte Carlo方法, 來(lái)估計(jì)其95%的置信區(qū)間。結(jié)果顯示(見(jiàn)表6),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在低(?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5, 95% CI [0.01, 0.09];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3, 95% CI [0.01, 0.05])、高(+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3, 95% CI [?0.07, ?0.004])水平時(shí),
其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顯著; 而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在高(+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1, 95% CI [?0.03, 0.001]), 中(0 SD, 間接效應(yīng)"= 0.01, 95% CI [?0.003, 0.02])水平時(shí), 其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不顯著。綜上得出, 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間接影響, 呈現(xiàn)出斷檔且非線性的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趨勢(shì), 假設(shè)3得到驗(yàn)證。
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檢驗(yàn)。假設(shè)4提出, 正念會(huì)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從表5中的模型4可以看出, 正念與時(shí)間竊取平方的交互項(xiàng)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有著顯著的負(fù)向影響(β"= ?0.29, p"lt; 0.001)。為了進(jìn)一步了解正念對(duì)時(shí)間竊取行為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本研究計(jì)算了簡(jiǎn)單斜率, 并使用Monte Carlo法估計(jì)其95%的置信區(qū)間。結(jié)果如表7所示,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處于低水平時(shí), 正念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顯著(?2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53, 95% CI [0.29, 0.77]; ?1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30, 95% CI [0.15, 0.45]);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處于高水平時(shí), 正念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也顯著(+1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16, 95% CI [?0.31, ?0.01]; +2 SD, 簡(jiǎn)單斜率差異"= ?0.39, 95% CI [?0.63, ?0.15])。基于此, 假設(shè)4得到驗(yàn)證。最后, 本研究繪制了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圖, 以更直觀地表示正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如圖5所示, 正念正向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 員工的正念水平越高, 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越強(qiáng)。
有調(diào)節(jié)的間接效應(yīng)檢驗(yàn)。假設(shè)5提出, 正念調(diào)節(jié)了時(shí)間竊取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為了驗(yàn)證有調(diào)節(jié)的間接效應(yīng)差異的顯著性, 我們使用Mplus 8.5檢驗(yàn)了在低正念水平和高正念水平這兩種情況下,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處于低水平、中等水平以及高水平時(shí), 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值, 并使用Monte Carlo方法估計(jì)其95%的置信區(qū)間。結(jié)果如表6所示, 在高正念水平情況下, 時(shí)間竊取水平較低時(shí), 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為正且顯著(?2 SD,"間接效應(yīng)"= 0.10, 95% CI [0.03, 0.19];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6, 95% CI [0.02, 0.10]); 時(shí)間竊取水平較高時(shí), 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為負(fù)且顯著(+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4, 95% CI [?0.08, ?0.01]; + 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9, 95% CI [?0.17, ?0.03]), 這與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 進(jìn)而影響創(chuàng)新行為的研究假設(shè)相吻合。并且,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處于低水平時(shí), 其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在不同正念水平下存在顯著差異(?2"SD, 間接效應(yīng)差異"= 0.09, 95% CI [0.03, 0.18]; ?1 SD, 間接效應(yīng)差異"= 0.05, 95% CI [0.02, 0.10]); 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行為處于高水平時(shí), 其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在不同正念水平下的差異依舊顯著(+1 SD, 間接效應(yīng)差異"= ?0.03, 95% CI [?0.07, ?0.001]; +2"SD, 間接效應(yīng)差異"= ?0.07, 95% CI [?0.14, ?0.02])。因此, 時(shí)間竊取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瞬時(shí)間接效應(yīng)在不同正念水平下存在顯著差異, 假設(shè)5得到驗(yàn)證。
3.3.4""補(bǔ)充檢驗(yàn)
以上章節(jié)匯報(bào)了包含控制變量的分析結(jié)果, 為了保證研究結(jié)論的透明度和穩(wěn)健性, 我們也匯報(bào)不含控制變量的分析結(jié)果。數(shù)據(jù)結(jié)果顯示, 時(shí)間竊取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具有顯著的線性效應(yīng)(β"= 0.21, p"lt; 0.001)。另外鑒于平方項(xiàng)有助于解釋未被線性模型捕捉到的額外方差, 我們繼續(xù)將時(shí)間竊取平方項(xiàng)納入分析模型, 以更全面地理解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結(jié)果表明, 時(shí)間竊取平方項(xiàng)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β"= ?0.15, p"= 0.004)以及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β"= 0.15, p"= 0.001)依舊顯著, 再次證明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 并進(jìn)而影響員工的創(chuàng)新行為。同時(shí), 時(shí)間竊取的平方與正念的交互項(xiàng)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影響也顯著(β"= ?0.32, p"lt; 0.001), 表明沒(méi)有控制變量的結(jié)果依舊支持正念對(duì)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這進(jìn)一步支撐了本研究的結(jié)論。
此外, 為了檢驗(yàn)變量間反向因果的可能性, 根據(jù)Kline (2011)的建議, 本研究比較了假設(shè)模型(時(shí)間竊取→恢復(fù)體驗(yàn)→創(chuàng)新行為)和反向因果模型(創(chuàng)新行為→恢復(fù)體驗(yàn)→時(shí)間竊取)的赤池信息準(zhǔn)則(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貝葉斯信息準(zhǔn)則(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指標(biāo), 較小的AIC和BIC值表明模型與數(shù)據(jù)的擬合度更高。結(jié)果顯示假設(shè)模型(AIC = 1797.185, BIC = 1890.03)的指標(biāo)要小于反向因果模型的指標(biāo)(AIC = 5008.05, BIC = 5122.01), 表明假設(shè)模型比反向模型更優(yōu), 本研究理論模型存在因果關(guān)系倒置的可能性較小。
最后, 為分析時(shí)間竊取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復(fù)雜影響是否是由創(chuàng)新二元性所造成的, 我們將創(chuàng)新行為分為創(chuàng)新想法提出和創(chuàng)新想法執(zhí)行, 分別將它們作為因變量進(jìn)行了回歸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 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對(duì)創(chuàng)新想法提出(TT ? 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7, 95% CI [0.01, 0.13]; TT ?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3, 95% CI [0.01, 0.07])和創(chuàng)新想法執(zhí)行(TT ? 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8, 95% CI [0.02, 0.15]; TT ?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4, 95% CI [0.01, 0.08])均產(chǎn)生積極效應(yīng), 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則會(huì)通過(guò)降低恢復(fù)體驗(yàn)而阻礙創(chuàng)新想法提出(TT + 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7, 95% CI [?0.13, ?0.01]; TT +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3, 95% CI [?0.07, ?0.01])和創(chuàng)新想法執(zhí)行(TT + 2 SD, 間接效應(yīng)"= ?0.08, 95% CI [?0.14, ?0.02]; TT + 1 SD, 間接效應(yīng)"= ?0.03, 95% CI [?0.07, ?0.001])。這一結(jié)果與本文的假設(shè)觀點(diǎn)一致, 即時(shí)間竊取通過(guò)恢復(fù)體驗(yàn)間接地影響創(chuàng)新行為, 包括創(chuàng)新想法提出和創(chuàng)新想法執(zhí)行。
4 "結(jié)論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的非線性關(guān)系和正念特質(zhì)在其中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以及其對(duì)員工后續(xù)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研究1的實(shí)驗(yàn)結(jié)果表明, 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呈倒U型關(guān)系:當(dāng)時(shí)間竊取處于中低水平時(shí), 員工可以暫時(shí)從工作需求中解脫出來(lái), 從非工作活動(dòng)中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 然而, 一旦超過(guò)某個(gè)程度, 員工從事越多的時(shí)間竊取, 越擔(dān)心被發(fā)現(xiàn)和被懲罰, 恢復(fù)體驗(yàn)反而會(huì)削弱。而這一關(guān)系的強(qiáng)弱依賴于正念特質(zhì)這一重要邊界條件。具體來(lái)說(shuō), 具有高正念特質(zhì)的員工在從事時(shí)間竊取時(shí), 更容易產(chǎn)生過(guò)猶不及的效應(yīng)。研究2通過(guò)問(wèn)卷調(diào)查進(jìn)一步檢驗(yàn)了整個(gè)模型, 再次驗(yàn)證并拓展了上述結(jié)論, 即時(shí)間竊取會(huì)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產(chǎn)生非線性影響, 進(jìn)而間接地促進(jìn)或抑制創(chuàng)新行為, 這一關(guān)系受到正念的調(diào)節(jié)。
4.1""理論貢獻(xiàn)
具體而言, 本研究從三個(gè)方面做出理論貢獻(xiàn):首先, 本研究從資源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時(shí)間竊取這一行為, 挑戰(zhàn)了以往研究將其視為一種意圖傷害組織的生產(chǎn)偏差行為的傳統(tǒng)觀點(diǎn)(Harold et al., 2022; Martin et al., 2010)。傳統(tǒng)觀點(diǎn)認(rèn)為, 時(shí)間是一項(xiàng)重要的組織資產(chǎn), 員工從事時(shí)間竊取就是在損害組織利益(Harold et al., 2022; Henle et al., 2010)。然而, 本研究發(fā)現(xiàn), 適量的時(shí)間竊取可以作為一種特殊的工作內(nèi)恢復(fù)形式, 滿足個(gè)體在工作中“即時(shí)”補(bǔ)充資源的需要。一旦資源得到即時(shí)修復(fù)與重建, 員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因此, 我們認(rèn)為, 時(shí)間竊取作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一種消極偏差行為并不總是有害的, 在某種適宜的情境下可能會(huì)發(fā)揮獨(dú)特的恢復(fù)價(jià)值, 進(jìn)而對(duì)員工的工作表現(xiàn)(創(chuàng)新行為)產(chǎn)生積極影響。這一觀點(diǎn)增進(jìn)了我們對(duì)時(shí)間竊取本身的再認(rèn)識(shí), 同時(shí)也回應(yīng)了之前學(xué)者提出的探討工作內(nèi)恢復(fù)效果和機(jī)制的呼吁(唐漢瑛"等, 2019; 吳偉炯"等, 2012)。
其次, 本研究以資源保存理論為基礎(chǔ), 揭示了時(shí)間竊取會(huì)對(duì)員工恢復(fù)體驗(yàn)產(chǎn)生非線性影響, 進(jìn)而影響其后續(xù)的創(chuàng)新行為, 拓展了時(shí)間竊取的后效研究。具體而言, 我們發(fā)現(xiàn), 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能夠讓員工暫時(shí)地?cái)[脫工作壓力, 停止資源損耗, 并通過(guò)一些非工作活動(dòng)獲取恢復(fù)體驗(yàn); 而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由于被發(fā)現(xiàn)和被懲罰的風(fēng)險(xiǎn)增加, 導(dǎo)致員工在從事非工作活動(dòng)時(shí)更加容易緊張與擔(dān)憂, 反而會(huì)阻礙其恢復(fù)體驗(yàn)。通過(guò)這種對(duì)恢復(fù)體驗(yàn)的曲線作用, 時(shí)間竊取可以間接地影響員工后續(xù)的創(chuàng)新行為。這一發(fā)現(xiàn)不僅厘清了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之間的倒U型關(guān)系, 為時(shí)間竊取的過(guò)猶不及效應(yīng)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 同時(shí)也豐富了我們對(duì)時(shí)間竊取后效影響的認(rèn)識(shí)。
最后, 本研究探討了正念在調(diào)節(jié)時(shí)間竊取與恢復(fù)體驗(yàn)和創(chuàng)新行為之間關(guān)系時(shí)的雙重作用, 揭示了正念作為調(diào)節(jié)變量的積極效應(yīng)與潛在成本, 這為理解正念的復(fù)雜作用提供了新的視角。具體來(lái)說(shuō), 正念能夠使員工更清晰地意識(shí)到當(dāng)前的想法、情緒和環(huán)境(Hyland et al., 2015)。當(dāng)從事中低水平時(shí)間竊取行為時(shí), 由于違規(guī)程度低, 行為隱蔽性高, 員工不太擔(dān)心被發(fā)現(xiàn)。這時(shí)來(lái)自工作環(huán)境的可用線索少,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員工更關(guān)注當(dāng)下內(nèi)在體驗(yàn), 更容易從非工作活動(dòng)中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 進(jìn)而激發(fā)創(chuàng)新行為。但當(dāng)從事中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時(shí), 隨著可隱蔽性優(yōu)勢(shì)的降低, 員工的行為很容易被領(lǐng)導(dǎo)和同事察覺(jué), 招致他們的不滿與懲罰。而正念增強(qiáng)了員工對(duì)工作環(huán)境中可用線索的意識(shí)和注意力(Kao et al., 2021)。這時(shí),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員工更容易感知到來(lái)自組織規(guī)范的壓力, 從而增加了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獲得恢復(fù)體驗(yàn)的難度。綜上而言, 本研究發(fā)現(xiàn), 正念在不同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中發(fā)揮不同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4.2""實(shí)踐啟示
傳統(tǒng)的管理觀念強(qiáng)調(diào)時(shí)間與產(chǎn)出直接相關(guān), 認(rèn)為時(shí)間竊取必然會(huì)降低員工的工作產(chǎn)出(Baskin et"al., 2017)。為此, 在實(shí)踐中, 管理者往往會(huì)采用諸如時(shí)間監(jiān)控軟件等手段來(lái)減少這種行為。然而, 有研究發(fā)現(xiàn), 這反而會(huì)增加員工的壓力, 進(jìn)而導(dǎo)致員工工作效率的降低(Fu et al., 2021)。因此, 我們要重新審視時(shí)間竊取這一行為。首先, 管理者要意識(shí)到員工從事時(shí)間竊取不一定是意圖損害組織效益, 而是可能將其作為一種壓力應(yīng)對(duì)方式, 盡管這種應(yīng)對(duì)方式并不總是有效的。我們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 適量的時(shí)間竊取可以作為一種工作內(nèi)恢復(fù)形式, 為員工提供恢復(fù)體驗(yàn), 實(shí)現(xiàn)即時(shí)的資源修復(fù)與重建, 進(jìn)而激發(fā)創(chuàng)新行為。這種情況下, 過(guò)度采用時(shí)間控制等手段可能會(huì)降低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 反而阻礙創(chuàng)新績(jī)效的提升。我們建議, 管理者需要找到適合企業(yè)自身文化和工作環(huán)境的管理顆粒度, 既不過(guò)度監(jiān)控, 也不放任自流, 以兼顧效率和創(chuàng)新績(jī)效。其次, 本研究發(fā)現(xiàn), 時(shí)間竊取行為并非一成不變的利好。高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反而可能產(chǎn)生過(guò)猶不及效應(yīng), 阻礙員工的恢復(fù)體驗(yàn)和創(chuàng)新行為。因此, 員工應(yīng)當(dāng)理性地管理自己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 可以將其視作一種應(yīng)對(duì)壓力的策略, 幫助自己實(shí)現(xiàn)恢復(fù), 同時(shí)也要意識(shí)到過(guò)度時(shí)間竊取可能會(huì)損害自身的恢復(fù)體驗(yàn)和創(chuàng)新績(jī)效。此外, 本研究強(qiáng)調(diào)了培養(yǎng)員工正念的重要性。正念不僅有助于員工更好地進(jìn)行工作內(nèi)恢復(fù), 還能幫助他們更清晰地感知到過(guò)度時(shí)間竊取對(duì)自身恢復(fù)體驗(yàn)的消極影響。通過(guò)培養(yǎng)正念, 員工可以敏銳地在時(shí)間竊取中找到平衡, 通過(guò)非工作活動(dòng)獲得最大化恢復(fù)效果的同時(shí), 最大程度地降低其負(fù)面影響。
4.3""研究局限與未來(lái)展望
首先, 本研究結(jié)合了情景回顧實(shí)驗(yàn)和多時(shí)點(diǎn)?多來(lái)源的問(wèn)卷調(diào)查方法, 以提高研究結(jié)論的可靠性, 但在研究設(shè)計(jì)上仍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 為了降低干擾因素對(duì)內(nèi)部效度的影響, 我們?cè)谘芯?中采用精簡(jiǎn)的實(shí)驗(yàn)設(shè)計(jì)僅驗(yàn)證了模型的前半段, 未來(lái)的研究可以嘗試采用更加嚴(yán)格的實(shí)驗(yàn)控制條件, 對(duì)整個(gè)模型進(jìn)行完整的檢驗(yàn)。第二, 中低水平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具有隱蔽性, 同事與領(lǐng)導(dǎo)很難準(zhǔn)確評(píng)價(jià)。因此, 本研究采用員工自我報(bào)告的方式來(lái)測(cè)量時(shí)間竊取行為, 這可能受到社會(huì)稱許性偏差的影響。未來(lái)的研究可以考慮采用問(wèn)卷與客觀數(shù)據(jù)相結(jié)合的方式來(lái)測(cè)量員工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 如利用員工在非工作網(wǎng)頁(yè)與APP上的流量數(shù)據(jù)等, 以降低測(cè)量誤差, 保證研究結(jié)論的穩(wěn)健性。第三, 不同于Shin和Grant"(2021)提出的適度拖延給予個(gè)體更多時(shí)間進(jìn)行思考和孵化新想法, 本研究強(qiáng)調(diào)員工通過(guò)時(shí)間竊取可將注意力和意識(shí)從工作需求中脫離出來(lái)(而不是在大腦潛意識(shí)中繼續(xù)處理工作任務(wù)), 以實(shí)現(xiàn)資源的即時(shí)恢復(fù)與重建, 進(jìn)而促進(jìn)創(chuàng)新行為。因此, 本研究認(rèn)為時(shí)間竊取與拖延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機(jī)制不同, 并未控制拖延這一變量。但鑒于兩者在概念上都包括不當(dāng)利用工作時(shí)間的要素(Harold et al., 2022), 未來(lái)關(guān)于時(shí)間竊取的研究可以考慮將拖延納入控制變量范圍。第四, 本研究嘗試在補(bǔ)充分析中將創(chuàng)新行為細(xì)分為創(chuàng)新想法的提出和執(zhí)行兩個(gè)維度來(lái)更全面地探討時(shí)間竊取的影響。然而, 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創(chuàng)新行為量表本身為一維結(jié)構(gòu)(Scott amp; Bruce, 1994), 未明確區(qū)分這兩個(gè)維度, 因此在測(cè)量效度方面存在局限。未來(lái)的研究可考慮采用能夠區(qū)分并測(cè)量創(chuàng)新二元性的多維量表, 以提高研究的精確度和實(shí)用性。
其次, 員工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可以分為主動(dòng)型和被動(dòng)型, 同時(shí), 員工也會(huì)出于不同動(dòng)機(jī)從事不同類型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Baskin et al., 2017)。例如, 為了獲得積極社交情感而與同事閑聊。這些不同類型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對(duì)員工的心理狀態(tài)和工作表現(xiàn)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因此, 未來(lái)研究可以繼續(xù)探究不同類型的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及其作用機(jī)制。
此外, 本研究認(rèn)為, 應(yīng)辯證地看待時(shí)間竊取行為, 它不僅僅是一種消極表現(xiàn), 還是員工應(yīng)對(duì)壓力的一種自我保護(hù)機(jī)制, 能夠在某種適宜的情境下為創(chuàng)新行為提供新的動(dòng)力與資源。這啟示我們:未來(lái)研究可考慮從時(shí)間竊取這類偏差行為的雙面特性入手, 在更廣泛的情境中系統(tǒng)地探討偏差行為對(duì)創(chuàng)新的復(fù)雜影響, 從而為平衡員工的行為監(jiān)管與創(chuàng)新激勵(lì)提供理論啟示。
最后, 隨著數(shù)字化技術(shù)和算法監(jiān)控的廣泛應(yīng)用, 員工的工作行為和績(jī)效逐漸被數(shù)據(jù)化和實(shí)時(shí)跟蹤。在這種情境下, 員工究竟會(huì)因算法監(jiān)控過(guò)嚴(yán)而不能即時(shí)補(bǔ)充資源進(jìn)一步導(dǎo)致其創(chuàng)新受阻, 還是會(huì)在與算法的博弈中激發(fā)自身的創(chuàng)新潛力, 仍是亟待深入探討的問(wèn)題。因此, 未來(lái)研究應(yīng)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數(shù)字化與算法管理背景下時(shí)間竊取的新表現(xiàn)形式及其對(duì)創(chuàng)新行為的影響機(jī)制, 以豐富和加深我們對(duì)數(shù)字化工作環(huán)境中時(shí)間竊取行為的理解。
參 "考 "文 "獻(xiàn)
Anderson, N., Poto?nik, K., amp; Zhou, J. (2014).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tate-of-the-science review, prospective commentary, and guid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anagement, 40(5), 1297?1333.
Babalola, M. T., Kwan, H. K., Ren, S., Agyemang-Mintah, P., Chen, H., amp; Li, J. (2021). Being ignored by loved ones: Understanding when and why family ostracism inhibits creativity at 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2(3), 349?364.
Bakker, A. B., Demerouti, E., Oerlemans, W., amp; Sonnentag, S. (2013). Workaholism and daily recovery: A day reconstruction study of leisure activiti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4(1), 87?107.
Baskin, M. E. B., McKee, V., amp; Buckley, M. R. (2017). Time banditry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profiling of time bandit types. Journal of Leadership amp;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4(1), 39?54.
Bennett, A. A., Bakker, A. B., amp; Field, J. G. (2018). Recovery from work-related effor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9(3), 262?275.
Bergin, A. J., amp; Pakenham, K. I. (2016). The stress-buffering role of mindful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Mindfulness, 7(4), 928?939.
Brock, M. E., Martin, L. E., amp; Buckley, M. R. (2013). Time theft in organiz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banditry questionna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21(3), 309?321.
Brown, K. W., amp; Ryan, R. M. (2003).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esent: Mindfulness and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4), 822?848.
Chong, S., Kim, Y. J., Lee, H. W., Johnson, R. E., amp; Lin, S.-H. (Joanna). (2020). Mind your own break!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workday respite activities and mindfulness on employee outcomes via affective linkag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9, 64?77.
Eschleman, K. J., Madsen, J., Alarcon, G., amp; Barelka, A. (2014). Benefiting from creative activity: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eative activity, recovery experiences, and performance-related outcome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7(3), 579?"598.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amp; Lang, A.-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1(4), 1149?1160.
Fisher, D. M., Kerr, A. J., amp; Cunningham, S. (2019).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ors and strain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26(1), 78?88.
Fu, S. Q., Greco, L. M., Lennard, A. C., amp; Dimotakis, N. (2021). Anxiety responses to the unfolding COVID-19 crisis: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experience of prolonged exposure to stressor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6(1), 48?61.
Good, D. J., Lyddy, C. J., Glomb, T. M., Bono, J. E., Brown, K. W., Duffy, M. K., ... Lazar, S. W. (2016). Contemplating mindfulness at work: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42(1), 114?142.
Harold, C. M., Hu, B., amp; Koopman, J. (2022). Employee time theft: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75(2), 347?382.
Hayes, A. F., amp; Preacher, K. J. (2010). Quantifying and tes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when the constituent paths are nonlinear.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5(4), 627?660.
Henle, C. A., Reeve, C. L., amp; Pitts, V. E. (2010). Stealing time at work: Attitudes, social pressure, and perceived control as predictors of time thef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4(1), 53?67.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3), 513?524.
Hobfoll, S. E., Halbesleben, J., Neveu, J.-P., amp; Westman, M. (2018).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The reality of resour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1), 103?128.
Hu, B., Harold, C. M., amp; Kim, D. (2023). Stealing time on the company’s dime: Examin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laissez-fair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time thef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83(2), 475?493.
Hu, J., Zhang, Z., Jiang, K., amp; Chen, W. (2019). Getting ahead, getting along, and getting prosocial: Examining extraversion facets, peer reactions, and leadership emerg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4(11), 1369?1386.
Hülsheger, U. R., van Gils, S., amp; Walkowiak, A. (2021). The regul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in enacted workplace incivility: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6(8), 1250?1265.
Hunter, E. M., amp; Wu, C. (2016). Give me a better break: Choosing workday break activities to maximize resource recover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2), 302?311.
Hyland, P. K., Lee, R. A., amp; Mills, M. J. (2015). Mindfulness at work: A new approach to impro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4), 576?602.
Jiang, P., Yang, F., amp; Zhang, L. H. (2020). How does leader humor stimulate employees' innovation? A dual process model analysi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amp; T, 41(4), 98?112.
[姜平, 楊付, 張麗華. (2020). 領(lǐng)導(dǎo)幽默如何激發(fā)員工創(chuàng)新:一個(gè)雙中介模型的檢驗(yàn). 科學(xué)學(xué)與科學(xué)技術(shù)管理, 41(4), 98?112.]
Kao, K.-Y., Thomas, C. L., Spitzmueller, C., amp; Huang, Y. (2021). Being present in enhancing safet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safety behaviors, and safety climate on safety outcom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36(1), 1?15.
Ketchen, D. J., Craighead, C. W., amp; Buckley, M. R. (2008). Time bandits: How they are created, why they are tolerated,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them. Business Horizons, 51(2), 141?149.
Kim, S., Park, Y., amp; Headrick, L. (2018). Daily micro-breaks and job performance: General work engagement as a cross-level moderat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3(7), 772?786.
Kim, S., Park, Y., amp; Niu, Q. (2017). Micro-break activities at work to recover from daily work demand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1), 28?44.
Kline, R. B. (2011).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3rd ed). Guilford Press.
Li, Y., Zhang, Y., Lu, L., Zhang, J., amp; Sun, X. (2023). Laughters nurturing tears for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leader humor for leader workplace devi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88(3), 603?621.
Liu, Z. Q., Xu, Y. P., Xu, J. W., Zhou, R., amp; Long, L. R. (2023).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A self-regulatory perspectiv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5(2), 272?285.
[劉智強(qiáng), 許玉平, 許建偉, 周蓉, 龍立榮. (2023). 創(chuàng)新期望差距與團(tuán)隊(duì)突破性創(chuàng)新:自我調(diào)節(jié)理論視角. 心理學(xué)報(bào), 55(2), 272?285.]
Lorinkova, N. M., amp; Perry, S. J. (2017). When is empowerment effective? The role of leader-leader exchange in empowering leadership, cynicism, and time theft.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5), 1631?1654.
Mao, J., Quan, J., Li, Y., amp; Xiao, J. (2021). The differential implications of employee narcissism for radical versus incremental creativity: A self‐affirmation"perspectiv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2(7), 933?949.
Martin, L. E., Brock, M. E., Buckley, M. R., amp; Ketchen, D. J. (2010). Time banditry: Examining the purloining of time in organiz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 26?34.
Maruping, L. M., Venkatesh, V., Thatcher, S. M. B., amp; Patel, P. C. (2015). Folding under pressure or rising to the occasion? Perceived time pressur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temporal leade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5), 1313?1333.
Methot, J. R., Rosado-Solomon, E. H., Downes, P. E., amp; Gabriel, A. S. (2021). Office chitchat as a social ritual: The uplifting yet distracting effects of daily small talk at 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4(5), 1445?1471.
Ng, T. W. H., Shao, Y., Koopmann, J., Wang, M., Hsu, D. Y., amp; Yim, F. H. K. (2022). The effects of idea rejection on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idea generation: Intention to"remain and perceived innovation importance as moderato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3(1), 146?163.
Ni, D., Liu, C. L., amp; Zheng, X. M. (2021). The effects of employee mindfulness on spous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 engagemen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3(2), 199?214.
[倪丹, 劉琛琳, 鄭曉明. (2021). 員工正念對(duì)配偶家庭滿意度和工作投入的影響. 心理學(xué)報(bào), 53(2), 199?214.]
Preacher, K. J., amp; Selig, J. P. (2012). Advantages of Monte Carlo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6(2), 77?98.
Qin, X. N., Zhang, Z. X., amp; Yan, S. L. (2022). The influence of employees' innovation behavior on their counterproductive"behavior: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moral identity.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43(5), 86?93.
[秦許寧, 張志鑫, 閆世玲. (2022). 員工創(chuàng)新行為對(duì)反生產(chǎn)行為的影響:心理所有權(quán)和道德認(rèn)同的作用. 科研管理, 43(5), 86?93.]
Scott, S. G., amp; Bruce, R. A. (1994).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la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7(3), 580?607.
Shin, J., amp; Grant, A. M. (2021). When putting work off pays off: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and creativ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4(3), 772?798.
Smallwood, J., amp; Schooler, J. W. (2015). The science of mind wandering: Empirically navigat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1), 487?"518.
Song, Z. Y., amp; Gao, Z. H. (2020). \"Well-balanced tension and relaxation\" is powerful for innovation — A dual moderating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ch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1(4), 132?144.
[宋孜宇, 高中華. (2020). “張弛有度”方創(chuàng)新有力——教練型領(lǐng)導(dǎo)與員工創(chuàng)新行為關(guān)系的雙調(diào)節(jié)模型. 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 41(4), 132?144.]
Sonnentag, S., amp; Fritz, C. (2007). The recovery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for assessing recuperation and unwinding from work.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2(3), 204?221.
Sonnentag, S., amp; Fritz, C. (2015). Recovery from job stress: The stressor-detachment model a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S1), S72?S103.
Steffensen, D. S., McAllister, C. P., Perrewé, P. L., Wang, G., amp; Brooks, C. D. (2022). “You’ve got mail”: A daily investigation of email demands on job tens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37(2), 325?338.
Tang, H. Y., Yue, S. S., Shi, Y. W., amp; Ma, H. Y. (2019). To work better: The definition and mechanism of recovery from work.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2(5), 1186?"1193.
[唐漢瑛, 岳閃閃, 史燕偉, 馬紅宇. (2019). 為了更好地工作:工作恢復(fù)的內(nèi)涵及實(shí)現(xiàn)機(jī)制. 心理科學(xué), 42(5), 1186?1193.]
Teng, Y., Zhang, H. T., Zhao, S. Q., Peng, K. P., amp; Hu, X. M. (2024).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enhance human altruism toward robo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mind percep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2), 146?160.
[滕玥, 張昊天, 趙偲琪, 彭凱平, 胡曉檬. (2024). 多元文化經(jīng)歷提升人類對(duì)機(jī)器人的利他行為及心智知覺(jué)的中介作用. 心理學(xué)報(bào), 56(2), 146?160.]
Vahle-Hinz, T., Mauno, S., de Bloom, J., amp; Kinnunen, U. (2017). Rumination for innovation? Analysing the longitudinal"effects of work-related rumination on creativity at work and off-job recovery. Work amp; Stress, 31(4), 315?337.
van Knippenberg, D., amp; Hirst, G. (2020). A motivational lens model of person × situation interactions in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10), 1129?"1144.
Wang, T., Chen, C. H., amp; Song, Y. X. (2019). A research on the double-edge effect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2(5), 90?100+141.
[王甜, 陳春花, 宋一曉. (2019). 挑戰(zhàn)性壓力源對(duì)員工創(chuàng)新行為的“雙刃”效應(yīng)研究. 南開(kāi)管理評(píng)論, 22(5), 90?100+"141.]
Wu, W. J., Liu, Y., amp; Xie, X. X. (2012).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recovery experiences. Foreign Economics amp; Management, 34(11), 44?51.
[吳偉炯, 劉毅, 謝雪賢. (2012). 國(guó)外恢復(fù)體驗(yàn)研究述評(píng)與展望. 外國(guó)經(jīng)濟(jì)與管理, 34(11), 44?51.]
Wu, Y., amp; Wen, Z. L. (2011).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859?1867.
[吳艷, 溫忠麟. (2011). 結(jié)構(gòu)方程建模中的題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學(xué)進(jìn)展, 19(12), 1859?1867.]
Xu, C., Yao, Z., amp; Xiong, Z. (2023). The impact of work-"relate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ter hours on time thef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87(1), 185?198.
Yin, K., Zhao, J., amp; Nie, Q. (2022). How to improve team creative performance with two brushes simultaneously: Creative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oriented human resource"management practices.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4(2), 86?100.
[尹奎, 趙景, 聶琦. (2022). 如何“雙管齊下”提升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新績(jī)效——?jiǎng)?chuàng)新型領(lǐng)導(dǎo)與創(chuàng)新導(dǎo)向人力資源管理實(shí)踐. 首都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4(2), 86?100.]
Yuan, F., amp; Woodman, R. W. (2021). The multiple ways of behaving creatively in the workplace: A typology and mode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2(1), 20?33.
Zeng, H., Wei, J., amp; Liu, Y. (2024). Does it really matter if it is far away?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spatial distance on consumers’ friends circle sharing reward program: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actance experience."Nankai Business Review, 27(1), 148?159.
[曾慧, 魏靜, 劉燕. (2024). 遠(yuǎn)一點(diǎn)真的沒(méi)有關(guān)系嗎?空間距離對(duì)消費(fèi)者朋友圈分享獎(jiǎng)勵(lì)計(jì)劃的影響研究——抗拒體驗(yàn)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南開(kāi)管理評(píng)論, 27(1), 148?159.]
Zhang, J., Song, J. W., amp; Wang, Y. (2017). Mindfulness in the workplac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Foreign Economics amp; Management, 39(8), 56?70+84.
[張靜, 宋繼文, 王悅. (2017). 工作場(chǎng)所正念:研究述評(píng)與展望. 外國(guó)經(jīng)濟(jì)與管理, 39(8), 56?70+84.]
Zhang, N., Shi, Y., Tang, H., Ma, H., Zhang, L., amp; Zhang, J. (2023). Does work-related ICT use after hours (WICT) exhaust both you and your spouse? The spillover-crossover mechanism from WICT to emotional exhaustion. Current Psychology, 42(3), 1773?1788.
Zhang, W. X., amp; Wang, C. (201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Chen, X. P., amp; Shen, W (Eds.),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3rd ed., pp. 464?489).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張偉雄, 王暢. (2018). 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 見(jiàn): 陳曉萍, 沈偉"(編), 組織與管理研究的實(shí)證方法(第三版, pp. 464?489).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Zheng, X. M., amp; Ni, D. (2018). Review of mindfulnes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Management Review, 30(10), 153?168.
[鄭曉明, 倪丹. (2018). 組織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評(píng). 管理評(píng)論, 30(10), 153?168.]
Zhu, J. Q., Xu, S. Y., Zhou, J. Y., Zhang, B. N., Xu, F. F., amp; Zong, B. Q. (2020). The cross-level double-edged-sword effect of boundary-spanning"behavior on creativit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2(11), 1340?1351.
[朱金強(qiáng), 徐世勇, 周金毅, 張柏楠, 許昉昉, 宗博強(qiáng). (2020). 跨界行為對(duì)創(chuàng)造力影響的跨層次雙刃劍效應(yīng). 心理學(xué)報(bào), 52(11), 1340?1351.]
Zhu, Z., Kuykendall, L., amp; Zhang, X. (2019). The impact of within-day work breaks on daily recovery processes: An event-based pre-/post-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92(1), 191?211.
How “slacking off” sparks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scenario experiment and a survey study on curvilinear mediation of recovery experience
XU Shiyong1, YANG Chunmeng1, LI Chaoping2,3, LI Hairong1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3"The Center for Talent and Leadership,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mployees’ time theft—defined as engaging in unapproved non-work-related activities during work hours—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idden and widespread. Most prior studies have assumed that such behavior negatively impacts performance, focusing on mechanisms to reduce time theft within organizations. However, few have considered the potential positive effects of time theft o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may yield positive or negative outcomes. Drawing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the “too-much-of-a-good-thing” effect of time theft and explores how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t influences"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to identify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ime theft’s effects.
To ensur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y, we adopted a combination of experimental study (Study 1) and survey study (Study 2). In Study 1, we utilized a single-factor, three-level between-subjects design, randomly assigning 182 participants to one of three conditions. Participants first assessed their mindfulness traits and provid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y were then instructed to recall and describe a recent workplace time theft incident at one of three levels (high, medium, or low). Afterward, they completed measures of mindfulness and recovery experience"and a manipulation check. In Study 2, we used a multi-wave, multi-source design to collect data from 633 employee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ree phases, with a one-month interval between each phase. In the end, we obtained a leader-employee matched dataset with 503 observations across all three waves to test the proposed model.
The experimental data (Study 1)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medium-level time theft group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covery experience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low- and high-level time theft condition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mindfulnes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Employees with higher mindfulness experienced a stronger positive effect of time theft on recovery. In Study 2, given that the data was nested (i.e., multipl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was assessed by the same leader), we employed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and this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mindfulness. Additionally, following established methodologies, we used the “instantaneous indirect effect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indirect effects of"time theft on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recovery experience. To further assess these indirect effects, we conducted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ith 20 000 replications to gener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in R 4.2. Th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ime theft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with mindfulness strengthen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Drawing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we explored how time theft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recovery experience. We also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time theft on employee innovation, we offered a novel perspective that time theft, rather than being solely detrimental, can also provide benefits to organizations. Second, we identified the curvilinear mediation effect of recovery experience, suggesting that time theft and recovery exhibited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hich indirectly influenced innovative behavior. Finally, we highlighted both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potential costs of mindfulness as a moderator between time theft, recovery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 thus clarify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ime theft affected recovery experience.
Keywords "time theft, recovery experience, mindfulness, innovative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