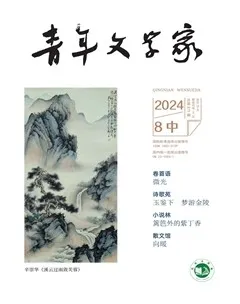南唐仕宋文人的詩學觀


南唐(937—975),是五代十國時期李昪在江南地區建立的王朝,享國三十八年,最盛時幅員三十五個州,人口眾多,地大力強。南唐三代君主對文人學士最為禮待,興科舉、建書院,文化發展尤為昌盛。開寶八年(975),宋兵攻占金陵,李煜奉表出降,江南政權正式滅亡,部分文士追隨后主前往開封新朝為官。宋初政策較為寬松,太祖對這些由南唐轉而仕宋的文人采取較為包容的態度:“群臣皆從北遷,宋詔江南故臣皆許錄用。”(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三十)經調查與統計,參考脫脫《宋史》、馬令《南唐書》、陸游《南唐書》、任爽《南唐史》等文獻記載,梳理統計出由南唐入仕的文人有周惟簡、湯悅、王克貞、徐鉉、張洎等共四十四人。根據《全宋詩》的輯錄,其中有十八位文人在仕宋之后創作了詩歌,累計四百九十二篇。這些士大夫普遍文學造詣普遍頗高,在宋初政壇受到了統治者和朝中人士的歡迎,他們的詩學觀念為當時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鮮力量,也影響了后世文人的創作。
一、“情思郁結”而作詩的緣情觀
所謂“情思郁結”,是指情感需要排解,思緒糾纏郁結于心。這種情感的郁結需要一定的抒發與表達,早在春秋時期,《毛詩序》就記載道:“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喜怒哀樂之情是推動詩作寫成的原初動力,這里“情”和“志”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因此,孔穎達在作《毛詩正義序》時,直接把“志”換成了“情”:“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這奠定了詩歌基于內心情感闡發而傳情達意的特征。陸機也闡發“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龍·物色》)的文學觀念,人的情感跟隨外界事物不斷變化,其中詩便是情感抒發和表達的載體。
自唐朝末年開始,詩歌逐步趨于日常化、通俗化,對待日常小事的感受也可以落筆成詩。南唐后主喜愛宴飲作樂,常在宮闈之內與歌舞伎以及臣子對飲當歌相娛,并用詩記錄下當時心境,相互酬唱贈答,因此文人之間形成了用詩以娛情的文化傳統。南唐文人入宋之后,身處復雜政治環境之中,新舊易主的變遷沖擊著他們的心靈,在情感上比其他詩人有著更為跌宕的波瀾,更使得詩的緣情功能達到了頂峰,情感基調也由閑適散漫轉向為沉郁深廣。因此,他們多因“情思郁結”而作詩,吟詠性情、感傷自身遭際。徐鉉作為南唐入宋文人的中心人物,他在《蕭庶子詩序》中曾說:“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郁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為詩。”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是沿襲著前人的緣情觀而出發,認為詩是人情感通達的結果,能夠展現出人自身的靈性之處,將“不可以言盡”之物表達出來,情動而發言為詩,詩即為情思的郁結。
從唐末、五代到宋初,整個社會長期處于混亂不堪的無序狀態,精神文化較為貧瘠。在朝文人多數以白居易為典范,繼承白詩中的隨遇而安與平和淺淡。宋初帝王對文化頗為重視,鼓勵文人抒發自身際遇寫詩獻詩,使得朝野之間形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崇文風氣。李虛己也是南唐入宋文人之一,《續資治通鑒·宋紀》記載:中丞李虛己“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余,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帝悅,批紙尾曰:‘朕得良二千石矣。’”這是文人緣情而作,抒發自身遭際的敘感詩,寄予的不只是個人苦悶,還不乏對生活瑣事,即人情、事情的感懷。吳淑仕南唐時官至內史,《詩話總龜》中記載,其入宋之后,同朝為官的朱昂懇求歸家頤養天年時,圣上在錫宴玉津園中,傳旨令賦詩為送,他贈行詩云:“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可見,吳淑的詩情受到環境和人事變遷的影響,在南唐與宋朝交替的歷史背景中,通過詩歌抒發了對往昔歲月的懷念與對未來的憧憬。詩歌中不僅僅是對個人遭遇的傾訴,更是對整個時代變遷的反思與記錄。在宋初詩壇,這種用詩歌傳情表意的緣情觀十分盛行,這種對情的探尋為宋代的詩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通政教,察風俗”的詩用說
南唐文化氣息濃郁,統治者較為注重對文人的培養,形成了以“廬山—西山—仰山”為脈絡的文學中心,吸引周邊文士來到這里筑廬治學,發揚了尚儒傳統。宋朝伊始,天下初定,新朝政權需要文化建設,太祖、太宗皆崇文,力主發揮文學、詩學的功能性作用。宋初開明的文化氛圍,使南唐入宋的文人也受到了感染和熏陶,在詩歌理論上注重反映社會現實,強調文學的教化的功用。
吳淑認為詩能夠“故謂之為述。又以為能畢舉萬物之形,亦謂之為畢”(《筆賦》),將萬物的形狀描繪書寫,輯錄事物以傳情。但其實筆是創作的媒介,作品是創作的結果,這其實也是從創作的源頭的角度來談,緊扣“緣事而發”的緣情觀。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評價道:“逸少驚入木之七分,仲尼止獲麟之一句。”正是這種追求內心感受的細膩表達和對情感的深切感受,使得南唐入宋文人的詩作格外動人。
南唐入宋文人普遍秉持著經世致用的思想,徐鉉說“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成氏詩集序》),這種用途不僅僅停留在淺顯的表意傳情層面,而是弘揚儒家傳統禮教,對世人起到教化作用。詩是明君圣主“通政教,察風俗”的途徑,能夠“物情上達,王澤下流”(《成氏詩集序》),詩歌是時代精神與個人情感的深度結合體,詩人將物與情感相契合,以物寄情,以詩言志。同一事物、同一觀賞者,在不同環境下也會產生不同的心情;或者曾經看到一樣事物,在觀賞者經歷了一定的生活磨難之后,心境上產生的改變,都是詩人創作的靈感來源。這種重視和強調事物的感召作用,將心中感情與外物相契合,也是詩歌實用性的表現。他的詩學觀念秉承著對現實清醒的批判態度,也特別強調詩歌的政教作用。他希望詩歌可以“掩鄴中之舊制,流樂府之新聲”,這樣能夠“厚君臣之情,敦風化之本”,從而達到“夫其貞退之節,樂善之風,實教義之所臻,亦詠歌之盛觀也”(《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這種重視和強調事物的感召作用,將心中感情與外物相契合,是詩歌實用性的表現,并且在他的詩學觀念之中,詩歌已經成為將民情上傳下達的紐帶和工具,立足于社會的狀況進行創作。
另一方面,受到傳統思想影響,加之自身政治處境的尷尬,南唐入宋文人們很難在朝野中真正得到信任和尊重,因此常懷抱著功利性的態度,在創作中不乏很多對統治者的逢迎之作,為自己的前程謀一份安穩。《宋朝事實類苑》記載張洎“在江南已居要近,曾將命入貢,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以悅其主”,因此歌功頌德,贊頌賢臣明君的詩作在南唐入宋的詩人中很常見,使文學反映和批判現實之弊的功能有所減弱,但不失為一種文人自保的手段。除了自下而上的主動作詩之外,宋初君主也經常要求文人獻詩。太宗親征北虜,還朝之時在途中作御制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云飛”之句,遂令南唐入宋的臣子何蒙到鑾輿之內,作《賦得御制句朔野陣云飛》詩,有“塞日穿痕斷,邊云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沈護御衣”之句。詩中描繪了塞外戰場惡劣的生存環境,展現將士保衛邊疆的不易和艱辛。何蒙的回對更是呼應和展現了大宋江山的氣魄,歌頌賢君圣主。太宗聽聞大加贊賞,對他進行了嘉獎。可見,此時詩的政治教化和社會功用性極度加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文人晉升的一種工具。徐鉉提出的“觀風之政闕,遒人之職廢”(《蕭庶子詩序》),也是這個道理,詩不只是用來吟詠的閑碎篇章,還是記錄政通人和,展現安邦保民一派和樂景象的媒介。詩發端于“精誠中感,靡由于外獎”,加之創作技巧的闡發,“觀其人,察其俗”(《蕭庶子詩序》),遵循儒家教化原則,同時站在鮮明的政治立場上來反映社會生活,甚至在某種層面上,將詩的功用提高到了與君主治理國家相同類似的作用。“通物情而順時令者”,是帝王應該做的事情;“感惠澤而發頌聲者”(徐鉉《北苑侍宴詩序》),是臣子應該踐行的準則。奉詔寫詩并不是對于詩本來功能的背棄,而是在不同的社會需求之下的順應時勢的變通之法。
三、“自然成文,音韻和諧”的詩美標準
南唐文士眾多,能作詩者足有一百七十多人,其中四十多人留有詩文集存世,在五代詩壇中,令其他諸國難以望其項背。南唐詩歌創作總體上呈現出清麗自然的詩美標準。方回《送羅壽可詩序》云:“宋刬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說宋初的詩壇已經摒棄了五代詩壇的舊習氣,將詩分為三個派別。其實宋初詩壇效法白居易作詩,而演變出宗白的審美范式,很大程度就是受到這批由南唐入宋詩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自然成文的天賦才情的贊賞、清詞麗句的褒揚,以及對音韻自然作詩標準的推崇。
徐鉉主張嘉言麗句都應該是“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成氏詩集序》),強調自然成詩的狀態和詩人自身的天賦才情,認為詩歌要有感而發,抓住瞬間靈感的迸發,不能矯揉造作,正是這種“精誠”和“天成”所造就的直抒胸臆、率意而為,使得詩人創作形成了自然不拘一格的風格。宋代詩論名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一就引梅圣俞《隱居詩話》的說法,極力稱賞徐鉉的“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之句,認為這句話“尤閑遠也”。井泉、砧杵本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之物,詩人并未刻意雕琢,而是保留了自然的狀態記錄下來。這種描繪自己閑適生活,風格較為清雅的詩作在張洎身上也有體現。張洎,五代南唐時進士,后主提拔他為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參預機密,恩寵很盛。歸宋之后,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與寇準同列。作為南唐入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詩歌也以自然和清雅著稱,《郡齋讀書志》贊揚他:“洎風神灑落,文辭清麗。”張洎的詩“清妙而句美麗奇絕,蓋得于意表,迨非常情所及”(陸心源《唐文拾遺》),推崇并奉行白居易詩歌中的淺易風格,除此之外,基于自身的政治遭際,對這種描繪閑適與自然生活的題材十分認可。后世的評論家很贊賞南唐詩人創作中自然成文的風格。鄭文寶仕南唐至校書郎,入宋登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第,除修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州錄事參軍事,在位期間創作了十余首詩,多為清麗之作。這種對身邊事物的隨性書寫,絲毫沒有滯澀之感,使詩歌呈現出自然平易的風格,這正是南唐入宋詩人所推崇的。
南唐入宋詩人在創作中,常常把音韻和諧當作詩美的重要標準。徐鉉在《文獻太子詩集序》中先是肯定了天賦才情和自然作詩的作用,“夫機神肇于天性,感發由于自然”,但除了要抓住一閃而過的靈感之外,還要注重音韻方面的統一和諧,“被之管弦,故音韻不可不和。形于蹈厲,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言之有物的基礎之上,將音韻諧美融入詩歌創作中,這樣使得詩歌兼具文采和韻律。這種對音律和格律的注重還體現在李虛己的創作中,《困學紀聞》記載李虛己曾經和曾致堯倡酬,曾致堯對他說:“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李虛己剛開始沒有領悟,后來吸納了沈約所說“前有浮聲,后須切響”(《宋史》)的音韻觀念,而后更加精于格律,進一步踐行了音韻和諧的詩美標準。但這種雕琢用詞和韻律的寫作手法,在某種程度上過度追求也會陷入空乏浮麗的誤區。李虛己在《建茶呈使君學士》中寫道:“試將梁苑雪,煎勛建溪云。”用梁蒼山的雪水來煎茶,以勛建溪的云霧茶為比較。這句話音韻諧美,一句之內舉兩個地名的例子,雖然對仗工整,但地名的堆疊卻背離了自然成文的詩美標準,而趨向于西昆體的華麗。方回《瀛奎律髓》評價這兩句為:“昆體也,凡昆體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錦繡等以實之。”由此可見,南唐仕宋文人大多在作詩時提倡音韻諧美、韻律和諧,這種文學樣式在宋初詩壇別具一格,為后世宋詩的蓬勃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