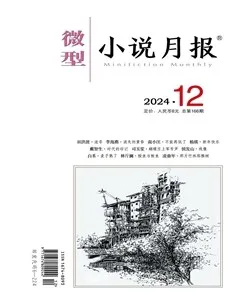將軍街
五月,是小街最美的時節。
小街不大,兩邊站滿了筆直挺拔的槐樹。等到中旬,槐花綻放,香氣繚繞,一串串密密匝匝的像小燈籠一樣,懸掛在蔥翠的嫩葉間。
我家離小街不遠,因為剛搬來,人生地不熟。我則因前一年高考失利,成了無業游民。我媽讓我好好想,以后能干啥。我前后思忖,把心里想說的又咽了回去,家里實在太困難。我說,我要去打工掙錢。我媽說也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于是,惆悵的夜晚,我徜徉于小街,將心事和不舍,反復萃取,嗅著沁人的花香,如酒醉一般,也撫平我白日打工的辛酸。
一沒技術,二沒經驗,我只能在飯店洗盤子。盤子碗一摞摞,油漬麻花,被稀里嘩啦地堆積在水槽里,像一座雪山,高不可攀,叫人眼暈。家里洗碗的活,都是我媽干的,她從來不讓我伸手,說我的手是用來拿筆的,這是粗人干的。每每想起我就心酸,轉而又下定決心,大不了我就學廚師。老板卻說,你先把盤子刷明白再講。可接連幾天我都打碎了盤子。老板訓斥我,最簡單的活都干不好,還能學廚師?!因為手上有了傷口,我媽說,不行就別干了,傷口沾水容易感染。我沒吭聲,咬著牙還是去了。稀里嘩啦的又一天,挨到下班,我就在小街的樹下看花,聞香。小街熙熙攘攘,落日下,人們的臉上都溢滿幸福安逸,似乎只剩我,懷著淺淺又悠長的心事。
說起來已經好長時間了,打小街泛起綠波,就有一個老人,總在街口。他有時坐著,有時躺在一把椅子上。花開以后,他總是掐一把槐花聞,時不時還放進嘴里嚼幾下。我見他很怪,偶爾瞅他幾眼,他會沖我笑笑。時間一久,我卻發覺他沒啥異常。
我手上的口子又多了幾處后,我媽勒令我別干了。我不同意,她就把我的傷口包扎得很夸張。其實每次一來到街口,我就會把包好的一層厚白紗布給扯下來,一個打工的,哪那么矯情。
那天下班,我又來到街口。那老人居然跟我說了話:“小子,傷好啦?細皮嫩肉的,那都不算啥。”傷的確好了,因為不沾水,盤子碎得太多,老板不讓我刷了,說我再刷下去,都沒東西給客人盛飯了。他讓我干勤雜工,給別人打下手,遞個盤子碗,扒個蔥姜蒜,接送米面、蔬菜肉蛋的力氣活。跟刷盤子比,這些更沒啥技術含量了。我暗嘲自己,我還能干啥?
老人說完,我臉上一紅。似乎我的糗事和心里的不快都被他窺個干凈。我笑笑,拔腿想走。他說:“陪爺爺坐會兒吧。”
我詫異,但還是坐了下來。
“我觀察你有陣子了,小伙子。你年齡不大,咋不上學?我在這疙瘩住半輩子了,這條小街,最好看的就數這會兒。你看兩排槐樹筆直筆直的,英俊威武,整裝待命,齊刷刷的就像要出征的戰士。”
我又笑了笑,沒言語。我不知道咋接他的話茬。
他又接著說:“這槐花多俊,吃起來也甜甜的。”老人閉上眼,我以為他要睡覺了,沒承想他又睜開眼。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我沒說好,也沒說不好。
“戰場上,有個小兵蛋子,因為太餓,他就忘了部隊的紀律。那也是槐花開的季節,滿樹的槐花,透著香甜。小兵蛋子想著母親做的槐花餅,就咽了幾次口水,終究沒忍住,就偷著去摘幾串槐花,電光石火間,鬼子的機槍響了。團長一個大步就飛了過來,千鈞一發之際把小兵蛋子撲倒在身下。小兵蛋子知道犯了錯,違反了紀律,可身下如雪的槐花,已經沁滿了鮮紅……”
大體是這樣,老人講完故事,眼睛有些濕潤。
我揪了幾朵花,嚼了嚼,的確很香甜。他說花期馬上就過,再開就得等明年,可明年的事,誰也說不好。
“那次錯誤給小兵蛋子的打擊很大,他始終記得團長臨終前說的——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犯錯誤,咱不怕。”
我說:“團長要是沒犧牲,一準能當將軍。”
有風吹來,帶過一片花香。老人看向落日,落日透過窸窸窣窣的槐樹叢,像是在竊竊私語。
臨了老人說:“不管咋樣,路在腳下,你得好好走,小街很小,也能通向遠方。”
老人的故事,對我觸動很大。我知道他就是那個小兵蛋子,也是一個老兵,立過功,受過獎。他還上過朝鮮戰場,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那晚一回家,我就跟我媽說:“我要復讀,明年再高考。”我也鼓起勇氣,將那段不成熟的早戀撕個粉碎。
我媽笑了。
如今我有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每到槐花開,我都要回小街。小街就叫將軍街,有著輝煌的歷史,是當初那個老兵講給我的。他還資助我一筆復讀的費用,讓我重新開始。
選自《小說月刊》
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