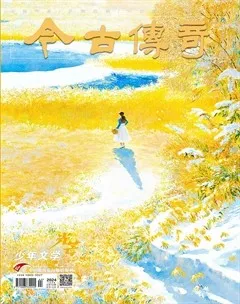玫瑰與青銅像
2024-12-29 00:00:00劉欣揚
今古傳奇·少年文學
2024年11期
“今天你什么都不是,
只是我誦讀你鏗鏘詩句時的聲音。
我懇求我的神或者時間的總和,
讓我的日子無愧于遺忘,
我的名字像尤利西斯一樣默默無聞,
但是在宜于回憶的夜晚,
或者在人們的早晨,
某些詩句得以流傳。”
——《致一位撒克遜詩人》
我必須得說,博爾赫斯的詩集《另一個,同一個》是難以評價的。它所展現的形態正如《致一位撒克遜詩人》,不是一個故事,不是某種思想,不是某種確定且擁有中心的事物,而是一首又一首出于瞬息的激情的詩,是零散又跳脫的詞句的結合,是混雜在沙與沫中的珍珠和鉆石,能將其撿起多少要依靠運氣。
然而在這份稍微有些令人迷茫的不確定之中,又的確擁有著什么永恒的東西——像破碎的棱鏡折射出的玫瑰園,它在光線之下呈現出的絢麗轉瞬即逝,但這也意味著在某一個地方的確有一座玫瑰園,園中也許就有一座永恒的青銅像。
使用這樣的比喻,是因為博爾赫斯的詩句總是讓我無端地想到各種各樣的玫瑰:“朱紅、淡黃或純白的玫瑰/神奇地留下你古老的往昔/在這首詩里煥發出光彩/看不見的玫瑰金黃、殷紅、象牙白/或者像你手里那朵一樣昏暗。”(《玫瑰與彌爾頓》)
他使用的詞句總是無與倫比地簡練又難以捉摸,形象又無比抽象,像開得太快太美的玫瑰一樣,帶著一閃而過的靈感與啟示;像昏暗的閣樓里金色的六弦琴,用琴弦一次簡短的震顫讓滿屋的灰塵都為之嘆息。誠如此書的序言所說,“語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詩歌要回歸那古老的魔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