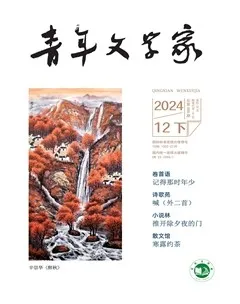譯文學視角下看詩歌翻譯的特殊性問題

譯文學,是繼翻譯學、譯介學后衍生的第三種當代中國翻譯研究模式。翻譯學側重于語言轉譯的忠實性,媒介學側重于文化交流的媒介性,而譯文學兼顧譯文的忠實性與審美性。詩歌是一種獨特的文體樣式,因其情感飽滿、想象力豐富、審美內涵深厚,在文學翻譯中的難度尤其突出。從譯文學富于審美觀照的獨特視角,探討詩歌翻譯的特殊性問題,不僅有利于深入探索詩歌翻譯的藝術,而且會為翻譯實踐提供新的理論指導。
一、新型的譯文學
王向遠在《譯文學—翻譯研究新范型》中提出“譯文學”這一概念,旨在回歸具體的翻譯文本,以譯文為中心向外輻射至語言學、文學理論、美學等多個層面。譯文學有兩個內涵:從文學類型的角度看,譯文學是翻譯文學的略寫,與以外語寫就的外國文學、以母語寫就的本土文學相對;從學科概念的角度看,譯文學從比較文學的立場出發,對具體的翻譯文本進行細致分析。譯介學側重翻譯的媒介性,重視翻譯文學的接受問題,把翻譯作為跨文化的行為和現象加以理解,對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伯特·埃斯卡皮的“創造性叛逆”持開放與樂觀的態度。譯文學不同于譯介學,是以翻譯文學為本體,認為譯文本身具有獨立的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對“創造性叛逆”持審慎的態度,主張翻譯的叛逆有積極的“創造性叛逆”與消極的“破壞性叛逆”。
譯文學這一學科涉及譯文生成、譯文評價兩個方面。在譯文的生成問題上,譯文學正面回應長期以來困擾學界“可譯與不可譯”的爭論,指出翻譯本身包括“翻”與“譯”這兩種不同的語言轉換行為。“譯”主要指一種平行式的傳達,在古代漢語中“譯”與“傳”是通用的,《說文解字》言:“傳,遽也。”而當兩種語言出現較大差別且難以平行傳達時,就需要較大幅度的“翻”,《說文解字》言:“翻,飛也。”引入“翻”這一概念,就可以很好地解決不可譯者提出的音聲不可譯、文體不可譯、風格不可譯等問題。譯者可以在認真考量語言忠實與文學審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從原語言向目標語的轉換過程中進行翻轉飛躍。小幅度的“譯”與大幅度的“翻”是互為補充的關系,難以用前者傳達譯本精髓時,就可以用后者來替代,而用前者就可以很好地表達原文本的內涵時,就不必再去大幅度地翻轉。譯文學認為在翻譯實踐中有三種具體方法:平行式的迻譯、解釋性的釋譯、創造性的創譯。迻譯屬于平移式的“譯”,釋譯與創譯屬于立體翻轉式的“翻”。譯文學模式強調譯本的自性,它是一種特殊的獨立的文學作品。“翻”與“譯”的有機結合形成具有獨特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譯文,從實際效果看譯文會不可避免地減損或增添原文的光輝。對于如何調和原文本的客觀實在性和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的問題,譯文學提出譯者可通過把握和控制“翻譯度”,即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傳達以及轉換過程中的程度或幅度,以期兼顧譯文的忠實特性與審美特性。如果翻譯度不足則難以傳達原文的內涵,而翻譯過度又會背離忠實性的原則,譯者應努力尋找一條循序漸進的中間道路。
站在比較文化立場上的譯介學和文化翻譯,更加關注翻譯在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效果,對于譯文的評價側重于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創造性誤解。羅伯特·埃斯卡皮在《文學社會學》中認為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因為譯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忠實于原文,在翻譯的過程中總會對原文有意無意地背離、丟棄、叛逆,因此譯文是譯者二次創造的產物。譯介學普遍認為翻譯的“創造性的叛逆”在文化的溝通與交流中功不可沒,譯者基于接受群體的需求對原文進行扭曲、變形等叛逆的行為,將有利于翻譯文學的傳播與文化的相互交流。對于“創造性叛逆”的鼓勵和弘揚,引起“忠實派”與“叛逆派”的爭論。“忠實派”認為“忠實”與“叛逆”是截然對立的,譯者應堅守譯文忠實于原文。“叛逆派”認為既然絕對的“忠實”并不存在,那么就應該對譯者的主觀能動發揮持開放的態度,因為“叛逆”會在跨文化的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譯文學以譯文為本體,首要關注的是譯文的生成過程本身,而非流通傳播的環節。譯文學主張譯文的“忠實”與“叛逆”應互為補充而非互相對抗。百分之百的“忠實”難以達到并不意味著要放棄對譯文忠實性的考量,而在特定的情況下又應該允許譯者進行“創造性叛逆”,如上文所述需要兩種語言大幅度翻轉的情況。譯文學提醒我們要謹慎對待“叛逆”,不僅有很好地實現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創造性叛逆”,還會有破壞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破壞性叛逆”。我們應辯證看待“忠實”與“叛逆”的關聯,“很多情況下與其說是‘叛逆’,不如說是翻譯家為求‘忠實’而采取的特殊的、非常規的、個性化的表現”(王向遠《譯文學—翻譯研究新范型》)。總而言之,“忠實”是主要的、基礎的、主流的,而“叛逆”是為實現更高的“忠實”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其為次要的、附屬的、支流的。
二、詩歌翻譯的特殊問題
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基本上都意識到翻譯的復雜與困難,尤其是對詩歌的翻譯難度有著更為清晰而深刻的認知。很多持“不可譯論”的學者尤其強調詩歌的“不可譯”,究其原因在于詩歌翻譯極具特殊性。下面列舉較具典型意義的詩歌翻譯特殊問題:
(一)語音問題
許淵沖在《文學與翻譯》中提出翻譯應該做到音美、形美、意美。音美是詩歌翻譯的重要一環,因為音聲會涉及詩歌的韻律、節奏等問題。朱光潛認為翻譯過程中聲音節奏的損失或消弭將會損害文學的韻味,詩歌的翻譯更甚。例如,漢語以韻聲為結尾,因此天然就有和諧、響亮的特質,簡單的音節結構促使漢語詩歌容易形成整齊劃一的效果。四聲使詩歌逐漸發展出平仄的要求,由此創造出獨特的韻律之美。可以說,漢語詩歌的魅力,首先體現在聲音的和諧生動上。西語多復音,無四聲,大多不以韻聲為結尾。因而從漢語向西語進行詩歌翻譯時,難以平行傳達漢語特有的“音聲”之美。
(二)形式問題
詩歌的形式問題涉及詩體、修辭、意象等層面。最為明顯的是詩歌不同的體式問題,每個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都形成了獨特的詩體。中國發展出對仗工整的格律詩,日本發展出短小精悍的和歌,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創制出西洋韻式的十四行詩。帶有鮮明民族特色及語言風格的詩歌體式,轉換為其他民族語言具有相當大的難度,因此許多翻譯家在詩體上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比如,豐子愷與林文月對和歌的翻譯,前者仿照中國古典詩歌采取七言二句和五言四句,后者采取三行的楚辭體翻譯。特殊語言修辭在詩歌形式上也比較突出,如詩歌中的隱喻和換喻問題。俄國形式主義美學家羅曼·雅柯布森在《隱喻和換喻的兩極》中,認為隱喻和換喻不僅體現在語義,而且體現在主題上,前一主題是通過相似性關系或毗連性關系引出下一個主題。詩句的格律對偶和韻腳音響的對應關系,也會關涉語義的相似性問題,因此詩歌翻譯也要注重特殊的語言修辭,如果只是單純的字詞對照式翻譯很容易就會破壞詩歌的“形美”。
(三)意象問題
“不可譯論”的主張者強調“不可知論”,因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存在物質、精神文明深刻的差異,即讀者會難以理解翻譯中不同文化的新概念、新觀念。在翻譯的過程中,物質文化層面的差異相對而言容易突破,但是精神文化方面卻難以逾越,尤其是不同文化系統中的特殊意象。意象不僅凝聚著作家的思想情感,而且蘊含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意義。意象作為文化符號的深層表征,是歷史積淀和傳統延續的結果,能夠喚起特定群體的情感共鳴。意象涉及象征、隱喻、換喻等特殊手法的運用。《天凈沙·秋思》中前三句話的九個意象,很鮮明地存在組合與毗連的換喻手法,許淵沖的英譯將其中未直露的聯系補充出來,轉譯為中文是:“傍晚的烏鴉在纏繞著腐爛藤蔓的樹上飛翔,在小屋附近的小橋下小溪流過,古老的道路上行駛著一匹瘦馬。”雖然許淵沖的翻譯非常明確,也注重詩歌的英文音律,但是換喻的置換會沖淡意象的突出性和曲的韻味,意象的翻譯還需譯者多方面的考量斟酌。
(四)風格問題
如果將詩歌創作比喻為高樓建筑,音聲、文體詩型、語言修辭是建筑材料,而作家風格、文學味道則是整體層面予人的感受。詩歌風格體現為詩人的個體表達和藝術探索,創新的形式、深度的內容、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都會催生出獨特的詩歌風格。周煦良在《翻譯三論》中多次強調原文的風格是無法轉譯的,翻譯家是無法通過模仿來譯出原作的風格的。高健在《翻譯中的風格問題》中批駁了兩個觀點:其一是譯者如果緊跟原作的內容與形式,那么原作的風格就會突破語言文化的隔閡而體現于譯文中;其二是由于風格遵循一般的寫作規律,所以能夠在不同的語言中找到相對應的表達形式。高健主張譯者一方面要在內容和形式上仿效原作,另一方面要把握原作精微的氣質、神韻,如果二者能夠得到完美處理,風格的“奇跡”才會出現。總體而言,風格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帶有作者強烈的個人色彩,囊括語音、形式、意象等方面,因此詩歌的風格問題在翻譯中尤其突出。
三、譯文學視角下詩歌翻譯的特殊性問題
大多數人對于翻譯可能會有這樣一個認知,那就是譯作無法同原作相提并論。東晉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形容翻譯就若嚼飯喂人。這樣的看法主要還是以原作為中心,將原作過分神圣化。譯文學主張譯文本身就具有獨立的文學價值和獨特的審美價值,經過譯者轉移生成的譯文是可以再現甚至超越原作之美的,張揚譯者的主導性和創造性。譯文學對于詩歌翻譯的特殊性問題有獨到的見解。
首先,是詩歌翻譯最基礎的語音問題,也即“音聲”難以翻譯的問題。要在譯作中完全保留原有的節奏和韻律是不可行的,只是個別字詞的“音譯”還可以。譯文學厘清“翻”與“譯”的概念,指出前者翻譯度較大的翻轉,后者是翻譯度較小的平行傳譯。傳統“不可譯論”實際上是強調平移式的“譯”無法實現,而非側重譯者能動性和創造力的翻轉式的“翻”。“翻”對于譯者自身的技術和審美都是很大的考驗,如果能夠翻譯度適宜,恰切精妙地再現原文之美,雖與原文存在少許的出入,也是積極意義上的“創造性叛逆”,否則便會是“破壞性叛逆”。
對于詩歌的體式,譯文學主張保留原有詩體的特征并進行合理化的改造。比如,對于和歌這一體式,就要注重其特有的“五七五五七”的歌體。無論是豐子愷的五言對仗式、七言對仗式翻譯,還是林文月的楚辭體翻譯,既容易造成和歌是漢詩的變體這樣的誤解,也會破壞和歌不對稱式的美感。王向遠、郭爾雅合譯的《古今和歌集》以翻譯度的理論為指導,采取“五七調”的翻譯,同時考慮到和歌的內容容量較小,所以將日語五句“五七調”的格式翻譯為漢語三句“五七調”的譯案,以此更準確地傳達歌意。《古今和歌集》的譯案給翻譯實踐以啟發,詩歌的翻譯可以結合“翻譯度”的理論靈活又不失原則地處理詩歌體式的問題,以最大限度保留詩體,傳達詩意。
對于意象的問題,則需要根據不同的語言體系進行考量。比如,漢語和日語在文化背景和語言表達上有諸多相通之處,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意象的直接移植不會過分損失原有的文化內涵和語言色彩。但是在漢語和西語的翻譯過程中意象的處理將會極其棘手,因為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比如,杜甫《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中“落木”這一意象的處理就非常復雜。“落木”相對于“落葉”,強調的是樹木整體的凋零,著重營造秋季凄涼肅殺的氛圍。漢語的“落木”在英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匯,許淵沖在翻譯中沒有執著于意象,而是注重整體的音韻、對仗和意涵,“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許淵沖譯唐詩三百首》)。雖然許淵沖沒有嚴格譯出“落木”的意象,但是整體的意境把握得非常精到,可見“翻”的妙處。
譯文學也主張用“翻”來處理詩歌翻譯的風格問題,譯者可以通過對語體的把握來確保詩歌的風格,還可以考量翻譯度適當突破原有的音韻節奏和語法結構。當然,這種突破也要注意翻譯度的問題。許淵沖的英譯考量中國傳統詩風,采取正式的文學性語體;《古今和歌集》考量和歌優美的歌風,采取典雅漢語語體。從譯文學的角度看,二者都是對于翻譯度的良好把握。在譯文學視角下,詩歌的翻譯不應是簡單的重塑而是美感的解放,要通過譯者的創造將被固定的詞語的美感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