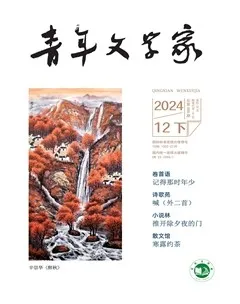活在月光下

牙牙學語時,我會背的第一句詩就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明月”這個詞從那時起,就亮晶晶地、不由分說地印在吾心。
上小學時,這個白白的、圓圓的小點無數次出現在吟哦之中,“海上生明月”“明月幾時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在內心朦朧搖曳。
上初中,我在某個午夜輾轉難眠,只好掌燈讀書,隨手一翻,就看見唐寅的《美人對月》:“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青天明月知。”當初也許在畫堂南畔,刬襪輕溜,來如春夢,去似朝云。而此番他一去不返,一懷愁緒該如何訴說呢?朱唇一啟便要越禮,那只好讓明月來解相思之意。此句如皓月清輝般灑在心上,讓我頓悟到,月亮所寄托的就是—世間一切藏不住、剪不斷、理不清、說不出、道不明的情意。
胸中塊壘,唯明月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游子的鄉情太濃,太暗,只有家鄉的明月可以填補心中的黑洞。“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太白化孤獨為狂歡,以自然為莫逆,引造物為知己。如水的月光就是這樣溫柔而包容,在茫茫黑夜中開了一個小小的口,讓一顆顆苦悶的心靈得以聽見自我肆意的回聲。
當然,月下也不全是自我的呢喃,也有人驅遣美麗的想象。李商隱在月夜宴飲,與意中人隔座送鉤,分曹射覆。或許,是一首琴曲,一個眼神,兩個寂寞的靈魂便相互懂得,愿攜手攬腕,比翼雙飛。他大概想象著,二人并肩坐在碧城玉欄前,共賞玉輪,閑話燭光……但在日光出現時,月下的狂想注定消散。太陽升起,鼓聲陣陣,馬蹄嘶鳴,催他策馬蘭臺。只見,塵煙四起,青袍翻飛,二人從此天涯陌路。在十年來日復一日的夢中,在夜夜相似卻又物是人非的月光中,李義山與女子那息息相通的心,早已被埋藏于昨日的星辰、昨夜的微風中。
如果李義山是在月下拾取回憶,那么納蘭性德就是用一縷細細的月光支撐著沉重的人生。“銜恨愿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納蘭性德熟讀佛經,參悟生死。但他愿意相信,相信盧氏就是懸在天上,化作了一顆“暫滿還虧”的淚眼,與他隔著河漢,脈脈不得語。與其說他在逃避陰陽兩隔的絕望,倒不如說他在永恒的月光中拽出了一絲希望。只要他的生命不滅,天上的明月不老,就沒有什么能阻礙他與亡妻的重逢。
有西方學者說,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一直占據中國的主流。這是因為中國人活得太現實,總想著扶搖而上,金榜題名。他看見的是活在日光下的詩人—被厚厚的朝服所包裹,裹成一個個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唱道:“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這些人的確活得現實,卻并不真實。
但還有一類詩人是晝伏夜出的,只活在月光之下。神奇的月光替他們融化了功利、禮俗、邏輯,甚至融化了現實。他們坐在書桌前、山野、清風中,讓一輪金黃燦爛的明月從百孔千瘡的心中一次次升起、高懸,再鋪平雪白的紙,蘸上真性情的黑墨,寫下藏不住、剪不斷、理不清、說不出、道不明的千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