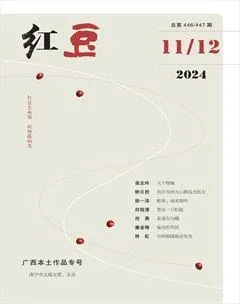隱秘的潛伏
漢朝建立后,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區(qū))劉家先祖就開始記錄族譜。劉氏家族為躲避天災(zāi)人禍等,散落到各地,其中一支輾轉(zhuǎn)來到白州(今廣西博白縣)。在白州生活安定后,劉家開始感嘆于往日榮光,于是研修風水學,并以此為生,報應(yīng)一說也開始在族中流傳。我的太祖父出生了,我的祖父出生了,我的父親也出生了,可惜的是,祖父卻在不惑之年就飄零離去。祖父患病期間曾輾轉(zhuǎn)各大醫(yī)院,各種中藥、西藥如同粥飯一樣成為日常,但遺傳病的存在未曾揭秘,也未曾被消弭。特別是祖父的四個兒女均長大成人,遺傳病的存在更隱秘。
一
生活如水般流淌過我的人生,發(fā)出叮咚作響的悅耳鈴聲。不幸就像河流突然改道,平地突遇懸崖。平靜溫柔的溪水,沖過險灘,化作瀑布,兇猛地沖擊我。
我曾有過長達一個月的咳嗽,我決定去醫(yī)院檢查。在醫(yī)院,當我發(fā)現(xiàn)抽血的管數(shù)多達十二管時,我拍照發(fā)給朋友看,哼哼唧唧地表示晚上要吃安慰飯。檢查結(jié)果下午出來了,“肺癌兩項檢測”“腫瘤標志物”的所有數(shù)值均不在參考值內(nèi),CT檢查的診斷意見更是使我無法接受。我開始發(fā)慌,急急忙忙回到醫(yī)院復診。
醫(yī)生對我充滿了同情,安慰我說:“積極治療還是能延長存活期的。”隨后又忍不住說道,“你年紀輕輕竟然就得這種病。”
晚上,我避開丈夫,開始上網(wǎng)搜索我這種情況的存活期,搜索出來的結(jié)果五花八門。篩選有用的信息后,“治不好了”“活不長了”,鮮明地宣告了我的處境。
第二天,我掛專科醫(yī)生號,重新做了檢查,包括驗血、螺旋CT掃描、MRI檢查。沒有意外,這些檢查甚至進一步確診和佐證了“我身體不健康”的事實。
是的,身體不健康。身體不健康的事實一瞬間就侵襲了我的內(nèi)心。但我仍抱有渺茫的希望。我以出差的借口,對單位和家人兩頭瞞,到南寧的醫(yī)院檢查。
醫(yī)生建議我進行具體的病因查找后對癥治療。胃鏡、肝穿刺等檢查手術(shù)都需要親人在旁簽字陪護。
瞞不下去了。丈夫和母親、姐姐、弟弟們都來到了醫(yī)院。
一個星期的折騰后,終于找出了病因。這讓我更加難以接受。原來,從父親的精子和母親卵子結(jié)合的那一刻我就注定了不健康。只是肝首先出了問題,將來我的腦袋也會出問題,直至我變得不是我,最后只剩一具軀殼茍延殘喘。這具軀殼在經(jīng)歷過所有的不可控后才會走向死亡。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可以說,檢查結(jié)果出來以后,我瞬間就變成了一個天生殘缺的人、不健全的人,隨時有徹底破碎的風險,像鏡子不經(jīng)意墜落了,難以再圓滿。
以前讀西漢賈誼的《"""鳥賦》,我跟隨著賈誼,對生命展現(xiàn)出灑脫的超凡理解,甚至在課堂上和學生侃侃而談。如今,一切都離我遠去。重讀到“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這一句時,我心中悲哀難忍,唯余“人與萬物在這世上就如放在一只大爐子中被熬煉”的哀苦。
我開始選擇放棄一些從前自己很在意的東西,減負出行,企圖獲得生命的質(zhì)量和深度。
我背上背包,第一站是桂林。
起初我跟著旅游團。匆匆看山,急急看水,如同我走馬觀花的前半生一樣,品不出任何韻味。于是我拋棄了旅游團。我到老城區(qū)去吃桂林米粉。從前我喜歡直接把湯倒進米粉里一起吃,這一次我坐在狹窄、熱鬧的店里,認真聽取桂林人關(guān)于吃桂林米粉的訣竅。先吃一口原汁原味的米粉,然后把米粉與調(diào)料、配菜徹底混雜在一起,吃三口,細細地吃,慢慢地等待余韻,再喝一口湯,徹底溫潤腸胃。
在陽光還未徹底占據(jù)桂林天空的回南天里,我仿佛變成了象鼻山上的一棵古樹,又仿佛一直是漓江里的一塊石頭,土埋過我,我長了出來;水淹過我,我依然靜謐。我低頭凝視,抬頭仰望,看見了草木旺盛,一夏過一秋,一冬還復春;江深水綠,事物無恒變,卻又滄海桑田;清風細雨,潤物細無聲,卻又轉(zhuǎn)眼干旱磅礴。世間種種皆如此。生命哪有快?又何來慢?我終于明白,我最終追求的不過是“人間至味是清歡”。
我叫來朋友,與我同游漓江。白日泛舟,漓江清澈見底,江面晃動,宛如大盤銀鏡,映照我長長的裙擺。夜晚乘船觀夜景,燈火閃爍,五光十色,晃動眼簾。朋友說她要離婚了。校園戀情,異地奔隨,定居桂林,相濡以沫,卻抵不過婆媳矛盾,最終落得個“拋棄婚姻,斷尾求生”的結(jié)局,著實令我唏噓。看著她煩愁的神色,我最終把“我生病了”幾個字咽了回去。
我走過柳州的街區(qū)巷弄,踏過北海銀灘,疾馳過大新的萬丈山路,撫摸過德天瀑布的清冽,曾歇腳在巴馬的長壽村。
在廣西的山山水水中,我與自然構(gòu)成了一種向上的鏈接,與生命達成了向下的兼容。
我開始思考旅途的繼續(xù)與終點。
恰在這時,父親和母親都打來了電話:“你應(yīng)該回家了。”
是啊,我應(yīng)該回到群體中去,回到丈夫、孩子的身邊,回到父母的身邊。不必煩憂,他們會完完全全地接納我、溫暖我。毫無疑問,這是最好的做法。也應(yīng)該回到醫(yī)院去,醫(yī)生也會接納我、愛護我。不管何種情況,總之,不應(yīng)該是現(xiàn)在這樣,拖著病體,獨自一人在外,忍受孤獨和寂寞,令人擔憂。
二
與死亡相對應(yīng)的是誕生。
我回到了故鄉(xiāng)來找尋我生命的起始。
父親在老家等我。我們一同去看望了祖父。
這個生前念經(jīng)講古的男人,軀體早已與泥土徹底融合在一起,把墳頭和四周的草木滋養(yǎng)得尤為旺盛。只見祖父墳?zāi)惯吷系耐恋亻L著叢叢芒萁,有人踩踏的痕跡,此刻已七扭八歪地糊成一團。旁邊是幾個鼓起的墳包,長著到我小腿高的崗松(又稱掃把苗)。還有一個因撿骨已經(jīng)掘開的墳?zāi)梗吷弦老∧芸吹礁癄€的棺木,深深的凹坑里長著高高的崗松,幾乎與坑頂平齊。
我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好長的掃把苗。”
父親也應(yīng)和我:“等會兒順便把它們砍回家。”
站在祖父的墳前,我問父親:“你還記得阿公長什么樣嗎?”
“他長得不好看,油嘴滑舌的。”
“他不在這么多年了,您現(xiàn)在還想他嗎?”
“想啊,怎么不想?”父親來了傾訴的欲望,向我描繪了祖父的一生。
劉家世居博白后,代代鉆研風水文化。祖父出生后都是太祖父帶著的,從小就被言傳身教。太祖父死后,祖父正式接過家族的衣缽,成為一名風水先生。即使在動蕩的年代,家族接力棒也沒有斷絕。但在父親和二叔這一代戛然而止。
隨著父親的娓娓道來,我仿佛看見了捧著經(jīng)書卻無后代應(yīng)和的祖父,端坐在祠堂的落寞身影。
父親另拜了師,學了水磨石手藝,二叔一門心思往廣東務(wù)工。守著封建古舊風水學的祖父,被時代的洪流徹底拋棄。
“你祖父死的時候是抱著遺憾去世的。”父親說。
“你會沒事的。你別怕。”父親又說。
回到家后,父親從柜子深處翻出祖父的八卦鏡,用袖子細細地擦了后,遞給我,說:“你從小就想要它,以前沒給你,怕你被你阿公迷了眼。現(xiàn)在,把它交給你。你拿著它,不要做一個仙婆,就做……”父親仿佛不知道該怎樣接下去,頓了頓,才又輕松地繼續(xù)道,“一個油嘴滑舌的人吧。”祖父在父親的嘴里,一直就是“拿著八卦鏡,油嘴滑舌騙人”的形象。祖父到死的那一天仍是“油嘴滑舌”的,逗得祖母哈哈大笑。在祖父咽氣后,祖母才由大笑轉(zhuǎn)為大哭。
我難得地笑了起來。生病以后,我怕開口就是抱怨,更怕開口就傷了人,特別是在惹哭了母親后,我更是沉悶了。對一個從小就“話多過米”的人來說,在生病后出現(xiàn)長時間的沉默,是會引發(fā)親人的各種揣測和擔心的。
想起小時候讀《聊齋志異》,還記得葉生,“魂從知己,竟忘死耶”,對比一下自己,竟覺自己雖然生來殘缺,卻也活得完整。
三
我開始住院治療。我突然意識到,自我始,死亡,會如影隨形籠罩在我們家的上空。
爸爸,姐姐和弟弟,兩個外甥,兩個侄女,包括我的兩個孩子,我們有著同樣的一套基因,基因里的致病因素無法被消滅,它們潛伏在我們身體的最深處,悄無聲息。直到某一瞬間,它們就會突然在某個人身上現(xiàn)出身,顯了形,從潛伏變成光明正大。
我一下子輕松了起來,這不是我的錯。一會兒,愧疚又像潮水一樣向我涌來,我不該和丈夫結(jié)婚的,更不該和丈夫孕育后代。
“現(xiàn)代醫(yī)學如此發(fā)達,肯定可以只生健康的孩子。將來有一天,我們家會徹底消滅這個遺傳病的。”弟弟安慰我道。
姐姐一邊給我編辮子,一邊也安慰我:“我也有兩個兒子啊,他們以后也要生孩子的,總不能就此絕代了。”
我一邊照著鏡子,一邊回應(yīng)他們。
“我現(xiàn)在的基因就像這枚鏡子,我一放手,必碎無疑。”我說,“有沒有發(fā)現(xiàn)我面相都變了?”
“胡說!你堅持吃藥臉色就會變回以前一樣的。”姐姐忍不住呵斥了我的悲觀。
“你一個大學生,怎么還信這種迷信的東西?”弟弟也說。
這話像突然打開了姐姐的記憶盒子,她來了興趣,說了許多我和祖父相像的地方。“要不是你是個女的,現(xiàn)在指定接了阿公的飯碗。”
“所以我和阿公一樣都得這個鬼病。看來,阿公是真喜歡我,要不然也不能隔代遺傳給我。”我回應(yīng)姐姐。
姐姐興致勃勃的話語瞬間就被我的回復掐斷了。姐姐和弟弟突然就抹起了眼淚。
哭著哭著,實在是勸不住,我只能拿出手機來看搞笑視頻。他們?nèi)允强蕖R曨l的聲效實在是感染我,我一邊安慰他們一邊笑得厲害。隔壁床的老奶奶和她的兒子看了幾眼我們?nèi)愕堋?/p>
住院的日子實在是難熬,所幸手機帶給我打發(fā)無聊的時間。和南寧信息戰(zhàn)線的同事聊天說我正在南寧。神交已久的她約我見面。我實在不想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醫(yī)院里,于是我溜出醫(yī)院,打車到了她家。
朋友家衛(wèi)生間的洗手盆上方空蕩蕩的,就連能反射人影的落地窗也被貼了貼紙。朋友苦笑著向我解釋:“我家婆說鏡子會把人的魂魄吸走。”朋友的家公已經(jīng)成為植物人十三年了。十三年的時間足以將親人的所有希望一一吞噬。朋友的家婆已經(jīng)從求醫(yī)問藥過渡到了尋仙問鬼。“隨她去吧,好歹是個心理安慰。”朋友說。
我要求進房間看望一下叔叔。剛走近,一股夾雜著消毒水的腐朽味道便若隱若現(xiàn)地飄進鼻子。一打開門,味道更是濃烈起來。我不知道該怎么形容,除了消毒水的味道,餿味、酸臭味極其沖鼻,我甚至還聞到一股死尸的味道,但,打眼一瞧,便能看見他微微起伏的胸膛。他形銷骨立地貼在床墊上,像只埋了淺淺一層的墳包,連個墳尖也未能立起。這使我又想起了葉生,“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十三年的植物人生涯,每時每刻,他是否有知覺?是否聽得見外界的一切?是否感知得到家人的喜怒哀樂?是否也愧負家人?十三年來,他存在于家人的生活里,卻又仿佛從不存在。
“他好像活著,又好像死了。”朋友輕輕地說。
我感懷身世,同病相憐,久久不愿離開這間逼仄的房間。我長久地凝視他,凝視自己。恐懼如蛆附骨。
從朋友家里出來,回醫(yī)院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經(jīng)過清川大橋,抬頭,月光依然靜謐清冷,幽幽地灑下光輝,星亮和橋燈互相交融暗語;低頭,河流靜謐深沉,只見端倪,難窺全貌;往前看,深夜往來的車輛在橋上穿行而過,又疾速而去。
我的情緒出現(xiàn)了反復的變化,樂觀和悲觀交替出現(xiàn),努力自救和放任沉淪不斷發(fā)生。
我又想起祖父的風水鏡,它已經(jīng)陳舊到了模糊的地步。但當父親遞給我的那一刻,我的指尖一觸摸到它,幾代人積蓄的勇氣和力量,勢不可當?shù)爻冶家u而來。現(xiàn)在僅僅是回憶一下,我的指尖竟也滾燙了起來,這股熱量蔓延到了我的全身。我打開車窗散熱,風把我的頭發(fā)絞亂。我往回一拉頭發(fā),用發(fā)圈一扎,它又輕飄飄地趴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再一劃拉,它又散了開來,迎風而舞。我感到有趣,就反反復復地玩弄它,它也那樣乖巧地在我手底下任由我撥弄。直到師傅的車在住院部門口停了下來,我才回過神來。看著住院部的大門,我意識到在這里只治療我的軀體是沒有用的。
我心情好了起來。幾百年前,我的先祖用雙腳從彭城翻山越嶺走到白州,如今,我輕輕一跨,就能去往千百年來無數(shù)祖先也達到不了的終點。還有什么困難能比得過家族千百年來的探秘而不得知、不得不受的哀苦呢?
【作者簡介】劉海媛,女,廣西博白縣人。作品散見于《廣西文學》《三月三》《當代廣西》等刊物。
責任編輯""練彩利
特邀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