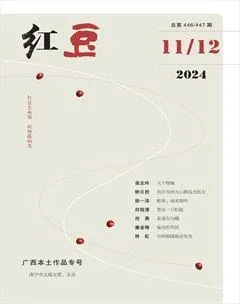草根記
金銀花
母親帶我去山上采草藥,采了一朵金銀花,別在我的發髻上。
以前母親將我當作女孩養,我穿的是碎花衣裳,留的是長發。
小時候我皮膚白皙,面如敷粉,的確像小女孩,我平時搽的是雪花膏。
雪花膏不管是搽在手上還是臉上,都會散發出一股好聞的濃香。我是極喜歡的,但是一定要假裝不喜歡。當母親打開雪花膏的鐵皮蓋子,伸出手指挖一點出來,試圖朝我臉上手上涂抹的時候,我總是躲閃開來,不能讓母親痛快地涂抹。
在安陲,沒有一個男孩搽雪花膏,他們都認為那是女人的專利,一個男孩搽雪花膏可是要被鄙視和嘲笑的。
母親當然知道,但母親可不管這些,她不僅不讓我受饑不讓我受寒,還要養護好我滋潤好我,把我撫育得像一朵在早春盛開的含霜帶露的小花,溫潤可愛,搖曳生姿。
我那時雖然長得白凈溫潤,性格卻并不可愛,很多時候不僅不可愛,還有點可惡。我常常搗亂,做惡作劇。
比如進屋捉狗。
在安陲,幾乎家家都養狗。我看見狗,很喜歡捉而玩之。我喜歡把狗捉住,強制它們睡覺、在地上打滾,或者是鉆我的褲襠。狗們都不喜歡我,每見我就躲著藏著,亂吠亂跑。我騷擾了狗,又打擾了養狗的人家,讓人家痛苦得搖頭,又無可奈何。誰叫我是我媽媽的兒子,而我媽媽是一個鄉村醫生呢?他們雖然大受騷擾,卻覺得必須無條件忍受。
只有我母親不一樣,她每看到一次就在眾人面前當場打我屁屁一次。但她揚起手掌欲做懲罰的時候,其實都在等著旁觀者及時干預,等待他們一擁而上伸出手來阻止。因此她的手總是高高地舉起,慢慢地放下。這時果然總會有好些村人及時地挺身而出,對我出手相救。這一場鬧劇也就總是以不了了之收場。大家都心知肚明,互相配合,都盡了表演的本分,演得生動認真,配合得天衣無縫。
只有我父親不滿,他常勸告我母親:“你這樣會寵壞孩子的。”
母親總是振振有詞:“我的孩子我知道!”
那時我也暗忖,母親這樣做,最后真會把我寵成壞孩子嗎?這不禁使我有點擔憂,但是并不會讓我收斂。
讀《水滸傳》讀到好漢們會在自己如雜草一般叢生的亂發際插上一朵野花,我總是覺得驚奇,一個粗壯粗俗的漢子,居然會在頭上插上一朵花,滑稽得很!我不禁莞爾,也更喜歡讀《水滸傳》這部書了。這些小細節,作者信手拈來,順筆寫來,書就生動起來,有情致起來。
而我沒想到我母親也會摘一朵金銀花,在我的頭上插起來。
她插好了,還命令我別動,她圍著我,左看看,右看看,就差拍手叫好了。一個孩子其實就是一個母親的作品,她書寫、修改、打磨,雖然最后可不一定像她希望的那樣好,但仍舊是她的寶貝。
魚腥草
越是不起眼的生命,往往生長得越茂盛。比如窮人家往往孩子眾多。我在安陲的時候,所見的正是這樣。越是食不果腹的家庭生養就越多。我周圍的許多小伙伴,他們一般總有四五個兄弟姐妹,不管是在家里還是出門在外都簇簇擁擁、成群結隊、熱熱鬧鬧,不像我是獨子,總是孑然一人、孤寂無雙。我常默默地注視他們、關注他們,內心充滿了對他們的向往。我也希望,我也渴望像他們一樣能擁有眾多的兄弟姐妹,并在不知不覺中就陷入幻想,要把我的身份置換了,置換成他們中的某一個。如此我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了,我也能成群結隊,也可以熱熱鬧鬧,不再孤寂。
可是,從幻想中走出來,發現自己仍是孑然一人,更感覺孤獨寂寞,更無可奈何。
我就去問母親:“為什么我沒有兄弟姐妹?”
母親總是愛撫著我的頭以笑為答,令我問而無果。后來我就不再問了。
也有小伙伴羨慕我,更多的卻是鄙視我。
安陲整個村莊的孩子里唯有我是沒有兄弟姐妹的。這使我常常感覺自己既在人群之中,又在人群之外。獨處成為我一生的狀態。不管是在一個人的時候,還是在集體中,最先我總有一種獨處的感覺,后來我常常有意識地保持這種在內心獨處的感覺。我在集體中,又不在集體中,不管在何處何時都警惕和要保持內心的獨立。我愿意這樣,我應該這樣。
魚腥草就像那些窮人家庭的孩子,總是生長得茂茂盛盛、漫山遍野,我走過的所有田基無不生長著魚腥草。我走過的所有陰涼潮濕之地,也無不生長著魚腥草。夸張地說,在安陲只要有一滴水一粒土的地方,就有魚腥草,安陲的天涯,何處無魚腥草?
安陲并不是窮山惡水的地方,這里土地肥沃、花草繁榮、樹木茂盛,可以說遍地是寶。可是以前安陲人卻很窮,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青黃不接的時節許多人家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陷入赤貧。安陲村莊許多人家平常是不上鎖的,出門,把門虛掩著,就走了。當然也是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可以夜不閉戶,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窮,因為家徒四壁,沒什么可以鎖起來當寶藏的。那時我很奇怪,安陲是一塊風水寶地,隨便上山砍幾根杉木賣,都不至于挨餓受寒了。長大了,才明白,不是安陲人不懂得如何脫離饑餓的苦難,而是當時人們空在寶山中而不能化寶為己用,令人嘆息。
作為一種觀賞植物,魚腥草是賞心悅目的。遠瞧,連片的翠綠,像綠毯一樣好看;近瞧,心形的葉片,在風中搖曳,很討人喜歡。我讀朱自清的《綠》,就想到了生長在安陲的魚腥草,作家可以就安陲的魚腥草,寫一篇如朱自清一樣的《綠》。朱自清的《綠》是一種水的美,魚腥草的綠是一種草的美。
韓愈寫有一首詩叫《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詩名不好,既繞也無趣,但其中的詩句卻絕好,大有情趣:“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在安陲的早春,我常吟著韓愈這首詩,想象著韓愈寫這首詩的心境,感受著韓愈這首詩蘊含的意境,假裝也在欣賞著眼前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其實南方的安陲冬天盡管也天寒地凍,但畢竟是南方,大自然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綠油油的,何況是春天呢?早春的安陲春色盎然,萬物競長,一派茂盛,哪只是“草色遙看近卻無”呢?
很多年后,記起這些情景,我居然很矯情很裝腔作勢地寫了一篇叫《淺草》的散文,假裝是在描寫安陲早春的“草色遙看近卻無”,發表在報刊欄目頭條上。那時我也是喜滋滋的、陶陶然的。那時我的寫作既不直面世界,也不敢直面內心,現在想來深感羞慚。
一篇作品在寫出來后,可能會在某一天,是要令作者汗顏的。
漫山遍野的魚腥草在安陲廣袤的天地間生長著,不知安陲有沒有人欣賞它。只見它一歲一枯榮,生了滅,滅了生。
桑葉
中國古代稱得上知識分子的,往往都懷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為國講王道,為民求溫飽。
春秋戰國時期,文人薈萃,其時文人立世的方式就是為王謀。那時的各國君王也都以一種求賢若渴的心態禮敬文人。他們常謙恭地向文人討教治國方略,并得而行之。一時思想活躍。
孟子生而逢時。梁惠王聞他名,請他來,向他討教。孟子正得其所,不客氣,傾心相授。孟子希望梁惠王懂得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要廣積糧多種樹,讓人民安居樂業。梁惠王聽了頻頻點頭,大受啟發,得益頗多。那時的君王謙遜好學、厚待文人,仍然是現在為官者的楷模和榜樣。那時候的文人遇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美好時代,他們也珍惜這個時代帶來的機會,為中國的文化、文脈,遺留下璀璨果實。
孟子在和梁惠王對談中,出主意道:“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直譯是說在五畝大的住宅旁種上桑樹,五十歲的人就可以有絲綢穿了。
古人那時的生活應該很簡單,有飯吃,有衣穿,就行了。中國文人幾千年來獻計獻策要幫助君王解決的就是這件事。豐衣足食了,人民生活便幸福了,安居樂業了,君王也就不但合格了,還可稱為明君了。
古時候桑在中國和稻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桑解決穿衣問題,稻解決吃飯問題。談到桑,《詩經》便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那種人們對其恭敬膜拜的態度,只有稻可以與其相比。
安陲有桑但不是人工種植之物,都是野生的。安陲蠻荒之地,舊時許多人以打獵為生,不事稼穡。
有一日安陲興起養蠶之風,我也跟風,拿醫用的盒子裝著桑蠶,采桑葉喂養。
我母親不僅準許,還同我一塊上山采桑葉,回家喂蠶。
我們看著蠶沙沙地埋頭吃著桑葉,甚是歡喜。
蠶漸大,藥盒已嫌小,母親居然為助我養蠶,把她的小碗柜給我,讓我的蠶寶寶們有舒適的安身場所。
那時安陲已經有電燈,母親便把一盞燈拉進小碗柜,日夜照明。她說這樣可增加蠶寶寶的食欲,讓它們多吃快長。
我半信半疑。
總聽到蠶寶寶們晝夜不息地啃食桑葉,聲聲入耳,我內心歡喜。
我計算著,養多少蠶,得多少蠶繭,可賣得多少錢。越算越多,越算越有錢。不得了,快成大富翁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父親看我那副嘚瑟樣,裝作沒看見,不言語。
可見我從小就是財迷。
最后一分錢也沒見著,蠶是養了,繭也得了,才發現無處可賣。最后怎么處理,我不記得了。
還采來許多的桑葉,母親將它們晾干了,時不時和著菊花煮成桑葉菊花茶,供我們喝,以清熱解暑。
捆仙藤
我們進山砍柴是不帶繩子的,只帶一把砍柴刀。砍柴刀插在刀套里,背在腰間。把柴砍好了,就用捆仙藤捆扎。
柴也不是亂砍的,我們主要砍杉木的枝條。公社把成年的杉木砍倒了,放置在原地數天,自然曬干晾干,然后拖走或扛走。拖杉木的場面往往很壯觀,要搭廂橋,人和杉木都在廂橋上走,像乘坐在如今城市里的輕軌上。
砍倒的杉木身上的枝條就是我們要砍的柴火。
哪一山砍了杉樹我們就去哪一山砍柴。
砍柴的人消息靈通,知道哪一山有這種柴砍。阿貝就是消息靈通人士,下課了他總是能領著我們找到公社放倒杉木的地方。
公社砍杉木的方法是看好成年杉木后,再一坡一坡一山一山地成片砍倒。場面壯觀,看上去總讓我產生一種天已荒、地已老的感覺,倍感窒息。
隨著一山一山的杉木被伐了,我也越來越憂愁:待這些杉木全砍光了,我們還燒什么?
志強總嘲笑我杞人憂天。
我真是杞人憂天嗎?我不知道,可是我確實暗暗擔憂,憂愁揮之不去。后來我們家離開安陲了,我也就忘了這種憂愁。離開安陲我們回到了縣城,開始時依然燒柴,但不須己砍柴,也沒條件去砍柴了,到柴火巷買柴。不久改為燒煤,繼而改為燒煤氣,一直到現在。柴不知不覺淡出了生活,那種憂愁卻常隱隱地浮現,揮之不去,今天仍存。
砍柴是講刀功的,光有蠻力不行。會砍的人第一得有勁,第二是將勁用得巧,然后才能事半功倍。
我在上小學前生長在上海,我本不是安陲人,如今來到安陲,做山里的活兒,事事都顯得笨拙,砍柴也一樣,人家砍兩刀三刀得一根柴,我砍五刀六刀還沒得一根柴,成為笑柄。我父親母親都不讓我去砍柴,那時安陲街上有柴賣,他們主張買柴。可是我堅決不同意。在安陲每戶人家的柴都是由各家小孩砍來的,我認為我也應該這樣,也應該為家庭負擔起同樣的責任。我的倔強和固執令父母無奈,最后也只好由著我了。能承擔家庭這樣的責任令我很滿意。
把柴砍好了,攏成堆,然后就地扯根捆仙藤把柴捆扎起來。有時是捆成一捆,背在肩上扛回家,更多的時候捆成兩捆,然后再拿一根柴作扁擔,把兩捆柴兩頭一穿,挑起走。這需要捆柴時用點技巧。剛開始我沒掌握技巧,捆好柴了,挑沒幾步,柴呼啦就散開了,好丟人。
學捆柴我學了好久。起初干脆由阿貝幫我捆。可是我不能總讓人家代勞啊,這不僅傷我自尊,也不現實。我學農事總是很笨拙,用捆仙藤捆柴學了一兩個月,才算真正學成,再也不會讓柴散架。
“捆仙藤”是很有趣的名字,可是為什么會叫“捆仙藤”呢?我卻不明白。阿貝明白,說這背后是有故事的,但他又狡猾地眨眨眼睛說:“就不告訴你。”
雷公根
喜歡這樣的葉子,翠綠而嬌嫩。雷公根就長著這種葉子。
雷公根是柳州人的叫法,我母親教我辨草識藥時稱之為金錢草,我一位北方文友則叫它積雪草。
關于積雪草,這位文友還有故事。她極喜積雪草,索性便用“積雪草”作筆名。自她用了積雪草作筆名,奇跡就發生了。此前她用本名發表不出的文章,用“積雪草”作筆名后,則通通都極順利地發表出來了。
“積雪草”這個筆名,一次次給她帶來好運。
我的文友仕芳兄有一個觀點,他說每個作品都有自己的命運,作品寫出來了,作者的任務便完成了,其后就看作品自個兒的命運了。
說得挺神秘、挺神奇的。
真是這樣嗎?我有點不信。
柳州人語速比較快,有時候講話像吵架。我剛從桂林回到柳州時,對柳州人大著嗓門像喊話一樣的講話方式感到非常不習慣。我便笑自己:我可也是柳州人啊,時隔十年再回柳州,怎么就與柳州如此格格不入了呢?
桂林雖然同柳州比鄰,但十里不同俗,兩地人性格就完全不一樣。僅僅從講話的語氣上就充分體現出來了。桂林人講話,調子慢,語氣柔,像唱歌。我的一名桂林同學第一次來柳州,被柳州人嚇壞了。她去有名的飛鵝市場打算購買一件衣服,挑了這件又挑下一件,總感覺不太滿意。正想再看下一件時,忽然賣衣服的老板娘把衣服從她手里一把搶奪過來,放在衣架上,惡狠狠對她喊道:“你快走吧,老子不賣了!”嚇得她逃也似的走了。
“你們柳州人怎么這樣兇呀?”她非常不解。我聽了便哈哈地笑。柳州人不是兇,柳州人是做事麻利、干脆,不喜黏黏糊糊。
柳州人選擇了雷公根這個名稱,而拒絕選擇其他,正符合了柳州人火暴的性格。雷公根,多么硬朗、多么響亮的名字啊,像迎面遇著一個霹靂炸響在眼前,簡單,粗暴,霸氣。
也許柳州人自知自己脾氣火暴需要調治,在街頭各處常有各種涼茶攤,售賣清熱去火的涼茶。
在駕鶴路上就有一攤,我表妹常去光顧。攤位上擺賣有各種各樣的涼茶,如生地茶、羅漢果茶、茅根蔗茶等,當然也少不了雷公根茶。表妹特喜好這一口,每次到駕鶴路上玩,必喝一杯。她常年喝雷公根茶,人果然變得越來越溫和,講話也不那么大嗓門了。
現在柳州的年輕人基本已經不再大嗓門說話了,都向輕聲細語發展。而且很多都不講柳州話了,全講普通話。我父親聽了喜滋滋的,說:“這都是雷公根涼茶的功勞啊!”
【作者簡介】羅海,現居廣西柳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發表于《紅豆》《散文百家》《青年文學》《天涯》《山東文學》《散文》《廣西文學》《山西文學》等刊物。
責任編輯""藍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