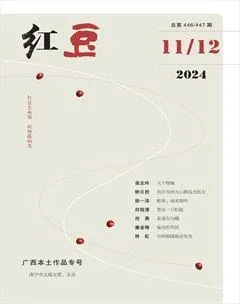農家樂
我不知道該怎么辦,只有在她面前,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要她一不高興,我就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也只有在她面前,我才覺得我是個徹徹底底的失敗者。我真的沒用啊,我又惹她生氣了,我竟然不能讓她高興一回,哪怕讓她臉上偶爾有一抹笑意。我心情低沉到了極點,我對自己產生了陌生感。
那個熟悉的母親,陌生的兒子。我在母親面前時常恍恍惚惚。我的記憶時而停留在農村的老屋,時而輾轉于城市的街道和小區。而母親皆為一律的漠然、痛苦,甚至有時是憤怒。她表達這些情緒的時候,要么回憶她年輕的時候,要么否定我年少的時候,要么摔打抓在手上的東西……母親眼里的一切都不合她的意——除非將她放回農村去,回到她親手建起來的土坯房里去——那仿佛是她精心營造的宮殿,那里仿佛有錦衣華服。那里仿佛什么都有,包括母親稱心的一切。如果沒有那些,不管我如何勸說、如何努力、如何順從,都是徒勞。看著母親賭氣扭轉的身軀,我一時也僵在客廳里。
我們同時靜止在房子里,但是房子在動,只有我知道。那叮咚叮咚的聲響從我的手機里冒出,就像夜空里不停噴薄而出的焰火,是一條微信消息:佳和城,農家樂,帶上你母親,有驚喜,快點來。
微信里趙經理發來的定位圖我有點熟悉,而且“帶上你母親”定格在我眼簾。我像一只遲疑再三的鴨子,跳進冰冷的春水里。我試著攪起輕波,對母親說:“出去走走吧,帶你去逛逛。”母親的回絕不假思索。我又說:“不是去逛街逛商場,是去鄉下,去看果樹看池塘……”母親這才慢慢轉過頭,看著我的臉。我扯了一下母親的衣角,母親移動了一下步子。我馬上去開車,暫時忘記了那個渾身受挫、信心全無的自己。我調整呼吸,加大油門,向佳和城的方向駛去。
母親不知何時睜開了眼,看著窗外。她先前有點佝僂的身子這會兒直了一些。我對母親說:“到了。”我的車開過一道用蘆葦和松樹皮制成的柴扉。我盡管不是第一次來,但還是忍不住又笑了,說:“像我們村外頭茅廁的門。”這次,我為討好母親,特地在“門”前加上了定語“像我們村外頭茅廁的”。但母親的臉上卻沒有變化,她也許是沒聽懂“茅廁”的意思。
我好像自言自語:“那是龍眼樹,那是荔枝樹,那是杧果樹,那是木瓜樹,那是香蕉樹,那是石榴樹……”母親仍面無表情,她像剛跨入學堂的門檻卻面對的是初中的課本,那些名詞就像“天外飛仙”,來自江西省井岡山下小山村、大字不識一個的母親壓根兒就沒聽說過。我覺得我是自作多情了,或者說是難為母親了,我看見她嘟起干裂而枯老的嘴唇,腮幫子像充塞著某種物質,微微隆起。但我又不知該如何表達歉意。我沉默了六七秒,挖空心思想再一次活躍氣氛,我指著果樹綠葉深處,說:“在南寧,秋天了花還很多。”母親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又轉向了其他地方。我很想補充一句,“那是三角梅。”但母親沒問,我便沒有說。
進了農家樂的門,路兩旁有亭臺樓榭,上面爬滿了百香果的藤蔓。車旁草叢里流出一段段白花花的水,水上立著一兩座水車,還有石磨。我往那片廣闊的水域方向開,速度卻越來越慢,路兩旁時不時擠來三兩個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或嬉嬉鬧鬧,或嗔怪喊叫,或說說笑笑,或蹦蹦跳跳。隔著車窗玻璃,都能感覺到嘈雜。
車挪到大水域的岸邊。我知道,我的朋友,農家樂的主人趙經理,稱那地方為“蓮花蕩”。我第一次去時,嫌那名字土。他說:“就是要土。名字不土,城里人不愛。”他又說,“‘蓮花’這個詞老人喜歡,小孩也喜歡。”我指著水域中間種的那些蘆葦說:“那里就是‘蕩’吧?”他說:“我知道你也不喜歡,可青年男女喜歡,劃著船在那里繞圈,別提多浪漫。”我說:“叫荷塘更恰當。看荷花,品茶閑談;賞晚霞,燒烤、打撲克,是多少城里人的理想生活。”
趙經理看見我母親下了車,撇下我,直接奔過去,雙手摟住我母親的雙手,熱情地說:“老人家,歡迎歡迎啊!”松了手,他轉向我,好像是向我下命令,“要讓你母親高興啊。”我說:“她反正不會喜歡你的荷塘,她年輕時養過荷挖過藕,都累怕了,現在見到荷塘都怕。”母親在旁好像沒聽見,陰著臉,不說話。我問:“不是有個挖紅薯的項目嗎?”趙經理說:“有啊,你小子上次沒完成任務,沒有在規定的十分鐘內挖出十斤紅薯,空手而歸噢。”我說:“滿十斤免費帶走,不滿十斤,想買回去,三塊錢一斤,你小子原來在這里設了個陷阱、挖了個坑。”趙經理說:“這個項目最受城里人歡迎,盡管很少有人能在十分鐘內挖到十斤紅薯,但前來挑戰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他說完,瞅了我母親一眼,對我說,“是啊,帶你母親去挖紅薯吧,她老人家準喜歡。”
我對母親說:“我帶你去挖紅薯吧,你喜不喜歡?”母親說了走出家門后的第一句話,而且似乎是輕描淡寫的一句簡短問話:“挖什么紅薯?這里有紅薯挖嗎?”母親問后,臉上繃緊的肌肉松弛了一些。我趁熱打鐵說:“就是我們老家的那種紅薯呀,你喜歡,我就帶你去挖,就在后面。”我說完轉了一下身子,背對著荷塘,指了指果園的山坡上。母親先邁動了腳步,她遲疑地丈量著腳下,喃喃自語:“還是以前在家種紅薯的時候挖過……”我連忙趕在母親的前頭,引導著她向山坡上走去。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和我們擦身而過,他們的腳步充滿著興奮與自信,速度比我們快幾倍。我牽引著母親腳下的“馬達”,使蹣跚的她也加快腳步,但她的腳步還是被后來居上者撞著。她的腳后跟被別人碰到,她“嘖嘖”地叫著。我知道,那是母親特有的表達不滿甚至憤怒的方式。撞到她的大多是小孩子,他們奔跑著,全然不顧我母親的情緒與感受。他們的父母也不管,他們只管自己的小孩是不是趕在前面,他們知道,前方有紅薯地,紅薯地里有一個個紅薯。他們信心滿滿的腳步,將七十八歲的母親甩得遠遠的,母親在我不緊不慢的牽引下氣喘吁吁。
紅薯地在半山腰,紅薯地旁能領到挖紅薯的工具。田埂上站的都是人,人像開閘的水,四處漫延,有的傾瀉到紅薯地里去了。紅薯地里,看不到多少土,地被黑壓壓的人及零星的苗葉覆蓋了。紅薯地旁,有幾個穿著統一服裝,甚至連年紀與發型都差不多的女子在分發工具。但很少有人從她們的手里拿,而是直接去搶,在她們手上搶、在地上搶,那些工具驚慌失措。我隔著一塊紅薯地,看到一個統一著裝的女子,一只手拎著一個簸箕、一只手拎著一把鋤頭正往前走。我忙跑過去,一把將她手中的簸箕和鋤頭奪了過來。當我把簸箕和鋤頭放在母親身邊時,母親雙眼睜了一下,又瞇了一下,眼角露出兩抹笑意。
我不知道是這個狂亂的場面引得她發笑,還是她為我搶得了一副工具而滿意地笑,反正,母親笑了,但她的兩抹笑意很快被那些狂熱的喧囂所吞噬。紅薯地很快被海嘯般的人潮席卷。農家樂的工作人員努力掌控著局面。她們看見有鋤頭刨進了地里,便馬上制止。她們將人群分隔成一組一組,每組不管是一家人還是陌生人,一律不得多于三人,或者說三人以內。每組只有一把鋤頭、一個簸箕。很快,人群被分隔了開來,分組站在一畦一畦的紅薯地前。我與母親被一名工作人員拉到一畦紅薯地前,她指著前方說:“你們就挖這一段,等我計時開始,你們才可以開始挖。”
這時,紅薯地里的工作人員對我微笑了一下,然后變戲法似的掏出手機,四周看看,然后問我們:“準備好了沒有?”周圍的人像潮水一樣激昂地回答:“準備好了!”工作人員還沒有喊“開始”,地里便亂成了一團。我也奮力舉起鋤頭往土里砸去。我將土挖開時,看見了一個紅薯,但紅薯被挖成了兩半,一半露在外面,另一半還在土里。母親不緊不慢地說:“你這樣挖紅薯,紅薯遭罪。”停了兩秒鐘,她又說,“鋤頭要離紅薯的根蔸遠一點,這樣就不會挖爛紅薯了。”我朝手心又吐了一口唾沫,挺直腰板,聽母親的話,朝根蔸遠一點的地方大力挖下去。土被掀翻了一大塊,卻沒有看見紅薯。我不甘心,又使勁地挖了幾下,仍然不見紅薯的影子。母親終于笑了一下,說:“你把吃奶的勁兒都使完了,也挖不到紅薯。”接著,她又慢慢說,“要找有裂縫的地方挖,裂縫是泥土下的紅薯撐開形成的,裂縫越大,說明下面的紅薯越大。”
我聽了母親的話,順著紅薯的藤蔓,尋找有裂縫的泥土,朝著有裂縫的泥土往下面挖,果然挖到了紅薯。我驚叫了一聲,仿佛發現了寶藏。我扭頭看看四周,那些大人與小孩雖然個個滿頭大汗,但收獲不多。以前的大喊大叫、歡聲笑語,被氣喘吁吁代替。頑強的,一聲不響,艱難地舉著鋤頭在挖;軟弱一點的,干脆丟了鋤頭,坐在田埂上唉聲嘆氣;還有的干脆惱羞成怒,雙手使勁地拔紅薯的根蔸,或者扒泥土,但收獲不多。
我的驚叫聲在地里成了難得的喜悅,對旁邊幾位家長卻是刺激。或許他們不想在孩子們面前放棄,便增加快揮動鋤頭的速度與力度。紅薯地里的人,男女老少,東倒西歪。母親笑出了聲來,說:“像你們這樣,累到天黑,都挖不到十斤紅薯。”她否定的不只是他們,還包括我。她奪過我手中的鋤頭,她不是將鋤頭高高掄起,也不是往泥土里狠狠地挖,而是撥開紅薯葉,順著泥土有裂縫的一端,將鋤頭挖到泥土里,順勢慢慢用力拉扯。只見一塊塊泥土順著鋤頭被翻起,一串串紅薯從泥土里跳了出來,露在了地面,而且沒有一個紅薯有傷痕。我拎著一串串紅薯,像小時在農村一樣,快速擰斷根須,去除沾在上面的泥土,一個個放進簸箕里。
母親仍不疾不徐,仔細地在紅薯地里查找。鋤頭在她手里好像慢板音樂的指揮棒,輕輕地在泥土里劃著弧線。她的周圍不知何時聚攏了一些人,人越聚越多,先是三四個,再是五六個,然后是一群,將整畦紅薯地都包圍了。我也被包圍了,我蹲下身子,盯著母親的鋤頭,看著一串串紅薯隨著她鋤頭的運動軌跡翻滾了出來。人群一陣陣歡呼了起來。母親的手臂似乎開始在暗暗增加力量,她手中的鋤頭在泥土里更加剛毅、更加有力,也更加勇猛。鋤頭的勢頭不可阻擋,速度比之前更快了。
人群繼續活躍,有的小孩興奮地蹲下來,捧著簸箕里的紅薯“哇哇”地叫起來。母親笑著搖了搖頭,用土話說:“城市里的小孩真的沒見過世面。我們在村里時,哪一年不要挖幾百斤紅薯?你小時候哪一年不要跟我和你爸到地里去撿紅薯?”我說:“是啊,他們比起我們小時候,是有點可憐……”我說這話是想逗母親開心,我又說,“那時我穿開襠褲呢,還不照樣在紅薯地里打滾?”
人群中有家長模樣的人問母親:“您老人家是怎么挖到紅薯的呢?一挖一個準,一挖一大串,地里的紅薯被您一個人挖光了。”母親手不停,嘴也不停:“你要找到一個小包,或者有裂縫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下面才藏紅薯呢。”有人一聽,散去幾個,紛紛回去繼續挖。人群中有老人“嘖嘖”羨慕說:“人家挖得多,還不出汗呢,好像玩呢。”接著,有人添一句問話:“您老人家高壽?”母親終于停下鋤頭,支住下巴,攏了一下耳邊的銀發,得意地笑著說:“今年七十八呢。”人群一聽,“嘖嘖”聲又多了幾個。母親似乎不想挖紅薯,而是想說話了。她聲調也越來越高:“在我們村,我們這么老的老太婆,哪個不是還在田地干活?有的割禾,有的種菜,還有的上山找柴,都能自己養活自己呢。現在我來到城里,什么都做不了,人都要坐出病來了。”
人群沉默了下來,慢吞吞地散了,回到了各自的地盤里。他們似乎都精疲力竭了,有的坐著,有的踢著空空的簸箕,還有的拿著鋤頭追人玩,他們臉上的笑容仿佛被太陽蒸發了、稀釋了。工作人員一個個走到紅薯地,盯著各自負責的組別催促:“快到時間了,怎么樣了?成績如何?”她們一一巡察每一個簸箕后,臉上泛著笑容,嘴里卻說:“重在參與,開心就好。”
真正開心的是母親與我。規定的十分鐘到了,大家要將簸箕里的紅薯過秤。母親挖的紅薯有十二斤,超過了十斤,也就是說,母親在規定的十分鐘之內,挖了十二斤紅薯。這一輪挖紅薯活動成績經現場公布,僅有兩組選手完成了目標,母親與我是其中一組。按照活動規則,如果超過了十斤,所挖到的紅薯免費贈送。這是我始料未及的,當然母親更是沒有準備。我們甚至都沒有準備一個小小的塑料袋。但現場的工作人員很熱情,她們紛紛為我尋找可以裝得下十二斤紅薯的袋子。
十二斤裝在簸箕里的紅薯重新被人群圍了上來,他們臉上的表情沮喪。而我與母親則強行壓抑著開心與興奮,目光不敢與圍觀的任何一個人對視,我怕與他們的目光相遇。母親突然說:“紅薯也值不了幾個錢,何況還不好拿回去,干脆送掉算了。”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說:“怎么?送掉?你曉得這紅薯在城里多少錢一斤嗎?兩三塊錢一斤呢,怎么能隨便送人?”母親一聽,眼睛睜得比我的還大,說:“吃金子噢,兩三塊錢一斤的紅薯。在我們老家,五六毛錢一斤都了不起了。”我搶下母親的話:“五六毛錢一斤也不送,這是你的功勞,全是你的功勞,怎么能送人呢?”母親這次是真正開心地大笑了,她斜了我一眼,眼神生動,表情有點嗔的意思,就像她年輕時受到父親或村民表揚時的表情。
母親從簸箕里拿起兩個大大的紅薯,朝前走去,她追上一個挎著一只布包的老阿姨,將紅薯放入她的布包里。老阿姨起初很慌亂,她緊張地扭過頭,看見兩個紅薯,她怔了兩秒,馬上換成了感激。老阿姨身旁的男子也停住了腳步,他將懷里的小孩從左邊換到了右邊。他看了一下身旁的老阿姨,說:“媽,人家好意給你,你就收下吧。”接著,沖我母親說,“謝謝,謝謝啊。”老阿姨見母親要轉身,輕輕地拉住她,從布包里掏出一個蘋果給母親。母親說啥也不肯要,說:“我要是要了,一個蘋果換兩個紅薯,你劃不來呢。”說完,笑瞇瞇地摸了一下男子懷里的小孩的臉蛋,說:“我孫子讀大學了呢。”
工作人員幫我找到一個紙殼箱子,說這個箱子裝三十斤紅薯都沒問題。我笑著說:“那再給我十分鐘,再挖十二斤紅薯拿回去。”工作人員笑著說:“上午挖紅薯的活動結束了。”我問:“明天還搞嗎?”工作人員連忙說:“明天也沒有了。”我說:“你騙人。我認識你們這里農家樂的趙經理,今天就是他叫我來的。你們的挖紅薯活動持續到下周,我下周再來。”
工作人員將目光轉向我母親,說:“你媽太厲害了,比另一組都是青年男子的還多挖了一斤。你再多帶你母親來幾次,我們的農家樂就要虧本了。”母親可能聽懂了意思,她笑著將一個個紅薯往箱子里放,每放一個笑一下,樂呵呵的。
我抱著箱子往回走時,母親超過了我,她臉上的肌肉完全放松了下來。她的眼角折著,藏著隱隱的笑意。趙經理在我的車旁等著。他接過我的箱子,掂了一下,說:“收獲不小啊。我聽山上的服務員打電話來要箱子,今天你媽媽出名了。今天上午,很多人認識了你媽媽。”
趙經理將正想上車的母親往下拉,說:“不要急,吃了中午飯再回去。”我客氣地說:“不了吧?”趙經理說:“叫你來是特地要你拉你媽媽到我們農家樂來吃午飯的,想不到你們還有意外收獲。”說完,又笑吟吟地對我母親說,“再次恭喜老人家。”
恭敬不如從命。我跟著母親,被趙經理引著,走過一段四五十米長的浮橋,鉆進一座用茅草搭蓋的、類似蒙古包的房子里。里面擺著一張大圓桌,圓桌上擺了幾道菜。趙經理指著菜說:“中午,隨便點了幾道菜,但都是產自我們的農家樂。有韭菜炒雞蛋,雞蛋是土雞蛋;有白切土雞,土雞是我們散養的,滿山莊都是;還有小白菜,是在旁邊的菜地里擼的;絲瓜肉片,絲瓜種在池塘邊,也是現摘的。”
我笑了一下,說:“就這盤白切雞值錢些。”趙經理說:“你吃人家的,嘴還那么尖酸。”我正要勸母親先吃,卻不見母親在桌上。趙經理走出屋外,看到母親,他說:“還是我了解你媽媽的心思。本來開飯之前要先征詢你媽媽的意見,問她想不想到我們農家樂來給客人們表演挖紅薯——當然,還有栽紅薯種菜……包吃包住,每個月我還給她開三千塊錢工資,怎么樣?”
表演?我不解。趙經理說:“我本來就有這個打算。你看,現在的城里人,哪懂得挖紅薯、種菜哦?放心吧,你媽媽來這里表演,我除了給錢,還管吃住,我會照顧好她的。”我說:“只要不是太累,她老人家巴不得種菜呢,可能身體會更好也說不定呢。”
我們走到母親身旁,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將趙經理的想法對母親說了。母親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這里的地太荒了,不知要下多少肥呢。何況,這里太鬧騰了,每天那么多人來,而我,一個也不認得呢!”
【作者簡介】陳紙,本名陳大明,一九七一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西作家協會理事。發表長篇小說《下巴咒》《逝水川》《原鄉人》,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天上花》《少女為什么歌唱》《玻璃禪》《問骨》《尋找女兒美華》,隨筆集《撥亮內心的幽光》《舍陂記》等。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刊物上發表中短篇小說若干,作品曾被《散文選刊》《小說月報》轉載。曾獲第十一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第六屆《北京文學》獎等獎項。
責任編輯""練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