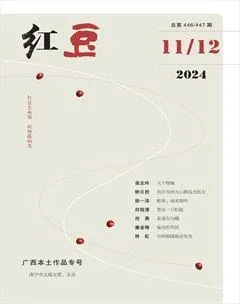斷章,或者劇終
未知的落日為那些過時的風景鍍上余暉。遺忘的河流的逃難者們,在岸邊倉皇逃竄,又流連躊躇。
風景
站在房客退租的房子門口,遠望夕陽,我心里五味雜陳。這所房子,曾是我和秋子愛情的避難所,也是我們婚姻的終結地。我時常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被歲月碾碎的記憶片段。
前房客提前撤離,留下一間空蕩蕩的屋子,仿佛從未有人來過。這猝然到來的悄無聲息,令人悵然若失。此前的房客來來往往,遺下許多奇怪的東西,有摔碎的情侶水杯、不成對的情侶拖鞋、撕毀的情書、銀行賬單、用過的安全套、滿地紙巾、散落的千紙鶴、被遺棄的寵物,甚至還有排泄物。
而我,又何嘗不是被人遺棄的垃圾呢?五年前,我同一個叫秋子的女人發誓,要在這所房子里一起生老病死。后來,我們的婚姻病了,從前愛得死去活來的那個人突然就舊了、老了、看不見了。
一塵不染的屋內,赫然出現一根白發。長長的,微微卷曲。肯定不是秋子的。循著這根白發,我意外發現了前租客驚人的秘密。
衣柜里,藏著多幅婚紗照,半人高的,迷你的,方形的,圓形的,大大小小共八幅,另有一本厚重的相冊。我不自覺地發怔。愛也罷,恨也罷,這些感情都如火如荼地灼燒著人們,那些定格在相片上的恩愛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婚紗是愛情走向幻滅的通途。一場婚姻褪去了華麗的婚紗,只余赤裸裸的現實和真相。若是愛已不可為,婚紗照又該如何處置?
婚紗照就像一面鏡子,照出圍城的真相:空虛、浮夸與冷漠,甚至還有暴力。
他們是真夫妻,還是未結成婚,抑或是已離異?也許只是一對露水鴛鴦,而我恰巧為他們提供了婚床?他們完成了婚姻的儀式,卻毀滅了愛的證據。
多次撥打前房客的電話,許久才接通。男房客輕描淡寫地說:“扔了吧。”
正如一袋過期的食物,一只腐爛的蘋果,一件過時的衣服,破損了,被蟲蛀了,遭雨淋了。不合時宜的東西,似一潭泥沼、一個無底的漩渦,里面爬滿了惡毒的蝎子。
如何扔掉自己?我是個事業受挫的失敗者,婚姻破裂的失意者,一個糟糕透頂的人。自小,我就被父母看作是一個古怪的孩子,喜歡收藏舊物,郵票、老照片、老式相機、陳年書籍等,反復聆聽懷舊的老歌,看老電影淚眼婆娑,一只破碗能研究半天,一雙鞋穿出了破洞也不愿舍棄。
“你不敢面對任何不確定性,喜歡追求穩妥,心里極度缺乏安全感,始終在逃避真實的自己。通過收藏,你能夠找到某種與世界的連接點,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同時,你也是一個懷舊的人,極重情感。”
秋子的話令我徹底淪陷了。世間竟有一個人如此懂我。一想到秋子,我的眼淚就會流淌,淌成一條河流,從一道平緩的山坡流過,流向深處,流向遙遠之地,流到沒有盡頭的盡頭。只是,她僅陪了我五年多,就要將我像垃圾一樣丟棄了。
可笑的是,我從三歲開始收藏,如今卻要毀掉人世間最美好的瞬間留下的紀念。除了留下自己的影子和痕跡,我這一生并未留下過什么。而此刻,我需要把殘留的為數不多的東西毀滅。
樓上
這七八成新的日子,每天都被新的一天毀滅。
“扔了吧。”我說。
“扔了?”木頭質疑道。
“像婚姻一樣,壞了,就扔了吧。”
“拋棄意味著踐踏!”木頭正色道。他從未如此嚴肅。我隱隱感覺他在侮辱我千瘡百孔的婚姻。
“從前照相館里被人摒棄的相片,你都不扔,一直保存到現在嗎?”
“不是不想扔,是不敢扔。婚姻大事,怎能隨意處置?就讓那些陳舊的、破舊的婚紗照,長久地停留在那里,停留在荒謬的深巷。”
我似懂非懂。
“馬尾,這輩子,我們哥兒倆一定要干一件驚世駭俗的大事。”木頭言之鑿鑿,我嗤之以鼻。
我本名馬偉松,木頭習慣叫我馬尾,木頭說:“年紀輕輕怎么能松呢?”于是刪繁就簡。一天,我們聽到海子作詞的一首歌《九月》,聽到盲人詩人周云蓬反復吟唱著“一個叫木頭,一個叫馬尾”時,我和木頭抱頭痛哭,酩酊大醉。
那晚,我和木頭東倒西歪地鋪陳在木頭倒閉半年的照相館里,在他的相片上吐得七葷八素。事后,木頭心疼地擦拭那些恩恩愛愛和和美美的結婚照,卻無論如何也擦不干凈。
我遞給木頭一支“紅雙喜”。自從我們雙雙失業后,消費也日漸降級,從五十元一包的“真龍”改抽“紅雙喜”。木頭說,抽紅雙喜討個吉利。
煙蒂快燒完了,木頭舍不得撇下。許多事我們都放不下。快燒到手時,木頭驟然起身,扔掉,又用腳踩踏著。突然,他重重地拍著我的肩頭,手舞足蹈地說:“馬尾,我們很快就要發達了!”
木頭拍著胸脯,豪情萬丈地說:“我們開一個婚紗照粉碎店,保證賺得盆滿缽滿!”
木頭偉大的發財計劃,我認為是天方夜譚。
“你身邊有多少離婚的?”木頭問。
“還真不少。除了我,還有朋友、前同事、親戚、鄰居……”
“那就對了。如今離異的、分手的,甚至去世的比比皆是,之前的結婚照繼續留著,既不合適,也沒法同下一任解釋。所以,我們的生意就來了。”
我毫不留情地潑了一瓢冷水:“沒有人會閑得無聊,或者錢多得發慌,大老遠把相片送過來給你粉碎,直接甩到垃圾堆不好嗎?”
木頭駁斥道:“那么大一幅婚紗照直接投進垃圾桶既不方便,也不吉利,畢竟照片涉及個人隱私。設想一下,你的婚紗照上面鋪滿垃圾,還有濃痰,被人看來看去,踩來踩去……”
我打斷木頭的話,我不敢想象恩愛繾綣的我和秋子被人隨意圍觀、任意踐踏。
木頭鉗住我的肩,激動地說:“馬尾你知道嗎?有一天,我經過一個垃圾堆,一幅跟我差不多高的婚紗照躺在路邊,引得大量路人圍觀。一個保潔大姐說:‘你看這結婚照拍得多好啊,丟了太可惜了。我們當年想拍沒有錢,現今有人拍得這么好看卻不想要。’我好奇地問大姐:‘不能賣廢品嗎?’大姐嘆道:‘這就是一堆廢物,賣廢品也沒人收。’我又問:‘要不要撿回去留作紀念?’大姐連連擺手:‘我可不敢。’兩年多過去了,我一直記得那幅當廢品都遭人嫌棄的婚紗照。”
我沉吟道:“他們為什么不自己剪掉?”
木頭說:“這些年來,我經手過幾千張婚紗照,摸照片就像自己的左手摸右手。相冊的封面分皮質、鋼化玻璃材質,內頁紙足有硬幣那么厚,一體相框是亞克力的,八毫米厚,還有金屬的、水晶的,僅憑一把剪刀,你以為就能輕易剪斷?”
雖不懂那些專業名詞,但好歹也是拍過婚紗照的那頭“豬”,我能想象婚紗照的厚度。
木頭繼續道:“婚紗照雖絢麗,銷毀就難了。那時追求的堅硬和恒久,如今都變成了堅硬的麻煩。有些人狠心直接一棄了事,有些人選擇用暴力摧毀。網上曾流傳過一段視頻,一個中年男人不惜用鐵鍬將自己的婚紗照拍碎,拍了半個多小時,玻璃碎了,相片還是毀不掉。”
“這是有多大的怨恨啊?可不處理看著又咯硬。拍不碎,用火燒總可以吧?”
“人還活著,人像卻進了焚化爐,總歸不吉利。并且,傳言焚燒會影響相片中人的身體健康,甚至影響運勢。我曾試著往婚紗照上倒酒精,結果只燒掉了一面,殘留下的一大片黑漆漆的油灰,幾天后才消散。另外,法律規定禁止露天焚燒產生煙塵污染的物質。”
“那么昂貴而精美的婚紗照真的一無是處了?”我有些絕望。
“也不盡然。我的一個客戶物盡其用,用結婚照在院子里給狗搭了個窩,還請我為他獨特的創意拍照留念,還將照片發給他前妻。看到那間我親手拍攝的豪華、精致的狗窩,我哭笑不得。那哥們兒說:‘就當十年的感情喂了狗。’”
我腦海中出現一個男人將一根肋骨狠狠擲向狗窩的畫面,那根骨頭不偏不倚撞到了照片上二人甜蜜的臉上,像一記嘲諷的耳光。
“婚姻如雞肋。”木頭一聲長嘆。
我有些動搖,仍負隅頑抗:“就算你說得都對,那人家憑什么相信你,把曾經珍貴的婚紗照交給你處理呢?”
“婚紗照承載的不僅是一段感情的點點滴滴,更是對愛情和婚姻幻滅后的絕望、痛苦與不甘。這些客戶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宣泄和一個可以終結過去的儀式。”
“就是儀式感,對吧?現代人不是都追求儀式感嗎?生日和葬禮、結婚和離婚都需要儀式,拍婚紗照是一種儀式,銷毀它同樣需要儀式。”
“太對啦!”木頭猛拍我的大腿,“你終于開竅了。”
“那么,啟動資金呢?”學金融的我問。
“不需要太多成本。拓展業務只需要開視頻直播、在網上發帖、發朋友圈等,再合資買一臺粉碎機,我們偉大的項目就可以啟動了。”
如同一個新生兒一般,需要起一個驚世駭俗的名字,公司才能大火。為此,我們絞盡腦汁想了許多個名字——萬碎堂、碎碎念、破鏡閣、斷憶齋、滅相閣、斷夢小筑、破碎人生、葬愛家族……每一個都不吉利,每一個都被否定了。直到我們開著電視看無聊的肥皂劇,見到屏幕上跳出兩個粗黑的大字“劇終”時,木頭拍著我日漸稀疏的顱頂說:“就它了——劇終。”
“還沒開始就要劇終?”
“人最后的結局都是劇終——你也一樣。”木頭說。
我釋然。預備大干一場。
關于場地,直接啟用木頭倒閉的照相館。照相館本就是租用的廢舊廠房,稍事清理,便可用作“劇終”的施工場所。
至于收費,分為幾個套餐,價格最低的九十九元,還有一百九十九元,最貴的是三百九十九元。我執拗地偏愛“九”,希望所有相愛的人都能長長久久。
只是,再甜再苦、再長再短的故事,終究是要劇終的。
明月
那些相片上的記錄,被現實的馬車無情碾過,丟棄在遺忘的糞堆。
“劇終”店轟轟烈烈地開張了。木頭雄心萬丈地說:“我們是全國第一家首創的結婚照處理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們一定會火遍全國,乃至全世界!”
“可是,我們的生意越紅火,意味著離婚的人越多,這不就跟棺材鋪希望生意興隆一個道理嗎?”我慣于唱反調。我這個擅長遞刀子、潑冷水的不合時宜的人,難怪不討秋子喜歡。
面對我的質疑,木頭火了:“那能一樣嗎?我們不粉碎婚紗照他們就不離婚了嗎?我們是在幫他們完成婚姻的最后一步,讓他們給自己的感情一個交代,也對一段關系了斷舍離。”
劇終亦是開端。起初,“劇終”的生意舉步維艱。我和木頭在各大平臺開直播,大肆推銷“劇終”,卻引來一片罵聲。那些素昧平生的網民罵我們希望天下大亂、希望有情人分道揚鑣,并惡毒地詛咒我們早日關門。
我和木頭在煎熬中苦挨了四天。第五天,一條私信叮當作響。我慵懶地打開,看了一遍,又看一遍,隨即高喊:“開張了!”
第一位客戶是一位女性,不知年紀,她對個人情況諱莫如深,只說孩子的歸屬談好了,財產已分割完畢,銷毀完婚紗照,整個離婚流程才算全部結束。該女士極其謹慎,用QQ小號加我為好友,事無巨細地咨詢了三天后,才選擇信任我們。當天,我收到了她發來的快遞單號。
兩天后,三個巨大的包裹從天而降。我和木頭欣喜若狂,仿佛新婚。木頭還對著這三個碩大的箱子拜了三拜。小心翼翼地拆箱,幾幅婚紗照,單人的,雙人的,一應俱全。令人驚詫的是,除了婚紗照,潔白的婚紗、大紅的婚被,以及奢侈的婚鞋都一并寄了來。我跟女客戶反復確認,這三大箱物品是否要全部銷毀,她言辭激烈:“全部銷毀!越快越好!”她的每一句話末尾都加了一個大大的感嘆號,酷似決然高舉的利劍。
首位客戶,我堅持只收優惠價一百九十九元。客戶爽快地轉來二百元紅包。我退回了一元,并祝福她能找到真愛、天長地久。這一塊錢她并未收下。或許,她和我一樣不相信永久和永恒吧。
噴漆,粉碎,我和木頭兩個劊子手將客戶的相片處理后,又將婚紗、婚鞋等物件分批次粉碎,并逐一將視頻發給她。
我們滿懷期待,迎候客戶的夸贊。她打了八十五分的好評,至于被扣的十五分,她解釋道:“碎片會散落在空中,而我希望它化成齏粉。”
對一個人愛到多深、恨到多深才希望他化為齏粉?婚姻又是什么?一張床,一口棺材,一間牢房,一地青苔,一片沼澤,一抔齏粉。
如何讓一個人化為齏粉?若私自焚燒碎片,很快就會遭到鄰居投訴、物業制止,相關部門將紛紛上門指導和監督。
突如其來的瓶頸,幾乎使我們的“劇終”一開篇便要劇終。一夜輾轉反側。次日,木頭猛捶大門,并熱情擁抱了我。他一坐下,便開始拍他的腦袋和我的大腿。我知道,車到山前了。
“我有一個同學在電廠工作,負責焚毀垃圾。”
“趕緊約出來,爭取一餐飯搞定。”
事實上,我們緊巴巴的預算也僅夠請兩餐飯。當晚,木頭的同學如約而至。通常都市人約飯局都要故作矜持推托一番,但我和木頭兩個久旱的人一遇到甘霖,便餓狼般撲了上去,絲毫不顧及顏面。
那個白白凈凈的女孩,閃著調皮的笑。世界驟然亮了。
女孩嘴碎,喝一瓶啤酒可以嘮一整晚,那晚她喝了八瓶。我為她取名“碎碎”,她欣然接受。幾瓶“漓泉”下肚,雙方愉快地達成了協定:甲方將粉碎的婚紗照等物件交給乙方焚燒,每完成一單乙方可以提成百分之十五。
趁著酒勁,我好奇地問:“你一個姑娘家,為什么要干焚化垃圾的活兒?”
碎碎干了一杯酒,說:“干啥不是干?我不像你可以上大學,我跟木頭一樣,都是這個社會沒人要的垃圾。我爹媽托了關系費了老大勁才把我送進電廠,我不喜歡那工作,但也沒有更好的去處。”
“讀了大學也好不到哪里去,你看我,還不是失業了?”我抿了一口酒,感覺在喝潲水。
“你喜歡這份工作嗎?”木頭問。
“最開始特討厭,覺得是男人干的活兒。時間長了,竟慢慢喜歡上了。”碎碎邊說邊將啤酒瓶貼撕下來,揉爛,“我從小就喜歡撕紙,經常被我媽罵。被老師批評,被同學欺負,考砸了,我就撕紙,上課時在抽屜里撕,回家后躲在房間里撕,撕完怕我媽看見,又躲進衛生間燒碎紙片……你說,我是不是個天生的垃圾焚燒工?”
碎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一片晶瑩的形狀不規則的雪花。
“我從來沒有走出過這座小城市,沒見過雪,把碎紙片撒到空中,就像下雪一樣……”
碎碎邊揮舞著雙手,邊張牙舞爪地找服務員借紙。服務員遞過來兩張白紙和一支筆。碎碎接過,三兩下熟練地將白紙撕成了碎片,又歡快地撒向空中。紙片紛紛揚揚地落到我們頭上,又落進我們冒著熱氣的湯里。碎碎旁若無人,快活地吟起了詩:
“一想到一生中后悔的事,雪花就落滿了南山。”
我并不想糾正她,落滿南山的應該是梅花。或許,她的世界落滿了皚皚雪花。
一直喝到餐廳打烊。將碎碎平安送到家后,我問木頭:“這女孩兒靠譜嗎?”
“放心吧,這活兒又臟又累,沒幾個人愿意干,所以她這崗位幾乎沒人管。能接私活賺外快,她自然樂意。”
“你說,她話怎么那么多?”
我想起了秋子,婚前她也像啾啁的小鳥,婚后卻變成了沉默的羔羊,或者咆哮的獅虎。
“她的工作接觸的不是人,而是垃圾,她成天接收各種垃圾,堆積久了無處釋放。滿肚子話不能對人說,只能對垃圾傾訴,換誰能受得了?”
“相片碎片焚燒后可以適當處理,既可按危險廢物填埋,也可以固化穩定化處理。垃圾焚燒后產生的飛灰經固化穩定化后,體積可縮減到原來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碎碎曾說。
這些專業術語我們不懂,也不想懂,正如我不懂婚姻這東西。
一些東西結束了,更多東西還將繼續。
窗子
接單,銷毀,焚燒。生活就是一個自我康復的過程,縱使愛情的頑疾不定期發作。
此后的日子,我的生活被婚紗照所填充。無論是幾千元還是幾萬元的婚紗照,結局無一例外是被投進粉碎機。碾碎之后,再送進電廠焚化爐,化作塵埃,化成齏粉,直至煙消云散。
頭一個月,“劇終”只接了十五單。頭一季度,總流水不到五千元。這個破碎的店經營得比我的婚姻還慘淡。
“還繼續嗎?”我問木頭。
“我們有退路嗎?”
我和木頭更加賣力地在網絡上吆喝,卻收效甚微。
“其實我們拓展業務還有一個好辦法。”木頭的車又開到了山前,我一臉疑惑。
“你老婆,不,你前妻不是婚姻登記處的嗎?”
“讓我找她?不,不……”
“這是條捷徑。離了婚的人誰愿意把前任的結婚照留在家里?直接扔吧,不吉利,還會泄露隱私;剪掉吧,根本剪不動,捶都捶不爛;燒掉吧,容易壞了風水;放在家里吧,礙眼還硌硬人。所以,我們的‘劇終’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你說的都對,可讓我找秋子,我辦不到。”
“你打算跟她老死不相往來嗎?”
在木頭的慫恿下,也為了五斗米,我觍著臉聯系秋子。本想請她吃飯,她卻開門見山地說:“吃飯就免了,有事直說吧。”
我極不自信地提出了我的想法。本以為她會劈頭蓋臉地將我怒斥一通,再講一番大道理,她卻撲哧一笑,說:“你終于睡醒了。這么多年,你始終沉浸在你的世界里,你所有的收藏不過是用以自保的堅硬的幌子。恭喜你,你終于開始粉碎自己了。”
有了秋子的加入,我們的業務充實了些,但打一百個電話也僅能成交四五單。剛離完婚的人多半在氣頭上,一接到外人的電話,仿佛身上丑陋的傷疤被人偷窺了、揭開了,遂惱羞成怒地謾罵一頓方才解恨。木頭提議給秋子的提成同碎碎一樣,十五個點,我卻強硬地提高到了二十個點。木頭屈服了,還揶揄道:“不忘舊情只會傷到你自己,不真正粉碎這段感情,你永遠沒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我試圖通過業務關系,彌合同秋子的關系,秋子卻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除了談業務,絕不浪費半分感情。
不知為何,在“劇終”苦撐半年之后,我和木頭的視頻突然火了,轉發量高達二十多萬次,評論也有八千多條。我受了驚嚇,不知如何是好。木頭興奮得開了瓶他珍藏了十五年的茅臺。我接過昂貴的茅臺,翻來覆去地研究。我雖非行家,但收藏多年,早已煉就火眼金睛。見木頭一臉真誠與亢奮,我欲言又止。當晚,我倆干了這瓶酒,次日,我頭痛欲裂。
“木頭,你頭痛嗎?”
“我頭痛該怎么處理這些雪片般的訂單?哈哈哈……”
木頭爽朗的笑聲飄蕩在“劇終”的粉碎間。一夜之間,我們的訂單暴增了三百多單。我和木頭忙成兩個陀螺,輪番回復客戶的信息,下單,收款,收貨,噴漆,粉碎,熔化,也將自己熔化。
我們一邊被罵得狗血淋頭,一邊被擁躉們稱為“銷毀師”“婚紗照擺渡人”,還有“愛海捐軀客”。夜深人靜時,我孤枕難眠,渴望將這具空心的軀殼捐給那個我割舍不下的女人。
夢
婚紗照每天都在重復,翻了一頁又一頁,只是換了一個文本。沒有憧憬,沒有懷舊。
我和木頭轟轟烈烈地開始了焚毀,為了劇終。
每天加我們為好友的客戶有近百人,有真心咨詢的,有好奇心驅使來驗證這個行業的真假的,也有將我們當成心理咨詢師來免費咨詢的,更有專門來罵我們傷風敗俗違背公序良俗破壞社會治安的。有當即痛快下單的,有咨詢后幾個月才下定決心的,也有事后反悔的……
咨詢者中,惜字如金的反倒是下決心要銷毀的,滔滔不絕的多半在猶豫,沒有下文。一個女客戶從晚上九點聊到深夜一點半,最終也沒下單。
木頭憤憤不平地說:“得虧你性子好,要是我,早就拉黑了。”我用一句很俗的話回答他:“淋過雨的人,也希望給人送傘。”
實際上,我的傘已千瘡百孔。為了更好地服務客戶,我還讀了許多心理學的書。久病成醫,有時我覺得我的頑疾不治而愈,有時又覺得有個結始終沒打開。
對客戶,我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從不催促客戶,甚至隱隱希望被放鴿子,只希望客戶不后悔自己的抉擇;第二,絕不打探隱私,僅傾聽客戶自愿分享的故事。
每一個故事都是悲傷的,每聽一個故事我的世界就會下一場雨。我像一個枯朽的樹洞,客戶關于婚姻、愛情的埋怨和憤慨,無休止地向我傾倒。有好幾次,我快承受不住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一身爛泥、鍋底漆黑呢?
但天再黑,總會透亮的。
從收快遞、開箱,到噴漆、銷毀、焚化等一系列環節,我和木頭都會嚴格拍照片、拍視頻記錄下來,發給客戶,客戶還可以通過微信視頻見證整個銷毀過程。我們奇異的工作還引來七名客戶親臨現場,監督銷毀過程。
客戶多半為女性。也許女性心思更細膩,愛憎更分明。
北方某地有一種風俗,人去世了個人物品也要一起燒毀,但合照無法燒掉,留在家中也會睹物思人。因此,北方的生意超越南方。
客戶寄來的婚紗照,有從未拆封的,也有被千刀萬剮的,精美的婚紗照上,新郎的臉被劃得傷痕累累,有些還被畫上一只大大的烏龜,更有甚者,在男方頭上畫了一頂大大的綠帽。這一幕幕,令我忍俊不禁,笑著笑著便笑出了淚。這頂帽子,我也曾戴過。兩年多過去了,我依舊摘不下來。
客戶的要求千奇百怪。有的要求給自己噴白色漆,卻給對方噴綠色漆。自己清清白白的,卻要讓對方“綠”一輩子。還有講究風水的,指定在某個時辰銷毀,早一分鐘晚一秒鐘都不行。這些奇葩的要求令我和木頭百思不得其解,也不便多問,只能照單全收。還有咬牙切齒地催促立即銷毀的,似乎“毀尸滅跡”了方才解恨。
來自武漢的一個少女,讓我買一束香水百合放進粉碎機里一起銷毀。她講述了一個悲慘的故事:未婚夫在疫情期間不幸離世,他生前最喜歡香水百合。她想以愛的信物同他告別。
一個男孩將離世的寵物貓的用具寄來,貓包、貓砂盆、貓爬架,還有貓咪生前穿過的衣服等。他沒有選擇轉讓或贈送,而是以這種方式同天國里的愛寵道別。
訂單有加急的,也有反悔的。一個男人頭一天心急火燎地說:“趕緊燒,馬上燒,一分鐘都不能耽擱!”次日中午,又風風火火地打來電話說:“把婚紗照寄回來吧,我媳婦回來了。”那一單,我沒有銷毀,卻收到了匯款。這是一筆幸福的訂單。
自此,接到訂單后,我都會同客戶反復確認是否確定要銷毀,會不會后悔,并且盡量拖延幾天。拖延期類似離婚冷靜期。銷毀的不僅是婚紗照,更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感情走走停停,遲疑著拖延是會走到終點,還是中途下車呢?
這一年多,我銷毀過發黃的老舊照片、打著補丁的浴巾、記錄禮金的賬本。印象最深的是,一張照片上還有孕婦,男客戶堅決要求銷毀,似乎只要跟對方沾邊的,統統都不想要了。可那個無辜的未出世的孩子呢?
有一次銷毀照片時,一張年輕男性的臉剛好卡在機器中,“他”直立掙扎著,仿佛一個溺水者在大海中掙扎求生。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我試圖將“他”從粉碎機中搶救出來,木頭卻殘忍地將“他”摁進粉碎機里。這張扭曲的臉此后多次出現在我夢里,撕扯著我的睡眠。
一名中年婦女聯系我,希望加入我們的團隊。她聲稱自己近期失眠,疑似抑郁了。她多次觀看我們的視頻,尤其喜歡看粉碎東西的場景,一聽到破碎的咔嚓聲,壓力隨即緩解。中年婦女的話讓我想起了碎碎,她們碎裂得讓人心疼。我心一軟,想邀請她加入,木頭卻極力反對說:“首先,我們目前的業務遠沒達到可以請人的地步;其次,你怎么能保證她精神沒有問題?還有,萬一她出了什么事,你能負得起責任嗎?”我被木頭嗆得啞口無言,此事便作罷。
我習慣在焚毀時放音樂,有些是客戶自選的,有些是我依照心情挑選的。一位客戶選了一首喜慶的《今天是個好日子》,還有客戶選了《明天我要嫁給你》。
為了拓展業務,我突發奇想,在銷毀的過程中念出客戶想說的話,像在追悼會上念悼詞一樣,舉行一場正式的告別儀式。這項服務收費僅二十元,但最終也沒有哪位客戶選擇該服務,我的異想天開也落了空。
最重的包裹有一百二十多斤。過去了的有多重?過不去的有多重?
或輕或重的婚紗照,盛著暮光的黑漆漆的鏡頭,將各色噴漆潑在它們身上,空洞的美好就像玫瑰花一樣,一瓣一瓣地飄浮在乳白色的天幕上。照片上被噴了黑漆的人,渾身散發著刺鼻的油漆味,未干的黑漆順著照片流淌,在親密依偎的新人之間淌出一道刺眼的淚痕。
也許,這既是結束的墓志銘,又是新生的里程碑。
就讓那些過去了的和過不去的安全地徹底地消失。
劇終未遂
相片外,千篇一律的日子從熙熙攘攘的腳步中溜走。
離婚兩年了,這張婚紗照也在我獨居的另一套小居室墻上孤零零地掛了兩年。自秋子第一次對我說出“離婚”二字時,我便開始極力抵觸婚房里婚床上方掛的那幅碩大的結婚照,橫豎都看不順眼。面對這幅巨大的婚紗照,我用顫動的雙眼打量著從前與此后的生活。它比我的身體還寬闊,我只看到了它背后絢爛華美的生活的冰山一角。
我凝視著那張結婚照,半晌,才默然道:“開始吧。”
“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才能建設一個新世界。”木頭極盡煽情,將一管噴漆遞給我,我遲疑地接過。這張巨幅結婚照,見證了我和秋子五年的婚姻。照片上的秋子輕舞翩躚,嘴角揚出的那個笑,如今看來,更像是一串輕蔑的戲謔。
“你這個人不壞但也沒有太大的出息。除了倒騰舊物你別無所長。跟木頭這樣的混混在一起你只能混一輩子。我當初瞎了眼才會跟你結婚……”
我和秋子本應養在花瓶里的婚姻,卻被種在土里、長在樹上。
有些人的婚姻是一口險惡的井,里面棲居著廝殺的人們,充斥著混沌的噪聲。我聽到或感受到這不安的回音時,就會被里面散發出來的模糊而焦躁的悲傷所吞沒。
沉淀了五年的抱怨,從照片上生出的喉舌里,一一彈射到我身上。輕蔑、嫌惡從秋子眼中射出,穩狠準地擊中了我。我將燃燒著的熾烈的火焰盡數傾瀉在秋子身上,朝著照片上她的臉噴出了第一下。她如花的笑靨變成一張滑稽的熊貓臉,我積蓄已久的悲傷被突如其來的快樂一點點吞噬。我繼續噴出第二下、第三下。噴到第五下時,秋子仿佛從照片上消失了,化成一個黑乎乎的影子。
我顫抖著手接過噴漆,朝照片上的我噴了三下。
“你最近有點疲軟,射程不夠。”
木頭揮拳捅了我一下,捅出了我的一汪眼淚。陪伴了我近兩千天的結婚照,已經化為兩道漆黑的影子。一想到影子即將進入粉碎機里,從此陌路,我便心如刀割。
粉碎機張著血盆大口,試圖將照片上的我和秋子吞噬、撕爛、嚼碎,然后像吐穢物一樣吐出來。
“進去吧。”木頭說。
這句話如此熟悉。七年前,秋子說,進去吧。隨后,我被她慫恿進了民政局,跟她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拍婚紗照,又一起走進大紅的婚房。一道道深不可測的門,將我吸進去。如今,我想逃離這重門了。
照片上面目模糊的我和秋子,臉對臉、手牽手,共同走向粉碎機。當冰冷的機器一點點殺死照片上的LOVEISFOREVER時,我的雙眼潮濕了。最先消失的,是“愛是永恒”。永恒過后,照片上我和秋子即將成為萬劫不復的碎屑。
“不!”我沖上前,奮不顧身地將我和秋子的殘骸照片搶了出來。
木頭憤怒地吼道:“你不要命了!”我和秋子被封存在咖色的亞克力相框上,我緩緩地撫摸著。那極致的凹凸感,像鉆石的表面。可鉆石不就是用以烤火的炭?
我決然將半截相片推進粉碎機中,像奔赴一場注定犧牲的戰爭。從頭開始,接著是身體、手、腳。伴隨著噼噼啪啪的碎裂聲,照片上我和秋子這對穿著黑西服和白婚紗緊密相擁的戀人,就此消失了。
相片被粉碎的那一刻,我仿佛聽到了骨頭碎裂的聲音。二十年前,我的尺骨粉碎性骨折時我也有這樣的感覺。相片一點點被粉碎,我全身的骨頭隨之隱隱作痛。不知為何,我竟生出一種扭曲的快感。
我和秋子在相片上,在悲喜之間進進出出,一堆堆碎片從粉碎機里釋放出來,平躺在地上,像是緬懷過去的美好時光。
“劇終”的宗旨是“我們會讓這些東西消失得干干凈凈,就像從沒來過一樣”,可為什么那些碎屑像漫天的霧霾,迷住了我的眼和心?
木頭將我銷毀婚紗照的過程全程錄了像,并將視頻傳給了我。我剛想打開,右手食指痙攣了一下,我立即刪除了。事后,我有些后悔,如果將這段視頻發給秋子,她會有何感想?
我也曾問過木頭:“你一個開照相館的,有那么多相片,為什么非要粉碎我的結婚照?”木頭嬉皮笑臉地說:“我一個大齡未婚男,沒有結婚照可以粉碎呀。”我將一腔哀怨夯在他肩頭,他逃得飛快。
其實我本想反問他為什么不粉碎他初戀的照片,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我和木頭好得像親兄弟。他眼見著我考大學,工作又失業,結婚又離婚,我見證他高考落榜后開了一家照相館,從開業到倒閉。木頭堅持單身,可身為發小,我知道他心里藏著一個人,他從不提及,我也從不過問。只一次,他相親歸來,喝得找不著北,抱著我哭得鼻涕眼淚一大把,他語無倫次地說:“今天見的這個人,怎么那么像我的初戀?怎么那么像……感情這把刀,一刀下去,直捅心窩,你說,心上的那把刀插到了最深處,傷痛多少年才能痊愈呢?后來,我遇到許多人,來來往往的,但沒有一個人是她,沒有一個人能代替她……”
我無言以對,默默地拾起地上的美工刀,在我和秋子面目全非的照片碎片上畫了一個大大的×。
“真的要燒得干干凈凈嗎?”在我和秋子相片的碎片進入熔爐之前,我問木頭,又帶著幾分哀求。
“如果你用盡全力都沒法保護它,不如讓它平平安安地離開。”
走吧,該走了。我狠心地將重達五斤多的相片碎屑親手送進了熔爐。一麻袋殘破很快化作一堆灰黑色碎屑。
它們提前為我的婚姻完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葬禮。
斷章
生活是一座橋,一頭連著我沒有的,一頭連著我不想要的。
一日,木頭來到店里,一本正經地說:“馬尾,這個店全盤交給你了。”
我大驚道:“才剛開始就要劇終了?”
“我要結婚了。再繼續粉碎下去,我怕我找不到媳婦了。”
“你的準媳婦是碎碎吧?”
木頭狡黠地一笑。
木頭走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事實上,自婚后第三年起,我便開始委頓,根本無法滿足秋子。我不忍心看到秋子在漫漫長夜里長吁短嘆,瞪著一雙澄澈的大眼睛,望著天花板到天明。所以,我向秋子提出離婚,也為自己保留最后一絲尊嚴。
奇怪的是,近期每粉碎一幅結婚照,我身體里的男人便會活轉過來。眼見著結婚照從硬挺到粉碎,我的那話兒也由軟弱變得剛強,接連三天都是如此。
日子在不期而遇的晨晨昏昏中逝去,就像一串只剩枝丫的葡萄,被人僥幸撿拾,躲進角落悻悻吃完。
隨著視頻的熱度下降,我的訂單也漸漸地少了下來。平均每月可以收到一百二十多個訂單,刨去人工費和租廠房、購噴漆的費用,以及碎碎、秋子的提成等成本,每月的收支基本能持平,夠我和木頭喝幾頓酒了。
一轉眼,我跨過了不惑的門檻,身邊陸續有因為心肌梗死、腦梗和車禍去世的人,朋友圈也有些人猝然離世。“趁現在,趁還活著,能愛就愛吧。明天還不定是風是雨呢。”木頭在電話里說。
是風是雨,活著就好。
半年后,木頭丟了魂似的回到“劇終”,頹喪地說:“劇終了。”
我望著他手里的婚紗照,問:“客戶的?”
“不,我的。”
晨光打在金色的相框上,為框內的人鍍上了一層現實而傷感的微笑。喜悅和神秘漸漸地從他們臉上褪去,化為平靜和安寧。
【作者簡介】徐一洛,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屆高研班學員。廣西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作品散見于《作家》《十月》《大家》《民族文學》《小說選刊》《思南文學選刊》《紅豆》等刊物。發表長篇小說《覓兒》,出版小說集《歡歌》《沒有圍墻的花園》和長篇小說《等風來在世界彼端》等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