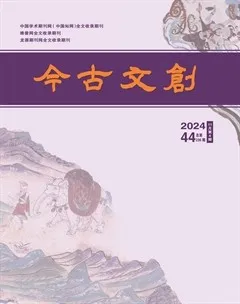《流俗地》中的“ 死亡書寫 ”
【摘要】黎紫書是東南亞華文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作家,《流俗地》是她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黎紫書將故事展開的地點——錫都視為流俗之地,敘述視角聚焦于一群社會中下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對小人物而言,死亡無疑是生命中的大事。小說中的死亡書寫所占篇幅甚廣,具有深化作品藝術內涵和啟發讀者在思考死亡這一超越國境、地域、語言、族裔、文化等層面的普遍命題的意義,詮釋了黎紫書的生命意識和死亡觀念,寄寓了她在對人的關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肯定和探尋。
【關鍵詞】《流俗地》;死亡書寫;黎紫書
【中圖分類號】I3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44-002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4.005
王德威曾如此解讀《流俗地》的標題,“黎紫書將錫都比為流俗之地,一方面意在記錄此地的浮世百態,一方面聚焦一群難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1]。但錫都并非全是市井俚俗的,錫都也有著以拿督馮為代表的上流群體,《流俗地》并未聚焦于他們的原因在于:對于流俗地中的小人物而言,錫都的陽春白雪見不到、接觸不到,流俗的錫都,其實只是這群小人物印象中所能觸碰到的社會底層視野下的錫都。《流俗地》沒有宏大敘事,也沒有出奇制勝的傳奇,娓娓道來的只是馬華市井凡俗生命幾十年風雨悲歡的一個個故事,卻打動了整個中文世界,令讀者感受到溫柔、悲憫和悲傷。很多人一生只是活幾個瞬間,尤其對于俗人、小人物而言,死亡無疑是生命中的大事件,黎紫書用日常生活敘事取代宏大敘事,用平民百姓取代英雄人物,小說中的死亡書寫其實是在對人的關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肯定和探尋。
死亡和疾病一直是文學創作中永恒的母題,現代小說中形形色色的死亡敘事,都包含了作家對“死亡”這一命題的認識和思考。死亡問題為何如此重要?首先,死亡是必然的,是生命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正是由于誰都無法逃脫,人們會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更大的生命價值,才會去審視死亡的含義,因此對死亡的審視可以被視為人類認識世界、探求本我的一個途徑。再者,人無法直接感知死亡,死亡因而具有神秘性。維根斯坦曾言:“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沒有經歷過死的。”[2]對于人類在經驗上無法感知的“死亡”,作家在文學中的表達往往是“想象性”的。黎紫書在后記中稱自己是帶著“活不下去的恐懼”來寫《流俗地》的,而“最終寫了稍微超過二十一萬字,其中三分之二便是在這種死去活來,每日誠惶誠恐的狀態中寫成的”[3]153。創作時,黎紫書一邊承受著病痛,一邊帶著對死亡的恐懼,故而《流俗地》中的死亡書寫一定會帶有她對死亡的獨特感觸與領悟。
一、《流俗地》中死亡書寫的類型
死亡具有普遍性,但死亡的方式是不同的,死亡的必然性與敘述言語的復雜性決定了死亡書寫在文學中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流俗地》中的死亡書寫類型豐富,二十萬字的小說中與死亡直接相關的內容已有兩萬多字,幾乎占了全書篇幅的十分之一。小說中涉及的死亡人數眾多,光是有名有姓的就有:奀仔、何門方氏(方亞鳳)、梁蝦、梁金妹、拉祖、卡巴爾辛格、亨利七人,更不用提“樓上樓”無名無姓的二十五位自殺者以及嬋娟學校自殺的女學生等。小說中關于死亡的敘述有些詳細完整,有些則簡略隱晦。
小說中敘述完整的死亡大致包括衰老死、疾病死,以及意外死亡。其中衰老死的代表人物為方亞鳳和梁蝦,蕙蘭、懺悔者兩章詳細描述了何門方氏“壽終內寢”的死亡場景,南乳包一章則寥寥幾筆便簡單完整地敘述了梁蝦的死亡。疾病死的代表人物則是梁金妹,良人一章敘述了梁金妹因病走向死亡的過程:“那時梁金妹已被診斷出直腸癌,終日腹痛便血,人越來越干癟,藥越用越重,已自知將死,仍想撐著再過一個新年。”[4]69顧老師一章也補充道:“梁金妹的癌癥一被發現即來勢洶洶,很快去到末期,被醫院逐回家中,讓她服用嗎啡加阿司匹林止痛等死。”[4]117因疾病而被提前判決的死亡在亡者與生者之間劃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精神鴻溝,在死亡即將降臨的背景下,患病人物的行為不免得到了放大和關注。
意外死亡是最能展現生命“無常”的一種方式,小說中意外死亡的方式主要為車禍,代表人物是奀仔和拉祖的偶像卡巴爾辛格,意外死亡的人物的身份會被特意強調,作為父親的奀仔、作為政客和公眾人物的“日落洞之虎”,他們的意外離世或會影響生者的生活軌跡,或作為對照引發讀者的思考。謀殺也是一種意外,拉祖之死便是典型的謀殺,這也是小說中唯一對死亡過程進行細致敘述的片段。相較于死于車禍的“生命無常”,這種兇殘血腥的暴力謀殺無疑更具有沖擊性,這種不和諧的悲劇,以震撼人心的力量直接調動起讀者的情緒。
自殺死亡是特殊的意外死亡,是相對于生者的意外,是對自己的謀殺。小說中自殺死亡的人物包括嬋娟的女學生、“樓上樓”以懷孕年輕女孩為代表的二十五名自殺者等。自殺揭示了個體對于生命的態度,但據此僅能了解人物的冰山一角,為何選擇自殺、自殺前經歷了什么才是藏于冰山之下的關鍵所在。自殺事件引起的小說中其他人物或群體的反應,也是作者死亡觀念和死亡意識的體現。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存在大量敘述缺失的死亡書寫,主要包括潛在的和間接提及的死亡書寫。潛在的死亡書寫包括因失蹤、發瘋等原因而被“當作”死亡,代表人物包括大輝和關二哥的弟弟,從生理角度上講他們當然活著,但以他人的視角來看,他們已經與“死人”沒什么兩樣了。潛在的死亡書寫還包括“獨特的”死亡體驗,如小說中春分的自然流產和銀霞的人工流產,其實都是隱含著生命的離去,對于小說塑造女性形象而言,這種在醫院中的死亡體驗也展現了女性人物對生死和日常生活之間關系的思考。
非人類的死亡雖往往不被重視,但也是死亡書寫的一種形式。小說中非人類的死亡包括“樓上樓”印度姊妹之母殺貓以及下棋過程中“死去”的棋子,這些非人類的死亡是人死亡的延伸,與小說中的眾生隱隱有著對應關系。社會性死亡往往不會被一般的小說強調,但群像戲的《流俗地》中出現了細輝為救命喝羊屎、馬票嫂因家貧出丑而被叫作瀨尿燕這兩處明顯的社會性死亡的場景,這也可被視為潛在的死亡書寫,主要起推動情節的作用。
二、《流俗地》中死亡書寫的藝術性
小說中死亡書寫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敘事結構、情節安排和人物塑造三個方面。從敘事結構來看,死亡書寫的顯著作用是構建出明確的時間流變。小說并未按自然時間進行線性敘述,而是順敘、倒敘交叉敘述,用一個個物件或地名等符號喚醒人物的一個個記憶碎片,漸漸拼湊出一個個完整的故事,產生物是人非的滄桑感和時空錯亂的恍惚感,讀者往往需通讀全書,來回翻看前篇,方能恍然大悟。小說中的敘述往往基于“小人物”生命中的“大事件”,如敘述細輝的人生:“幾乎每年一件大事——便利店開張,新居入伙,與嬋娟結婚,生下女兒小珊,細輝馬不停蹄,連著當了老板、屋主、丈夫和父親。”[4]82黎紫書通過一系列死亡書寫,包括奀仔之死、梁蝦之死、梁金妹之死、跳樓女學生之死、拉祖之死、何門方氏之死,最后再到顧老師杏壇友人的追思會,構建起銀霞所經歷的一條較為清晰的主時間線。其中除了何門方氏之死的時間可以通過報上訃告中“慟于二零一六年八月廿四日”明確,還可以通過紅白事一章中梁金妹死后七年何門方氏離世、奔喪一章中拉祖死亡后五年何門方氏葬禮舉辦等場景中推斷出其余死亡所在的時間。
死亡書寫明確了小說中的時間流變,使得小說的市井敘事歷程更為清晰。這種敘事結構也有其他好處,何門方氏、拉祖等人在主時間線上早已經“死”了,但在故事時間的不斷回溯中,他們還是能經常出現在后文中,仿佛“沒死”,這消減了人物離世的悲傷感,也淡化了人物死亡對整體敘事的影響。
《流俗地》中的死亡書寫充分顯示了黎紫書講故事的技巧和能力,小說中的死亡往往以記憶疊加補充的形式呈現出來,在表現技巧上呈現出重復與復調的特點。何門方氏、梁金妹、拉祖、嬋娟女學生、奀仔等人的死亡都是在多個章節中進行明顯的重復敘述,如梁金妹的死亡在良人、紅白事、顧老師、惡年四章中反復出現,奀仔的死亡則在奀仔之死、蓮珠、紅白事四章中重復。這種重復敘述并不是機械無端地重復,而是非常具有目的性的,在情節的重復中,許多細節被不斷還原。黎紫書每次所敘述的死亡記憶的不同都與回憶者當時的處境相關,隨著這種回憶碎片的不斷疊加,文本的意義價值也變得復雜起來,如從奔喪、顧老師兩個章節中,銀霞關于已經死去的拉祖的記憶在特定的“九皇爺誕”這一場景中出現,簡單一句“拉祖死了,居然就這樣死了”[4]120,讀者便會感受到銀霞情緒的突然爆發與她如鯁在喉的悲傷感。
復調本是音樂術語,巴赫金借此區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傳統歐洲小說模式的不同:“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之眾多,恰恰是將那些擁有各自世界,彼此平等的眾多意識,在這里組合成某種事件的整一,而相互間并不發生融合……復調的藝術意志就在于將眾多意志組合起來,在于形成事件。”[5]不同的敘述者,不同的視角,在敘述中發揮不同的藝術功能。
何門方氏、拉祖之死的敘述明顯呈現出復調小說的特點,何門方氏之死在蕙蘭、蓮珠、懺悔者、紅白事四章中得到敘述,由不同人物的視角觀照同一客觀世界的死亡,蕙蘭、蓮珠、細輝、銀霞等人對其死亡的感受不同,他們各有心思又各有獨特反應:蕙蘭是冷靜甚至冷酷、蓮珠和細輝是真情流露的傷感、銀霞和馬票嫂則是感慨回憶的旁觀者心態。拉祖之死使銀霞、細輝心痛,但讀者感知其死亡的方式并不只是銀霞、細輝的反應與奔喪情節,還在于詢問巴布理發店關門時關二哥平淡的回答之中:“巴布全家出門去了,應該是到都城吧。關二哥說。他的小兒子死了。”[4]109甚至連拉祖死亡的場面也是由鄰居轉述出來的,以人稱轉換的方式來完成對死亡敘述的跨越,這種由眾人的記憶彌漫出來的敘事使小說避免了單一視角,每個人物都是生動的、活生生的,敘述靈動、流動而充實,全方位投射了眾聲喧嘩的馬華社會。
小說中的死亡書寫對情節也有頗多作用。一是推動情節發展,除了敘述完整的死亡書寫對情節發展有顯著影響之外,黎紫書也用敘述缺失的死亡來引出關鍵事件或者物件,這些一筆帶過的死亡其實是后續故事得以展開的關鍵。如“有眼無珠”的女鬼引出跳樓的懷孕女孩,再引出大輝家中做法事、大輝去日本謀生等種種事件;與顧老師關系復雜的亨利的死被隨便帶過,只是為了引出顧老師的跑車,銀霞和顧老師乘此車出行、經歷了看普乃在車下玩耍等事件,兩人的心逐漸靠近;顧老師友人追思會也引出了銀霞與顧老師出行感情升溫和受困電梯等重要事件,這些敘述缺失的死亡書寫使情節敘述緊湊而流暢。
二是通過死亡書寫來塑造人物形象,如通過反復出現的何門方氏之死塑造出理性但冷漠的嬋娟、懦弱卻溫柔的細輝、重情重義的蓮珠等眾生相;通過多次描述梁金妹對身后事的交代“晚間記得客廳和門廊要亮燈;門外多放一、兩雙男人的鞋子……”[4]117塑造出一個擔心盲人女兒的慈母形象;通過敘述大輝惹下情債導致懷孕女學生自殺、大輝自述吊銷駕照是因為撞死了大肚婆,兩次一尸兩命塑造出大輝自私自利、我行我素的惡棍形象。對生者來說,親人死亡嚴重影響人的成長軌跡,使人物形象迅速發生變化。奀仔之死對何門長子大輝來說太過突然,這強迫他快速由少年成長為男人來考慮一家如何在異國立足,他的心理不成熟、極端自負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特點的形成原因在此便得到了解答;而對何門小兒子細輝來說,父親死亡時有哥哥和母親,但母親之死意味著他不得不改變和成長,這使他從軟弱懦弱變得勇敢,這在其不遵從嬋娟意愿為侄女春分作保、無視嬋娟不滿幫女傭治牙上有所體現,也通過一路上一章中蓮珠姑姑的一句“嬋娟對我說呀,你媽死后你的性情大變,像換了個人”[4]142直接表現出來。
三、《流俗地》中死亡書寫的意義
《流俗地》中的死亡書寫充滿文化意義、社會意義和象征意義。首先是“白事”承載的文化意義,小說中的“白事”包括奀仔、梁蝦、梁金妹、何門方氏這些平凡的上一輩的四次葬禮和顧老師杏壇友人的追思會,這些死亡書寫反映了由獨特的地域文化所形成的文化語境。對這些“白事”的細致描寫體現出了中國傳統喪葬風俗進入馬來西亞后產生的變異,“奀仔的喪事是在新街場那頭的棺材街上辦的。組屋里畢竟各族混雜,諸天神佛全擠在一個院子里……只記得駱道院內設靈三天兩夜,他連日坐立不安,像一個紙扎公仔,又像一個花圈,在那靈堂內任人擺布。他的母親守在靈柩旁沒日沒夜地折紙元寶”[4]11。“銀霞的母親去世時未滿六十歲,白燈籠上以天、地、人之名義硬硬為她添足,可稱享壽”[4]103,梁金妹的喪事則顯示了喪葬文化在異國得到的保留。“紅白事”像是黏合劑,黏住了如今四散的人們,在這種生者的聚會中,生者們的集體意識得到再現和喚醒,成為價值與情感的共同體,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馬來西亞華人心中的中華意識。
喪葬文化往往也表現出民俗對人無形的控制作用,紅白事一章中銀霞的思緒從奀仔、梁蝦的喪禮“幾乎有點喜慶的氣氛”到梁金妹的喪事“人來得零落,也少有誰帶著孩子;無孩童活蹦亂跳滿場飛,便無父母大呼小叫,連念經的道士也死氣沉沉,鐃鈸聲有一下沒一下,聽著徒覺欺場”[4]103,再到何門方氏的喪禮“由嬋娟出面請來一隊佛教團體的人到府誦經,殯葬公司派來穿白衫黑褲,甚至還戴了塑料手套的人做招待,彬彬有禮地為賓客奉上茶水,紅豆沙……卻也像是在高級俱樂部里享受下午茶,賓客們無不自覺地降低音量說話,變成了三三兩兩交頭接耳,滿場竊竊私語”[4]103,這種喪禮日漸無聊不只是因為銀霞逐漸長大成人,更多是顯示出現代社會對傳統的沖擊。可無論是傳統的喪禮還是現代的追悼會,都給人一種尷尬、別扭和無聊的感覺,喪禮的“變味”不僅反映出黎紫書對于傳統與現代如何融合而進行的反思,更體現了馬華群體所面臨的族群認同危機。
死亡書寫也有著抨擊現實的社會意義。從黎紫書的死亡書寫中,可以看到一個男女權力失衡的馬來社會,從嬋娟的意外自然流產、到因“情債”而死的女鬼們,尤其銀霞的流產可以視為一種雙重謀殺,既是對孩子,也是對銀霞,“對面墻上的一臺冷氣機開得不遺余力,呼呼作響,仿佛這是停尸間,床上躺著的是一具剛解剖過了的尸體”[4]129,黎紫書從切身感受出發,從女性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處境的角度出發洞察社會,將生育等構成了女性生命磨難的父權社會中的外部因素揭露出來,展現出女性獨有的悲哀體驗。
從黎紫書的死亡書寫中,還可以看到一個正義缺失的馬來社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謀殺的少數族裔代表拉祖、“在死了二十五個人以后”才在“樓上樓”裝上的欄桿,這些或多或少都表現了社會的混亂、體現了當地政府或警察的無能以及對“非我族類”的人群所受到的傷害的無視;常在嬋娟夢中出現的因校園霸凌而自殺的女學生、垃圾箱中發現死去的棄嬰,也是社會百態中的一面,同樣反映了社會正義感和責任感的缺失。
而在拉祖之死與卡巴爾辛格之死的對照中,一個階級分層、族群分隔嚴重的社會也被展現出來,拉祖與卡巴爾辛格都是“遭遇橫禍,死于非命”,但媒體與社會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對于執業律師拉祖“在住家門前被砍殺這么一宗血案”“由于死者非我族類”,華文媒體的報道只占極小的篇幅,內容也單薄潦草,“沒有附上死者的遺照或其他圖片”;而作為偉人,“卡巴爾辛格的死訊則震驚全國,可謂舉國哀痛,連華文報上也刊登了許多天巨幅挽辭,大題非同一般”[4]106。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同一個社會之中,因為死亡之人地位的不同、所在群體的不同,二人之死所造成的影響差異卻無比強烈,這不由得引人反思。
小說中對于“潛在死亡”的書寫則極具象征意義。首先是以失蹤代替死亡,這里大輝和關二哥的弟弟雖都是失蹤,相似卻有差異。關二哥的弟弟因為一些精神上的疾病而被送往“紅毛丹”,在其親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死”去了;而大輝則是由于自己不道德的所作所為,而被視為“該死”。其實大輝之死與拉祖之死也是一個對照,拉祖也曾對細輝點評過大輝“說你哥這種人,還替這樣的人辦事,死于非命是合理不過的事”。而按照人們的一般意愿,拉祖這么一個正直的人理應比人渣大輝生活得更幸福,然而結果卻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尸骸,大輝好好活著甚至還關心政治要去給大選投票,拉祖卻被謀殺慘死,天命難料,展現出一種極大的諷刺感。
小說中有代表性的潛在死亡是細輝十二歲前的社會性死亡,為了在十二歲前治好哮喘,細輝被何門方氏強灌羊屎水,再在氣味消散后才敢于走出家門,但卻被關二哥等人或無心、或有意地在公眾場所提及此事,被嘲弄后發出無力的反擊,“‘你全家都吃屎!’銀霞聽到這一聲吼叫,覺得那聲音聽起來就像在喊‘救命’一樣”[4]60,一個孩子自尊心被擊碎其實就象征這個孩子生命中陽光、美好的一部分死去了,對異國的少數族群個體來說,外界的舉動會強烈影響自己敏感的神經,在族群混雜的地區,還是需要互相換位思考、溫柔地對待彼此,從而盡量能使不同族裔的人群可以和解共存,安安穩穩地生活在一起。
小說中動物或物件的死亡也極具有象征意義,這里以棋子為例:下棋是“鐵三角”羈絆體現的重要情節,棋子的死與生,顯示出了銀霞這一盲女形象的超越性。作為一名接線員,銀霞對全城路徑了如指掌,幫助所有要到達自己目的地的人指明前路,這簡直像是傳說中的先知,也難怪的士司機們議論她“前世一定是個傳教士,天天對人講耶穌”。在迦尼薩一章中,可以看到銀霞的神性流露非常自然,對于死去的棋子,“她用指頭觸摸那上面的紋理,動作很輕,仿佛在安慰它們,又像在施法想讓它們復活”[4]30,其悲憫之心如菩薩一般;而從下棋手法來看,銀霞戰勝拉祖總是通過“祭獻”棋子的方式以犧牲換取勝利,如馬獻九宮等,在這些情節中,銀霞不僅僅是棋局中的棋手,實際上棋子也是銀霞本人的象征。
拉祖之母迪普蒂總把銀霞視為象神迦尼薩的化身,“那些人生下來便少了條腿啊胳膊啊,或有別的什么殘缺的,必然也曾經在前世為別人犧牲過了”[4]66,拉祖也總在銀霞低落時問她迦尼薩的斷牙是哪個,銀霞之盲就是迦尼薩的右牙啊,“象征她為人類做的犧牲”,所謂前世后世之說當然是無稽之談,對于拉祖一家來說這不過是對可憐盲女的安慰,可對銀霞來說,犧牲的崇高感從此在心中扎根,此后即便作為生活這個大棋盤中的一個卒子,也要懷著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勇敢地面對生活,黎紫書所珍視的,認為可以使得各族之人和解的,也正是這一份善良與光明。
《流俗地》中的死亡書寫向人們講述了生命的價值所在,在死亡面前,生命的每一次震顫,都顯得如此有價值。正如黎紫書自己所言,“盡管寫的是偏隅地,馬華事,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也沒有聳人聽聞的事件和光怪陸離的社會背景,但無礙我們馬華作者寫出超越國境疆域的作品,打動整個中文世界。”[6]157通過對生活中無視國族、地域、性別、社會地位等外在條件而普遍存在的死亡書寫,通過對個體生命、個體尊嚴的關注,濃重的人文主義關懷得以彌漫開來,這便是這些發生在所謂“流俗之地”的故事能如此動人的原因吧。
參考文獻:
[1](美)王德威.盲女古銀霞的奇遇——關于黎紫書《流俗地》[J].山花,2020,(5):159.
[2](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賀紹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03.
[3](馬來)黎紫書.吾若不寫,無人能寫[J].山花,2020, (5).
[4](馬來)黎紫書.流俗地[J].山花,2020,(5).
[5](蘇)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顧亞玲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4.
[6]劉俊.黑暗·地方志·寫實/象征——論黎紫書的《流俗地》[J].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1):82-87.
[7]翟業軍.錫都就是錫都,馬華就是馬華——論黎紫書《流俗地》[J].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22,(2):43-47.
作者簡介:
張欣楊,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華文化跨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