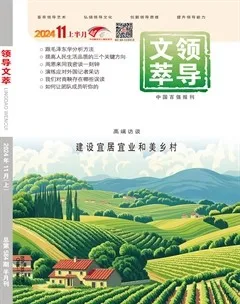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

同治六年(1867)秋,趙烈文在日記中錄下了曾國藩的感慨:“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
曾國藩從咸豐初年治軍以來,就一直吸納人才、擢拔人才,打敗太平天國后,他仍致力于搜尋人才,心情相當迫切。“人才實難,求者或不肯來,來者又非吾所求。”誠然,求宏才偉識者共濟時艱,殊非易事。
《清史稿》這樣評價曾國藩:“國藩又罷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曾國藩識拔人才以濟久遠,成功率很高,這一點,就連最不肯低首下心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服氣,道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確實難得。
為什么曾國藩能夠網羅如此之多的人才,在他墨绖從戎、艱難開局時期,就如同磁石吸鐵一般產生了人才匯聚的效應?王闿運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答:“曾文正成功大于胡(林翼)、左(宗棠),以其作侍郎有文學廉正之名,人肯從之游也。故欲求賢,雖折節禮請,不若以氣類感召。己既能賢,始可致賢士。”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賢者感召賢者,乃是必然之理路;何況曾國藩還輔以折節下士的誠意,效果之顯著更能產生馬太效應。
咸豐、同治年間,湘籍文武人才進入高潮期,據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統計,正錄一百零五人,除開洋將華爾、戈登等四人外,湘籍將帥多達五十五人,其他各省將帥合在一起共四十六人。在附錄中,湘籍將領的比率還要更高一些。另據《曾國藩幕府》一書的作者劉建強仔細梳理,曾國藩的幕府人才在仕途上的表現堪稱優異。直接出自曾國藩幕府的一品、二品大臣多達數十名,其中就有左宗棠、李瀚章、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楊岳斌、劉蓉、郭嵩燾、曾國荃、陳士杰、李興銳、陳寶箴這樣的佼佼者。曾國藩樂推佳士,禮遇精英,成效可謂壓倒古人。李鴻章賦詩為贊,“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真不是吹噓,事實就是如此。
曾國藩膺任兩江總督時,門下還集結了一批游幕的才子,他們或為獵取功名而來,或為增長閱歷而來,或為切磋學問而來,曾門四學士薛福成、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自不待言,周騰虎、王闿運、高心夔、莫友芝、趙烈文等人也極為出色。巴蜀才子李鴻裔倜儻風流、不拘小節,曾國藩欣賞他、善待他,簡直視同子侄。當年曾國藩幕府中有“三圣七賢”的名目,曾國藩給他們提供讀書治學的條件,吃住全部包干,還派送零花錢,至于繁雜的行政事務,很少讓他們沾邊。某日,曾國藩與李鴻裔在書房中閑談,中途出去見客,李鴻裔留在房間,從書桌上翻看到一篇《不動心說》,是池州進士楊長年的手筆——這位老儒頗有名氣,在“三圣七賢”之列。李鴻裔的好奇心被激活了,他倒要看看道貌岸然的楊長年怎樣自圓其說。文章是這樣寫的:“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于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李鴻裔讀完這幾句,頓時反胃作嘔。宋學派的偽君子個個緊跟在朱熹后面,整天唱響“存天理,滅人欲”的高調,淪為榆木疙瘩,竟忘乎所以。這篇《不動心說》只可欺騙三歲小孩子,用它來欺騙中等智商的成年人不免捉襟見肘。李鴻裔決定狠狠地嘲弄一下楊長年,他拈起筆來,在空白處題寫了一首打油詩:“妙曼蛾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多不動,只想見中堂。”題完詩,李鴻裔便離開書房,自顧尋快活去了。曾國藩會完客,回頭看見這首打油詩,全明白了。曾國藩立刻派人持手令去秦淮河邊的畫舫上召回李鴻裔。后者頗為忐忑,原以為只是戲謔幾筆,沒想到闖下大禍。曾國藩說:“我也知道,這些宋學派陋儒純屬盜取虛名的角色,他們言行相悖,知行脫節。但這些人在外面獵取豐厚的待遇,全靠虛名撐起門面,如今你斗膽戳穿他們的謊言,揭破他們的假面具,阻斷他們的財路,他們勢必會仇視你、痛恨你,又豈是尋常的睚眥之怨可比?可能會埋下禍根,令你家破人亡。你何不收斂一下直率的性子?”李鴻裔聽完曾國藩的教訓,仿佛冷水澆背,又如同當頭棒喝,頓時清醒過來,從此深自斂抑,不再以惡謔為快事。有人可能認為曾國藩太世故、太圓滑了,但他也是吃過許多暗虧后才明白過來:正直者的生存之道并不是時時處處與偽君子、真小人硬碰硬,明智的做法是盡可能繞開“路障”,在有限的空間里做一番事業。如果你總是站在那些偽君子、真小人的對立面,向他們宣戰,他們所施加的陰險打壓和野蠻報復就會令你煩惱無窮、痛苦不休——捅了馬蜂窩之后的那種境遇,可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得了的,除了害慘自己,還可能連累家人和朋友。人心險惡,世道坎坷,曾國藩一語喚醒夢中人,李鴻裔樂意受教,這是他的福氣。
對真精英要重用,對假精英也要厚養,曾國藩這么做,耐人尋味。他的做法具有很高的技術含量,涇渭固然分明,畢竟還得合流,真偽善惡莫不相反相成。
(摘自《湖南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