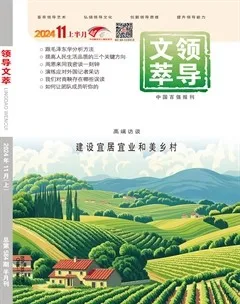如何利用好東南亞機遇
東南亞國家充滿活力,尤其越南、印尼等這些起點較低、過去10年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國家。從經濟總量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東盟10國合計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且經濟增速處于全球前列,比世界年均水平高出2個百分點。從發展序列看,東南亞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同樣引人注目,印尼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馬來西亞人均大約1.2萬美元,屬于中高等收入國家;而新加坡是典型的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8萬美元。
重視東南亞不僅是因為東南亞經濟蓬勃發展,市場潛力大,也因為中國面臨著來自美國的圍堵、遏制和打壓,因而也需要在全球尋找能夠替代美國市場的地方。面對動蕩不安的國際局勢,中國企業必須做好深耕東南亞的全方位準備。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之后,東南亞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中轉站”。中國大量產能在向東南亞轉移,中間品貿易即基于價值鏈的增加值貿易尤其發達,形成了更精細化的三角貿易模式。中國目前在東南亞的投資和經貿合作是全方位的,不僅有基礎設施、農業、水資源領域的投資,還有各種發展水平的產業合作,包括工業園區等特色內容等。
如今,不少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情況是,同時向中美兩頭推動進出口,因而需要新的理論來理解東南亞的貿易模式。
東南亞地位更加突出
中美貿易摩擦仍在持續且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東南亞的地位比以往更加突出了。以貿易為例,在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后,東南亞地區很快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23年,中國—東盟貿易額占中國外貿總額的15.4%,為第一大貿易伙伴,比2018年上升2.7個百分點。在動蕩不安的世界里,這是中國外貿方面難得的好消息。
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十分深遠。在此背景下,對美、對歐貿易增速出現下滑,中國企業主動加大了對東南亞的投入。過去5年,中國—東盟貿易額凈增加約2.5萬億元人民幣,而美歐合計僅增加了不到1.5萬億元人民幣的貿易額,特別是美國的增量不足5000億元人民幣。
中美貿易額占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已從貿易摩擦爆發之初的13.7%下跌至目前的11.2%,跌幅2.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迅速上漲,占比甚至超過亞洲增量的一半。一定程度而言,中國在美國市場的損失,通過東盟市場彌補回來了。
考察東南亞主要經濟體的進出口結構后,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的特點,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行業的比例是很類似的,即進口的產品和出口的產品都屬于同一個類型,兩者在進出口中的占比極為接近。
在典型的南北貿易模式中,發展中國家通常出口的是原材料,進口的是制成品,兩者分屬于不同的貨物范疇,因而進出口結構是很不同的。在增加值貿易主導的時期,越南乃至東南亞的地位有點像加工“中轉站”,xxKAYSLnGKdhXpaOLd6TOw==對中美都能出口一些適合的產品,因而這些國家難以選邊站,而是兩頭謀求利益。
零部件貿易實際上更有利于中小國家參與產業鏈,因為在一個工業體系不完整的國家,很難在本國完成一個產品的所有生產環節,很少有國家會追求大而全,各國均可以利用各自的特色謀求生產鏈中的位置。
冷戰結束以來,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大量進口原材料、出口制造業產品,機械、ICT和電氣產品出口成為價值鏈貿易的核心產業部門。信息技術加速發展,大大降低了溝通協調的成本,使得分工鏈條進一步細化和加強,不同國家可以根據自身在成本上的不同優勢,積極參與到價值鏈生產中。
由于強大的金融能力,美國在經濟規律的驅使下,大幅度壓低了本土的制造能力,而將其轉移到其他國家進行加工,本國則坐收金融之利。在美國霸權鼎盛時期,沒有國家挑戰這種分工秩序。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不再像以往那樣能提供足夠龐大的市場,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必須自謀出路,通過聯合自強,加強區域合作制度建設,將彼此作為部分損失了的美國市場的替代。
機遇與挑戰
東南亞人口將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結束之際超過7億。曾有機構預測,到2030年,東盟7億人口中的65%將成為中產階級,即大約4.5億人口。其中,每人每天的支出范圍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間,這會形成一個十分可觀的消費市場。對于那些注重消費市場的企業來說,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龐大群體。
審視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存在感時,總的來說要看到,中國增量快但存量還弱于美國及其盟友。東盟給出的數據顯示,美國仍是東盟最大的外資來源地,2022年為369億美元,占東盟當年吸收外資的16.4%。日本列第二位占12.1%,2022年為270多億美元。中國列第四位占6.9%,約為155億美元。
從國別來看,新加坡吸收的外資最多,占到東南亞吸收總量的近68%;其次是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三國合計約占東南亞吸收外資總量的28%;最后是中南半島的較貧窮國家。在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美國的投資額領先其他國家,中國僅在柬埔寨和緬甸的投資額占據首位,而日本在泰國的投資額占總量的30%以上。
不過,從行業領域看,美國在新加坡的投資很多集中在金融領域,這與中國、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有很大的不同。目前與中國企業競爭最為激烈的主要是日資企業,因而日資企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優先考慮。
日本企業在東南亞布局較早,形成了一套在當地經營的方法,其中包括通過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事先進行詳盡的調查。該機構在馬來西亞、泰國的分支機構均設立于1950年代末,在印尼的辦事處設立于1960年代。相較于服務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的這些輔助性機構,中國在這方面的準備和投入是遠遠不夠的。
日韓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比中國早了一至兩代人,它們下沉的程度比中國企業要深得多。在雅加達這種大城市,可以看到華為這些大企業的廣告,但到了萬隆、日惹等二三線城市,就難尋中國品牌的蹤跡了。這些日韓企業在東南亞經營已久,甚至已經出現了二代、三代為這些企業工作的本地人。中企在當地的經營是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必須靠長時間的跨文化交流來積累互相之間的信任。
當然,東南亞普遍存在“都市主義”特征,即大城市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吸納了來自全國的年輕人口,消費很發達,它的中高端消費領域和其他國際大都市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中企在初期更容易進入這些市場。但是,二三線城市的本地化色彩更重,要進入這些市場,所耗費的時間和信息成本是巨大的,除了自己派合適的員工前往之外,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也是重要路徑。
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經營時的另一個思想誤區,是照搬國內的項目治理思維。許多企業不熟悉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生態,習慣了跟“一把手”打交道解決一切問題的方式,但是在選舉體系里,官員是會周期性更替的。另外,在權力分散、社會組織發達的東南亞,衡量誰有影響力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在不同事情上,不同機構的影響力也不一樣。如果沒有深入地在地調研,很難在復雜的關系中找到解決具體問題的方式。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