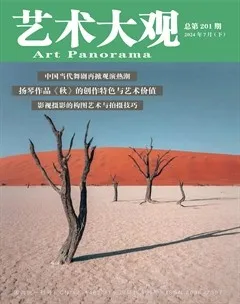中西方16世紀(jì)人物繪畫風(fēng)格演變與異同

摘 要:本文探討了中西方繪畫在16世紀(jì)前后的發(fā)展與演變,尤其是從“線”到“涂”兩種風(fēng)格的對(duì)比與交融。16世紀(jì)前,中西方繪畫均強(qiáng)調(diào)線條勾勒,色彩依附于線條。文藝復(fù)興后,西方繪畫逐漸弱化線條,追求視覺真實(shí),通過光影與筆觸展現(xiàn)物體立體感,形成“涂繪”風(fēng)格。中國(guó)明代晚期,人物畫在繼承傳統(tǒng)線描基礎(chǔ)上,受西洋技法影響,出現(xiàn)以墨骨、渲染等手法增強(qiáng)立體感與真實(shí)感的“涂繪”傾向,同時(shí)追求筆墨意趣與深層含義。兩者雖在技法上有所差異,但均體現(xiàn)了從形式到視覺真實(shí)的轉(zhuǎn)變,展現(xiàn)了中西方繪畫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追求與獨(dú)特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人物畫;線描;涂繪;中西繪畫對(duì)比
繪畫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shù)形式,不僅記錄了歷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時(shí)代人們的審美觀念與思維方式的演變。線條,作為繪畫中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其運(yùn)用與表現(xiàn)形式的變化,深刻影響了繪畫藝術(shù)的發(fā)展軌跡。本文旨在探討中西方繪畫中線條與涂繪風(fēng)格的演變,特別是聚焦于16世紀(jì)這一關(guān)鍵時(shí)期,通過對(duì)比分析中西方繪畫的共性與差異,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文化與思想根源。
一、中西方繪畫中的線條
將個(gè)體強(qiáng)烈的個(gè)人差異中并存的共性歸納起來(lái),一個(gè)明顯的時(shí)間分界出現(xiàn)了——16世紀(jì)。自它之前和之后的人物繪畫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海因里希·沃爾夫林的視角中,繪畫的形式被分為線描與涂繪[1],線描來(lái)源于觸覺,而涂繪來(lái)源于視覺。16世紀(jì)以前,西方繪畫的總體面貌可以被稱為“線條的時(shí)代”:無(wú)論是文明源頭的希臘文化中聲名顯著的瓶畫,還是拜占庭藝術(shù)中莊嚴(yán)的鑲嵌畫、中世紀(jì)中神態(tài)僵硬的神像,無(wú)不是以“勾勒填彩”的底層邏輯進(jìn)行著,顏色依附在線條上,線條是物體輪廓結(jié)束的終點(diǎn),也是顏色附著的盡頭。
但是在中國(guó),繪畫的形式似乎也遵循著這樣的規(guī)律。16世紀(jì)明代晚期之前,纖細(xì)的線條在絕大部分作品中處于主體形式。史前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魚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人物龍鳳圖》,漢代馬王堆帛畫,以及唐宋元和明晚期之前的繪畫,盡管在顏色與線條的形式上有著許多發(fā)展,但仍屬于線條主導(dǎo)的范疇。
在西方的文藝復(fù)興前,中國(guó)的明朝晚期前,繪畫除了諸如材料、題材、思想等地區(qū)文化導(dǎo)致的差異,繪畫的底層邏輯都處于“勾勒填彩”的階段,并且線條處于支配性質(zhì)的地位。但是在日后這種主導(dǎo)性質(zhì)的繪畫邏輯被顛覆之后,中西方又呈現(xiàn)出相同的普遍規(guī)律以及截然不同的特質(zhì)。而這種特質(zhì)將中西方思想文化層面的差異升華到無(wú)法忽視的地步。
二、16世紀(jì)中西方繪畫中的線條革命
模仿自然始終是西方繪畫重要的追求之一。在近現(xiàn)代藝術(shù)興起之前,藝術(shù)家力求通過真實(shí)的面貌夾雜以真實(shí)的感情撼動(dòng)世人。16世紀(jì)以前,藝術(shù)家的作品往往被貼上“刻板”的標(biāo)簽,這樣的印象在中世紀(jì)的藝術(shù)作品中尤為強(qiáng)烈。盧布廖夫是俄國(guó)著名的圣像畫家,在他的畫中,對(duì)人物輪廓的強(qiáng)調(diào)似乎比人物本身還要重要,無(wú)論是衣服還是五官上的線狀結(jié)構(gòu),都被推到一個(gè)顯眼的位置。齊馬布埃的圣像,人物的輪廓仍然像剛硬的鐵絲一樣緊緊箍在人物的邊緣。諸如此類的畫家往往有一個(gè)共性特征,即把線條作為一個(gè)不可隱藏的元素。這種對(duì)線條的執(zhí)著,可以被稱為“刻板”,但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可以看到這種習(xí)慣的轉(zhuǎn)變。有資料證明,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繪畫轉(zhuǎn)變與以小孔成像為主的科學(xué)規(guī)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線條的運(yùn)用在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lái)更加純熟。在波提切利的作品中,人物的輪廓仍然是十分鮮明的,但并不一定是以黑色勾勒,它可以是物體本身的顏色在邊緣處形成一條清楚的邊界,這種將線條藏起來(lái)的方式更加肯定了線條的主導(dǎo)作用:即使線條失去抽象的形式,以物體的形式凝固在邊緣,仍然給人以平面、封閉、多樣、清晰以及形如雕塑般的強(qiáng)烈觸摸感。看到這樣強(qiáng)烈的邊緣,好像手就已經(jīng)放在這輪廓上,感知它的堅(jiān)硬或者輕柔。這也體現(xiàn)了波提切利最典型的形象特點(diǎn):以線形為主的平面藝術(shù)整體造型設(shè)計(jì)風(fēng)格典雅,充滿了異教主義人文氣氛。[2]在尼德蘭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凡·艾克、維登、梅姆林等人的作品中,這種運(yùn)用線條的方式更加強(qiáng)烈。線條處在一個(gè)合適的位置,平面顏色的填充也被替換為按照結(jié)構(gòu)形體填涂的方式。這時(shí),對(duì)線條的部分取舍,可以稱之為“嚴(yán)謹(jǐn)”,線條似乎失去了獨(dú)立的形式,但是卻無(wú)處不在,無(wú)所不用其極地發(fā)揮它觸感的作用。
線條通過失去獨(dú)立的形式而使畫面達(dá)到一個(gè)新的高度,而后續(xù)的藝術(shù)家,通過適度的忽視線條,讓繪畫作品達(dá)到更杰出的效果。在達(dá)·芬奇的作品中,線條往往被選擇性地展現(xiàn)。在《蒙娜麗莎》中,五官、右側(cè)頭發(fā)與臉龐、大臂衣服褶皺、胸部衣服與手的疊放處,都出現(xiàn)了難以捉摸的模糊,這種模糊中除了一團(tuán)色塊,難以分辨出線條的存在。我們知道人的臉龐有著明確的輪廓,衣服的褶皺也一定會(huì)形成復(fù)雜交錯(cuò)的紋路,但是用模糊且舍去線條的方式來(lái)描繪,給人一種視覺上新的感受,這是涂繪式繪畫的特征之一。不能說(shuō)它不再嚴(yán)謹(jǐn),只是這種新的視覺上的沖擊,給人一種光線迷散的朦朧美感。在此之后17世紀(jì)的魯本斯、倫勃朗、哈爾斯、維米爾、委拉斯貴支等的作品中,這種感覺越來(lái)越強(qiáng)烈。很多時(shí)候物體變成了一道肌理突出的筆觸,雖然失去了事物本身的形狀,但是僅僅從視覺的角度來(lái)看,那一瞬間的印象卻極其接近真實(shí),甚至更加強(qiáng)烈。
有這樣的效果出現(xiàn),一方面是人們對(duì)風(fēng)格興趣的轉(zhuǎn)變,這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給人以更加強(qiáng)烈的視覺效果;另一方面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也是極其重要的。在卡拉瓦喬的繪畫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暗繪風(fēng)格完全符合小孔成像為基礎(chǔ)規(guī)律的暗箱的使用:即強(qiáng)烈的單一光源、人物猶如舞臺(tái)般布置。事實(shí)上關(guān)于卡拉瓦喬的描述,也提過他如果離開了模特,寧可一筆也不畫。維米爾,荷蘭小畫派的大師,他的畫中更加凸顯出單孔鏡頭般的特質(zhì):畫面中總是出現(xiàn)反常的虛焦現(xiàn)象,即近處模糊遠(yuǎn)處細(xì)致,同時(shí)一些小細(xì)節(jié)上總是躍動(dòng)著閃爍的光斑。同時(shí)在維米爾的作品中,光線都來(lái)自畫面左側(cè)的窗戶,封閉的房間猶如一個(gè)迷你型的盒子,由一側(cè)透進(jìn)來(lái)的光線使畫面有了猶如電影劇照似的氛圍[3]。這些證據(jù)足以證明光學(xué)設(shè)備的進(jìn)步與使用,以朦朧為特征的視覺風(fēng)格占據(jù)主導(dǎo),科學(xué)光學(xué)的輔助致使接近視覺真實(shí)的效果至上。
三、16世紀(jì)中國(guó)繪畫線條藝術(shù)的演變與突破
中國(guó)人物畫長(zhǎng)期以勾勒填彩為正統(tǒng),雖有畫家嘗試突破,但勾勒填彩仍占主流審美。早期人物畫,線條界定邊界,如《人物龍鳳圖》與馬王堆帛畫,區(qū)分人物與背景。漢至明,線條纖細(xì)勁力,敷色含蓄,造型自然,技術(shù)純熟卻未突破勾勒填彩框架。五代、宋人物畫,如周文矩、顧閎中、李公麟,線條運(yùn)用精湛,具審美價(jià)值,但仍為邊界與附庸,未實(shí)現(xiàn)形式到內(nèi)容的全面革新。
然而,在這漫長(zhǎng)的歷史進(jìn)程中,總有一些先驅(qū)者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探索新的藝術(shù)道路。五代時(shí)期的石恪,便是這樣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畫家。傳為其作的《二祖調(diào)心圖》中,強(qiáng)勁的動(dòng)勢(shì),大塊的墨漬,邊界不復(fù)存在以至于衣袍和獸毛仿佛微微顫動(dòng)。其特點(diǎn)是人物的手腳、臉都用淡墨勾畫,而軀體,服飾用減筆、潑墨法隨意地抒寫,使精細(xì)的形象刻畫與粗放的筆墨皴擦形成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畫面水墨淋漓,一氣呵成,令觀者產(chǎn)生心靈的震撼。[4]似乎畫家的眼中只有停留在視網(wǎng)膜中倏忽閃爍的暫像。南宋梁楷的《潑墨仙人圖》《太白行吟圖》中,又出現(xiàn)了這種不拘泥于邊界而重視團(tuán)塊的內(nèi)涵。這種與線描截然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是與“線描”對(duì)立的概念——“涂繪”式的繪畫。
元代的人物畫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shí),也展現(xiàn)出了一定的創(chuàng)新意識(shí)。錢選的《貴妃上馬圖》與王鐸、倪瓚合作的《楊竹西小像》等作品,雖然在整體上仍然保持著線描的風(fēng)格,但在細(xì)節(jié)處理上卻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王鐸的肖像畫,通過淡墨的斡染手法,巧妙地表現(xiàn)出面部五官的凹凸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dòng)逼真。這種手法的運(yùn)用,不僅豐富了畫面的表現(xiàn)力,也為后來(lái)的人物畫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16世紀(jì)明代萬(wàn)歷、天啟年間,涌現(xiàn)了一批記錄官員的肖像的作品。這批名為《明十二人像》的系列肖像,呈現(xiàn)出與以往繪畫觀念中明顯不同的獨(dú)立樣式。《明人肖像》中人物造型并非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線描造型,如《劉伯淵像》其臉部沒有一根連貫的線條,包括輪廓,完全依據(jù)人物骨骼、肌肉甚至明暗布以粗細(xì)、濃淡、斷續(xù)不同的線。特別是劉伯淵下巴處肌肉與衣領(lǐng)之間的空間處理,以及眼眶周圍的肌肉骨骼處理及用筆走向等細(xì)節(jié),表明作者熟諳解剖學(xué)與素描關(guān)系,其技巧之高甚至是當(dāng)代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美術(shù)院校畢業(yè)生難以企及的。[5]在人物面容五官上,除了眼皮、鼻底、嘴縫這些確實(shí)是由視覺直觀的線條組成的結(jié)構(gòu),其他的結(jié)構(gòu)多以斡染的方式完成,并非以線條表示,而是靠染的方式強(qiáng)調(diào)出來(lái)。也許是民間受到西方人物繪畫效果的影響,使得這些肖像呈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真實(shí)感。這也許是“線描”向“涂繪”轉(zhuǎn)向的另一實(shí)例。極其有趣的是,《明十二人像》中正有徐渭的肖像,并且確實(shí)是以朦朧、無(wú)邊界的團(tuán)塊的顏色來(lái)塑造視覺上的真實(shí)感。
明末清初的曾鯨,在繼承粉彩渲染傳統(tǒng)技法的同時(shí),汲取西洋畫的某些手法,形成注重墨骨、層層烘染、立體感強(qiáng)的獨(dú)特畫法,特別強(qiáng)調(diào)墨的表現(xiàn)能力,用淡墨渲染出面部細(xì)微的變化,著力于表現(xiàn)五官的高低起伏,重體感。[6]從學(xué)者甚眾,遂形成“波臣派”。其代表作如《李亨像》等,展現(xiàn)了色彩塑形與結(jié)構(gòu)弱化的藝術(shù)特色,追求畫面的自然與真實(shí)。同時(shí)期的禹之鼎也受到波臣派影響,其《江鄉(xiāng)清曉圖》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實(shí)立體。此外,西洋傳教士郎世寧的技法嘗試,更推動(dòng)了這種近似西方的繪畫風(fēng)格的發(fā)展。盡管清代仍有勾勒填彩的傳統(tǒng)作品,如羅聘的《易安像》,但曾鯨等人的創(chuàng)新無(wú)疑為清代人物繪畫注入了新的活力與風(fēng)貌。
如果說(shuō)《明十二人像》及曾鯨、禹之鼎、郎世寧等人的探索,是將中國(guó)人物畫從“線描”的細(xì)膩推向“涂繪”的立體逼真,旨在通過色彩與結(jié)構(gòu)展現(xiàn)形象生動(dòng),那么清末任伯年的《酸寒尉像》則開創(chuàng)了另一維度的“涂繪”風(fēng)格。此“涂繪”非單純追求形似,而是融入畫家情感與觀念,通過筆墨的抽象與表現(xiàn),實(shí)現(xiàn)神似之境。在《酸寒尉像》中,任伯年以淡筆勾勒面部,略施皴擦,衣袍則即興揮灑色墨,巧妙融合民間寫真與波臣派技法,展現(xiàn)出純粹而富有傳統(tǒng)韻味的“涂繪”藝術(shù),達(dá)到了形神兼?zhèn)涞男Ч?/p>
四、中西方繪畫技法與審美的演變差異
西方繪畫在對(duì)“線描”式風(fēng)格的厭倦與更迭下,一方面逐漸形成了不拘泥于線條的表現(xiàn)形式,以魯本斯、倫勃朗等人為例,他們的作品筆觸肌理強(qiáng)烈,重視在光源條件下的瞬間視覺效果;另一方面在科技進(jìn)步和光學(xué)知識(shí)極大豐富的前提下,西方繪畫形成了效仿單一鏡頭下的視覺效果,代表人物為卡拉瓦喬、維米爾等,他們的作品并不會(huì)依照畫家本身的個(gè)性隨意在畫面上更改對(duì)象的視覺造型,因?yàn)槲鞣嚼L畫的寫實(shí)根基是素描,必然會(huì)注重很多如結(jié)構(gòu)、透視、解剖等理性因素。[7]這兩種層面形成的“涂繪”風(fēng)格繪畫,無(wú)論畫面呈現(xiàn)的結(jié)果如何,都是以繪畫對(duì)象的外貌與精神逼真為目的,這一目的首要方面自然是以外貌的酷似為主。文藝復(fù)興早期,“線描”式風(fēng)格那種理性冷靜剖析人物面貌的方式,是一種人腦中理念的真實(shí),但并不一定符合視覺所察;之后“涂繪”式風(fēng)格中極其符合真實(shí)的視覺效果,更像語(yǔ)言中豐富詳細(xì)的定語(yǔ),給所繪人物一個(gè)更加符合現(xiàn)實(shí)邏輯的修飾,從而讓人們感覺所繪的人物更加真實(shí)生動(dòng),盡管塑造的手段并不一定接近人腦中理性的真實(shí)。真正將筆觸、色彩等繪畫本身的語(yǔ)言抽離出來(lái)則是之后興起的風(fēng)潮。
中國(guó)在明代時(shí)期出現(xiàn)的新的創(chuàng)作形式,也是基于這樣的邏輯之下,只是與西方的方式相比,線條仍然占據(jù)一席之地。一方面,中國(guó)的人物繪畫在吸收民族傳統(tǒng)技藝的同時(shí),西洋畫中對(duì)暗部的處理,即染低,和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中對(duì)亮部的處理,即染高,結(jié)合在一起,層層積染使得畫面中的人物更富凹凸感,遂發(fā)展了以墨骨與渲染法豐富畫面的波臣派;另一方面,吸取明清陳淳、徐渭、陳洪綬、八大山人、石濤和“揚(yáng)州八怪”等諸家之長(zhǎng),又受清代金石學(xué)的影響,畫面更加追求深層次的意趣與含義。這一點(diǎn)與西方的發(fā)展方向極其不同。
五、結(jié)束語(yǔ)
中國(guó)與西方人物繪畫的轉(zhuǎn)變具有普適性質(zhì)的規(guī)律,但是轉(zhuǎn)變的內(nèi)核與外表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國(guó)與西方的繪畫都經(jīng)歷了一個(gè)追求形似而不似、形似而形神兼?zhèn)洹⑸袼贫尾凰频倪^程。在這個(gè)過程中,“線描”“涂繪”式的風(fēng)格只是觀察世界角度的轉(zhuǎn)變。未來(lái),新的繪畫視角的轉(zhuǎn)變,可能會(huì)從傳統(tǒng)中汲取有用的養(yǎng)料,也有可能會(huì)產(chǎn)生質(zhì)變般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xiàn):
[1]沃爾夫林.藝術(shù)風(fēng)格學(xué):美術(shù)史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2]唐坤.坦培拉繪畫材料語(yǔ)言探微——以波提切利作品為例[J].武夷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42(07):27-31+36.
[3]逯哲辰.“逼真”的秘密—維米爾畫作中的透視法則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xué),2013.
[4]陳慶華.從《二祖調(diào)心圖》看中國(guó)繪畫之空無(wú)觀[D].西安美術(shù)學(xué)院,2006.
[5]程敏.“曾鯨肖像畫參酌西法”新考[J].美術(shù)觀察,2020(03):49-54.
[6]張一涵.傳承與演進(jìn):明清肖像畫藝術(shù)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嬗變研究[D].天津大學(xué),2017.
[7]陳閱敏,申大鵬.尋找中西畫語(yǔ)中的靈魂——寫實(shí)與寫意[J].美與時(shí)代(中),2015(09):28-29.
作者簡(jiǎn)介:李嘉迅(1999-),男,山東青島人,碩士研究生在讀,從事工筆人物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