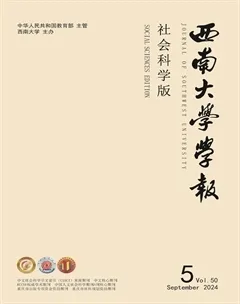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解讀
摘 要:哈特和奈格里認為,整個西方社會正在步入以網絡化、信息化和服務化等為特征的后工業時代。這種轉變的標識是非物質勞動逐漸取代工業勞動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勞動方式,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發揮著引領作用。非物質勞動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生命政治意蘊,創造了無法被資本完全占有的共同性,而這種共同性使諸眾獲得了對抗資本帝國的力量,蘊含著生命政治解放的潛能。哈特和奈格里從活勞動和主體政治的視角深入闡釋了非物質勞動的內涵及其引發的社會歷史效應,并將這一觀點視作對馬克思勞動理論的繼承與創新。然而,他們對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解讀違背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解放學說,存在著對階級關系和現實歷史過程的簡單化理解。用馬克思的立場反思他們的非物質勞動觀點,對于在后工業時代推進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化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非物質勞動;生命政治;共同性;勞動價值論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24)05-0128-12
一、引 言
在全球化時代,伴隨著信息、網絡、服務等第三產業的發展,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發生了轉型并呈現出新的特質。其典型表現是以信息化、網絡化、智力化等為特征的非物質勞動逐漸取代傳統工業中的物質勞動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勞動方式。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哈特和奈格里在生命政治語境中對這一歷史進程進行了獨特的闡釋,建構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話語體系和理論范式。他們抓住了資本主義勞動的新形式及其特質,對其進行了生命政治闡釋,并嘗試與馬克思的一般智力、資本吸納等觀點結合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馬克思哲學的強大生命力和當代意義,但同時也對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提出了挑戰,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解。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已開始圍繞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動理論及其社會政治效應展開學術研究,并出現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總體來看,現有主要學術觀點可概括為以下三類:
一是以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等文本為基礎,探討非物質勞動的內涵和特征。在生產方式從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非物質勞動的興起及其對整個生產領域的引領效應。張一兵結合信息革命所帶來的后現代經濟轉型,把均質化、情感性、內在性的合作與互動,看作是非物質勞動區別于馬克思經典勞動的重要特征[1]。李春建在對非物質勞動的學術史梳理中概括了奈格里非物質勞動概念的內涵,并以之為基礎展望了非物質勞動所塑造的全新社會主體[2]。唐慶在一般生產勞動與非物質生產勞動的比較中指出了內格里(奈
格里)非物質勞動的核心要義、理論價值和局限[3]。唐正東認為非物質勞動和生命政治勞動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只是側重的角度不同,并認為哈特和奈格里對非物質勞動進行了過度的主體政治闡釋[4]。徐宇曉指出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非物質勞動和生命政治生產這兩個概念側重點有所不同,前者側重于勞動過程和產品的非物質性,后者側重于這種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社會政治效應[5]。以上研究將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動理論置于生產方式的后現代轉型或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為在整體上把握非物質勞動的思想史淵源、本質特征和表現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基礎。
二是在對哈特和奈格里帝國、諸眾等思想的研究中討論非物質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在資本不斷塑造世界歷史的過程中,建構了一種不可直觀的超越民族國家和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構序力量,這就是帝國。張一兵在對帝國的生命政治闡釋中,透過哈特和奈格里的文本提出非物質勞動作為后現代新型的生產方式正在創造一種史無前例的帝國版圖[6]。汪行福指出非物質勞動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顛覆了傳統生產方式的線性邏輯和內在等級結構,蘊含著反抗資本帝國的新型革命潛能[7]。劉懷玉等指出非物質勞動是諸眾得以形成的基礎,諸眾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受資本直接剝削的無產階級,而是涵蓋了與資本對抗的全部主體[8]。以上這些研究在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諸眾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非物質勞動這一新型生產方式,并指出了非物質勞動是前者的經濟基礎或社會本體論基礎。
三是哈特和奈格里與西方學者的比較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哈特和奈格里的研究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方向是把他們置于思想史的視域中與其他哲學家進行比較式研究,以突出他們思想的內涵、重要特質和理論淵源等。莫偉民從生命權力、生命生產、主體性生產三個方面系統闡釋了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產思想,并在這一基礎上對比了奈格里與福柯的思想差異,得出了奈格里是一位“新帝國論者”的結論[9]。藍江指出,在對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權力概念誤讀的基礎上,哈特和奈格里建構了自己的生命政治生產思想,并因而發展出一條不同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學路線[10]。馮波從思想史的線索指出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理論借用了斯賓諾莎的哲學資源,比如他的自由諸眾、民主政治等思想,但同時又存在著對他的誤讀[11]。宋曉杰對比了奈格里與阿甘本的思想分歧,并指出二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徹底對立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模式,前者追隨海德格爾,基于生命的有限性,憑借向死的決心,領會生命的意義;后者追隨斯賓諾莎,訴諸生命的自主性力量,拒絕主權權力的政治秩序[12]。以上這些研究對把握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史淵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同時在比較的視域中凸顯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特質。
國內學術界對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動及其相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優秀成果。其中,關于非物質勞動內涵與特質的研究,關于諸眾與傳統無產階級區別的研究,關于非物質勞動與資本帝國關系的研究,為本文的展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啟示。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理論不足,比如,如何挖掘他們的非物質勞動理論的生命政治意蘊,他們對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解讀有哪些貢獻與不足,這一解讀在哪些方面推進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如何從馬克思立場看待他們的非物質勞動理論及其社會政治效應,如何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評判他們的以非物質勞動為基礎的共同性理論。回答這些問題,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一項重要課題。
二、后工業時代的非物質勞動
相對于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哈特和奈格里認為,整個西方社會正在步入以網絡化、信息化和服務化等為特征的后工業時代。其中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非物質勞動取代傳統物質勞動,作為占據支配地位的勞動方式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發揮著引領作用。然而,無論勞動方式怎樣變化,當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統治關系即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始終未變。盡管當代資本主義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物質財富呈指數級增長,但整個世界的貧民和難民并未由于這種增長而消失。這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判斷依然有效:“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13]32哈特和奈格里作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在其著作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承認資本權力對勞動的剝奪、控制和規訓。令人欣慰的是,他們在后工業時代的經濟境況中,認識到非物質勞動的崛起必然引起資本對勞動的統治關系的變化,并在這種變化中看到新型無產階級崛起和共產主義實現的可能性,試圖建構一條不同于馬克思的通往共產主義的路徑。
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非物質勞動代替工業時代物質勞動的統治地位并不意味著物質勞動的消失,而是說它已無法在全球經濟中處于引領地位。“我們說非物質勞動有擔當霸主地位的趨勢,并不意味著,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數工人在生產非物質產品。相反,農業勞動在數量上來說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一如幾百年來的情形。而工業勞動在全球層面上、在數量意義上并未衰退。”[14]139在每一種經濟模式中,各種勞動方式都同時并存,但總有一種勞動方式處于支配地位,它將影響和改變其他勞動方式并使之具有日漸相同的特質。非物質勞動通過信息、網絡技術、人工智能等手段改造傳統物質勞動,從而使后者也顯示出信息化、網絡化和服務化等非物質特征,這體現了非物質勞動的霸權。在全球化過程中,民族國家走向后現代化的過程并不是同步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去工業化的進程較為明顯,這些國家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和服務業,勞動力從工業領域向非物質產業領域發生了轉移,在整個經濟發展中,非物質勞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然而,在諸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工業時代福特主義色彩的工廠制造業仍方興未艾,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仍是就業大軍的主流。從整個世界來看,社會生產組織形式呈現出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的混合特征:一方面體力勞動者在數量上仍然占據壓倒性優勢;另一方面從事信息或服務的知識工人在勞動結構中逐漸占據霸權性地位。哈特和奈格里準確地把握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后現代化過程對世界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施加了不可逆轉的支配性影響,使其受制于以非物質勞動為核心的服務業和信息產業。
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非物質勞動呢?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中把非物質勞動界定為“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的勞動”[15]290,其產品包括情感、交往、信息、符碼、圖像、語言等。他們強調所有的非物質勞動都包含物質性和精神性兩個方面,都不能離開勞動的物質形式而獨立開展,其非物質性指的是勞動產品的非物質性而不是勞動過程的非物質性。非物質勞動在商品生產中的支配和引領作用并不意味著物質勞動減少或消失了,而是指物質勞動在價值增殖層面越來越從屬于非物質勞動。非物質勞動盡管在數量上只占了全球勞動的很小一部分比例,其霸權地位體現在從質的方面決定其他勞動方式乃至社會的發展態勢。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在《諸眾》中也公開承認,非物質勞動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說法,對其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在他們的解讀思路中,非物質勞動與生命政治勞動或生命政治生產指涉的是同一個對象,即在后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工業中出現的新的勞動方式。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二者表達相同的含義,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非物質勞動強調與傳統物質勞動的區別,側重于勞動產品的非物質性特征;生命政治勞動或生命政治生產側重于自身創造新型的社會生活、社會關系和主體性的功能。
關于非物質勞動包含哪些種類這一關鍵問題,哈特和奈格里在不同著作中有不同界定,但大致包括兩類:一是智力或語言勞動,包括圖像藝術設計、計算機編程、網絡信息平臺的設計和維護、廣告和公關等活動,它所生產的是符號、信息、觀念、圖像、語言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產品。這類勞動并不直接創造物質產品,但卻是物質生產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二是情感勞動,這是生產滿意、興奮、輕松、幸福、激情等情感的勞動方式。這兩類非物質勞動之間的區別并非那么明晰,絕大多數非物質勞動都綜合了這兩種形式[16]108。在越來越多的智力勞動中都能辨識出情感勞動存在的必要性,反過來亦然。與傳統排他性的物質產品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認為,諸多非物質勞動產品具有社會性的共享品質,可以增加全社會共同分享的財富,遵循的不是稀缺性原則。與傳統物質勞動相比,后工業時代的非物質勞動顯現出以下三個重要特質。
一是非物質勞動使勞動時間與生活時間的傳統區分趨于無效,生活與勞動之間的界限愈益模糊,勞動與生活難以區分。在傳統工業社會,工人的勞動時間集中在工廠里,他們的崗位在一定時期內是固定的,其潛能也只能在工廠里實現。與此相對照,在后現代社會的非物質產業部門中,勞動表現出了向工廠—社會的過渡。“工廠不再是勞動和生產的典型場所或集中地;勞動過程已經轉移到工廠圍墻之外,并蔓延至整個社會。”[17]工業社會中勞動的產品是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非物質勞動的產品是觀念、圖像、符號、交往、協作、關系等,因而是社會生活本身,它不局限于經濟現象和經濟領域,而是牽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命政治勞動的表現,如情感和智識天賦,創生協作與組織網絡的能力,交往技能和其他能力,都不需要固定的場所。”[18]111可見,當生產的目的不是物質產品而是非物質勞動產品時,生產不可能完全在固定時間段內進行,勞動時間需要擴展至生活的所有時間,這需要勞動者擁有組織自己時間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非物質勞動創造的價值無法用固定的時間單位量化,作為價值度量單位的抽象勞動時間的統一性已經不復存在,因此,他們主張在后現代非物質勞動的境況下要修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二是非物質勞動使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協作、溝通、互動等新的特質。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論及機器大工業時,馬克思認識到勞動者在創造物質產品的過程中確實需要協作,但這種協作是資本通過工廠制度、生產程序、自動化機器體系等外在方式強加在工人身上的,并不是工人的自主行為。而在非物質勞動中,勞動者自身在勞動過程中能夠自主地溝通和協作,不再依賴于資本組織的協作關系。他們指出:“非物質勞動的協作屬性并不是像之前的勞動方式那樣由外界強制或組織的,相反,協作完全內在于勞動活動本身。”[15]294情感性、交往性或智識性的非物質勞動依賴于勞動者之間的密切協作,這種協作是從勞動者自身的生產性能量中產生的。非物質勞動越來越具備自主協作的能力,日益脫離資本所強加的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協作形式,創造出扁平的社會網絡協作形式。人們共同展開非物質勞動,建立發達的流通和協作機制,組成平等而獨立的協作網絡。“在非物質生產中,協作的創造已經變得內在于勞動而外在于資本。”[16]147非物質勞動的產品由高度協作的網絡產生,成為共同的財富,而這反過來又會促進非物質勞動的進一步發展。哈特和奈格里認為,沒有人能夠獨立地思考和活動,觀念、圖像、符號、知識等都是基于協作關系而產生的,而這些新的非物質勞動產品反過來又會產生新的協作關系,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得到加強。
三是非物質勞動產品遵循的不是稀缺性和排他性邏輯,它在流通和使用的過程中會得到進一步強化和衍生。非物質勞動產品受眾越多,傳播越廣,說明越具有生命力。非物質勞動的產品資源向每一個人開放,在實踐上可以由所有人共同使用,用之彌多。因而,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非物質勞動產品既非私有,也非公有,而是采取共同性的存在形式。財產的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這種意識形態決定發達國家統治全球經濟的主要策略,即通過版權、專利和知識產權等方式使非物質勞動產品成為私有財產。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公有物通常指由國家控制的財產或商業企業等,實際上仍然貫徹財產使用的嚴格界限。私有和公有雖然相互對立,但遵循的都是排他性和稀缺性邏輯。私有和公有都是排斥共同性的財產制度,非物質勞動產品的共同性形式既不是私有也不是公有,而是在兩者之外的另一種根本不同的財產形式。非物質勞動產品直接都是共同的和社會的,它可以共享和共有,而不是專屬于某些個人、階層或群體所有。他們認為,在知識生產和信息經濟等非物質領域,非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創造已經逾越了資本的控制,其共同占有和使用成為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內在要求。非物質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力是由資本之外的因素建構起來的,而不是由資本建構的,更不可能與資本達成實際上的從屬關系,資本正因為如此而無法控制勞動過程[4]。當一個人與他人分享圖像、觀念或語言時,他的思想能力并沒有減弱,相反會由于彼此交流而增強了他的能力。人們在對共同性的公開而直接的使用中,共同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
非物質勞動是資本帝國形成的經濟基礎,帝國的合法性不是來自于國際條約,也不是來自于國際組織,而是來自于勞動范式從物質勞動向非物質勞動的轉型。在后現代社會的全球經濟中,非物質勞動在全球財富創造中占據引領地位,不斷締造著帝國這一資本的全球新秩序。帝國是一種控制世界的不可直觀的主權形式,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它區別于國際組織、民族國家和帝國主義。帝國是一個無疆界、無中心的控制裝置,借助于信息、網絡、符號、交往等不斷加強對全球領域的統合。帝國的控制權力實現于靈活多變的網絡系統之中,其權力范圍已經遠遠超出由福柯所列舉的一系列客觀機構所構成的可見的社會場域。“權力已經延伸到社會結構的每一個神經末梢,并布滿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之中”[15]24,甚至延伸到身體和意識的最深處。哈特和奈格里關注的焦點并非是批判帝國對全球社會生產和具體生活的微觀控制,而是在帝國中尋找反對帝國的社會改造之途。
三、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意蘊
非物質勞動在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規劃中處于核心地位,它是帝國得以建構的存在論基礎,是分析當今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和社會存在的基本概念性工具。帝國貫穿著雙重邏輯和雙重存在形式,他們借用奧匈帝國的雙頭鷹國徽來表達它的這一特征。帝國之鷹的第一個頭意味著控制的邏輯,帝國的生命政治控制機器無所不在,使全球的所有領域幾乎都陷入微觀權力的支配之中;帝國之鷹的另一個頭是解放的邏輯,帝國在構建全球控制秩序的過程中蘊含著自由和解放的潛能,生成著反抗自身的革命主體。根據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旨趣,他們的闡述重點顯然是后者,非物質勞動在構建資本帝國秩序的過程中,又在社會生產力的創造性和建構性這一側面蘊含著諸眾這一新型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創新性和革命性。“從一個角度看,帝國顯然凌駕于諸眾之上,并使之屈從于自己全面覆蓋機器的控制,這是一種新的利維坦。然而,從社會生產力和創造力角度看,也就是從我們稱之為本體的視角看,二者之間的關系被顛倒了過來。諸眾才是我們世界的真正生產力量,而帝國僅僅是一個遠離諸眾活力的捕獲裝置。”[15]62他們認為,在關于規訓社會或控制社會的一切討論中,生產或勞動都是理論的核心,它是產生支配權力的存在論基礎,也是新的主體的誕生地。任何階級主體的形成都依賴于某種處于霸權地位的勞動方式,這種勞動方式的變革決定著階級主體的變革。傳統物質勞動向后現代非物質勞動的轉換意味著階級主體從工人階級轉換為諸眾,非物質勞動是諸眾這一新型無產階級誕生的社會經濟基礎。非物質勞動的開展本身即是新型主體的生產和再生產,這一主體超出經濟領域,在社會、文化、政治和精神等領域成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生命政治意蘊。諸眾是一種本體論的力量,這意味著諸眾代表一種期望改變世界的機制。更準確地說,諸眾希望以它的形象創造世界,這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由自由人構成的共同體[19]。
對生命政治內涵的理解可謂眾說紛紜,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概念呢?我們可以在與對他們有直接影響的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比較中,界定他們關于這一概念的特殊含義。在《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這兩個概念,但他并未對二者進行嚴格區分,生命權力是生命政治的權力,這種權力形式對作為整體的人口進行有效的調節和控制,借助于民族學、健康學、公共衛生學和人口統計學等規范社會生活和整體人口。福柯指出:“我簡單地向你們強調生命政治學建立于其上的某些點,它的某些活動和首要的干預領域、知識領域和權力領域:出生率、發病率、各種生理上的無能,環境的后果,正是關于這一切,生命政治學抽取其知識并確定干預和權力的領域。”[20]可見,生命權力不在細節上考慮單個人的存在狀態,而是通過調整和保障機制,針對整體人口,建立某種生理平均數,使生命健康和安全獲得總體平衡,這種生命權力的應用產生了生命政治這一全新的政治形式。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繼承福柯對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的這一理解,而是把二者看作相互對立的概念。生命政治不再是生命權力的實踐方式,而是對后者的對抗與超越。如果說生命權力代表了資本對勞動的規訓和控制權力,那么生命政治就是生命權力的對立面,它強調的是無產階級通過自治和協作反抗資本主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生命政治是這一關系最為發達的領域:在生活現實內部,動搖了可悲的臣服形象,反對資本主義入侵現實的動力即生命權力。”[21]在后工業時代的非物質勞動語境中,生命政治意味著新型無產階級主體通過協作、自治、民主、出走等方式從資本的控制關系中脫離出來,占有和共享共同性這一勞動成果,建構能夠使自身獲得充分實現的新的生命形式和社會關系。非物質勞動在創造帝國控制秩序的同時,又創造出反抗帝國的力量,共同性為人的自由解放創造了新的空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路徑。
在非物質勞動中,人既生產,也被生產。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過程不僅意味著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生產新型無產階級主體即諸眾,諸眾是能夠摧毀資本且能夠創造全新未來的革命力量。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質勞動的主體形象具有生命政治的傾向。它……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形象,也是一個再生產、交流、關系、生活方式等等的形象。我們從這個假設出發構建大眾的概念:大眾不再是一個反叛的群體,不再是機構的一種,比如‘人民’或‘國家’,而是潛在的一代人,具有社會性,并充滿生機。”[14]7諸眾不是人民,它不是由政治權力建構的統一體;諸眾不是階級,它不是一個根據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關系而界定的統一體;諸眾不是國家,它不是建立在一定意識形態之上的針對其他敵對國家的統一體。諸眾是由奇異性的個體組成的具有生產力的聯合體,同時也是擁有革命性的反抗資本帝國的政治主體,在其中,任何個體都不能被通約為統一的身份。哈特和奈格里關于諸眾的觀點將導致一個重要轉變:無產階級從一個政治和經濟的范疇退縮為原子化個人之集合,將非物質勞動范式下的無產階級新主體轉換為帝國支配下的生命政治的個體存在,這是一個看起來新穎但實際上是完全錯誤的唯心主義論斷[22]。諸眾是由單個個體構成的網絡,它的存在如同“星叢”,“星叢”是本雅明和阿多諾哲學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范疇,在這里,喻指非同一性的革命主體,這是不能被某個中心整合的由各種并立的變動因素構成的集合體,這些因素不能被通約為一個本源的基本原理。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在后工業時代,資本的價值和生產力都由構成諸眾的個體勞動力創造,生產力以協作性的、理性的、智力性的、情感性的形式存在,即以生命政治的形式存在。因此,諸眾不單是一個經濟概念,而是在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轉變的過程中由階級升華而來的生命政治的存在形式。
伴隨著資本和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化,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無產階級的主體范圍已經超出工業時代直接在生產領域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具有生產力的諸眾在整個社會層面都被納入到剩余價值的創造之中,從這個角度看,諸眾即是指那些直接地或間接地屈從于資本帝國的所有個人。這同時意味著勞動和資本的矛盾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整個社會層面表現出來,而不只是局限在工廠里。非物質勞動的廣闊圖景使我們認識到新型無產階級存在的普遍性,同時又使我們看到無產階級主體在今天的表現范圍。“活躍在今天的各種生產成分中,包含通訊、協作、情感的生產和再生產在內的非物質勞動力量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無產階級的構成結構中都占據了一個日益劇增的核心位置。”[15]53工廠車間中的工人階級盡管從未消失,但其霸權地位已經被分散在社會各個層面的非物質勞動者取代,無產階級不再是昔日的舊模樣。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確定諸眾的身份構成并不是最重要的,其生命政治學的旨趣是在新型無產階級主體的基礎上尋求革命的可能性。諸眾超出生產過程,在全球社會生活范圍內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命政治存在,它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諸眾的活動構建了一個開放包容的網絡,這提供了所有差異相遇的機會,使超越資本支配的共同生活成為可能。
問題是,諸眾作為一個開放性的主體形式是如何聯結在一起的呢?哈特和奈格里認為,諸眾中的個體之所以不被消減為一片混亂,是因為非物質勞動的產品即共同性在其中起到了中介和聯結的作用,共同性使諸眾能夠在政治、經濟和生活領域內布展其反抗資本的力量。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把共同性概括為兩類:一是自然形式的共同性,包括土地、水、天然氣和礦物等自然要素,這些資源受制于稀缺性邏輯;二是人工形式的共同性,包括語言、符號、圖像、情感、知識和智力等,它不受制于稀缺性邏輯,相反,在流通和使用過程中會得到強化和衍生。哈特和奈格里的闡釋重點顯然是后者,因為后者才為諸眾實現生命政治解放提供可能空間和條件。在非物質勞動這一主導性的勞動方式中,對共同性的生產、分配和維護越來越具有關鍵意義。“生命政治生產能且只能在共同性的領域進行。觀念、圖像和符碼,這些不再只由天才或者大師生產,讓學徒做幫手,而是由相互協作的生產者所構成的龐大網絡所生產。”[18]125可見,共同性既是生產的基礎和前提,又是生產的結果。例如,若要產生知識,以往所積累起來的相關方法、觀念和信息必須向廣大的科學共同體開放,同時建立高度發達的協作與流通機制。當新知識產生的時候,它應該成為科學共同體的共享財富,將來的知識生產將以此為起點。只有當非物質勞動以這樣一種方式從已有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從而確立良性循環時,才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對共同性的分化和私人占有必將破壞這個良性循環,非物質勞動的生產力就會因而降低。資本是非物質勞動創造共同性的最大障礙,它通過知識產權等方式不斷地把共同性私有化,從而最大限度地占有社會生產力。資本剝削實質上是對共同性的剝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馬克思的以物質產品和物質價值為無償占有對象的剝削理論過時了。
在非物質勞動方式中,資本對共同性價值的全部或部分占有,是對諸眾的自由協作能力和自主活動能力的剝奪,因而也是對諸眾生命政治的微觀控制。然而,在非物質勞動創造共同性的過程中總是會包含一些資本所不能完全占有的部分,知識、符號、語言、情感、圖像等共同性形式由于其自身的特點,不會被資本或全球政治體所完全占有或操控。“相比機器大工業,這種生命政治生產的循環越來越脫離資本,越來越具有自主性,因為其協作圖式乃是內在于勞動過程而生成,所以任何外在強加的命令都成為生產力的障礙。”[18]176盡管資本帝國通過信息技術、網絡技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對諸眾的微觀控制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強化,但是非物質勞動的自由協作網絡內含了消解資本微觀控制權力的反抗力量。正是這種無法被完全占有的共同性內含著解放和革命的潛能,諸眾對資本反叛的能力和機會來自于自身創造的且無法被完全占有的共同性,共同性成為諸眾對抗資本帝國的基本支柱。哈特和奈格里基于非物質勞動創造的共同性尋求反抗資本帝國的生命政治力量,這一思路較之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審美救贖、文化藝術、意識形態等領域尋求革命潛能的觀點來說,是值得稱道的,因為他們試圖從社會存在的最根本領域即生產和勞動出發思考馬克思主義如何實現人的解放這一最根本問題。
非物質勞動創造的共同性不斷逾越資本帝國控制的邊界,資本的社會關系出現裂痕,諸眾憑借對共同性的占有獲得了自主性的可能,因而需要采取新的階級斗爭形式。“生命政治語境下的階級斗爭采取出走的形式。我們所謂的出走,是通過實現勞動力潛在自主性的方式從與資本的關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過程。”[18]112諸眾通過生產和占有共同性的方式逾越與資本結成的關系,從而建構使非物質勞動生產力得以實現和拓展的新的生命形式和社會關系。因此,“出走”并不是走向別處,而是停留在原地改造社會關系和生產組織方式。哈特和奈格里承認雖然共同性的生產使諸眾具備了“出走”的基礎,但也存在不利的客觀條件:原有的社會結構不斷地腐化已有共同性和阻礙新的共同性的產生;資本主義新的剝削形式不斷地占有非物質勞動創造的共同性。在共同性的生命政治領域內,諸眾不可能自發地實現“出走”,而是需要組織和籌劃。然而,對于如何組織和籌劃,哈特和奈格里并未給出有信服力的論證,他們忽視了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對社會發展過程的內在矛盾的客觀分析,忽視了生產關系的階級維度,看重的是勞動方式的變化所顯現出的主體力量,并據此實現生命政治解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的思想陷入了主體政治學的烏托邦之中。
四、基于馬克思立場對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質勞動觀念的批判性反思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工業化步入后工業化的過程中,非物質勞動在生產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成為處于引領地位的勞動方式。哈特和奈格里對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解讀具有重要的哲學效應,對于推進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建構具有重要啟示,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他們認為非物質勞動是對社會生活、社會關系和諸眾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這是非物質勞動區別于以往一切勞動方式的根本之處。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馬克思勞動觀點的繼承和發揮。在馬克思那里,勞動不僅僅是工具性的活動,它并不局限于物質產品的創造,而必然是社會活動,牽涉到社會關系的維持與轉換、人類主體屬性的改變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勞動“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23]666-667。可見,勞動既創造產品,又生產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從對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這一視角看,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動理論與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二是他們從非物質勞動的生命政治意蘊出發,積極探尋共同性對于建構新型無產階級和實現生命政治解放的積極意義,這對于在全球化時代推進和拓展馬克思的階級政治學無疑具有重要啟示。三是他們深刻地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比如,勞動方式的新變化、勞動時間與生活時間的新關系、剩余價值的新的產生方式、剝削的新形式等。這些新現象無疑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過程和生活方式產生深刻影響,這既是資本帝國形成的經濟基礎,同時也將引起資本與勞動關系的變革。他們對這些新現象和新問題的深刻分析將會推進歷史唯物主義走向社會歷史的微觀之處,豐富馬克思的物質生產理論,從而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建構。
然而,他們過多地側重于從活勞動和主體政治的視角闡釋非物質勞動及其引發的社會歷史效應,因而在闡釋生命政治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存在著理論上的薄弱之處,也存在著對馬克思的誤解。盡管他們聲稱其思想還在馬克思的傳統里,所做的工作只是繼續分析馬克思所分析過的經濟狀況,并沒有補充馬克思的理論。然而,他們對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的忠誠顯然遠遠不夠。在這種情況下,用馬克思的立場反思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質勞動觀點將具有重要意義,這既有助于我們看到哈特和奈格里如何跨越與馬克思的時代間距思考革命的可能性,加深對他們理論貢獻的了解;同時也能夠使我們看到他們對馬克思的背離表現在哪些方面,發現其非物質勞動理論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以思考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推進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化應注意的問題。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認為,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發生了從物質勞動向非物質勞動的轉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無法適用非物質勞動,因而必須修正。非物質勞動與生活的緊密關系模糊了勞動時間和非勞動時間的界限,非物質勞動產品并不像物質產品那樣能夠用固定的單位勞動時間測量。他們指出:“馬克思根據相應的數量提出了勞動和價值之間的關系,即一定數量的抽象勞動時間等于一定數量的價值。根據這個定義資本主義生產的價值規律,價值通過可度量的、同質的勞動時間單位來表現。”[16]145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勞動能否用勞動時間測量出來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非物質勞動總是逾越勞動時間的界限從而表現在整個社會生活領域,無法用固定的時間單位量化,因而必須重新調整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實際上誤解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商品交換關系出發探索商品價值,兩種特殊性的商品之所以能夠交換,就是因為二者存在著“相同的人類勞動”這一共性的東西。對于價值的計量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23]58復雜勞動的計量不是由個人來完成的,而是由交換關系背后的社會過程決定的,屬于本質定性層面的計量,是為了說明商品交換之所以能發生的原因。計量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可能通過人為的方式準確地測量出來。所以,在勞動價值論中,無論是物質勞動還是非物質勞動都不可能人為地用時間單位計算出來,他們的計量只能是本質層面的抽象計量,而不是現象層面的具體計量。
其次,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非物質勞動條件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他們提出基于共同性的價值理論,認為共同性是非物質勞動創造的最重要的價值,而這種價值是資本無法完全占有和捕獲的,因而蘊含著生命政治解放的可能性。“在生命政治語境下,價值溢出政治和經濟控制。”[18]222非物質勞動價值具有物質勞動價值所無法涵蓋的新的屬性,比如不可度量的屬性、生產者共同分享的屬性等。價值的生產表現為共同性的生產,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剝奪表現為對共同性的剝奪。他們指出,勞動成為生產共同性的勞動,價值來自聯合行動和共同性。共同性的價值是資本無法完全占有的,信息、圖像、符碼、情感和協作等共同性價值在很多情況下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并且其生產需要勞動者越來越多的自由和范圍越來越廣泛的協作,這為創造新的勞動與資本關系以實現生命政治解放提供了可能性。在他們看來,共同性已經脫離資本,正是在共同性與資本的間隙之間才具有生命政治解放的可能性。然而,他們并未充分且有效證明為什么在資本的微觀控制權力無所不在的情況下共同性能夠被諸眾自己控制。從馬克思的基本立場看,這一生命政治解放的路徑陷入樂觀主義的空想。
由于時代原因,馬克思并未對語言、符號、圖像、情感等共同性形式給予具體關注,但是對于協作這一哈特和奈格里也極其重視的共同性形式,卻給予了充分闡釋。我們可以透過馬克思關于協作的立場思考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問題。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生命政治生產中,資本并不決定協作的組織,起碼不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甚至在最嚴格的、剝削最嚴重的情況下,如呼叫中心或餐飲業,認知和情感性勞動也會普遍擺脫資本家的統治,自主地進行協作。”[18]104也就是說,在非物質勞動條件下,雖然資本會壓迫勞動力,剝奪其產品或服務,但是卻已經不再提供或無法組織協作。我們看一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協作的理解,“協作并不是他們自己結成的關系,而是資本家給他們安排的關系,不是這種關系屬于他們,而是他們隸屬于這種關系……這不是他們相互的聯合,而是一種統治著他們的統一體,其承擔者和領導者正是資本本身”[24]。可見,作為勞動結合方式的協作對于勞動者而言是屬于資本的異己的權力,由資本掌握的協作已經在本質上改變并控制了勞動。在馬克思那里,協作是對資本的一個極具批判性的概念。當代非物質勞動視域下的協作形式在表象層面也許獲得了某些自主性,但不可避免地會被資本這一客體化的社會權力所模鑄。哈特和奈格里認為,資本的控制關系已經延伸到非物質勞動的一切領域,完成了對整個生活領域的內在殖民。然而,在知識、情感、信息、服務的勞動中,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協作形式,即勞動者“出離”資本自主形成的協作形式,由此重構反抗資本的階級主體,推動生命政治解放[25]。根據馬克思關于協作的立場,通過非物質勞動對共同性的生產和占有實現生命政治解放這一路徑需要冷靜的反思:被資本所模鑄的協作如何為生命政治解放提供可能空間呢?協作如何能夠真正成為理想社會的交往方式呢?
最后,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性價值理論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它服務于諸眾這一新型生命政治主體的建構,這既與馬克思從商品交換的客觀關系出發所理解的價值不同,也無法將諸眾與馬克思從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出發所理解的無產階級畫等號。他們的共同性價值不是商品價值,而是政治價值,即在非物質勞動的價值生產中創造出能夠反抗資本帝國的生命政治主體力量。“新的價值理論應該基于經濟、政治和社會創新的力量,而這些力量在今天已經成為諸眾欲望的表達。”[18]224可見,價值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服務于生命政治主體的解放籌劃。盡管他們把諸眾看作新型無產階級,但這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范疇相距甚遠。在馬克思那里,產業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主體,這一階級解放的實質是“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13]45,而不是采取和平“出走”的方式脫離資本帝國的控制。“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于這一目標”。[26]可見,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無產階級遭受剝削和控制的基礎,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實現經濟解放才是達致全人類解放的有效路徑。哈特和奈格里把馬克思時代的無產階級主體轉化為非物質勞動境況下受資本帝國控制的所有個人之集合即諸眾,這實際上是唯心主義的錯誤判斷。他們的諸眾概念否定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而在資本的全球化時代,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將不可能準確把握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實質,只能流于現象層面的分析。正如哈維所言,就資本主義的生存和延續來說,相比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種族以及其他身份形式,階級身份最為根本,我們無法想象沒有階級的資本主義[27]。
五、結 語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非物質勞動不限于資本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創造出摧毀資本的革命主體即諸眾。哈特和奈格里所說的解放潛能蘊含在非物質勞動對共同性的創造中,生命政治勞動能夠自主地進行協作和交往,具有擺脫資本普遍統治的可能性。他們在生命政治勞動創造的共同性中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契機,但卻作了過于樂觀的判斷。哈特和奈格里所看到的生命政治主體之間的自主合作關系盡管是重要的勞動關系,但如果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立場上看,它只是現象層面的外在社會關系,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作為一種客觀的權力仍然規訓著勞動者的存在形態和生活方式,勞動依然從屬于資本。只要資本掌控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勞動方式無論怎樣變化,最終都難逃資本編織的無所不在的權力體系。哈特和奈格里對潛能、主體和革命的解讀不可避免地走向主體政治的道路。
在資本編織的微觀權力體系滲透進生活的一切領域的情況下,為什么共同性能夠由生命政治主體自己控制,哈特和奈格里并未對其客觀現實性作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在他們的致思理路中,非物質勞動境況下的資本至多只能占有其產品和價值,根本無法占有或征服生產合作關系和勞動過程,這種觀點與普遍存在的如下事實不符:信息、符碼、知識、交往與合作等共同性形式大部分是在資本的支撐和組織下完成的,比如信息和軟件的開發,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等。在這種情況下,生命政治主體如何掌握共同性,以及如何通過這種共同性形式實現解放,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具有太強的主體政治的色彩。他們把生命政治主體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民主自治之上,這顯然夸大了資本帝國控制下民主自治的社會歷史作用。既然資本帝國已經控制了人的整個生命和生活的全部領域,為什么民主自治這一生命組織的方式能夠逃脫資本的擺布呢?以奇異性和雜多性為根本特質的生命政治主體又是如何進行組織以實現民主自治的呢?他們在全部著作中都未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只能求助于具有倫理色彩的價值預設。不管是哪種勞動,只要被納入到資本增殖的經濟關系之中,就會被資本所控制。因此,要真正實現勞動解放,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實現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28]。那種單憑非物質勞動和共同性的發展就能夠實現諸眾的生命政治解放的想法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背離。
參考文獻:
[1] 張一兵.非物質勞動與創造性剩余價值——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國》解讀[J]. 國外理論動態,2017(7):35-48.
[2] 李春建.對安東尼奧·內格里“非物質勞動”概念的學術考察[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1):123-130.
[3] 唐慶 . 非物質勞動與生命政治學——內格里非物質勞動理論考察[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6):132-137.
[4] 唐正東 . 非物質勞動與資本主義勞動范式的轉型——基于對哈特、奈格里觀點的解讀[J]. 南京社會科學,2013(5):28-36.
[5] 徐宇曉 . 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產理論研究——從“非物質勞動”、“生命政治”到“生命政治生產”[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122-129.
[6] 張一兵 . 資本帝國的生命政治存在論——奈格里、哈特的《帝國》解讀[J].河北學刊,2019(2):32-40.
[7] 汪行福 . 《帝國》:后現代革命的宏大敘事[G]//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3-366.
[8] 劉懷玉,陳培永 . 從非物質勞動到生命政治——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大眾政治主體的建構[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2):73-82.
[9] 莫偉民 . 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產及其與福柯思想的歧異[J]. 學術月刊,2017(8):58-67.
[10] 藍江 . 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產——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譜系學蠡探[J].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19-27.
[11] 馮波 . 奈格里論斯賓諾莎的生命政治[J]. 世界哲學,2017(1):15-21.
[12] 宋曉杰 . 斯賓諾莎與海德格爾:奈格里與阿甘本政治理論的不同基調[J]. 江西社會科學,2018(11):23-33.
[1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內格里 . 超越帝國[M]. 李琨,陸漢臻,譯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5] HARDT M,NEGRI A . Empire[M]. Cambrid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6] HARDT M,NEGRI A.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
[17] HARDT M,NEGRI A. 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 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8.
[18]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 . 大同世界[M].王行坤,譯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19] NEGRI A,DUFOURMANTELLE A . Negri on Negri[M]. DEBEVOISE M B,tran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4:114.
[20] 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M].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68.
[21] HARDT M,NEGRI A. Assembl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234.
[22] 張一兵 . 反抗帝國:新的革命主體和社會主義戰略——奈格里、哈特《帝國》解讀[J]. 東岳論叢,2018(5):5-13.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6.
[25] 孫樂強 . 馬克思“一般智力”范疇的當代重構及其效應評估[J]. 探索與爭鳴,2021(1):50-59.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6.
[27] 大衛·哈維 . 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評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J]. 王行坤,譯. 上海文化,2016(2):49-59+64.
[28] 黃學勝,易江 . 從“市民社會”到“人類社會”——世界觀變革與《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兩種社會觀[J]. 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1):54-63.
A Bio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Immaterial Labor: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Views of Hardt and Negri from the Marxian Perspective
CHEN Fei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Hardt and Negri believe that the entire Western society is stepping into a post-industrial era characterized by networking,informatization,and servitization,etc. This transformation is marked by the gradual replacement of industrial labor by immaterial labor which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mode and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oduction. Immaterial labor has a broad and profound biopolitical implications,creating a commonality that cannot be fully appropriated by capital,and this commonality gives the masses the strength to fight against the empire of capital and contains the potential for biopolitical eman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labor and subject politics,Hardt and Negri have explained in depth the connotation of immaterial labor and the socio-historical effects it triggers,and regarded this view as a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s labor theory. However,their biopolitical reading of immaterial labor goes against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doctrine of emancipation,and suffers from a simp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lass relations and real historical processes. Rethinking their view of immaterial labor with Marx’s stance ha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arxian philosophy's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Key words:immaterial labor;biopolitics;commonality;labor theory of value
責任編輯 高阿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