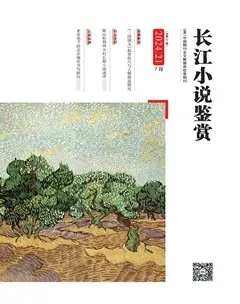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形象
[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21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形象,以也門(mén)作家穆罕默德·瓦利的《中國(guó)之路》和阿爾及利亞作家艾敏·扎維的《女王》為核心文本。通過(guò)文本分析和比較研究,探討了這些作品如何塑造和呈現(xiàn)中國(guó)形象,以及這些形象對(duì)中阿關(guān)系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小說(shuō)不僅展現(xiàn)了中國(guó)在阿拉伯世界的經(jīng)濟(jì)和文化影響力,還反映了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國(guó)的認(rèn)知演變。同時(shí),這些作品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阿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洞見(jiàn)。
[關(guān)鍵詞] 阿拉伯文學(xué) 中國(guó)形象 跨文化交流 一帶一路 文化認(rèn)同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2097-2881(2024)21-0065-04
隨著中國(guó)在全球舞臺(tái)上影響力的不斷增強(qiáng),中國(guó)在阿拉伯文學(xué)中的形象也日益豐富和復(fù)雜。這一現(xiàn)象反映了中阿關(guān)系的深化與拓展,同時(shí)也凸顯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獨(dú)特作用。新世紀(jì)以來(lái),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國(guó)的書(shū)寫(xiě)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東方主義視角,而是呈現(xiàn)出更加多元和深入的特征。本研究還將考察這種文學(xué)表征對(duì)中阿關(guān)系發(fā)展的潛在影響,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與互鑒。通過(guò)這一研究,我們不僅可以更好地理解阿拉伯世界對(duì)中國(guó)的文學(xué)想象,還能為促進(jìn)中阿之間的文化對(duì)話(huà)和相互理解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
一、跨文化鏡像:理論視角與方法論探索
1.形象學(xué)理論
形象學(xué)理論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chǔ)。作為比較文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分支,形象學(xué)主要研究一個(gè)國(guó)家或民族在另一個(gè)國(guó)家或民族文學(xué)作品中的形象。在本研究中,形象學(xué)理論有助于理解阿拉伯作家如何在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構(gòu)建和呈現(xiàn)中國(guó)形象。這一理論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中的國(guó)家形象不僅反映了作者的個(gè)人觀點(diǎn),還折射出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文化背景和集體認(rèn)知。通過(guò)形象學(xué)的視角,本研究深入分析《中國(guó)之路》和《女王》中的中國(guó)形象,探討這些形象如何受到作者個(gè)人經(jīng)歷、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以及中阿關(guān)系發(fā)展等因素的影響[1]。同時(shí),形象學(xué)理論也提醒研究者警惕文學(xué)作品中可能存在的刻板印象和偏見(jiàn),從而更客觀地評(píng)估這些作品對(duì)中阿文化交流的影響。
2.跨文化交際理論
跨文化交際理論為本研究提供了另一個(gè)重要的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主要關(guān)注不同文化背景的個(gè)體或群體之間的交流過(guò)程和結(jié)果。在分析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形象時(shí),跨文化交際理論有助于理解中阿兩種文化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碰撞和融合。特別是在《女王》這樣描繪中阿跨國(guó)戀情的作品中,跨文化交際理論有助于解析人物間的互動(dòng)、誤解和理解過(guò)程。這一理論強(qiáng)調(diào)文化差異對(duì)交流的影響,以及如何通過(guò)有效的溝通來(lái)克服這些差異。通過(guò)這一視角,本研究探討阿拉伯作家如何在其作品中呈現(xiàn)中阿文化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人物間的互動(dòng)和情節(jié)發(fā)展。同時(shí),跨文化交際理論也為評(píng)估這些文學(xué)作品在促進(jìn)中阿文化理解方面的潛在作用提供了理論工具。
3.文本分析與比較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與比較研究方法構(gòu)成了本研究的主要方法論基礎(chǔ)。文本分析方法用于深入探討《中國(guó)之路》和《女王》等作品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語(yǔ)言和主題,從而全面把握這些作品中的中國(guó)形象。通過(guò)仔細(xì)解讀文本,本研究識(shí)別出作者在塑造中國(guó)形象時(shí)使用的具體手法、選擇的敘事視角,以及隱含的文化態(tài)度。比較研究方法則是研究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如何理解這些作品。通過(guò)比較不同時(shí)期、不同作者筆下的中國(guó)形象,本研究追蹤阿拉伯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的演變軌跡[2]。同時(shí),比較研究也將這些作品置于世界文學(xué)的大背景下,探討它們與其他文化中的中國(guó)形象表現(xiàn)有何異同。這種方法不僅有助于理解個(gè)別作品的獨(dú)特性,還能幫助把握阿拉伯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的整體特征和發(fā)展趨勢(shì)。
二、絲路鋪就的文學(xué)畫(huà)卷:《中國(guó)之路》中的東方想象
1.作品背景與主題分析
《中國(guó)之路》是也門(mén)現(xiàn)代著名小說(shuō)家穆罕默德·瓦利于1959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shuō),其創(chuàng)作背景深深植根于20世紀(jì)50年代中也兩國(guó)關(guān)系的特殊歷史時(shí)期。在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正積極開(kāi)展對(duì)外援助,而也門(mén)則處于謀求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關(guān)鍵階段。小說(shuō)以中國(guó)援建薩那—荷臺(tái)達(dá)公路這一真實(shí)事件為藍(lán)本,巧妙地將歷史現(xiàn)實(shí)與文學(xué)想象相融合。作品的主題聚焦于中國(guó)援外人員與也門(mén)當(dāng)?shù)孛癖娭g的互動(dòng),通過(guò)描繪這種跨文化交流,深入探討了發(fā)展中國(guó)家之間的團(tuán)結(jié)互助精神。瓦利的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對(duì)一段歷史的記錄,更是對(duì)東方國(guó)家間合作模式的思考。通過(guò)對(duì)比中國(guó)援外人員與西方殖民者的不同態(tài)度和行為,作者隱晦地表達(dá)了對(duì)西方殖民主義的批評(píng),同時(shí)凸顯了中國(guó)援助的獨(dú)特性質(zhì)[3]。這種主題設(shè)置反映了當(dāng)時(shí)阿拉伯世界對(duì)中國(guó)的普遍認(rèn)知,即將中國(guó)視為一個(gè)友好的、能夠理解并支持他們發(fā)展訴求的東方大國(guó)。
2.中國(guó)援外人員形象塑造
在《中國(guó)之路》中,瓦利通過(guò)也門(mén)農(nóng)民工阿里的視角,生動(dòng)塑造了中國(guó)援外人員的形象。這些中國(guó)工人和專(zhuān)家被描繪成勤勞、友善、謙遜的群像,與作品中傲慢的西方人形成鮮明對(duì)比。作者著重刻畫(huà)了中國(guó)人員與當(dāng)?shù)毓と送使部唷⒉晃菲D險(xiǎn)的工作態(tài)度,突出他們?cè)谄D苦環(huán)境中展現(xiàn)的堅(jiān)韌精神和技術(shù)能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瓦利通過(guò)細(xì)膩的筆觸描繪了中國(guó)人員與當(dāng)?shù)毓と酥g的日常互動(dòng),如共同勞作、技術(shù)交流等場(chǎng)景,展現(xiàn)了兩國(guó)人民之間真摯的友誼。這種形象塑造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中國(guó)援外人員的敬意,也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也門(mén)民眾對(duì)中國(guó)的普遍好感。同時(shí),作者還巧妙地通過(guò)中國(guó)人員的言行,傳達(dá)了“授人以漁”的援助理念,展示了中國(guó)對(duì)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態(tài)度。這種形象塑造超越了簡(jiǎn)單的刻板印象,呈現(xiàn)出一種立體的、人性化的中國(guó)形象,為讀者提供了一個(gè)理解中國(guó)對(duì)外援助政策和中國(guó)人民品格的窗口。
3.“中國(guó)之路”的象征意義
“中國(guó)之路”在小說(shuō)中不僅是一條實(shí)體的公路,更承載了深刻的象征意義。首先,它象征著發(fā)展與進(jìn)步。通過(guò)描繪公路建設(shè)給也門(mén)帶來(lái)的變化,瓦利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對(duì)落后地區(qū)的深遠(yuǎn)影響。公路不僅連接了地理上的兩點(diǎn),更象征性地連接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落后與發(fā)展。其次,“中國(guó)之路”象征著一種新型的國(guó)際合作模式。與西方國(guó)家的援助不同,中國(guó)的援助被描繪成尊重受援國(guó)、注重技術(shù)轉(zhuǎn)移、促進(jìn)自主發(fā)展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小說(shuō)中被賦予了積極的道德評(píng)價(jià),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中國(guó)發(fā)展道路的認(rèn)同。再次,“中國(guó)之路”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文化交流的隱喻。在公路的修建過(guò)程中,中國(guó)工人與也門(mén)民眾的互動(dòng)實(shí)際上是兩種文化的交匯,象征著東方文明之間的對(duì)話(huà)與融合。最后,“中國(guó)之路”還可以被視為一種希望和力量的象征。小說(shuō)中“人比山更強(qiáng)大”的主題,不僅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工人的奉獻(xiàn)精神,也激發(fā)了也門(mén)人民的自信和決心。通過(guò)這個(gè)象征,瓦利傳達(dá)了發(fā)展中國(guó)家通過(guò)團(tuán)結(jié)合作可以克服困難、實(shí)現(xiàn)發(fā)展的信念。
三、愛(ài)情紐帶下的文化碰撞:《女王》中的中國(guó)新形象
1.作品背景與主題分析
《女王》是阿爾及利亞著名作家艾敏·扎維于2015年創(chuàng)作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其創(chuàng)作背景植根于21世紀(jì)中阿關(guān)系快速發(fā)展的新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中國(guó)在阿爾及利亞的經(jīng)濟(jì)存在感大幅提升,中國(guó)企業(yè)和勞務(wù)人員在阿爾及利亞的數(shù)量顯著增加,兩國(guó)民間交往日益頻繁。扎維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社會(huì)現(xiàn)象,將其轉(zhuǎn)化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素材。小說(shuō)以中國(guó)工程師余楚孫和阿爾及利亞法醫(yī)薩庫(kù)拉的跨國(guó)戀情為主線(xiàn),深入探討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作品的主題超越了簡(jiǎn)單的愛(ài)情敘事,通過(guò)個(gè)人情感的鏡像反射出更廣闊的社會(huì)文化圖景[4]。扎維巧妙地將個(gè)人命運(yùn)與國(guó)家發(fā)展、文化認(rèn)同等宏大主題相結(jié)合,呈現(xiàn)出一幅復(fù)雜而生動(dòng)的當(dāng)代中阿關(guān)系圖景。通過(guò)描繪兩位主人公的情感糾葛和文化沖突,作者深入探討了文化差異、性別角色、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碰撞等議題,為讀者提供了一個(gè)理解當(dāng)代中阿文化交流的獨(dú)特視角。
2.中國(guó)男性形象的重塑
在《女王》中,扎維通過(guò)塑造余楚孫這一角色,對(duì)阿拉伯文學(xué)中傳統(tǒng)的中國(guó)男性形象進(jìn)行了重塑。余楚孫被描繪成一個(gè)既有專(zhuān)業(yè)能力、又富有人文情懷的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他不僅精通工程技術(shù),還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認(rèn)同。這種形象塑造打破了阿拉伯世界對(duì)中國(guó)人的刻板印象,展現(xiàn)了一個(gè)立體、復(fù)雜的中國(guó)新形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著重描繪了余楚孫對(duì)女性的尊重和平等對(duì)待,這與阿拉伯社會(huì)中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義形成鮮明對(duì)比。通過(guò)余楚孫與薩庫(kù)拉的互動(dòng),扎維展現(xiàn)了中國(guó)新一代男性的開(kāi)放、包容和進(jìn)步特質(zhì)。同時(shí),作者也不回避中國(guó)人物的困惑和矛盾,如余楚孫在文化適應(yīng)過(guò)程中的掙扎,這種真實(shí)而細(xì)膩的刻畫(huà)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mǎn)和可信。通過(guò)這樣的形象重塑,扎維不僅挑戰(zhàn)了阿拉伯讀者對(duì)中國(guó)男性的固有認(rèn)知,也為阿拉伯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深度。
3.文化差異與身份認(rèn)同的探討
《女王》通過(guò)余楚孫和薩庫(kù)拉的跨國(guó)戀情,深入探討了中阿文化差異和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扎維巧妙地設(shè)置了一系列文化碰撞的場(chǎng)景,如飲食習(xí)慣、社交禮儀、宗教信仰等,通過(guò)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細(xì)節(jié)展現(xiàn)了兩種文化的差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滿(mǎn)足于簡(jiǎn)單地列舉這些差異,而是深入探討了這些差異背后的文化邏輯和價(jià)值觀念。例如,通過(guò)描繪余楚孫對(duì)個(gè)人空間的需求與薩庫(kù)拉對(duì)家庭親密關(guān)系的期待之間的矛盾,作者揭示了中國(guó)和阿拉伯文化在個(gè)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方面的差異。同時(shí),小說(shuō)也探討了在跨文化交往中個(gè)體身份認(rèn)同的變化和重構(gòu)。余楚孫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認(rèn)同,又要適應(yīng)新的文化環(huán)境,這種矛盾和掙扎生動(dòng)地體現(xiàn)了全球化時(shí)代個(gè)體身份的流動(dòng)性和復(fù)雜性。通過(guò)這些探討,扎維不僅展現(xiàn)了文化差異帶來(lái)的挑戰(zhàn),也暗示了跨文化理解和包容的可能性,為讀者提供了思考文化交流和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的新視角。
四、異質(zhì)與共性:兩部小說(shuō)中國(guó)形象的多維解讀
1.形象塑造的演變
通過(guò)比較《中國(guó)之路》和《女王》這兩部創(chuàng)作于不同時(shí)期的小說(shuō),阿拉伯文學(xué)中國(guó)形象塑造的演變軌跡變得清晰可見(jiàn)。《中國(guó)之路》中的中國(guó)形象主要聚焦于集體,中國(guó)援外人員作為一個(gè)整體被塑造成勤勞、友善、富有同情心的群像。這種形象塑造反映了20世紀(jì)50年代阿拉伯世界對(duì)中國(guó)的普遍認(rèn)知,即將中國(guó)視為一個(gè)友好的、支持第三世界國(guó)家發(fā)展的社會(huì)主義大國(guó)。相比之下,《女王》中的中國(guó)形象則更加個(gè)人化和多元化。主人公余楚孫被塑造成一個(gè)有獨(dú)特個(gè)性、復(fù)雜情感和文化認(rèn)同的個(gè)體。這種轉(zhuǎn)變反映了隨著中阿交往的深入,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國(guó)的認(rèn)知從宏觀、籠統(tǒng)逐漸轉(zhuǎn)向微觀、具體。同時(shí),兩部作品中的中國(guó)形象雖然在具體特征上有所不同,但都體現(xiàn)了對(duì)中國(guó)人勤勞、友善、重視文化等特質(zhì)的肯定。這種形象塑造的連續(xù)性與變化性,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對(duì)中國(guó)認(rèn)知的深化過(guò)程,也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在阿拉伯文學(xué)想象中的獨(dú)特地位。
2.文化交流視角的拓展
《中國(guó)之路》和《女王》這兩部小說(shuō)在文化交流的描繪上呈現(xiàn)出明顯的視角拓展。《中國(guó)之路》主要聚焦于工作場(chǎng)景中的文化交流,中國(guó)援外人員與也門(mén)工人之間的互動(dòng)主要體現(xiàn)在技術(shù)傳授和共同勞動(dòng)等方面。這種描繪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中阿文化交流的主要模式,即以經(jīng)濟(jì)合作為主導(dǎo)的官方交流。而在《女王》中,文化交流的視角則被大大拓寬了。小說(shuō)通過(guò)描繪中阿兩國(guó)個(gè)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入交往,展現(xiàn)了更為復(fù)雜和多元的文化交流圖景。從飲食習(xí)慣到社交禮儀,從價(jià)值觀念到情感表達(dá),小說(shuō)全方位地展現(xiàn)了中阿文化在個(gè)人層面的碰撞與融合。這種視角的拓展不僅反映了中阿關(guān)系的深化,也體現(xiàn)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zhèn)€人化、日常化的趨勢(shì)。通過(guò)比較兩部作品,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阿文化交流的認(rèn)知從表層的物質(zhì)交換逐漸深入到價(jià)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交流,這種認(rèn)知的深化為理解當(dāng)代中阿文化關(guān)系提供了重要的文學(xué)視角。
五、文學(xué)交匯中的國(guó)家形象: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的中國(guó)敘事
1.多元化與立體化的趨勢(shì)
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形象呈現(xiàn)出明顯的多元化和立體化趨勢(shì)。這種趨勢(shì)首先體現(xiàn)在中國(guó)形象的多樣性上。不同于早期阿拉伯文學(xué)中較為單一的中國(guó)形象,新世紀(jì)的作品呈現(xiàn)了各種類(lèi)型的中國(guó)角色,包括工程師、商人、學(xué)者等,反映了中國(guó)在阿拉伯世界日益多元的存在。其次,這種趨勢(shì)還體現(xiàn)在對(duì)中國(guó)形象的深度刻畫(huà)上[5]。作家們不再滿(mǎn)足于表面的描述,而是深入探討中國(guó)角色的內(nèi)心世界、文化背景和價(jià)值觀念,使形象更加豐滿(mǎn)和真實(shí)。例如,《女王》中的余楚孫就被塑造成一個(gè)有著復(fù)雜情感和文化認(rèn)同的立體人物。此外,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還嘗試從多個(gè)角度審視中國(guó),既有對(duì)中國(guó)發(fā)展成就的贊嘆,也有對(duì)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思考,甚至包含了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問(wèn)題的批評(píng)性反思。這種多元化和立體化的趨勢(shì)反映了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國(guó)認(rèn)知的深化,也體現(xiàn)了阿拉伯文學(xué)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視野拓展。通過(guò)這種更加豐富和復(fù)雜的中國(guó)形象塑造,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為讀者提供了理解當(dāng)代中國(guó)的多維視角。
2.對(duì)傳統(tǒng)刻板印象的突破
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在中國(guó)形象的塑造上顯著突破了傳統(tǒng)的刻板印象。早期阿拉伯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往往帶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將中國(guó)描繪成一個(gè)神秘、遙遠(yuǎn)、落后或極度發(fā)達(dá)的異域國(guó)度。然而,新世紀(jì)的作品開(kāi)始打破這些固有印象,呈現(xiàn)出更加真實(shí)和當(dāng)代的中國(guó)形象。首先,這些作品不再將中國(guó)視為一個(gè)抽象的符號(hào),而是將其置于具體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中。例如,《女王》中的中國(guó)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東方,而是與阿爾及利亞有著密切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的現(xiàn)代國(guó)家。其次,新世紀(jì)的作品開(kāi)始挑戰(zhàn)一些長(zhǎng)期存在的刻板印象。比如,傳統(tǒng)印象中的中國(guó)人往往被描繪成封閉、保守的形象,而《女王》中的余楚孫則展現(xiàn)了開(kāi)放、包容的特質(zhì)。此外,這些作品還嘗試展現(xiàn)中國(guó)的多樣性和復(fù)雜性,避免了將中國(guó)簡(jiǎn)單化或理想化的傾向。通過(guò)這種對(duì)傳統(tǒng)刻板印象的突破,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不僅更新了阿拉伯讀者對(duì)中國(guó)的認(rèn)知,也為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3.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意義
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敘事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文化交流意義。首先,這些作品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民心相通提供了重要的文學(xué)基礎(chǔ)。通過(guò)生動(dòng)的故事和豐滿(mǎn)的人物形象,這些小說(shuō)幫助阿拉伯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感知當(dāng)代中國(guó),從而增進(jìn)了兩國(guó)民眾間的情感聯(lián)系。其次,這些作品展現(xiàn)了“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文化交流實(shí)踐。例如,《女王》中描繪的中阿跨國(guó)戀情,可以被視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人文交流的一種具象化表達(dá)。再者,這些小說(shuō)也反映了“一帶一路”倡議給阿拉伯世界帶來(lái)的變化和影響。通過(guò)描繪中國(guó)在阿拉伯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存在和文化影響,這些作品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社會(huì)文化效應(yīng)提供了獨(dú)特的文學(xué)視角。此外,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敘事也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跨文化對(duì)話(huà)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六、結(jié)語(yǔ)
新世紀(jì)阿拉伯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形象呈現(xiàn)出多元化和深層化的特點(diǎn),反映了中阿關(guān)系的深化和阿拉伯作家對(duì)中國(guó)認(rèn)知的演變。這些文學(xué)作品不僅豐富了阿拉伯文學(xué)的內(nèi)容,也為中阿兩國(guó)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人文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學(xué)素材和思想資源。未來(lái)的研究可以進(jìn)一步探討這些文學(xué)作品對(duì)中阿關(guān)系實(shí)踐的影響,以及如何利用文學(xué)作品促進(jìn)兩國(guó)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增進(jìn)其友誼。
參考文獻(xiàn)
[1] 趙超.新時(shí)代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形象的歷史生成、文明意蘊(yùn)及實(shí)踐原則[J].大連干部學(xué)刊,2024(8).
[2] 焦榕.全球傳播背景下綜藝節(jié)目的中國(guó)形象建構(gòu)——以《花兒與少年·絲路季》為例[J].全媒體探索,2024(7).
[3] 黃麗,張麗花.“娜拉形象”的中國(guó)敘事變奏——從易卜生到曹禺[J].四川戲劇,2024(7).
[4] 金艷紅.管窺外國(guó)小說(shuō)中的中國(guó)人印象及研究意義[J].華章,2024(7).
[5] 賈婷.《面紗》中的東方主義敘事與中國(guó)形象書(shū)寫(xiě)[J].戲劇之家,2024(17).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