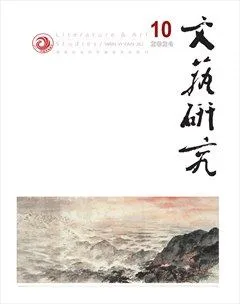鄧以蟄美學文本所涉器物圖像考論
鄧以蟄、宗白華、朱光潛等人的美學,構成了20世紀中國學人重建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劉綱紀指出,不同于宗白華“著重于美的欣賞的直觀把握”和滕固“著重于史的演變的風格探討”,鄧以蟄“把畫史與畫學、書史與書學緊密地結合起來,對中國書畫理論作一種哲理的研究,提出了一種關于中國書畫的具有相當完整的系統性的美學理論”。需要注意的是,在鄧以蟄的美學建構的同時期,發生了一個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大、學術意義深遠的事件,即以安特生、斯文·赫定為代表的瑞典探險家和以徐旭生、李濟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在甘肅、內蒙、山東、河南等地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科學考察和考古發掘活動。貫穿這次科考活動的,是中外學者關于“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爭論。如何科學、客觀地對此做出回應,既是當時知識界的共同任務,也是這一時期中華美學精神建構的根本立足點。鄧以蟄積極關注當時的考古發掘及相關論爭,與中外考古學家、文物收藏家都有著密切交往。這使鄧以蟄能夠立足器物圖像展開美學建構,他的美學思想體系及其價值亦應在此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一、從《國畫魯言》的一條附注談起
鄧以蟄從考古文物進行美學建構并非偶然。一方面,作為乾嘉時期碑學大家鄧石如的五世孫,鄧以蟄在接觸秦漢石刻畫像上具有先天優勢,他很早就看過家藏的趙明誠、洪適、黃易等人關于武梁祠畫像的記載和圖錄;另一方面,1923年秋,鄧以蟄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后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其間他與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兩位奠基人李濟、徐旭生及日本考古學家關野貞等人均有密切交往,這使他能夠及時獲得當時最新的考古信息和資料。這就不難理解,鄧以蟄的美學文本為何會關注考古器物的藝術特征,分析這些特征對中國美學和藝術的影響。對此,不妨從鄧以蟄1935年發表于《大公報》的《國畫魯言》一文展開分析。這篇文章原名“中國繪畫之派別及其變遷”,最初寫于1924年,發表于1926年的《晨報副刊》。鄧以蟄在重刊此文時,特意增添了一條近三百字的附注。這條附注篇幅短小卻內容豐富,透露出考古文物對鄧以蟄美學思想的潛在影響:
附注:近年安徽壽縣有大批戰國時楚銅器出土,據云(銅) 器藏于木格內,木上皆有彩漆畫。中央研究院得一巨片,漆上加彩畫,花紋為三代云雷紋格式穿插以龍爪鳳翼之類,顏色為金——即黃、白、紅、藍諸色。顏色或有象征意義。花紋表現正介在三代與漢作風之間。漢代漆畫近年出土亦不少,最著者為在朝鮮古樂浪郡古墓中掘出諸物,最完美者為彩篋一具,上畫孝圖人物彩畫,其線條顏色表現力之強,無有倫比,面孔情態,幾無一相同。視美國波斯(士) 頓所藏之洛陽古墓中出土之漢代彩色人物畫尤精尤古,生動之致可謂極矣。其他圖案式花紋彩繪正與壽縣彩繪亦復相近,足見漢代藝術繼續春秋時代一部分地域之藝術而發展者也。
這條附注提及了三個當時影響極大的新的考古發現:安徽壽縣的戰國楚銅器及彩畫、朝鮮樂浪郡遺址古墓的彩篋、波士頓美術館所藏洛陽古墓人物壁畫,再加上正文中提及的山東濟寧武梁祠石刻畫像,全文共有四處涉及考古文物。這條附注意義重大,從中可以看出鄧以蟄美學思想的獨特性。
首先,附注言及1933年壽縣朱家集的楚幽王墓的發掘情況。據《鄧以蟄先生生平著述簡表》記載:“本年,安徽壽縣發現大批楚銅器及木版彩畫,鄧以蟄得知,無比興奮,轉告中央研究院李濟之,派人前往調查。”但此處記述存在偏差:這里的“本年”為1934年,與壽縣文物的出土時間不符。實際情況是,壽縣文物于1933年出土,而鄧以蟄同年秋季赴歐,直到1934年下半年才回國。他回國聞知此事后,便告知好友李濟一同前往考察。1934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李濟被任命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因此可以組織人員赴壽縣調查,并代中央研究院獲得“巨片”這一重要文物。
據《李濟先生學行紀略》1934年部分記載:“本年,考古組組織了魯東、洹濱、豫西、新鄭、廣武以及洹水上游和壽縣的考古調查。”這可證實鄧以蟄與李濟對壽縣文物的考察,也可印證鄧以蟄所說的“中央研究院得一巨片”。這一“巨片”上的彩繪和云雷紋、龍鳳紋、花紋等,引起了鄧以蟄的關注。他認為,繪畫始于宗教歷史人物,目的在于“圖形事跡,垂示將來”,中國繪畫有著同樣的起源。這一觀點原本沒有漢以前的繪畫作為證據,而壽縣出土的銅器和木版彩畫正可提供佐證。鄧以蟄將這件木版彩畫的創作年代定于三代與漢之間的判斷也是準確的。直到1957年,鄧以蟄在討論書法與畫法的關系時,仍提到“壽縣所發現的楚器”在“繪”方面的特點。對于這次考察,劉綱紀指出:“這是一次對研究楚藝術有重要意義的考古調查,并對鄧以蟄的美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次,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樂浪郡古墓的發掘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考古事件。鄧以蟄對壽縣出土文物感興趣,可能與他此前關注的樂浪郡古墓出土的漢代彩篋有關。樂浪郡古墓的發掘早在1909年便開始,一直持續到1944年。1935年,在朝鮮古跡研究會主持的發掘工作中,彩篋冢和王光墓出土了一個彩篋,引起了學界關注,鄧以蟄也對此做出了積極回應。這一彩篋漆畫描繪了類似《二十四孝圖》的故事畫,以孝子故事為主要內容。鄧以蟄認為,畫中人物不僅表情生動、面貌各異,而且線條、顏色的靈活性和表現力已達到很高水平,這為魏晉人物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再次,當鄧以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17—1923) 時,洛陽古墓的畫像磚還未入藏波士頓美術館;他回國后,這組壁畫經歐洲被賣到美國,可能他于1933年秋至1934年夏在歐洲考察時見過壁畫圖片。鄧以蟄將該人物畫準確概括為“尤精尤古,生動之致可謂極矣”。他根據人物畫像的技法及其表現力指出,正是由于從春秋到漢代藝術的連續性發展,才能在漢代出現如此精妙的刻繪人物畫像。鄧以蟄所謂“精”“古”,指畫中的人物表現已達“傳神”境界,能夠體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和面貌;“生動之致”則不僅指對人物形貌和神態的準確、生動的表現,更指這種表現為漢晉人物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顧愷之的“傳神寫照”、謝赫的“氣韻生動”等觀念也就呼之欲出了。
最后,鄧以蟄還在正文中提到第四處考古遺址及文物:“漢代繪畫雖無流傳;但漢代石刻如山東濟寧武氏祠的石刻,為數甚多,有些是極淺的浮雕,有些簡直是白描的石刻。這種白描的鉤線,與顧虎頭的女史箴圖(英國博物院藏) 的筆調幾無二致。圖中所刻盡是些當時的風俗人情,同些孝的故事。但故事的表現——車馬的動靜與人物的情態——全在鉤畫的線紋,初不以為非文字不能表現的,這是線紋成了一種表現的工具。換言之,成了一種藝術的工具。”這說明,鄧以蟄在十余年前就已注意到山東濟寧的武梁祠畫像,并將畫中的石刻線紋視作一種藝術表現工具,指出它與顧愷之的人物畫畫法的內在演進關系。
除了上述四處遺址,鄧以蟄在1935年發表于《大公報》的《書畫同源》一文中,還提到與樂浪郡遺址相關的朝鮮高句麗遺址的古墓壁畫:“如朝鮮近時發現高勾(句)麗遺跡,古墓中有壁畫,畫蒼龍,玄武,天人,神仙,仕女俱見漢及魏晉遺風,蓋高勾麗承襲樂浪之漢代文化故也。”高句麗遺址的古墓器物、壁畫、石刻等的發掘,在當時是引人關注的考古事件。鄧以蟄指明,高句麗遺址的古墓壁畫承襲的是樂浪郡遺址的漢畫傳統。1935年9—10月,中國學者金毓黻、日本學者池內宏等人對高句麗遺址進行過兩次考察和拍照工作,鄧以蟄可能從在朝鮮京城大學任教的日本漢學家藤冢鄰那里獲得了相關資料。據藤冢鄰回憶:“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時,由舊知錢稻孫君介紹鄧中純、叔存兩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孫,且系日本留學生。余屢訪其西城北溝沿寓居……得展賞完白之肖像、遺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數十件。意外奇緣,驚喜不知所措。”從中可以看出,鄧以蟄收藏過朝鮮李朝手札等文物,他關注樂浪郡和高句麗遺址自在情理之中。
二、凈形論:器物作為美學本體
鄧以蟄的美學思想與當時興起的藝術考古研究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作為美學家,他注重從器物圖像中抽繹出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趣味、理想和觀念,指出器物圖像與“生動傳神”“氣韻生動”“意境”“心畫”等美學觀念的關系;作為藝術史家,他提煉出考古文物及其圖像藝術的特點,揭示出器物圖像與后來人物畫、山水畫的內在演進關系。鄧以蟄延續《周易》“觀物取象”“制器尚象”等觀念和命題,將器物圖像納入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序列,指出中國藝術本體經歷了從“形體一致”到“形體分化”的轉變。鄧以蟄所說的“形”主要指人物畫,同時也可用于山水畫:山水畫對山水林樹的空間布置方式源自早期人物畫,而山水畫之疏密技法亦受器物圖像的影響。鄧以蟄的美學思想以器物圖像為基礎,其核心概念是“凈形”。
鄧以蟄在1928年出版了《藝術家的難關》一書,他在該書收錄的同名文章中強調,繪畫和雕刻可以達到“純粹的構形”和“真正的絕對的境界”兩種藝術形式,而沖破人事情理、知識本能對藝術創作的束縛,正是藝術家的難關。鄧以蟄的“凈形論”美學觀于此初具雛形。他以柏拉圖對藝術的責難開篇,指出藝術的任務就是“造乎理想之境”,從而擁有一種“特殊的力量”,“使我們暫時得與自然脫離,達到一種絕對的境界,得一剎那間的心境的圓滿”。藝術家的創造要想達至此境界,須破除知識的干擾、捕捉感情、獨創性靈、克服官能的限制。但藝術有時仍會被知識束縛,故最能通達此境界的藝術首先是繪畫,其次是雕刻,再者為音樂。
鄧以蟄所謂“凈形”,指藝術形式要擺脫“膚泛平庸的知識”“人事上的情理”以及“百世而不移的本能”的限制和束縛,作為純粹的構形,與人類的性靈、情感相接。此類藝術帶有“蛻化”功能,即歷史性、時間性的事件糾葛須在藝術形式中脫去形跡,轉變為純粹的顏色、韻律、輪廓與形式;文學(詩) 與人事情理牽涉過深,因此無法成為純粹的構形。“我們看一段風景,這段風景與我們絕對沒有歷史上的聯想,它對于我們并沒有人事上的意趣,但是它的具體的印象,只要我們看到它的時候,總是有的。這種具體的印象,用文字來描寫,必定敵不上繪畫。”鄧以蟄的意思是,在風景的印象上,無論文字如何精妙,風景的顏色和輪廓都無法被絕對地描寫出來,因為文字所描繪的是概念而非具體印象;繪畫、雕刻等藝術之所以能使歷史境遇在形式中“蛻化”,是因為“它們表現的本旨原來就不在敘述事跡”。繪畫和雕刻最初都與神話、戲劇和歷史故事緊密相關,必然要表現人物的事跡或故事。然而,不同于詩側重表現時間性事件,繪畫和雕刻在表現人物時,側重表現外在自然(“形”或“體”)和內在性格特征(“神”) 兩個方面。
這牽涉了《藝術家的難關》一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即“凈形論”美學與繪畫、雕刻有何關系。鄧以蟄在書前使用了多幅圖像,包括菲迪亞斯、米開朗琪羅、呂德等人的雕刻作品,涉及巴特農神廟、西斯廷教堂等建筑,涵蓋命運女神、宙斯、尼俄柏、雅典娜、勒托、阿爾忒彌斯等古希臘神話人物,以及耶穌、摩西等基督教人物。鄧以蟄在《戲劇與雕刻》一文中指出,宙斯神廟上的雕刻幾乎是對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故事的完整呈現,但僅作為戲劇的附庸,直到菲迪亞斯,雕刻才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即從表現人物的動作變為表現人物的軀體和筋骨,他所雕刻的人物神情靜穆、身體端正、美到極處。抽象的神性使這些人體雕刻擁有極為純粹的美,無須假借人事來表現自己。一旦人事的繁雜和世俗侵入神像,便會使雕刻的純粹的美變得冗余,進而失去沉靜和流動的自然之美。所以,雕刻不僅不能像戲劇那樣使用人事,而且要棄絕它:“雕刻不但表現神,是要棄絕人事的,就是一個普通的人,要將此人的性格表現得真確,則非從靜中選擇一種態度不可。”所謂“靜”,就是雕刻在表現人物時,要強調人物的筋脈骨肉的內在力量和生命特點,使人物處于靜的狀態。鄧以蟄將這種狀態關聯于沃爾夫林所說的“壓制住的動作”(repressed movement) ,比如米開朗琪羅的摩西雕像,雙手持笏板的坐姿使摩西無法移動,望向遠方的動作也使他無法充分伸展。這種偏向靜止的形態,正是出于雕刻從內、外兩方面表現人體形態和內在血脈的結合這一特征的需要,并且雕刻從表現人的行動轉向表現人的內心。鄧以蟄在文章最后總結道:“雕刻家的工作在創造能成品格的‘形’。而形的含意必須是絕對的,唯一的,猶之乎一個字有一個字的含意,使觀者易于辨別了解然后可。”他所使用的“脫化”“棄絕”“洗盡”“蛻化”等詞語,都是“凈形論”美學的表征,意在強調繪畫和雕刻為了創造純粹的構形,并使之成為絕對唯一的存在,須去除人事的繁雜與多余,使觀者能一看便知“形”。鄧以蟄對雕刻作品的重視,可能與黑格爾將雕刻作為古典型藝術的代表有關。在《觀林風眠的繪畫展覽會因論及中西畫的區別》一文中,鄧以蟄提到了黑格爾的觀點,后者在談雕刻家創制此類理想形象時,強調要排除現象中的特殊細節,因為偶然性的細節會妨礙雕刻形象對對象之恒定個性和精神的表達。
在借鑒西方美學的同時,鄧以蟄始終將理論闡述建立在對具體藝術作品尤其是中國藝術作品的分析上。除了《國畫魯言》,他還在同時期發表了《以大觀小》《書畫同源》《氣韻生動》,這四篇文章共配有22幅中西藝術作品圖像,其中西方作品2件,青銅器紋飾、書法和繪畫等中國作品20件:戰國青銅器紋飾和圖繪9件,元代書法家張雨的唐人絕句書法1件,宋、明官窯器物4件,唐至清山水畫及人物畫6件。這些作品圖像體現了鄧以蟄美學的精神旨趣,也正是在這些文章中,鄧以蟄將他的“凈形論”美學貫穿到對中國藝術及其發展歷史的分析中,概括藝術的“形”與“體”間的辯證關系,進一步將器物本體論體系化。
鄧以蟄的建構方法帶有《周易》器象觀的底色。他所謂的“本體”首先指物質之“體”,物質的體積、重量、色彩等先天具有審美價值,可使主體感物動情,故而對藝術制作具有重要意義:“此一體而具有顏色輕重體積之物質,動人既深且切,并能切磋琢磨而制作之,誠無不美也;但終塊然獨立,與吾人心思動感不易打成一片。”物質之“體”的物理屬性是主體改造物質的基礎:從物質之“體”到藝術之“體”,須經由對客體之物質性的否定而成“形”,在這個過程中,“形”可避免物質本身的刻板,取其生動之一面,使生命的靈動氣息得以顯現,由此形成藝術之“體”。鄧以蟄以畫中山水為例:“畫之有山水,是物物皆有生命,生命不能離于物體而有;如何能離物體而單寫生命?曰,茲之所謂體,是經造作之體,而非獨立自成之體。體而能獨立自生自成,必其有生命也無疑。”鄧以蟄強調人工制作的重要性和器物制作的獨立性,器物制作所形成的圖像或形象須附著于器物表面,也就形成對器物的依賴,因而器物是藝術形象體系的最早的本體。“繪畫之興原為裝飾器用,是繪畫初不能脫器用而獨立也。繪畫既附麗于實器之上,則其體終以其所飾之器體以為體,固不能如今之一幅畫,反復掀視,仍止于一幅畫。若其能自存在,唯在其‘形’耳。”即強調繪畫早先所依附的器物作為繪畫之本體的根本性作用。這是物質之“體”向藝術之“體”的轉移和凈化。
鄧以蟄指出,“畫”與“繪”在施用對象上有所不同。當那些易于損毀的器物消失時,“畫”與“繪”也一并消失。那些堅固耐磨的器物,如陶器、銅器、石刻等,在對它們進行雕鏤、篆刻、范鑄、平脫時,雖有技法之不同,但最終都以“畫”的方式存在;歷經久遠,以顏色為主體的“繪”會消失,“畫”卻能依靠器物而留存下來。因此,依據器物的材質,人們采用不同的技法進行制作,這些制作方法其實都是“筆畫”,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繪畫作為形象體系,始終未能獲得獨立性,只能依附器物而存在,但繪畫本身的“形”已然具備,一旦在呈現材質方面實現突破,“形”的表現便可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分為形體一致和形體分化兩階段,形象之凈形與結構之凈形在此逐步實現。
所謂“形體一致”,指器物對紋飾、造形等形象制作的制約和限制,此時的“形”多為圖案化表現,無法脫離器物本體而獨立存在,故有著“一致”或“一體”的情況。所謂“形體分化”,指原本依附器物的圖案化表現,從對物理內容的描摹轉為對生命的描摹,雕刻、玉器、漆器圖像等對人物、禽獸等生命體的表現均以流動的生命為根本,生命體本身的形象獲得了獨立性。在此情況下,藝術傳統內部的結構、章法與規范逐漸形成,這時的藝術形象“有不恃器體烘托之概矣……形之美既不賴于器體,摹寫且復自求生動,示無拘束,故曰凈形。凈形者,言其無體之拘束耳”。在形體分化的階段,形象獲得了獨立性,實現了形象之凈化;前期依附器物本體所形成的形象體系和法則繼續發揮作用,使藝術實現了結構之凈化。
形體分化雖強調形象之獨立,但并不否定器物本體對形象的基礎性價值,其圖像、技法、精神轉變為傳統法則,對后世藝術形象的創造產生了影響。因此,“分化”不是斷裂,而是藝術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新的成長和延續。“漢代人物雖靜亦動,六朝唐之人物雖動猶靜。此最顯著之區別。蓋漢取生動,六朝取神耳,神能得物之全而去其膚泛,晶結散漫而納之于周洽。六朝唐之卷軸,篇幅結構仍法漢人如摹本女史箴圖與閻立本之歷代帝王像。但漢人水陸飛動,堆砌雜列,諸種不合理之章法則棄之不從,此又結構上之凈化也。”因此,形體分化乃指形象的獨立和結構的凈化,器物圖像對藝術發展的影響,從依附具體物質變為塑造內在法則和規范。就藝術而言,繪畫脫離器物本體而獲得獨立;就藝術創作而言,器物本體仍發揮著重要的限制,藝術家的創作須建立在對器物圖像的學習、摹畫的基礎上。鄧以蟄指出,“傳摹移寫”首先強調“拓畫”和“臨古”,它們的共同對象乃“魏晉勝流諸畫像”,這些鑄刻在宮苑墻壁和各種器具上的圖像,對后世的藝術創作具有決定性作用。這說明在形體分化后,藝術形象的“傳神”“寫生”“生動”等,仍須從“體”中得到藝術靈感和形象呈現方式。
三、楚風說:基于器物圖像的“六法”闡釋
可以看出,鄧以蟄關注的主要是戰國至漢代的器物圖像,尤其是漢代石刻畫像。他以“楚風”命名漢代藝術,對其表現飛動、氣韻流轉的審美特征給予了高度贊賞。他認為,漢代藝術為謝赫的“六法”、顧愷之的“傳神”做了鋪墊。鑒于“六法”的深遠影響,他以“凈形論”美學為基礎,結合具體器物,以“氣韻生動”為重點,對“六法”做了新的闡釋。這為鄧以蟄建立中國藝術發展史觀奠定了基礎。
鄧以蟄分別從客體對象、畫家、鑒賞家三個層面來闡釋“六法”,由此“六法”囊括了藝術活動的整個過程,其間每個階段對“六法”的側重有所不同:“傳摹移寫,隨類賦彩,應物象形三法皆主于外界,而有對象焉。畫既有對象,則以得象之似為先,故曰形似……畫家若欲有個人之表現,舍藝與意莫由也。故將骨法用筆經營位置二法歸之于畫家焉……然則,鑒賞者于畫何為?曰:賞于畫之意也。意之蕭條澹泊,閑和嚴靜實氣韻生動之謂也。故氣韻生動為鑒賞家法。”鄧以蟄的劃分非常明確:“傳摹移寫”“隨類賦彩”“應物象形”側重客體對象,為畫家創作提供依托和摹仿對象;“骨法用筆”“經營位置”指畫家以筆墨技法、位置架構來表現內心之意,實現“藝”與“意”的融合;鑒賞家則從畫作整體的角度去領略畫中的意趣、境界,以“氣韻生動”為根本原則,對作品進行品評。鄧以蟄的解釋調和了西方現代美學將摹仿與表現對立起來的傾向。
鄧以蟄闡釋了“六法”的第一層次內容(客體自然) 對第二層次內容(主體創作)的轉移、影響,將藝術的起源界定在器物圖像之描繪與制作的最初階段中,這也是形體一致的最初階段。在此階段,“畫”與“繪”從合而為一到分離發展,進而演進為獨立的表現技法,對中國書法和繪畫產生了深遠影響。鄧以蟄指出,上古三代器物的表面裝飾以顏色為主,顏色本身則按照器物所呈現的對象、方位、功能而具有象征意義。
“類”乃自然萬物之類別,顏色使用要與之匹配。這種對裝飾顏色的使用便成為后世繪畫技法的來源。鄧以蟄認為,“隨類賦彩”就是針對這種情況的:“今謝赫列隨類賦彩為畫之一法,其必為畫與繪共事相須時之法,而為畫之最初之一法,可無疑矣。”他的依據是,“畫”與“繪”分離后,設色失去獨立性而成為用墨技法的附庸,此時的賦彩技法與“隨類賦彩”的本義已無太大關聯。可見,謝赫雖將“隨類賦彩”列為“六法”的第四法,但其起源實則最早。作為第三法的“應物象形”,才是“畫”與“繪”分離后被運用到創作中的專屬繪畫的技法。
對“氣韻生動”內涵的新界定,是鄧以蟄“六法”闡釋的核心內容。“氣韻生動”這一觀念貫穿了中國藝術的發展歷史,若能將其思想來源、內涵演變梳理清楚,也就能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國藝術史的發展脈絡梳理清楚。鄧以蟄對歷代學者、藝術家關于“氣韻生動”的觀點進行了總結,認為這些觀點皆空乏無據,難以確指實在內容,要想準確理解“氣韻”,應從中國繪畫作品及其發展歷程談起。他屢次指出,由于“氣韻生動”首先特指漢代藝術,應將這一觀念與漢代藝術作品聯系起來,使“氣韻生動”從神秘虛空的概念轉移到客觀可感的作品上。自謝赫提出“氣韻生動”命題以來,歷史上各種畫論類著作均未提及這種視角,這一點生動體現了鄧以蟄美學的立足點。鄧以蟄提出,“氣韻生動之理論雖倡自南齊謝赫,而氣韻生動之藝術則盛于兩漢”,從藝術作品的角度解釋了謝赫觀點的實踐來源。他進而說道:
竊嘗以為氣韻生動之藝術淵源于楚風。楚風者吾用以名漢代藝術之所自也。漢代藝術,一言以蔽之曰,氣韻生動之藝術也。蓋變三代之圖案式而一以生動,氣韻出之,雖在器用之裝飾如陶漆器亦無不然也。唯此時之氣韻生動,乃以生物如怪獸雜于云氣中,成一體之運行,動而有韻也;其畫法可謂極生動之能事!此在裝飾,不離云氣與怪獸,如三代之裝飾不離云雷紋與饕餮者且生動如此,至若禽獸人物畫,如墓中壁畫之四神與所謂東王父西王母、忠孝圖等普通彩畫,以及享堂如孝堂山、武梁祠等之石刻畫,皆益趨寫實,而其畫法之生動猶一致也。要之,氣韻生動在漢代裝飾畫為畫中所畫之實體,在人物車馬畫,畫中雖無云氣其體,而生動之趣則無異也。
這段話最集中地表達出鄧以蟄將“氣韻生動”與三代以來的器物圖像乃至漢代藝術相關聯的觀點,即漢代藝術對禽獸、車馬、人物等形象的刻繪所呈現的靈動飄逸之風格,為謝赫提出“氣韻生動”命題奠定了基礎。鄧以蟄提到的墓室壁畫、孝堂山及武梁祠的石刻畫等,都是漢代藝術的寶庫。根據典籍記載和現代考古發掘,可知戰國時期楚地的青銅器、漆器、玉器制作已十分發達,從某種程度上說,漢王朝的建立和統治是楚文化和藝術精神擴大到北方地區,進而波及全國的過程。楚文化和藝術的特質是想象雄奇、自由瀟灑、靈動飛舞、不拘一格、自由奔放,這一點不僅體現于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和漆棺彩繪,由磚石雕刻而成的圖像也具有同樣的特點。漢代藝術精神乃中國藝術精神的基本構成,沒有漢代藝術的成功實踐,就沒有中國藝術的“氣韻生動”之特質和觀念的形成。
鄧以蟄意在指出,以“楚風”為藝術特征和精神特質的漢代藝術是中國藝術精神的核心構成。在他看來,漢代藝術的審美風格和精神特質,并非漢代這個特定時代所獨有,漢代之前的器物圖像和紋飾對此已有充分表現,而漢代之后的器物圖像和藝術形象則將之作為精神遺產繼續發揚,以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和精神特質。這是鄧以蟄的“氣韻生動之藝術則盛于兩漢”論斷的主要內涵。所謂“盛于兩漢”,并不意味著這種藝術風格和精神專屬漢代,而是對中國藝術風格和精神特質的總稱呼、總命名。漢代藝術的特點和特質并非凝固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演進,表現于不同時代的藝術:它在三代的器物制作中體現為云雷紋和饕餮紋,在陶器、漆器上體現為禽獸、怪物的形象,在魏晉人物畫中體現為人物、車馬的形象,在唐宋以來的山水畫中體現為山水的靈動和筆墨的變化。
鄧以蟄指出,“楚風”藝術的彩繪技法對唐宋山水畫的用色、布局有著重要影響,后世文人畫的所謂“荒寒”“蕭條淡泊”的山水意境,均屬于“楚風”之變體;“楚風”藝術對金碧顏色的使用,深刻影響了此后山水畫的顏色技法,比如山水畫的“金勾赭絳之法”,“追溯其來源,恐非遠及于周末之‘楚風’不可也”。針對壽縣出土的楚國銅器及其彩畫藝術,鄧以蟄說:“此作風凡表現極飛動之點,如云氣中之各種怪獸在飛動時,其張之翼、伸之足與氣連結,鼓蕩成一極長之光條,如電之閃光者,即用鮮明之色如赭色、金黃色以表現之,此何異乎金碧山水中之勾金,以狀日光者耶?此固極表現生動之能事者矣!”直到南宋,中國山水畫的設色和結構仍依循漢畫的基本布局;即使以馬遠和夏珪為代表的畫家將場景縮減至山水一角,畫面仍與自然的整全之氣韻存在呼應關系。在這種變化的背后,不變的是山水畫對自然的整全之神韻氣勢的表現。鄧以蟄在評價明代學者徐賁《仿巨然山水長卷》時說:
余嘗以為山水畫不獨設色之變遷——由金碧而青綠而淺絳——源自“楚風”“漢畫”,即位置經營亦莫不然也。蓋漢畫山紋如蘆芹齋舊有之銅管,其上平脫之花紋為山峰尖聳,高低相亞而有多樣鳥獸棲止其上,以及漆畫山紋,實由楚風之云雷紋(如中央研究院壽縣漆彩畫),紋中穿插奇禽異獸以成一圖案畫者脫化而來,故其初位置高低相亞有如此者。北宋大幅山水注重主峰所謂大山堂堂者猶漢畫山紋之遺型耳。至南宋馬夏輩始有偏角不全之位置,可謂山水畫之變格也。
鄧以蟄指出,誕生于“楚風”藝術的“氣韻”流轉至唐宋后,則轉變為對有形無形之對象的表現。歐陽修的“蕭條淡泊”、王安石的“荒寒”、趙孟頫的“古意”、倪瓚的“逸趣”、明清時期的“士氣”“書卷氣”等,都是“氣韻”在不同時代的變體。這就將中國繪畫意境論納入了器物美學的體系。鄧以蟄說:“在漢代,氣韻原為畫中表現之實體也;禽獸生動之極,結于云氣,或云氣排蕩之極而生出禽獸,皆成為一體之運行,如文之有韻也。氣韻生動乃‘楚風’漢畫之特色,而為今之畫家、鑒賞家無上之原則矣。”由此,由漢至唐再至明清,中國藝術發展形成了一條有理可循的路徑,貫穿其中的便是“氣韻生動”。
鄧以蟄對漢代藝術所蘊含的民族精神的重視,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考古發現有著密切關系。現代以來,宗白華、徐復觀等人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對“氣韻生動”進行了闡釋,這些研究多在哲學本體論層面上展開,均未發現這一思想命題與古代器物制作間的關聯,這正是鄧以蟄美學的獨特之處。劉綱紀說:“目前,研究漢代藝術對后來藝術的深遠影響,還是值得我們細加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在這方面,鄧以蟄正是一個先行者。”鄧以蟄美學中的“本體”并非形而上的概念或邏輯,而是指向三代以來的器物制作及其圖飾,后者才是中國藝術的真正本體。在此基礎上,鄧以蟄將“凈形論”美學貫徹到中國藝術發展史的研究中。
四、“藝史”觀:中國藝術史的內在整一性問題
鄧以蟄將“凈形論”美學作為藝術批評方法加以使用。他始終主張在研究中國藝術史時史論結合,尤其強調器物圖像在中國藝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王氏畫苑》上題跋:“古人談藝,論與史向不分。有此,正吾之優點。分言之弊,流于穿鑿失真,如今之美學流于形而上,則繪事即流于形式。影響所及,為害滋甚。”為此,鄧以蟄借由對夏珪、馬遠等人作品的藝術批評,系統分析了中國藝術發展過程中的內在整一性特質,提出了獨具特色的“藝史”觀。
與通常意義上的藝術史不同,鄧以蟄所謂的“藝史”特指民族藝術的歷史傳統,為的是突出藝術本身所蘊含的有別于“詩史”的歷史反思意識。鄧以蟄提出“藝史”觀,除了將他的美學思想貫穿到藝術史領域中,也指向另一個問題:中國藝術史上是否存在漢晉、唐宋之變?鄧以蟄結合亞里士多德《詩學》中關于詩與真理的討論,指出“藝史”意在突出連續延綿的藝術特質對藝術史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他指出,藝術在發展過程中存在某種恒定不變的特質,這種特質在藝術史上一以貫之,使藝術成為滿足人心的情感需求、表征社會歷史治亂、呈現永恒真理的載體,故可稱之為“藝史”。藝術通過對主體情感世界的滿足和對社會歷史真理的揭示、呈現,實現了“厭人心之哀樂,發治亂之幾微”的功能。這是鄧以蟄著意使用“藝史”一詞的根本原因。
鄧以蟄在評價夏珪《春山歸隱圖》時提出了“藝史”觀。他當時所觀有三幅《春山歸隱圖》,分別為嚴嵩、夏珪和黃溍三人的作品。相比嚴嵩作為明代內閣首輔、黃溍作為元代翰林學士的身份,夏珪則生活于宋高宗南渡之后的時期,耳目所接皆為殘山剩水,這激發了他對北宋山河的懷戀之情。在這種背景下,夏珪的《春山歸隱圖》便具有深沉的歷史感,與嚴嵩、黃溍作品的隱逸和閑適主題截然不同。南宋中期的畫院創作以小幅作品為主,以尺幅一角呈現江南山水的浩渺悠遠之境,這種藝術境界符合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現實。但夏珪一反常態,創作了長達兩丈有余的《春山歸隱圖》,同時還創作了《長江萬里圖》《溪山無盡圖》《溪山清遠圖》等大幅作品。以創造“邊角之境”著稱的馬遠,也曾創作同等規模的《溪山無盡圖》;明末清初的遺民髡殘和龔賢也曾以夏珪作品為藍本創作《溪山無盡圖》。這說明藝術家以自己的作品來訴說歷史之思。鄧以蟄評道:“蓋其胸中塊壘,摩蕩以出,有寫乎其所不得不寫,萬里江山,一觸即發之于筆墨,故其《長江萬里圖》《溪山無盡圖》皆長至數丈。董玄宰謂長卷畫起于南宋畫院,信哉禹玉之畫,實多長卷;如此氣勢,豈可與殘山剩水同日語哉?說者謂山殘水剩,彼之畫則為長江萬里,溪山無盡,此其所以為藝史也。”夏珪等人有著不可一世的創作氣概,與當時畫院中涂紅抹綠以邀賞請功者截然不同。在這個層面上,“藝史”與“詩史”的意義是一致的。鄧以蟄說:
大凡畫亦如詩,詩之圣者有兩等:老杜,一等也;王、孟又一等也。老杜之詩,詩史也,真于事者也;王孟之詩,平澹天真,真于自然者也。畫之神品亦有兩等:王維之畫亦平澹天真,筆意精微,所謂南宗,所謂士氣者,一等也;李唐、夏珪、石濤、八大之畫蒼郁突兀,寓憤慨于筆墨者也,又一等也。此等之畫,如老杜之詩,稱之為藝史可也。
詩與畫作為“史”的價值分別體現為“真于事”和“真于自然”。所謂“真于事”,即“發治亂之幾微”,強調藝術對歷史規律的揭示與呈現;“真于自然”,即“厭人心之哀樂”,倡導藝術對人心的自然之情的感發與滿足。鄧以蟄引用了吳荷屋關于元代巨儒黃溍臨摹夏珪作品之深意的話:“古人之筆墨,可重也;古人所臨摹之古人之筆墨,尤為可重也。得一歸隱圖而夏珪、黃溍兩古人之精神、筆墨俱在,其可重又當何如哉?”這證明黃溍的臨摹具有歷史意識。所以,臨摹古人之作,不僅強調古人筆墨的重要性,也通過臨摹來保存古人筆墨所蘊含的可貴精神。這樣,對古人筆墨的臨摹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創造或摹仿的問題,而是一個蘊含著家國情懷的藝術精神傳承的問題。
鄧以蟄“藝史”觀的“真于事”和“真于自然”兩層內涵隱含于藝術史的發展過程,本身不發生變化,藝術史的變與不變亦受二者的制約。具體言之,藝術的發展演變受限于藝術本身的特質,即藝術要呈現對象的自然本質,這決定了在藝術史的發展中有著某種恒定的標準或規則:變化者乃是作為器物本體的形式格局或筆墨技法,不變者則是作為“心畫”本體的宇宙自然之本質。在討論無款立軸《元女授經圖》時,鄧以蟄引述了蘇軾《書吳道子畫后》的“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討論了藝術創造與傳述間的辯證關系:“創”與“述”并非各自獨立、互不干涉、有高低之分的兩個階段,二者結合才能實現藝術的不斷更新。所謂“創”,即“前人之法度”;所謂“述”,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創”“述”之結合就形成了藝術史上的“變”。1958年,鄧以蟄結合吳道子的創作解釋了三者的辯證關系:
“創”“述”“變”三者的關系是互相滲透,循環反復地上進而無所底止。如“述”中若無絲毫“創”意,就純粹成了前人的摹仿品,那有什么可貴?有時雖曰摹仿,卻創意甚多,我們平常要為四王、吳、惲爭一席地的緣故就在于此;“變”則“創”的成分更要多或幾等于“創”,實則對前人來說是“變”,若對繼述者來說也就是“創”了。
這種“藝史”觀強調了前人法度與藝術家創作中的新意相結合的重要性。藝術史的發展是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有時是“氣象”變而“筆法”不變,有時則是“筆法”變而“氣象”不變,當它們皆達到至高之境界時,某種藝術類型便發展到頂峰,出現代表性藝術家及其作品。蘇軾對此進一步總結道:“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鄧以蟄指出,吳道子的道釋人物畫在“法度”方面仍延續古人,但在“氣象”“筆法”等方面有了諸多變化,“變古人高古之游絲琴弦描,而為莼菜條蘭葉之描法”,達到“磊落揮霍,筆與氣并”的自由境界;“變古人簡靜醇穆之氣象,而為巨狀詭怪放逸之姿”,達到“精侔造化,極其自然”的至高境界。吳道子的創作使道釋人物畫達到了此類畫作之“止境”,此后諸作都是吳道子作品的余緒。藝術史中不變的“法度”是藝術在呈現對象時的某種內在的本質規定,無論“氣象”“筆法”如何變化,從而使作品呈現出各種新風格,這種本質規定仍制約著作品的創作。由此,不同時代、地域的作品只要在本質規定方面達到一致,就會體現出某種相似性或相通性。
根據“藝史”觀的理論邏輯,應重新思考中國藝術史上的域外因素的影響,以及漢晉與唐宋之變等問題。鄧以蟄之所以重點解釋中國藝術的漢唐之變,是因為有些學者堅持域外因素乃漢唐之變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往往強調印度和希臘雕刻對中國雕刻、繪畫藝術的質的影響,而忽視中國藝術發展本身的決定性作用。鄧以蟄在談到先秦兩漢的器物制作以及石刻畫像中的西王母、禽獸四神等形象時指出:“其截然與三代不同,幾使史家疑為外來影響之所致,其實由藝術自求解放之跡如饕餮之角脫器體而出與獵壺之以田獵之景為飾諸點而觀之,則殊自然。”這是藝術形象不滿足于被“器體”束縛、追求獨立的內在發展的需求所致,而非受域外民族和國家的神話信仰的影響。此處“器體”即中國藝術原初之本體,它是中國藝術發展演進的基礎。
鄧以蟄始終強調,中國藝術發展的根本力量在于自身,域外因素只是外因,僅在取材等方面產生影響,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藝術的發展歷程:“中國藝術從圖案花紋發展到山水畫,是一步接著一步地跳躍而致的;盡管中間有過多少次外來的影響,也只是吸收;并沒有被引入到旁的道路上去。”他指出,使中國藝術史始終保持這種整一性特質的核心思想就是“氣韻生動”:“六朝生動之法,蓋紹自漢代耳。由是觀之,晉人之畫又與漢代何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漢畫與晉畫的“無以異”,強調了中國藝術發展的內在脈絡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在唐宋之際,這一精神又影響了中國山水畫的形成,從而使中國藝術以“氣韻生動”為基礎,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歷史發展過程。劉綱紀據此指出,“楚風”影響了漢代文學和繪畫以及“氣韻生動”等觀念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它成為維系中國藝術發展的根本思想精神。
鄧以蟄并不否認中外藝術之間存在交流,但中國藝術在漢晉、唐宋之際發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在于中國藝術本身。中國藝術與域外因素既有斗爭也有融合,如何使中國藝術保持自身特質而不被域外因素異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種斗爭首先表現為不同技法的競爭。例如,來自佛教的暈染法進入中國后很快被當時的藝術家借用,但謝赫隨之提出“骨法用筆”,強調中國藝術尤重線條的傳統,不可讓暈染法改變中國藝術固有的技法。唐代的域外因素的進入也較為多樣,而這種斗爭仍然存在。正是在這個層面上,鄧以蟄強調中國藝術特質在傳承中的重要性:“大凡事之自身若無其存在之本體,雖有外來影響亦不發生關系,容得摹仿于一時,終必流產也;若其有之,則吸收之力乃大,凡可接觸者皆可發生影響,只非機體之湊合,而為生命之液體耳。漢至唐藝術之生命是由‘體’而入于‘理’,由平板而入于生動。其間轉動生長之跡固彰然于史績耳。”他認為,“影響”根本上在于一個民族、國家的藝術本身,若此種藝術沒有深遠、厚實的傳統,即使摹仿外來藝術,也終究會煙消云散。因此,漢唐時期的藝術變化,“雖曰佛教輸入,于莊靜華麗之風不無有助,但人物至六朝,由‘生動’入于‘神’,亦自然之發展也”。漢唐之變是中國藝術發展由“體”入“理”的自然結果,域外因素或有參與,但變化之根基是中國藝術本身。這是在強調中國藝術發展有其連續性和自足性,而非域外因素強行介入的結果。這種觀點是一種連續性的藝術史觀,其根基是以《周易》器象觀為基礎的中國藝術傳統。
鄧以蟄的“藝史”觀,對于重新認識中國藝術史上的漢晉、唐宋之變等問題,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一些學者將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歷史觀引入中國藝術史研究,認為中國藝術的發展在漢晉、唐宋之際出現了根本轉變。“漢晉之變”“漢唐之變”“唐宋之變”“宋元之變”等,都是這種觀念的變體。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將藝術史研究作為歷史研究的附庸,是某種意識形態偏見的產物,并不符合中國藝術發展的實際情況。這也造成了中國早期以器物圖像為載體的藝術史,與唐宋、元明時期以藝術家心靈為根本的藝術史的對立。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中國藝術史不僅不是完整的連續體,而且在發展過程中分離出兩種不同的藝術。鄧以蟄的“藝史”觀在矯正這一偏見方面意義重大,值得深入挖掘。
結語:回到1935年
鄧以蟄于1935年前后提到的考古發掘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大批考古學家參與了對這些遺跡的發掘、整理和研究,撰寫了大量成果。若將鄧以蟄的美學思想與這些成果進行比較,會發現其中蘊含的不同意趣和觀點,對我們認識鄧以蟄美學的世界性意義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這一時期,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殖民者來到中國進行考古發掘、盜運大量文物,此種情形引發了學者的強烈義憤,他們盡己所能地推動國民政府盡快對這些文物進行保護和發掘,徐旭生、李濟等人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此背景下,學界各領域對這一時期的考古文物都較為關注。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這種立足考古文物來闡釋中國藝術和美學的研究方法在學界已是共識,目的是通過藝術考古研究向世界宣揚中華藝術和美學精神,其標志是1937年5月18日中國藝術史學會的成立。鄧以蟄的美學思想也證明了這一點。
李濟等人的考古工作影響了鄧以蟄美學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后者對中國藝術史的內在延續性問題的思考和論述。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李濟當時雖協助安特生在華的工作,但并未盲從后者,而是有著自己的判斷。他在這一時期的考古發掘成果,基本是在批評和修正安特生的觀點。鄧以蟄對殷商青銅器,以及楚漢帛畫、漆畫、磚石畫等出土器物的重視,將器物視為藝術本體,對“楚風”之于中國藝術發展的重要性的強調等,都與李濟密切相關。鄧以蟄多次提到他與李濟1934年的壽縣考察,足見此事對他的美學思想的深遠影響。
鄧以蟄在藝術史上首次將武梁祠人物畫像與魏晉人物畫、隋唐佛教繪畫相聯系,并對武梁祠人物畫像在中國藝術史和美學史上的地位做出研判。謝閣蘭指出:“長久以來,中國歷代畫史、畫論均將關注的重點集中于繪畫作品和畫家身上,而忽視了數量眾多的雕塑作品。”謝閣蘭的觀點更加凸顯了鄧以蟄借助器物圖像來建構美學思想的學術價值。早在1926年,鄧以蟄就主張對歷史文化遺存展開研究,重新激活其生命力。對于古代文化和文物,研究者要在“同其意志而后可”的基礎上充分考察“歷史事跡”和風俗,使“事跡上的過去”轉化為“精神上的現在”。這種研究方法是基于民族精神發掘和建構的“復活論”,作為美學研究的考據學、考古學,不能把歷史遺址“當一種無機體的物質研究”,而應讓歷史遺跡“可以隨時原原本本的在他的精神里復活著;這樣,歷史才可以永遠存在”。
綜上,鄧以蟄的美學思想是20世紀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特的家世文化和時代環境、復雜的學術交往,決定了鄧以蟄的美學建構始終與時代發展的主題緊密相關,他的美學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鄧以蟄高度重視歷史遺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藝術精神,以器物圖像為基礎進行美學建構。這種建構將中華美學精神的具體內容和內在規定納入了中華文化的整體發展過程,同時促進了20世紀中華美學精神在特殊歷史時代的重塑與重建。鄧以蟄的基于器物本體的“凈形論”美學具有重要的范導性價值,值得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責任編輯 吳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