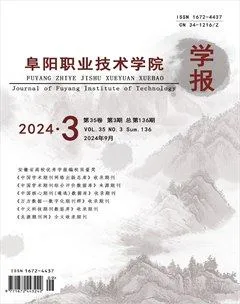論人“神”關(guān)系背景下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人性主題
摘要:人性作為科幻作家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常見(jiàn)主題,集中體現(xiàn)于《三體》系列作品及作者眾多短篇?jiǎng)?chuàng)作中。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人性主題分別體現(xiàn)于宇宙生存圖景和宇宙發(fā)展圖景中。其中,人“神”生存圖景體現(xiàn)劉慈欣以人性作為人與外星生物區(qū)分的重要準(zhǔn)則,并以之為基準(zhǔn)設(shè)想宇宙間物種的生存關(guān)系;人“神”發(fā)展圖景則體現(xiàn)劉慈欣對(duì)人性普適性的理解,并由此引申出對(duì)宇宙發(fā)展的終極拷問(wèn)。人性的存在,在宇宙生存圖景與發(fā)展圖景中分別起到不同作用,這將成為解讀一些特殊角色和追問(wèn)小說(shuō)深層內(nèi)容的關(guān)鍵,也將成為挖掘作者對(duì)于人性認(rèn)知的重要依據(jù)。
關(guān)鍵詞:人性;人與“神”;黑暗森林;劉慈欣
中圖分類號(hào):I1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4437(2024)03-0038-07
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外(以國(guó)內(nèi)為主)對(duì)劉慈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品的文學(xué)史意義、譯介工作及主要作品的主題和思想上,而對(duì)于劉慈欣作品頻繁出現(xiàn)的“神”的意象則很少提及。從小說(shuō)內(nèi)容看,“神”是人類對(duì)無(wú)法匹敵的文明程度(科技實(shí)力)的代稱。與國(guó)內(nèi)外流行的“外星人”科幻主題一樣,劉慈欣在其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三體》及許多短篇小說(shuō)中均描繪不同種類樣貌的外星生物。外星生物從未出現(xiàn),人類對(duì)其一無(wú)所知的情況下,許多科幻電影或小說(shuō)常采用“類人”形象,即從人的樣貌和生活習(xí)慣出發(fā),將外星生物的形象置于以人為原型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改造、想象。而劉慈欣筆下的外星生物則更為“隨意”,它們有的無(wú)法為人所觀測(cè),有的外形類似恐龍,有如白發(fā)慈祥的“上帝”形象,也有能隨意脫水補(bǔ)水的“三體”人。形象的各異并不影響其文明程度的發(fā)達(dá),作者筆下外星生物的特殊之處在于其文明程度相較于人類的領(lǐng)先,于小說(shuō)中的人類而言,其文明水平(主要集中在科技層面)已成為令人贊嘆和不解的存在,正如劉慈欣贊賞的科幻作家克拉克在其小說(shuō)《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繪的絕對(duì)比例的長(zhǎng)方體,以其無(wú)需質(zhì)疑的精確度無(wú)聲地與人類技術(shù)水平拉開(kāi)距離[[1]]。劉慈欣的“外星人”形象不再與人類在同一水平線上交流,它們成為令人仰望的存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精神寄托的載體,如《三體Ⅲ:死神永生》中眾人跪倒在作為三體文明代言人的“智子”腳下,企望它能為地球的出路提供指引[2]。可以說(shuō),“神”在小說(shuō)中是以科技水平為支撐、借以在人類心中樹(shù)立無(wú)可匹敵形象的外星生命體的統(tǒng)稱。
然而,對(duì)人“神”形象及關(guān)系的分析不能僅限于表面,劉慈欣對(duì)人與“神”兩類形象的描述依舊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其中“人性”,這一包括情感(共情)、計(jì)謀(欺騙)、自私(利己)等特征的屬性,在人與“神”的對(duì)比中顯得尤為突出,而“人性”主題的重要性同樣在差別對(duì)立的描寫(xiě)中彰顯無(wú)遺。
一、人“神”生存圖景——以人性為劃分準(zhǔn)則
(一)人眼中“神”的形象
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神”沒(méi)有古希臘神話中“神”近乎完美的體型,它們?cè)谌祟愌壑械耐?yán)建立在其科技水平領(lǐng)先所形成的神秘感和給人的危機(jī)感上。劉慈欣多以人類視角描述“神”形象。《詩(shī)云》中,“神一族”在人類的眼中“仿佛是從計(jì)算機(jī)圖庫(kù)中取出的兩個(gè)元素,是這紛亂宇宙中兩個(gè)簡(jiǎn)明而抽象的概念”[3]45;《夢(mèng)之海》中,“低溫藝術(shù)家”的形象無(wú)法用肉眼觀察,只能看到由于其冷凍場(chǎng)產(chǎn)生的冰球[3]3;《山》中,來(lái)自“泡世界”的生命體由機(jī)械構(gòu)成,短路對(duì)于它們便意味著死亡[3]354-355;除此之外,還有來(lái)自“吞食帝國(guó)”的外形為恐龍的“大牙”,來(lái)自三體世界的三體人等。此類生命體普遍具有以下共同點(diǎn):文明發(fā)展程度較高;外形不同于人類;能與人溝通。宋明煒曾在《中國(guó)科幻新浪潮》中提出,劉慈欣的小說(shuō)是在某種設(shè)想、前提下,在科學(xué)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guò)一系列嚴(yán)謹(jǐn)推理產(chǎn)生的[4]35,這也符合他“硬科幻”的評(píng)價(jià)。而在人“神”接觸并產(chǎn)生互動(dòng)的敘述中,以上三點(diǎn)能大致構(gòu)成“神”形象的基本前提。
而另一個(gè)描寫(xiě)的相似點(diǎn)似乎更需要引人關(guān)注——人“神”發(fā)生交流后,“神”對(duì)人的態(tài)度基本保持一致,冷漠、不屑是其感情基調(diào)。如《夢(mèng)之海》和《山》中的“神”,其文明處于人類難以想象的水平,它們甚至不愿以“蟲(chóng)子”稱呼人類;它們能輕易改變?nèi)祟惖纳姝h(huán)境,理由僅僅是滿足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那些人類稍能理解的文明里,不屑、不顧依舊是主色調(diào),《三體》中三體世界對(duì)三位面壁者和地球文明發(fā)出“主不在乎”的嘲諷以及“毀滅你,又與你何干”的不屑;《山》里機(jī)械文明掀起地球的排天巨浪,只是為了尋找能溝通的使者。如果說(shuō)“神”的文明水平、外形等是作者預(yù)先設(shè)立好的條件,是小說(shuō)得以推動(dòng)的起點(diǎn),那么“神”對(duì)人態(tài)度的一致性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以人性角度考慮,即使雙方實(shí)力存在較大差距,良好的交流、合作仍是存在可能的,但“神”的反“人性”說(shuō)明了在劉慈欣小說(shuō)的宇宙觀里,一直存在某種寫(xiě)作準(zhǔn)則和規(guī)律,它能使高等文明同低等文明的談話推演出不屑、冷漠的態(tài)度,而此“神性”與“人性”的不同之處,成為區(qū)分人與“神”的主要依據(jù)。
(二)“非人”與“神”:《三體》“非人”與短篇中的“神”對(duì)比
“非人”概念來(lái)自小說(shuō)《三體》,當(dāng)小說(shuō)人物章北海駕駛“自然選擇”號(hào)戰(zhàn)艦逃離地球、飛往外太空時(shí),戰(zhàn)艦中的人雖然逃避三體探測(cè)器“水滴”的追殺,但由于回歸地球的希望被完全切斷,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將會(huì)發(fā)生完全變化,艦長(zhǎng)東方延緒以“非人”來(lái)稱呼此類人。“非人”保留人的外形、習(xí)慣,但喪失了最基礎(chǔ)的“人性”。“非人”為了生存竭盡所能,不惜殺害同類。“非人”的存在,無(wú)異于太空中獨(dú)立生活的一個(gè)群體。從人變?yōu)椤胺侨恕保瑒⒋刃佬蜗笳f(shuō)明了建立在技術(shù)爆炸和猜疑鏈基礎(chǔ)上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則。“黑暗森林”法則是對(duì)“費(fèi)米悖論”的形象化說(shuō)明,《三體》如此描述:“每個(gè)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像幽靈般潛行于林間,輕輕撥開(kāi)擋路的樹(shù)枝,竭力不讓腳步發(fā)出一點(diǎn)兒聲音,連呼吸都小心翼翼”;“在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獄,就是永恒的威脅,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將很快被消滅。這就是宇宙文明的圖景”[5]446。艦體上的“非人”,與小說(shuō)中其他“神”的形象有些出入,他們本就是人類,只因?yàn)樯硖帯昂诎瞪帧钡挠钪嬉?guī)則之下,一些人性被迫泯滅——他們無(wú)暇顧及對(duì)別的艦隊(duì)的同情,滿腦子只有猜疑和算計(jì);章北海在關(guān)鍵時(shí)刻動(dòng)的惻隱之心,導(dǎo)致了整艘戰(zhàn)艦的覆滅。“非人”形象的提出,使小說(shuō)人物除人和“神”外又新增了一類,他們兼具兩者的共同點(diǎn),既有“神”的冷漠,又帶有人的習(xí)慣和文明,其與“神”的對(duì)比,恰恰可以說(shuō)明人性在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重要位置。
首先,對(duì)“非人”的描寫(xiě),從根本上闡明了人性是人與其他生命區(qū)分的主要依據(jù)。吳飛在《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xué)解讀》中指出,那些被人認(rèn)為的“神”一般的生命,其實(shí)只是擁有神一般科技的敵人[6]26。小說(shuō)中的“神”不再是庇護(hù)人類的形象,而是無(wú)情的殺戮者和征服者,人們對(duì)“神”的敬畏是建立在恐懼的基礎(chǔ)上,這不免讓人聯(lián)想“神”是否是人類發(fā)展到一定水平的產(chǎn)物。雖然作者并未在小說(shuō)中說(shuō)明,但從其中一些片段我們?nèi)阅馨l(fā)現(xiàn),作者對(duì)科技改造人性持否定態(tài)度。如《三體Ⅱ:黑暗森林》中,即使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人類經(jīng)歷“大低谷”,仍有人提出“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5]309;經(jīng)歷低谷后人類科技迎來(lái)大反彈,地球并沒(méi)有成為戰(zhàn)爭(zhēng)的試煉場(chǎng),而是向民主和自由的方向邁進(jìn)。無(wú)論處于低谷還是高峰,劉慈欣筆下的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都處于讀者的理解范圍之中,換言之,即從人性的角度出發(fā),可以接受如此的變化。而作者的精妙之處在于,他用同樣易于理解的“黑暗森林”法則,闡述了宇宙的真理,使得艦隊(duì)上“非人”的舉動(dòng)既在常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小說(shuō)如此描寫(xiě)“非人”的境遇:“以前,不管人類在太空中飛多遠(yuǎn),只是地球放出的風(fēng)箏,有一根精神之線把他們與地球相連,現(xiàn)在這根線斷了。”[5]410人性是與地球相連的,是與“黑暗森林”相對(duì)的,當(dāng)?shù)厍虿辉龠m合返航,航行變成幾乎漫無(wú)目的的前進(jìn)時(shí),人類便會(huì)在“黑暗森林”中喪失一部分人性。
其次,“非人”與“神”的區(qū)別也說(shuō)明了人性之于“黑暗森林”的獨(dú)特。小說(shuō)中,二者的最大區(qū)別并不在科技實(shí)力上,從宇宙的宏觀視角看,人類與“三體人”的科技差距可忽略不計(jì),但“三體人”之所以可歸為“神”,主要在于它們對(duì)“黑暗森林”理論的參透。“黑暗森林”的比喻中,二者都可視為嬰兒級(jí)別的文明,但不同在于人類還是引火自焚、主動(dòng)暴露自己的“傻孩子”,而“三體人”已經(jīng)是隱沒(méi)在黑暗中、端著獵槍的孩童。劉慈欣在提出這般宇宙圖景時(shí),將人類與地球放在最為特殊且幸運(yùn)的一點(diǎn)——絕大多數(shù)人不了解宇宙法則的情況下,人類尚未受到“黑暗森林”的打擊與制裁。“非人”與“神”的最大區(qū)別在于,“神”已把宇宙法則視為公理時(shí),“非人”則剛經(jīng)歷從人性到“黑暗森林”的轉(zhuǎn)變,艦長(zhǎng)的自殺、章北海的猶豫,及大多數(shù)船員的抑郁,雖糾人心弦,但也從側(cè)面證明人性相對(duì)于宇宙的獨(dú)一無(wú)二。
因此,在人與“非人”,或者說(shuō)人與科技水平較高的“非人”的對(duì)比中,能否領(lǐng)悟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則,以及是否收到“黑暗森林”的威脅,成為兩者最大的區(qū)別。“黑暗森林”法則下勾心斗角的宇宙,被宋明煒概括為“以生存為第一要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或‘犬儒主義’”[4]31。而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某種程度上能為人所理解接受,因?yàn)槠鋵?duì)應(yīng)人性的某一部分,比如對(duì)生存的第一需求、對(duì)敵人的猜疑等。實(shí)際上,劉慈欣的小說(shuō)還涉及另一類“神”,它們脫離了“現(xiàn)實(shí)主義”,并不是因?yàn)樗鼈儾辉谏娴募s束之下,而是生存對(duì)于它們來(lái)說(shuō)是近乎永恒和易得的,如《夢(mèng)之海》中的“低溫藝術(shù)家”脫離了肉體的束縛,駕駛以光速航行的飛船,在各星球間尋找藝術(shù)創(chuàng)作靈感。雖然它同樣置身于法則之下,但相當(dāng)高程度的科技水平使得它能很好地躲避威脅、維持生存,即完全游刃于宇宙法則之中。它在面對(duì)地球世界時(shí),并沒(méi)有因?qū)嵙︻I(lǐng)先過(guò)大而表現(xiàn)出應(yīng)有的人性的“善意”,而是盡可能地減少了除藝術(shù)之外的談?wù)撛掝},為了它心中的藝術(shù)作品,毀滅整個(gè)星球是理所當(dāng)然之事。如果說(shuō)宇宙“黑暗森林”的“零道德”是對(duì)標(biāo)人類社會(huì)“道德”的結(jié)果,那么劉慈欣描寫(xiě)的“神”中,當(dāng)文明發(fā)展越趨近于頂端,“道德”就越將失去它的約束作用和標(biāo)示意義,真正的生存規(guī)則將越向宇宙生存法則靠攏。《三體》中的三體世界,因其所處行星受三顆恒星不規(guī)律運(yùn)動(dòng)的困擾,生存環(huán)境極其惡劣,由此演化出思想透明、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群體。他們的情感很少有恐懼、逃避等因素,即使家園最后還是慘遭毀滅,身為三體世界代表的“智子”依舊表現(xiàn)平靜,而對(duì)于它們來(lái)說(shuō)完全陌生的“欺騙”,在與人類世界周旋的幾百年中也逐漸融入其思想。它們的特性與人性相比的不同,是由強(qiáng)烈的生存需求導(dǎo)致的,目的是更好地應(yīng)對(duì)災(zāi)難、更快地占領(lǐng)“殖民地”。而對(duì)于《夢(mèng)之海》《詩(shī)云》中超脫肉身的“神”,欺騙變得沒(méi)有必要,就如“低溫藝術(shù)家”所言:“生存,咄咄,它只是文明的嬰兒時(shí)期要換的尿布,以后,它就像呼吸一樣輕而易舉了”[3]11。“神”表現(xiàn)的態(tài)度如何,是否與我們認(rèn)知中的邏輯匹配,其實(shí)都是從人性出發(fā)、以人性為參照物的結(jié)果。文明水平相近或相差不遠(yuǎn)的“非人”和“神”身上,或多或少有人性的影子,而在遙不可及的“神”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全宇宙普遍適用的生存標(biāo)準(zhǔn)。吳飛曾說(shuō)明,宇宙概念里的“善”指雖有星際航行的能力,卻選擇在自己星球上生存,不去打擾他者[6]52-53。以此觀之,所有造訪地球的“神”都沒(méi)有達(dá)到宇宙的“善”,人類又有何能以人性標(biāo)榜,企圖以人性衡量和制約其他生命呢?
(三)“黑暗森林”與人性的閃耀
當(dāng)然,劉慈欣描寫(xiě)的由“費(fèi)米悖論”引發(fā)的“黑暗森林”圖景,終究是作為科幻小說(shuō)的一種想象,宇宙是否處于“舉目皆敵”的擁擠狀態(tài)尤未可知。前文也已提及,劉慈欣的小說(shuō)是在假設(shè)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guò)邏輯推理而創(chuàng)作的,這也使得其小說(shuō)的許多細(xì)節(jié)能前后呼應(yīng),以及一些重要觀點(diǎn)的提出有其明顯的作用與意義。例如《三體》中作為面壁者之一的雷迪亞茲,在某個(gè)黃昏見(jiàn)到夕陽(yáng)后患上了“恐日癥”,而這正與其面壁計(jì)劃相關(guān)。實(shí)際上,作者在小說(shuō)中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則對(duì)人性主題同樣有凸顯作用。
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人類,以《三體》主人公之一羅輯的話來(lái)說(shuō),就如同“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5]447。《三體》里羅輯通過(guò)葉文潔的提示悟出了宇宙終極理論,但全人類對(duì)宇宙依舊處于懵懂無(wú)知的狀態(tài);即使之后“黑暗森林”被大家熟知,仍有人身處太平歲月而選擇將其遺忘。劉慈欣其他短篇小說(shuō),雖未提及“黑暗森林”,但人類無(wú)一例外是被動(dòng)的、毫無(wú)準(zhǔn)備的接受者形象:被迫與“神”交流,從而得知宇宙的某些真理或無(wú)抵抗地被“神”取走其需要之物。就如前文所說(shuō),人類與地球仿佛是一座自生自滅、同時(shí)又自融自洽的孤島,在周圍的“神”已形成發(fā)達(dá)的“海洋文明”時(shí),“閉關(guān)”的人類還在苦苦思索“出關(guān)”之道。劉慈欣在談及《三體》及《流浪地球》等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過(guò)程時(shí)說(shuō):“這一階段的共同特點(diǎn),就是同時(shí)描述兩個(gè)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gè)是現(xiàn)實(shí)世界,灰色的,充滿著塵世的喧囂,為我們所熟悉;另一個(gè)是空靈的科幻世界,在最遙遠(yuǎn)的遠(yuǎn)方和最微小的尺度中,是我們永遠(yuǎn)無(wú)法到達(dá)的地方。這兩個(gè)世界的接觸和碰撞,它們強(qiáng)烈的反差,構(gòu)成了故事的主體。”[7]由是觀之,所謂的人與“非人”、人與“神”的區(qū)別,不如說(shuō)是地球與宇宙、“傻孩子”與“黑暗森林”的對(duì)比。“黑暗森林”法則將人性所處的境地具象化,同時(shí)將不同于人性的“神性”和“非人性”模糊化、背景化——結(jié)合小說(shuō)中人類面對(duì)“神”的被動(dòng),人性與其他“性”的區(qū)分更加清晰,隨之而來(lái)的是孤獨(dú)感與獨(dú)特感的加強(qiáng)。在對(duì)人性位置的獨(dú)立進(jìn)行強(qiáng)調(diào)后,小說(shuō)的主題和中心思想也可得到更好的闡釋。
人性位置的獨(dú)立也引發(fā)了另一個(gè)疑問(wèn):難道宇宙中沒(méi)有和人類相似甚至相同特性的生命嗎?在小說(shuō)未提及的外星生物中,是否存在相似的“人”尚未可知,而出場(chǎng)的“神”均有一個(gè)相同點(diǎn):他們不遠(yuǎn)萬(wàn)里前來(lái)地球造訪。這意味著他們不僅懂得“黑暗森林”法則,也知道如何運(yùn)用法則并在它之下生存。無(wú)論這些種群在開(kāi)始星際航行之前具有怎樣的特性,一旦融入宇宙法則之中,就決定了其與人性不相容。這也是劉慈欣為何很少暢想人類踏入星際旅途的未來(lái),因?yàn)閱我浴度w》中“自然選擇”號(hào)等四艘艦體為例,就能看出人性將在太空中發(fā)生怎樣的扭曲和異變。“黑暗森林”法則設(shè)立的巧妙之處在于它幾乎給宇宙中所有高等文明附加了“人性異變”的大前提,這使得小說(shuō)能在人性與“黑暗森林”圖景二者的比較中展開(kāi)。
此外,對(duì)于處在家園星球、未外出航行的生命的描寫(xiě),最有代表意義的須屬“三體人”。《三體》里“三體”文明通過(guò)一款擬真游戲,向主角汪淼講述了“三體人”生存環(huán)境之惡劣,這也為三體艦隊(duì)出征地球奠下基調(diào)。地球上之所以能發(fā)展出健全的法律制度、道德規(guī)章和普遍的人性,不僅在于“猜疑鏈”的不成立,還在于大多數(shù)人的生存能被滿足。《三體》中羅輯曾說(shuō):“猜疑鏈只能延伸一至兩層就會(huì)被交流所消解”[5]444,在有效、可靠的交流下,猜疑不攻自破,“黑暗森林”也難以成立,而“三體人”幾乎全透明的溝通更是保證這一點(diǎn),可惜它們的生存發(fā)展遠(yuǎn)沒(méi)有地球穩(wěn)定。可以說(shuō),“三體人”是在半逼迫下接觸宇宙法則。此外,劉莘在《宇宙的真理——?jiǎng)⒋刃揽苹梦膶W(xué)解讀》里提出了“倫理共同體”,這成為人性與“三體人性”之間的另一道鴻溝——就像我們對(duì)待狗和蚊子有不同的道德規(guī)則一樣,不同物種間的交流取決于兩者倫理聯(lián)系的緊密程度,人類是否在倫理上與“三體人”有較大關(guān)聯(lián)、人類是否全面了解“三體人”,以及“三體人”會(huì)如何看待人類,本質(zhì)上構(gòu)成了倫理關(guān)系上的“猜疑鏈”,兩個(gè)種群注定無(wú)法成為一個(gè)“倫理共同體”[8]。
二、人“神”發(fā)展圖景——人性的普適性
(一)人與“神”的共通之處:《山》中的宇宙發(fā)展圖景
人性與“神性”相隔,并不代表二者沒(méi)有共同點(diǎn)。情感、思維難以達(dá)到統(tǒng)一時(shí),人類卻和“神”有著相似的好奇心,包括對(duì)已知世界之外空間的探索、對(duì)真理的追求,這類探求的欲望在劉慈欣的筆下,是全宇宙共有的特性。如《山》中的機(jī)械文明,當(dāng)其祖先生活在狹小的“泡世界”時(shí),一代代的進(jìn)化使其“走到了對(duì)宇宙進(jìn)行思考的那一天”[3]347,對(duì)“泡世界”之外空間的想象成為文學(xué)的主要內(nèi)容,并引發(fā)了對(duì)外探索的狂潮,這與人類對(duì)太空的暢想和開(kāi)拓何其相像;《朝聞道》里的“排險(xiǎn)者”,作為宇宙的最高智慧體,掌握著一切真理,仍無(wú)奈于對(duì)宇宙終極意義的無(wú)知;《詩(shī)云》里的“神族”認(rèn)為“龍族”無(wú)法向更高維度進(jìn)發(fā)的原因在于其缺少對(duì)周遭的好奇心。正是這些好奇趨使不同生命體朝自己理想的遠(yuǎn)方努力,從而構(gòu)成劉慈欣小說(shuō)異彩紛呈的宇宙發(fā)展圖景。
發(fā)展不同于生存,不是生命的必需品,但卻是所有生物的本性。《山》曾以“登山”來(lái)比喻生命向高處進(jìn)發(fā):“登山是智慧生物的一個(gè)本性,他們都想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遠(yuǎn)些,這并不是生存的需要。比如你,如果為了生存就會(huì)遠(yuǎn)遠(yuǎn)逃離這山,可你卻登上來(lái)了。”[3]360當(dāng)《山》的主人公馮帆體驗(yàn)過(guò)“海上頂峰”的感覺(jué)時(shí),“他突然變成了世界上最怕死的人。他攀登過(guò)巖石的世界屋脊,這次又登上了海水構(gòu)成的世界最高峰,下次會(huì)登什么樣的山呢?”[3]362欲望是無(wú)止境的,攀上了這座山頭,欲望會(huì)使你遙望更高的山頭,即使攀爬的代價(jià)很大,依舊會(huì)有人冒著無(wú)法生存的風(fēng)險(xiǎn)去嘗試,就像《山》里的機(jī)械生命抱著無(wú)法返程的決心開(kāi)鑿巖石,也像《朝聞道》里的精英們以生命換取對(duì)宇宙真理的片刻擁有。由此,劉慈欣在“黑暗森林”的生存圖景之外,刻畫(huà)出另一幅發(fā)展景象——不同生命在各自星球或太空中,因?qū)ξ粗暮闷娑鴬^發(fā)向前,形成“百舸爭(zhēng)流”的喧鬧局面,宇宙在讀者眼中不再變得寂靜冷清。
(二)“無(wú)意義”存活的“神”
劉慈欣小說(shuō)中還存在另一類角色,它們?cè)谧髡叩拿枋鱿嘛@得“無(wú)欲無(wú)求”,它們的“生存”在某種意義上說(shuō)是“存活”,讀者很難從其言行中看到活著的意義。這類“神”主要分為兩種,一種如前面所述,如《夢(mèng)之海》的“低溫藝術(shù)家”和《詩(shī)云》的“神族”,生存對(duì)于它們不再是需要苦苦追求的東西,因此兩者不約而同地將興趣轉(zhuǎn)至“藝術(shù)”和“文學(xué)”,通過(guò)獲取其他行星的資源滿足創(chuàng)作需求;另一種的代表為《三體》中的“歌者”文明,通過(guò)不斷將自己與敵人降維,達(dá)到消除威脅、維持生存的目的。一個(gè)整日于太空游蕩來(lái)獲取藝術(shù)靈感,一個(gè)寧愿將自己從高維度降至平面化也要保持存活,從人的角度思考,它們的生活缺乏“意義”,也就是探索和向上進(jìn)取的好奇心。
設(shè)置技術(shù)、實(shí)力深不可測(cè)的文明,根本上是為了創(chuàng)造人“神”對(duì)峙或交流的大前提,這也是劉慈欣乃至許多科幻小說(shuō)的寫(xiě)作方式。而筆者認(rèn)為更重要的,在于“無(wú)意義”的“神”實(shí)際為人性的最大程度想象創(chuàng)造了空間。
首先,“神族”和“低溫藝術(shù)家”為“人”披上了最高技術(shù)的外衣。無(wú)論《三體》提出的“黑暗森林”理論是否適用于其他小說(shuō),“神族”和“低溫藝術(shù)家”所表現(xiàn)出的,并非如宇宙法則所說(shuō)的立刻對(duì)地球進(jìn)行毀滅性打擊,相反,它們?yōu)榱诉_(dá)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與人類進(jìn)行交涉談判。盡管技術(shù)不處于一個(gè)層面,談判往往以“神”的意愿為準(zhǔn),但它們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人類的共情一面。更為有趣的是,《詩(shī)云》有將“神族”附身于唐代詩(shī)人李白的設(shè)定,作者如此描寫(xiě)化身為人且喝醉的“神”:“李白的嘴上黑乎乎的全是墨,這是因?yàn)樵诤裙獾谒耐牒螅噲D在紙上寫(xiě)什么,但只是把蘸飽墨的毛筆重重地濺到桌面上,接著,李白就像初學(xué)書(shū)法的小孩那樣,試圖用嘴把筆理順……‘尊敬的神?’大牙伏下身來(lái)小心翼翼地問(wèn)。‘哇咦卡啊……卡啊咦唉哇。’李白大著舌頭說(shuō)。”[3]55-56這段讓人忍俊不禁的文字不僅說(shuō)明當(dāng)“神”褪去科技的外衣、回歸肉身后,與常人行為并無(wú)差別,也從側(cè)面說(shuō)明在排除“黑暗森林”的影響后,人性并不會(huì)隨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升華,甚至可以說(shuō)人性的發(fā)展仍在原地徘徊。
其次,“歌者”為人性提供了揣測(cè)“神性”的空間。“黑暗森林”法則下的“歌者”,盡管手握可以二維化整個(gè)宇宙的“二向箔”,但是自己也終將被其反噬,淪為二維生物。這也正是為人所不解之處:平面化地存活,真的有意義嗎?而這恰恰是作者留給讀者的想象空間。劉慈欣的所有人“神”敘事,都基于對(duì)“神”的想象,也就是從人性角度去揣摩“神”的思維。一方面,作者和讀者都是人,在沒(méi)有經(jīng)歷任何外星遭遇、且要保證小說(shuō)邏輯能在人類邏輯框架里發(fā)展的情況下,從人性角度出發(fā)是唯一的寫(xiě)作方式;另一方面,我們能也僅能從人性出發(fā)去理解“神”,這使得小說(shuō)中“神”的行為都是以人性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批判——努力向上攀登,我們認(rèn)為是正確的、正常的發(fā)展圖景。對(duì)于某些生命來(lái)說(shuō),生存就代表意義嗎?我們尤未可知。
最后,劉慈欣《山》中講到:“山無(wú)處不在,我們都還在山腳下。”[3]360《山》中的表述指明了人性的想象限度。山腳下的人很難領(lǐng)略到山頂?shù)娘L(fēng)景,就像進(jìn)入四維空間的三維人類一樣,無(wú)法用語(yǔ)言表述感受。因此,從人性出發(fā),無(wú)論從思考角度還是高度來(lái)看都有很大的局限。盡管如此,劉慈欣在描述“神”時(shí)仍摻雜了很大的“便利”,我們能以人的視角理解小說(shuō)中“神”的行為,本身就是神奇且幸運(yùn)的事,這一描寫(xiě)角度也進(jìn)一步證明了劉慈欣小說(shuō)中人性的普適性。
(三)發(fā)展圖景引來(lái)的終極詢問(wèn):宇宙是否有意義?
如果把人性的普適性理解為對(duì)未知探索的欲望,那么這種欲望的來(lái)源便成為一個(gè)疑問(wèn),正如《山》所言:“進(jìn)化賦予智慧文明登高的欲望是有更深的原因的,這原因是什么我們還不知道。”[3]360也是當(dāng)《朝聞道》里的霍金先生問(wèn)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的問(wèn)題時(shí),無(wú)所不知的“排險(xiǎn)者”第一次沉默的原因[9]。我們可以說(shuō)詢問(wèn)宇宙的目的、宇宙讓人充滿欲望的意義這類終極問(wèn)題,仍是從人性出發(fā)的思考,或許宇宙只是如此存在著,但可以肯定的是,劉慈欣將科幻文學(xué)的盡頭引向了哲學(xué)思考,這是發(fā)達(dá)科技無(wú)法解決的問(wèn)題;他將人們對(duì)生存意義的思考上升至全宇宙,無(wú)論結(jié)果如何、無(wú)論有無(wú)意義,都是人性對(duì)所能想象的最大限度問(wèn)題的探尋。這種詢問(wèn),如宋明煒?biāo)裕瑢?duì)于劉慈欣來(lái)說(shuō),“科幻小說(shuō)的終極理想,就體現(xiàn)在描繪崇高的體驗(yàn)中。”[4]120
三、人性之余
劉慈欣科幻小說(shuō)的人性主題比人“神”主題涉及面更廣,幾乎分布于每篇小說(shuō)。而通過(guò)對(duì)人“神”生存圖景和發(fā)展圖景的分析,小說(shuō)中人性存在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更加清晰地展現(xiàn)眼前。人性主題的表達(dá),對(duì)小說(shuō)寫(xiě)作傾向的表示、思想內(nèi)容的闡明以及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預(yù)警都有重要意義。
(一)《三體》與《微紀(jì)元》:人類的烏托邦
劉慈欣曾在《三體Ⅱ》里寫(xiě)道:“即使在毀滅性的三體危機(jī)面前,人類大同仍是一個(gè)遙遠(yuǎn)的夢(mèng)想。”[5]31的確,每個(gè)個(gè)性不同的人能相互理解包容、共同認(rèn)可一些規(guī)章制度,共同組建成社會(huì)和國(guó)家,本身已十分不易,就如吳飛在《生命的深度》中所言:“地球上的人類通過(guò)社會(huì)政治制度,不必攻擊也能存活,這是黑暗森林的最大奇跡。”[6]57然而不可否認(rèn)的是,劉慈欣的寫(xiě)作傾向仍朝著人類大同而去。
這種寫(xiě)作傾向與小說(shuō)內(nèi)在邏輯和作者主觀感情均有關(guān)系。首先,人類在小說(shuō)的處境是被迫、弱勢(shì)的,“神”的到來(lái)往往決定整個(gè)地球的命運(yùn),因此國(guó)際的劃分被削去了,人類必須組成共同體面對(duì)來(lái)者;其次,貫穿小說(shuō)的人性作為粘合劑,概括了全人類共有的特征,從天性方面進(jìn)一步加深人類的聚合;最后,劉慈欣的主觀傾向起著最大作用。《中國(guó)科幻新浪潮》指出,劉慈欣不同于韓松的“中國(guó)崛起”主題,他的科幻小說(shuō)更偏重于“后人類敘事”,這使得其并不會(huì)在小說(shuō)中刻意強(qiáng)調(diào)政治、種族、地域的劃分,相反,還會(huì)有意規(guī)避[4]16。體現(xiàn)在小說(shuō)中,除人類被迫團(tuán)結(jié)抗敵外,《三體》中未來(lái)人類的中英文混用、地球國(guó)際國(guó)家實(shí)力普遍削弱、太空艦隊(duì)沒(méi)有地域概念所屬、全球人集體搬遷澳洲等預(yù)言一次次將現(xiàn)有的國(guó)家劃分沖碎;在小說(shuō)結(jié)尾,程心寫(xiě)下“與宇宙命運(yùn)融為一體”,從而“召喚出了‘終極烏托邦’”,人和宇宙在歸零和重啟中合二為一[10]。
劉慈欣是否存在主觀的“烏托邦”傾向很難判定,因?yàn)槠鋵?xiě)作傾向正如小說(shuō)中的人類一般,有些被動(dòng)與無(wú)奈,在“后人類”與“神”兩個(gè)主題面前,特別是人“神”二元對(duì)立的結(jié)構(gòu)中,烏托邦式社會(huì)似乎已成定局,同時(shí)烏托邦的傾向有助于人類聯(lián)系更緊密、表現(xiàn)更一致,從而深化人性的主題;而在作者另一篇小說(shuō)《微紀(jì)元》中,人類為了躲避災(zāi)難將自己無(wú)限縮小,最后形成了一個(gè)無(wú)憂無(wú)慮的微型社會(huì)。結(jié)尾原人類火化胚胎,實(shí)際是對(duì)原有的人類世界和人性作最后的告別。看似沒(méi)有煩惱的“烏托邦”,在失去人性后,也成為了恐怖的“惡托邦”。由此,人性成為烏托邦理想的基石,也是人類社會(huì)敘事得以延續(xù)的基礎(chǔ)。
(二)人性與科技:對(duì)人性的最后堅(jiān)守
劉慈欣小說(shuō)的人“神”敘事之所以能夠進(jìn)行,很大程度得益于小說(shuō)中人“神”的友好溝通。除《三體》中恒星被類光速粒子快速擊穿以及“二向箔”平面化太陽(yáng)系外,我們很少再能見(jiàn)到外星文明對(duì)地球及其他星球的快速打擊。這當(dāng)然是出于人“神”敘事的需要,但要維持人“神”表面上的平等交流,人類必須拿出自己的優(yōu)勢(shì)。于是,劉慈欣又瞄準(zhǔn)了人性。
《三體》中的“面壁計(jì)劃”是人性優(yōu)勢(shì)最充分表達(dá)的一次,利用“三體人”沒(méi)有計(jì)謀的特性,面壁者試圖通過(guò)自我思考來(lái)躲避智子的監(jiān)視和破壁人的猜測(cè),但大多數(shù)面壁者仍敗給了同為人類的破壁人,只有不受關(guān)注且自我“破壁”的羅輯取得了成功;《詩(shī)云》中“神族”企圖用科技的力量窮盡詩(shī)句的組合,最終敗給了人特有的創(chuàng)造力和對(duì)詩(shī)的鑒賞力,這是人在藝術(shù)鑒賞上的勝利;《夢(mèng)之海》中的人類相比“低溫藝術(shù)家”,雖同是取冰創(chuàng)造“藝術(shù)”,一個(gè)竭盡所有水資源而不顧全人類死活,一個(gè)“只取一瓢”用作欣賞,人性的共情展露無(wú)疑。劉慈欣沒(méi)有直接說(shuō)明科技與人性孰優(yōu)孰劣,但他“硬科幻”的敘事往往落腳于人文關(guān)懷,人性、文化顯然是他留給人類社會(huì)的底牌,作為可能與“神”一較高下的特性存在。
作者也對(duì)人性的弱點(diǎn)進(jìn)行了提示,《三體》中“弱小和無(wú)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5]409點(diǎn)出從人性出發(fā)思考的局限;吳飛在《生命的深度》中也指出,由于羅輯對(duì)人類世界的成功保護(hù),人們漸漸忘記其存在的重要性,甚至懷疑“黑暗森林”的真實(shí)性[6]126。只有當(dāng)危險(xiǎn)來(lái)到眼前時(shí),人類才知道害怕,才會(huì)去尋找救世主,甚至相信人類必將存活,人性的懶惰、安逸、自大在這一刻被無(wú)限放大。
結(jié)語(yǔ)
科幻文學(xué)之所以被稱為“文學(xué)”,而非科幻想象或科學(xué)理論,是因?yàn)槠渥髌返穆淠_點(diǎn)最后在人,文學(xué)最終是“人學(xué)”,本質(zhì)上,劉慈欣與自“五四”始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傳統(tǒng)并無(wú)差別,這也是本文為何選擇以人性主題作為研究對(duì)象的原因之一。但劉慈欣的科幻小說(shuō)與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相異之處在于,他不僅將目光放置在人與人的關(guān)系、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之中,更將其投向遙遠(yuǎn)的未知,試圖在宏偉的想象、瑰麗的圖景與可能的預(yù)測(cè)中探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這種探討沒(méi)有確切的答案,但不失為可嘆的理想。
經(jīng)本文的論述,可見(jiàn)劉慈欣小說(shuō)中的人性主題以或隱或顯的姿態(tài)分布小說(shuō)之中,以人“神”關(guān)系為切入點(diǎn),不僅能在人與“神”的對(duì)立統(tǒng)一中發(fā)掘、凸顯人性,而且能在人性與科技、地球與宇宙等比較討論中發(fā)現(xiàn)作者的寫(xiě)作傾向和對(duì)人性主題的認(rèn)識(shí),從而逐步靠近作者在科幻寫(xiě)作中想要構(gòu)建的宇宙圖景和人類社會(huì)。
劉慈欣的創(chuàng)作伴隨著中國(guó)科幻文學(xué)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逐步繁榮的二十余年。用劉慈欣的話來(lái)說(shuō),“在中國(guó),科幻在大眾中還是一支曠野上的小燭苗,一陣不大的風(fēng)都能將它吹滅”[11]。筆者從劉慈欣的小說(shuō)入手,試圖在內(nèi)容與主題方面對(duì)其做一些討論與拓展,并希望中國(guó)科幻文學(xué)能愈燃愈旺,漸成星火燎原。
參考文獻(xiàn):
[1]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M].郝明義,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
[2]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253.
[3]劉慈欣.夢(mèng)之海: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shuō)集Ⅱ[M].成都:四川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5.
[4]宋明煒.中國(guó)科幻新浪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
[5]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6]吳飛.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xué)解讀[M].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出版社,2019.
[7]劉慈欣.重返伊甸園:科幻創(chuàng)作十年回顧[J].南方文壇,2010(6):31-33.
[8]劉莘.宇宙的真理:劉慈欣科幻文學(xué)解讀[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
[9]劉慈欣.帶上她的眼睛: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shuō)集Ⅰ[M].成都:四川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5.
[10]楊宸.從“終極烏托邦”到“宇宙中的人”[D].北京:北京大學(xué),2016.
[11]劉慈欣.從大海見(jiàn)一滴水:對(duì)科幻小說(shuō)中某些傳統(tǒng)文學(xué)要素的反思[J].科普研究,201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