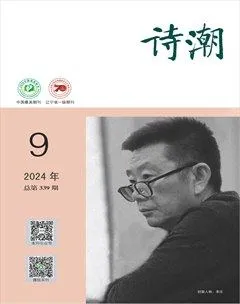“像事物隱秘的核心”
一、詩(shī)者根情
情感猶如詩(shī)歌的根性,與詩(shī)人的生命糾纏在一起。
如果說(shuō)這個(gè)詩(shī)歌的根性有什么獨(dú)特性,那就是它把獨(dú)特性摒棄在外,而自成世界。其原因在于,對(duì)很多詩(shī)人而言,情感就是其詩(shī)歌的生命線。去除了這條線,詩(shī)歌中所連綴的愛與恨、美與丑、生與死、信仰與背叛、絕望與希望,都將無(wú)所依附。唐代大詩(shī)人白居易就曾指出:“詩(shī)者:根情,苗言,華聲,實(shí)義。”(《與元九書》)所謂“根情”,即謂情感是詩(shī)歌的根本。榮榮的詩(shī)歌就始終游走在情感這條生命線上,她幾乎就是透過(guò)情感這條唯一的線建構(gòu)起了屬于自我個(gè)體的生命詩(shī)學(xué),無(wú)論是心靈上的映射,還是精神上的洗禮,無(wú)論是感性上的體驗(yàn),還是理智上的認(rèn)知,她所有的“眷戀”都源于一個(gè)焦點(diǎn)——情感,因此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其詩(shī)歌中始終彌漫著一股熾烈的情感氣息。在《愛相隨》中,她這樣闡釋自己的愛情哲學(xué):
一場(chǎng)共同完成的愛情,就是沉浸,
就是相互的綠和花開。
無(wú)法回避的凋謝,也必須分享。
可以肯定地說(shuō),這不是詩(shī)人對(duì)愛情的先驗(yàn)體悟,而是詩(shī)人透過(guò)切身的浸潤(rùn)感悟到的。盡管詩(shī)歌是以“兩只凄惶的小鳥”切入的,但我們不能認(rèn)定這就是詩(shī)人情感的直接來(lái)源。“兩只凄惶的小鳥”顯然是一個(gè)隱喻,詩(shī)人在這里以最直接的方式表達(dá)對(duì)情感的態(tài)度,而且顯得異常堅(jiān)決,所謂“必須分享”,并非僅僅是一種強(qiáng)調(diào),亦非表達(dá)一種理念。詩(shī)歌的結(jié)尾這樣收束:“一只百感交集。一只悲從中來(lái)。”無(wú)疑,這體驗(yàn)是經(jīng)受了痛苦和煎熬之后的一種期許。因?yàn)閻鄣谜鎸?shí),所以語(yǔ)言上才表現(xiàn)得毅然決然。
當(dāng)然,“愛得真實(shí)”也會(huì)在日常生活里展現(xiàn)。甚至,有時(shí)候正因?yàn)槭窃谌粘I罾镎宫F(xiàn),我們看到的才是最高的真實(shí)。在《水井巷》中,詩(shī)人借一個(gè)“外省女子”對(duì)日常生活的理解來(lái)表達(dá)女人對(duì)生活及情感的認(rèn)知,“她不喜歡討價(jià)還價(jià),但必須/忍痛割愛。在生活的另一面:/‘我喜歡零碎,你就是我絕望的零碎!’”通過(guò)心靈直覺,我們很難說(shuō)詩(shī)人要通過(guò)這樣的描述來(lái)捍衛(wèi)什么。她或許只是想“說(shuō)出”,至于其后引發(fā)的內(nèi)容,她秘而不宣,或者說(shuō)她根本就不在意。尼采曾經(jīng)說(shuō):“一種事物越遠(yuǎn)離現(xiàn)實(shí),就越純潔,越美,越好。”(《我妹妹與我》,陳蒼多譯,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頁(yè))然而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中的人不可能活在純粹的審美當(dāng)中,尤其是詩(shī)人的詩(shī)心,常常敏感于萬(wàn)事萬(wàn)物。有時(shí)候很小的隱秘可能構(gòu)成詩(shī)人最大的“牽系”,它引導(dǎo)著詩(shī)人去展現(xiàn)自我生命的存在以及靈魂瞬間的秘密。如詩(shī)人在《癡迷》中所寫:“我沒看開的光景一遍遍勒索著內(nèi)心,/它耗盡了我的力氣和耐心,讓消亡提前上路。/我有的是流離失所的愛,/有的是骨肉撕痛和分隔。/為何還不釋然?/你走了很久,我仍沒有流淚,/悲傷太高遠(yuǎn)了,眼淚要翻山越嶺。”
在《七夕》中,詩(shī)人指出一個(gè)人“被愛情迷醉”是危險(xiǎn)的,于是要去“阻止”:“阻止她,趕在傳說(shuō)之前:/阻止她的張望,/那一眼,她就要望見愛情了,/然后向下向下,/一只決然的鳥找尋另一只,/然后棲落,在那個(gè)春天里。/阻止春天,它讓短暫的幸福顯得具體,/也要阻止門前的槐樹說(shuō)話。/阻止一對(duì)花燭的淚水,/阻止手中的布匹展開命定的花紋,/阻止她的真火,他被喚醒的火山,/阻止破碎阻止銀河浩蕩的傷心。”表面上看,這是詩(shī)人對(duì)有危險(xiǎn)少女的一次垂死“力挽”,其實(shí)我們亦可認(rèn)定這是詩(shī)人在拿自己以往的經(jīng)驗(yàn)在進(jìn)行“告訴”。她曾經(jīng)沉浸于愛情之中,以心靈感驗(yàn)過(guò)愛情的一切,在自我對(duì)愛情的實(shí)現(xiàn)中,她曾經(jīng)那么本真地“失敗”過(guò)。然而情感畢竟是復(fù)雜的,愛情那么美好,當(dāng)你陷入到愛的行為之中時(shí),你會(huì)超出理性的思考,進(jìn)入到一種“迷狂”的境地,且看詩(shī)人在她的《心舍利》中所描述的:
多少年了,她用黑夜追著他的星光,
當(dāng)他猜忌,挑剔,使小性子,
她也正在猜忌,挑剔,使小性子。
“神啊,愿他是完美的。
不猜忌。不挑剔。不使小性子。”
“神啊,如果這輩子他無(wú)法完美,
讓我繼續(xù)迷信他的不完美。
無(wú)限依戀他的猜忌,挑剔和小性子。”
詩(shī)人這里所說(shuō)的“心舍利”無(wú)疑是一個(gè)隱喻,但是詩(shī)人并沒有將愛情往宗教情懷或者信仰意義的方面進(jìn)行滲透,而是徑直采用了一個(gè)“描述+直接引語(yǔ)”的寫作路徑。這種路徑簡(jiǎn)單、直觀,然而在表達(dá)愛情的效果上卻是最見效的。它超越隱秘和形而上的層面,直接進(jìn)入愛情的現(xiàn)場(chǎng),將故事主體的內(nèi)心世界和生命意志打開。顯然,詩(shī)人不滿足于儀式和暗示所帶來(lái)的莊重感和曖昧,而是直接表現(xiàn)人最本真的意念與訴求,不拘泥,不迂回,將愛情的火焰燃燒得至情至性。
不過(guò),也正因?yàn)槿绱耍?shī)人榮榮的詩(shī)歌才帶上了一種強(qiáng)烈的個(gè)人風(fēng)格。外在世界也因此著上“我”之色彩,從而成為詩(shī)人所創(chuàng)造的生命結(jié)構(gòu)之一種。這種呈現(xiàn)清晰地展示為,詩(shī)人在描寫外在自然時(shí),也個(gè)性十分強(qiáng)烈地讓我們感受到詩(shī)人像是在講述或者切入一個(gè)愛情故事,如在描寫黃河時(shí)說(shuō):“突然就碰到一起了,/突然就分出了彼此,/一些事物便無(wú)法掩藏。//之后也許會(huì)一馬平川,/之后也許仍沃野千里。//出星宿海入渤海,誰(shuí)為誰(shuí)一路跌宕?/‘你終究是我放不下的黃河!’”(《在黃河中下游分界碑》)無(wú)論這故事是詩(shī)人實(shí)際發(fā)生過(guò)的,還是讀者想象出來(lái)的,至少在敘事的模式上,它讓我們產(chǎn)生了這樣的聯(lián)想。或許因?yàn)橹燎榈纳w驗(yàn)過(guò)于刻骨銘心,在愛中浸淫太久,敘述也鼓蕩成一種心理機(jī)制了。這也從寫作的角度讓我們見出情感與寫作之間的張力是很強(qiáng)大的。《圣經(jīng)》中說(shuō):“愛是永不止息。”(《新約·哥林多前書》)于榮榮而言,愛在她的寫作中也會(huì)永不止息。
二、最高意義的歡樂
作為最令人刻骨銘心的情感,當(dāng)“分裂”的情形出現(xiàn),抑或當(dāng)它在精神上被還原為現(xiàn)實(shí)的層面,或者被上升至信仰的層面,一個(gè)反思意義上的詩(shī)人就會(huì)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最美好的詩(shī)歌滲透于生命最本質(zhì)的體驗(yàn)之下。榮榮的很多詩(shī)篇,情感上之所以能夠有迸發(fā)的力量,就在于她不脫離現(xiàn)實(shí),因?yàn)橹挥姓鎸?shí)的世界才能夠摩擦出生命的溫度,并經(jīng)由感官進(jìn)入生命存在的精神之中,從而成為一種蔓延著的精神存在。在詩(shī)歌《婦人之仁》中,榮榮這樣闡述她對(duì)生活的理解:
居家之愛,可愛,非常愛。
婦道之道,可道,非常道。
這兩句詩(shī)化用了《道德經(jīng)》中最著名的句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卻沒有給人造成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哲學(xué)話語(yǔ)印象,相反,從她這首詩(shī)一句一句的推理中,我們看出了一種“活在生活中”的精神,看出了一種對(duì)生活和情感進(jìn)行深入思考的意識(shí):“他在外面操勞,車水馬龍,/她遞茶端水,空懷仁厚之心。//安逸是一只眼前飛舞的蝶,/沒有顏色的女人總被溫情遮蔽。//回家,回家,回家,/一次次將生米煮成熟飯。”盡管其中呈現(xiàn)出無(wú)奈,呈現(xiàn)出自我生命被獻(xiàn)祭的味道,然而真實(shí)的生活,其終極意義是不是就在于此?愛情最終會(huì)變成什么,每個(gè)人都會(huì)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愛情不可能一直處于虛無(wú)縹緲的審美的層級(jí),當(dāng)倫理的一面介入進(jìn)來(lái),每個(gè)人都不得不面對(duì)整個(gè)人類共同的難題:情感如何保持持久的熱情,使其最終不淪落為一種平庸或者精神層面的東西?抑或,如何保持恒久的忠貞,不至于最終走向背叛以及相愛相殺的境地?與其說(shuō)榮榮在這里是借用《道德經(jīng)》中的話來(lái)給我們作答,不如說(shuō)她亦只是在告訴我們尋找這個(gè)答案的“艱巨”。
人們一般很少傾向于將詩(shī)歌寫作納入信仰的層面,我一直也是這樣一種認(rèn)知。即使一個(gè)詩(shī)人對(duì)詩(shī)歌再虔誠(chéng),我也始終覺得詩(shī)人的寫作也只是一種藝術(shù)行為。我們常常說(shuō)某些在詩(shī)歌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詩(shī)人,是以詩(shī)為生命,他們將詩(shī)歌當(dāng)成了自己的信仰。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這是一種修辭意義上的贊美。我們不否認(rèn),有些詩(shī)人將詩(shī)歌當(dāng)成了自己畢生的事業(yè),然而這絕不意味著他每天對(duì)詩(shī)歌進(jìn)行宗教意義上的“朝拜”。不過(guò),我們需要回旋一下來(lái)言說(shuō)詩(shī)與宗教(信仰)的關(guān)系。因?yàn)槲覀儫o(wú)法否認(rèn)詩(shī)歌可以從宗教(信仰)那里獲得營(yíng)養(yǎng)。我們無(wú)法確知詩(shī)人榮榮是不是有對(duì)宗教的虔誠(chéng),但是其詩(shī)歌中隱隱約約地閃現(xiàn)出這樣一種意識(shí)。如前文已提及的《心舍利》,雖然內(nèi)容與宗教無(wú)涉,然而卻借鑒了宗教的內(nèi)在精神。詩(shī)人另有一首《大覺寺》:
相愛未遂,她還在人間滯留。
功名未遂,他還在天南地北。
春風(fēng)從容,往事無(wú)數(shù),
你仍欠我一個(gè)了悟。
這首詩(shī)只有簡(jiǎn)短的四句,卻傳達(dá)出一種非常深刻的了悟。在寫法上,這首詩(shī)與《心舍利》基本是相似的,以一個(gè)宗教意象的題目來(lái)寫對(duì)愛情的思考。其主題異常明晰,內(nèi)容純凈無(wú)瑕,所指、能指亦一覽無(wú)余。自然,詩(shī)人并非是要借助這樣的意象來(lái)給人造成理解的錯(cuò)覺。這是一種極具張力的寫作技巧,借助理性的覺悟來(lái)對(duì)非理性的情感進(jìn)行詩(shī)意化的描述。當(dāng)然,詩(shī)人亦絕非要從形而上來(lái)為我們解開一個(gè)形而下的實(shí)在問(wèn)題,一旦陷入這樣的思維當(dāng)中,詩(shī)歌寫作將會(huì)邁入危險(xiǎn)的境地。不過(guò),作為至情至性的詩(shī)人,榮榮也基本上不會(huì)這樣處理自己的寫作。或許她有這樣一種憂患意識(shí),但更重要的是她的詩(shī)思基本上都系于情感的游絲里。她沉浸于這種以情感開路、以情感深入的寫作,即使信仰缺失,仍然不會(huì)阻斷她借助詩(shī)歌來(lái)喚醒個(gè)人對(duì)意義的省思。只要看她的代表性作品《這一天她還在人間走著》,我們就能有非常直觀的感受。詩(shī)歌的開篇,詩(shī)人這樣敘述:“這一天她還在人間走著/還是人間的。還在一次次歸來(lái)。”緊接著,詩(shī)人開始鋪敘“她”如何在人間、在凡俗里出現(xiàn)、打轉(zhuǎn),直到“那個(gè)瞧著手機(jī)跟唱的女子,/那個(gè)掛滿盆景跨坐電瓶車上的兜售者,/差點(diǎn)撞上她,夜色遮掩了他們的臉容。/她盯著微信里一句親密的話,/刪還是不刪?這來(lái)自遙遠(yuǎn)的硬漢柔腸,/也跌落于日常的瑣碎和抒情。”顯然,詩(shī)人敘述的根性問(wèn)題依然在于情感。她寫作的意念依然澄澈如此,然而詩(shī)人并不止步于此,詩(shī)人要借助自然風(fēng)物,以古典的方式來(lái)收束它:
這一天她還在人間走著。
還是人間的。還有些不舍。
路過(guò)小公園,冬天仍在深入,
銀杏已脫完一頭明黃,雞爪槭的葉子
蜷一半撒一半,扮演又一場(chǎng)春紅。
這一天所有昨日重回,似有新的抉擇,
往左是時(shí)間恍惚,往右是自然蕭瑟。
盡管感傷,但任誰(shuí)也無(wú)法拒絕詩(shī)人所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這樣一種感性與理性交融、時(shí)間與空間合一、剎那與永恒混一的境界。它讓我聯(lián)系起偉大的詩(shī)篇《春江花月夜》,其中滲透著詩(shī)人靈性寫作的光輝。
對(duì)于詩(shī)人榮榮而言,詩(shī)歌是承載了其心靈生活的載體。所有的這些詩(shī)句,“是現(xiàn)實(shí)的回響,是追憶、懷想、復(fù)述,并重新抵達(dá)——”當(dāng)她重新閱讀它們,她“看到了某種時(shí)間的魔術(shù)或秘密”,那是她一個(gè)人的,但又不是她一個(gè)人的。(《遠(yuǎn)離現(xiàn)實(shí)的隱秘傷感》)一如詩(shī)人在詩(shī)歌中所敘述的那樣:“最高意義的歡樂總鮮為人知,/它藏得那么深,/像事物隱秘的核心。”(《最高意義的歡樂》)
(趙目珍,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大學(xué)副教授。本文為深圳職業(yè)技術(shù)大學(xué)創(chuàng)意寫作研究中心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