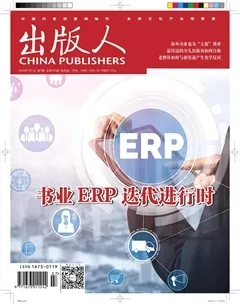一個編輯到品牌主理人的“普通”故事
憑著興趣愛好和激情,姚映然走過了21年的做書之路,她說靠著這些自己應該還可以走得更遠。
如果說不同出版品牌有不同的個性,那創立至今已20年有余的世紀文景(以下簡稱“文景”)一定是其中個性面貌都極為顯著的一個:既在人文理念上有持續的追求,也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功。
從成立之初就加入文景,由一名普通編輯成長為編輯部主任,再到總編輯、總經理,姚映然深入參與塑造了這個品牌如今的面貌。她與這個品牌彼此陪伴、相互見證走到了今天,其個人的成長路徑也因此與文景的發展軌跡幾乎完全同步:人文社科起家,意外在引進文學領域打開一片天地,一路踏實穩健,不斷在新的領域挖掘開拓,其間沒經歷過什么大起大落,一路螺旋上升。一晃不覺20多年,她自始至終都頗有默契地和自己供職的這家出版機構保持一個讀書人對情懷和人文理念的追求,也在不斷的做書實踐中將商業和市場的部分做得無可挑剔。
姚映然說自己是一個憑著興趣愛好和激情就能走挺遠的人,她不覺得自己是因為抓住了某個具體的機會或哪本書才能走到今天,也從沒有設立過一定要做成什么樣的目標,“反正有了機會我就試試,我很幸運,在每個階段都能找到自己的興奮點和興趣點,始終覺得自己在成長而不是倒退”。
從“讀書人”到“做書人”
姚映然的編輯生涯開始于21年前。即將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的她,原本想要出國深造,后來因種種原因沒去成,在老師的介紹下,姚映然幾乎沒多猶豫,一頭扎進了看上去“跟讀書生活離得最近”的出版圈。
進入北大以前,姚映然雖然也閱讀過一些文學書,但大多數情況下讀書都是以考試為目標而進行的一項活動。在北大的學習和生活,為她開啟了真正的讀書生活。
她至今記得當年的班主任是如何瘋狂地癡迷讀書的,“吃飯的時候在看,坐車的時候也拿一本書看,他的生活里好像全都是讀書”。除了老師,身邊的同學同樣給姚映然樹立了一個很高的讀書標桿——不僅讀得多,看的書也不是那種很容易就能讀懂的。“我的老師和同學在閱讀這件事情上,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啟蒙,讓我知道了有一種生活叫讀書生活。”
7年的北大學習生活,完全是姚映然心目中大學生活最理想的樣子,在這里的讀書和實踐,給了她一個機會去了解歷史/文學傳統、了解社會,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你會有個對照,會去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自己的興趣在哪里,或者自己到底想要改變點什么,我覺得這是北大生活給我最多的”。
另一方面,在那個市場經濟已經開始起飛、整體社會氛圍顯現出相對功利色彩的年代,北大同學們“現實但不功利,剛直但不偏激,理想但不空談”的特質更是深刻地影響了姚映然日后的出版態度。
2003年文景成立不久,姚映然即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在將這個新品牌介紹給她的老師口中,這是一個“新成立的、想法觀念非常先進的出版機構,將來肯定能做很多事情”。能繼續和書打交道,又可以做一些事情,無疑對姚映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學生階段就讀過不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書,對它旗下品牌自然地有了一種親切感,因此成為一名文景的編輯是當時的她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讀書和做書確實不太一樣”,這是姚映然接手做第一本書后的感受。
研究生時代,她就讀過臺譯本的《福柯的生死愛欲》,相比作為讀者時如癡如醉的閱讀狀態,編輯姚映然感受到了一定的挑戰。首先是要將臺譯本大量刪減的注釋補譯出來,加上兩岸對一些專有名詞的譯法不太一樣,原文本又涉及不止一個語種和文字,她花了大量時間查找補譯原文并核對各個細節。
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6個月時間,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疑難點,姚映然才終于把這本書做出來,她說那一刻自己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這個過程里,雖然一些前輩手把手教了她不少基本功,但真正親自實踐了,她才對做書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像入門磚一樣,它點位很正,跟我自己的專業也很對齊,讓我對做書這個職業、對這個行業,有了開頭就很默契的好感。”直到今天,這本書經歷多次修訂,仍然是文景眾多產品中一本長銷不衰的經典之作。
一個新編輯的頭幾年
正式入職沒多久,姚映然就參與了世紀出版集團的重點項目“世紀人文系列叢書”。這套叢書計劃收入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和前沿圖書,第一批文景有40多種選題入選,而且幾乎全是新出品種,壓力之大,不言而喻。
作為新人編輯,姚映然能參與這么重要的項目,得益于當時文景大膽起用新人編輯的理念。在文景的項目制管理模式下,她跟著前輩從選題策劃、作者聯絡、文本編輯,到圖書設計、后期營銷等,幾乎把所有出版環節都經歷了一遍。這段經歷對姚映然而言十分重要,不僅讓她的具體執行能力得到極大的鍛煉,也使她對一個大型項目如何謀篇布局有了初步的認識,前者對應一個好編輯應須具備的品質,而后者則是未來成為管理者的她所不可或缺的。
參與集團大型項目的那幾年,姚映然也在不斷尋找和規劃自己感興趣的選題。
那是200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讀到了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的臺譯本,“在宿舍一晚上沒睡讀完了這本書,覺得特別精彩,想著我能不能也試試做文學(書)”。學社科出身,又身在社科編輯部,姚映然那時對文學類的選題并沒有特別清楚的概念,純粹憑著直覺判斷覺得文本足夠好,就報了選題。有賴于文景長期以來對編輯“不設限”的傳統,彼時在國內還不太知名的帕慕克的書就這樣被引進了。
書出版兩個月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名單公布,已經下班的姚映然接到媒體朋友的電話,告知她帕慕克得獎了。此前從沒有想象過自己第一次做的文學書就能得諾獎,對姚映然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驚喜。更長遠地看,通過做這本書,她對選題的想象被大大拓寬,從此不再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社科編輯的范疇里。
“作為新編輯的前幾年,我都是非常激情澎湃的”,正因如此,多年以后開始管理團隊的她尤為看重一個新編輯的前幾年。
對新入職的編輯,姚映然鼓勵他們一進來就多嘗試、多表達,找到自己的關注點。“因為編輯剛入行,處在最新鮮、最有活力的階段,并不知道什么東西有困難、什么東西不能做,你覺得什么都可做,腦子里沒有那么多的條條框框,像我做帕慕克就是這樣,沒有人告訴我說你不能做文學,我讀到好的了,我就要抓住它。而到后來,一旦踩過坑,你就會害怕,你就會瞻前顧后。”
不過,在編輯姚映然看來,與多提選題同樣重要的是編輯的基本功和嚴謹認真的態度。
入職文景的第四年,基于擬搭建的學術社科領域框架,她決定為已故著名哲學家賀麟做一套全集。在與賀麟先生的家人和學生交流、整理書稿的過程中,她徹底為老一輩學者認真、細致的做事態度所折服,“那時黃人道先生(賀麟的夫人)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但賀麟先生的字只有她認得清,她就把手稿里所有改動、小批注都幫我們標清楚,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張祥龍先生(賀麟的學生)也多次指點,還為全集撰寫出版說明”。姚映然深切地感受到了手中書稿的分量,她要求自己務必用同樣嚴謹、認真的態度做好這套書。
在后來的許多年里,姚映然一直踐行這樣的編輯態度,并在她成為團隊的管理者后,影響了更多的文景人。
帶領團隊一起跑
加入文景的第10個年頭,姚映然再次迎來身份上的轉變:就任總編輯一職,主管選題與內容。和上一次“讀書人”到“做書人”的體驗完全不一樣,她形容自己從“單打獨斗的個體戶”變成了“要帶著團隊跑”的管理者。
以往做編輯甚至是編輯部主任時,姚映然只用安心做好自己的事,頂多是以老帶新的方式帶著部門同事一起做一個項目或者產品。但主管內容后,需要她更加全面地考慮問題,“我要想辦法,不管是通過制度,通過激勵,還是通過流程的設計,推動整個團隊的同事往前跑,是有很大變化的”。
領著團隊在選題方向上做了不少探索后,姚映然發現雖然有很多成功的,但也有不少失敗了。比如在人文領域,他們做的面很寬且在具體的領域很深入,電影理論、音樂理論方面的選題都有涉及,書本身都很好,但當時的市場和讀者并沒有給出太多的正向反饋。事后總結經驗,她覺得可能還是時機不成熟,“這些是偏理論性的,當時的讀者沒有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和水準,我們做得超前了”。
通過重新梳理產品線,以及進一步思考哪些東西該堅持、哪些可能要再等一等,姚映然和同事們度過了這段在內容探索上的瓶頸期。在想清楚未來該怎么走的同時,一條全新的產品線借由一本新書的上市開始初現雛形。
從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出發,并試圖去探索解決之道,這是文景團隊請上海交大教授陸銘做《大國大城》的底層思路。“我自己是學社會學的,所以一直都會關注社會生活的實際運轉邏輯或者社會問題的題材,我們團隊也希望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有一些社會關懷。”抱著這個目標,他們開始找各個細分方向的老師約稿。
事實上,再早個幾年,姚映然認為像《大國大城》這樣的作品未必能做得好,因為學術出身的寫作者普遍寫得太專,普通人可能看不下去,另外,由于高校教師大部分面臨考核壓力,可能不太愿意寫這種普及性讀物,“但到近幾年,我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老師愿意寫給大眾看的東西,而且他們也完全有能力駕馭”,姚映然說。
盡管陸銘交來的初稿已經相當不錯,但還是經過編輯和他的反復溝通調整才有了后來呈現出來的“為大眾寫作”的面貌。緊接著,團隊又在這一領域和寫作者磨合了一兩個產品,并取得了不錯的市場反響,此時姚映然和團隊終于確認這一類產品是可以做的。“我們并不是一上來就立了個flag要做‘中國之治’系列,而是說我們先運行了一些產品,覺得不錯,再有意地去尋找各個方向的寫作者和專家來為這一系列貢獻產品,屬于先有書再有產品線,文景長期以來都有這樣一個模式。”
2021年《置身事內》的出版使得“中國之治”系列在行業內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達到一個高潮,這條產品線算是徹底立住了。對姚映然和團隊而言,更為珍貴的是,他們積累了一套從零開始打造和運營一條產品線的經驗。尤其是對歷來以引進版權見長的文景而言,這套原創政經叢書給了他們極大的信心進一步發力原創產品。
作為文景的主理人,姚映然每年最大的焦慮來自頭部產品的產出。對當初創立沒多久就有了百萬級暢銷書的文景而言,這些年來頭部產品無論從營收還是社會影響力來看,都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板塊。她坦言自己和同事們雖然不斷在摸索暢銷書的生產和運營邏輯,但這件事極為不易。
反觀這幾年的圖書市場,出版熱點一波接一波,從公版、心理勵志到漫畫等,這些領域暢銷產品頻出。盡管渴望做出暢銷書,但姚映然和同事們幾乎一個熱點都沒有跟。“我們的編輯很少會看到什么熱就撲上去做。”她告訴《出版人》雜志,文景對選題不設限,但也絕不跟風,“不設限、不跟風、不低俗”,這是多年來她和同事們心照不宣的一種默契。
除了在產品上帶領團隊探索更多可能性,成為總編輯以來,尤其是2016年后,開始擔任總經理一職的姚映然身上的擔子變得更重了。其中擺在首位的是人才的培養。
姚映然覺得編輯是一個“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行當,但從公司和管理者的角度來說,有好的制度和組織架構設計才能保證一個優秀的編輯能夠立足,并獲得更好的發展。給予團隊和個人足夠的激勵,讓他們有足夠的動力做出一本好書,這是姚映然近幾年非常重視的一件事。在這點上,她認為自己做得還不錯,文景內部良好的企業文化和團隊氛圍已經建立起來,編輯們既能找到自己做書的真正樂趣,又有團隊之間一起打仗收獲的正向反饋。而每每有同事離職,他們最焦慮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自己的作者和書怎么辦。“我們的企業文化已經形成了,編輯們有一種無形的、精神上的相互支撐,或者內在動力,推動他們去精進自己的水平,讓自己做到更好。”
姚映然驕傲于文景的每一個優秀個體和企業文化,但身為管理者的她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遺憾:“我們已經20多年了,不算短,但我們還沒有做到很大的體量。”她未來最大的目標之一是讓文景人過上更體面、更無憂的生活。
始終尋找做書的樂趣
一晃不覺21年。姚映然說自己很幸運,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遭遇的挫折也少——如果非要說有什么特別難的時候,那是在她加入文景的第10年,遇到了自己職業和生活的瓶頸期。
這一年,姚映然的職業生涯走到第10年,她覺得自己有了倦怠感,對未來努力的目標和方向開始有些疑惑,與此同時,初為人母的她也感到了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間尋找平衡的困難。面對眼前的瓶頸,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兩條路可選:要么逃避,要么堅強面對、咬著牙走下去。所幸她選擇了后一條路。支撐她走下去的原因也很簡單,“本質上我還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
直到現在,姚映然仍然認為能在自己工作中尋找到真正的樂趣,是面對挫折和困難時最重要的支撐。“‘我’字底下是個‘找’,我覺得職業生涯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尋找的過程,尋找你自己的目標,找到你自己是什么、想成為什么,找到真我。一時的風光其實不代表什么,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都在尋找做書的樂趣,我和我的同事之所以能在這個行當里堅持下來,還是因為這件事情非常有趣,否則你很難去堅持,或是根本無法去抵御里面的挫折和困難。”
尋找的過程也伴隨著疑惑和沖突。加入文景不久,姚映然就發現她覺得必須做的一些書可能在市場上的表現并不會太好,但她最終還是執著地將這些書做了出來,“沒什么好商量的,好書必須做”。一開始她會努力在保證好書能被出版的前提下盡量平衡二者——這是從讀書人到做書人轉變的過程中極為自然的選擇和心理。隨著經手的書越來越多,她對情懷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漸漸有了不一樣的認識:一本書做好了,這兩個東西也常常是不沖突的。
好書自有其讀者。“好的、有文化價值的產品,它的市場或者商業價值不應該很糟糕,看你有沒有找到以及挖掘得好不好。”不過姚映然也清楚,不同的書,對它們的市場期待肯定還是不一樣的,有些書很專,讀者也就2000個,而有些書的讀者可能有200萬,把這一點想清楚就好了。
在尋找做書樂趣的同時,姚映然和同事們也在不斷擴展著做書這件事的外延。2012年開始的藝文季是文景成立以來做得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品牌活動。說起這些,姚映然覺得特別有成就感。
“做書不要讓它越做越窄。大家對我們的認知里,好像編輯就是一個看看稿子的職業,但是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內容產業,可以不只是做書,而是提供一種文化服務,從包括書在內的其他各種各樣的角度去影響我們的受眾,所以在相關的鏈條上我們做過很多事情,包括展覽、快閃書店等,這幾年我們還做了文景歷史寫作獎。”這些事情對姚映然和同事們來說每一樣都是挑戰,但他們在其中找到了不一樣的樂趣,也感到自豪。
不同階段姚映然的工作有不同的重點,但有一件事卻是她這么多年一直堅持且樂在其中的:幾乎每周都會花一定時間去找作者,聊新的選題。一方面她自認責無旁貸,另一方面,她認定這就是她的本行,做這件事時她感到十分開心。
憑著興趣愛好和激情,姚映然走過了21年的做書之路,她說靠著這些自己應該還可以走得更遠,因為幸運如她,“我的熱情一直都在,而且一直一直做得很快樂,從沒有覺得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