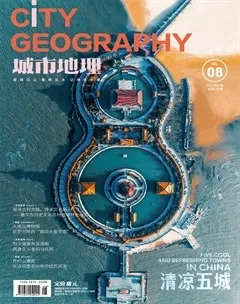萬州老巷里的煙火人家
2024-09-23 00:00:00李曉
城市地理
2024年8期

萬州,是一座綿延1800 多年文火的城市。如今的萬州,新城拔節生長,老城浸透包漿。在老城,那些苔蘚漫漫的老巷子,是這座城隆起的皺紋,也是這座城衣衫上打下的舊補丁。這些大大小小的補丁,與那些站立、攀爬、盤臥的老樹一樣,交織出城市的年輪。這座城市的年紀有多大,它蔓延在地下的根須有多長,我心中是有數的。我不慌張。
在一座城,我總喜歡去老巷子里轉悠。它的市井人聲,它的流光溢彩,它的販夫走卒,它的引車賣漿,它的煙火人家,它的地氣裊裊,讓一座城燈火可親,讓一座城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柔軟地覆蓋在我心田中央。
萬州老城,一條叫做偏石板的老巷子里,有一棵把裸露根須扎進巷子老墻上的黃葛樹,遠遠望去如樹的浮雕。那年夏天的早晨,我乘一艘江船去南京一家雜志社出席筆會。凌晨四點,城市還是睡意蒙朧時分,我向黃葛樹邊小屋里的宋哥道別。我沒敲開宋哥家的門,只想聽聽他的呼嚕聲就夠了。
奇怪,屋子里沒鼾聲,從窗戶還透出昏黃的光。我忍不住輕聲哼唱起了南斯拉夫歌曲:“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一天早晨,從夢中醒來……”正要轉身離開,屋子里突然傳出吉他伴唱聲:“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宋哥彈得一手好吉他,那些年,在一群文青聚會上,他背著一把吉他,修長的十指如蔥,一曲曲彈奏下來,我們都沉浸在音樂當中去了。那天早晨離開宋哥家的房子,我沿著巷子里草色青青的石階,乘船離開,悠長汽笛聲拖著尾音在大江晨曦里響起,我朝宋哥家巷子的方向望去,浮想起宋哥也趴在窗口,望著這條大江的方向,目送著我乘船離開這城。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