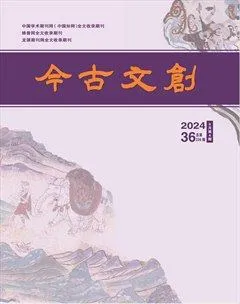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喜劇理論探析
【摘要】亞里士多德所提及俄瑞斯忒斯故事的喜劇版本反映出亞氏將思維慣性的打破作為喜劇性生成的基點。喜劇快感的生成則與求知的滿足與觀眾在觀看時暫時性的替代性滿足相關。對喜劇性和喜劇快感的思考與亞氏本身的政治倫理思考密切相關,即強調行動力之重要性、塑造更好的公民個人素質。
【關鍵詞】亞里士多德;喜劇;喜劇性;喜劇快感;政治倫理
【中圖分類號】I0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36-008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25
在國內學界中,對亞里士多德喜劇理論專門研究數量較少。亞里士多德在《詩學》對喜劇的論述之中假設了俄瑞斯忒斯的喜劇版本,這一點幾乎被現有研究忽視,但該例子能夠很好地對亞氏所思考的喜劇性和喜劇快感的生成論述作出補充。本文從喜劇性和喜劇快感的生成為切入點,以《詩學》為主要文本,同時結合亞氏的其他著作,對其喜劇理論進行分析,并借此指出其喜劇理論背后的倫理政治思考。
一、喜劇性
喜劇性的生成是喜劇理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有學者將亞里士多德喜劇理論中喜劇性歸納成“高階論”,即觀眾對摹仿對象居高臨下的輕蔑而產生的快感,如石可“高階論,或者說優越論,是最古老的說法,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些低于或者劣于我們的人或事會讓我們發笑。這實質上是認為,喜劇性本質上是輕蔑的一種形式:前現代時期社會成員的‘尊嚴’即建立在等級社會中社會地位的比較上”[1]3-7。有學者則認為喜劇性是由滑稽動作而產生的,如陳中梅認為“喜劇的目的在于通過滑稽的表演和情景逗人發笑”[2]59。
實際上,亞里士多德所論的喜劇性生成不指向動作的夸張和變形。亞氏指出“一種通過表演來表現一切的摹仿是粗俗的。演員們以為不加些自己的噱頭觀眾就欣賞不了,因此在表演時用了很多的動作”[2]190。由此可見,滑稽動作所產生的喜劇性非亞里士多德所贊同。
在論述喜劇時,亞氏以俄瑞斯忒斯為例進行分析“在喜劇中,傳說中勢不兩立的仇敵,例如俄瑞斯忒斯和埃吉索斯,到劇終時成了朋友,一起退出,誰也沒有殺害誰”[2]98。從中,能夠分析出亞氏的思考所在:喜劇性的形成并非是觀眾與摹仿對象之間由于地位優劣對比而產生的輕蔑感,而是由思考慣性打破而生發出。悲劇版本中的俄瑞斯忒斯遵照阿波羅的神諭,殺死篡奪王位的埃吉索斯和自己的親生母親完成復仇。俄瑞斯忒斯的悲劇性體現在他身上兩種倫理的沖突。作為阿伽門農之子為父報仇具有正義性,但報仇要以犧牲母親的生命為代價,弒母行為不具有正義性,因而俄瑞斯忒斯感到矛盾和痛苦。但殺死埃吉索斯則完全合乎其作為在家庭倫理層面上的兒子與作為國家倫理層面上的統帥之子身份的正義性。俄瑞斯忒斯遭遇了父親被殺、王位被奪、母親嫁給仇人的巨大恥辱。從情節上看,按照觀眾的思維慣性,俄瑞斯忒斯將完成最基本的復仇。但在亞氏所設想的喜劇場景中,俄瑞斯忒斯卻選擇與埃吉索斯和解,這使得觀眾思維集中之處被陡然打破,緊張感被解除。而從人物本身看,這個例子還暗指喜劇性來源喜劇人物自身“大”與“小”的不協調,即表面和實質的差異。里普斯指出“喜劇性乃是驚人的小……就是這樣一種小,即裝成大,吹成大,扮演大的角色;另一方面卻仍然顯得是一種小,一種相對無,或者化為烏有”[3]1256。俄瑞斯忒斯出身高貴,卻并沒有與其身份所適配的行動力,高貴的外殼之下實際埋藏著一個弱小的靈魂,使其最終做出和解的選擇,與敵人成為朋友。觀眾對俄瑞斯忒斯的行動期待落空。從這雙重思維慣性之打破中,喜劇性生成。而打破慣性要求創作者制造情節,激發觀眾理性。
亞氏認為荷馬是第一位為喜劇勾勒出輪廓的詩人,他“以戲劇化的方式表現滑稽可笑的事物”[2]48。“戲劇化”意為“著意于一個完整劃一、有起始、中段和結尾的行動”[2]163。亞氏更傾向通過理性思考而產生的喜劇性。在對喜劇語言的論述中,亞氏認為喜劇語言的使用需要考慮的不應只是“笑”結果的生成,還需要考慮玩笑的“適度性”。他對比了現在和過去兩種喜劇的不同“過去的喜劇用粗俗的語言取樂,現在的喜劇則是用有智慧的語言引人發笑,這兩者在禮貌上有很大的區別”[4]124,并對現在的喜劇做出了肯定。依靠粗鄙的語言和夸張的動作所產生的笑是一次性的,滿足的是人“無理性的欲念”,即未經思考而發生的欲念,此時人成為生理性快樂欲望的奴隸。而通過情節編制方式展示出來的喜劇性,亦需要觀眾借助理性進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亞氏所思考的喜劇性生成與理性相關。
二、喜劇快感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能夠“通過摹仿獲得最初的知識”[2]48,并能從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這是他不抵制詩的原因之一。通過觀看喜劇,觀眾獲得知識并產生求知的快感。而“求知和好奇,一般來說,是使人愉快的;好奇意味著求知的欲念,因此好奇的對象就成了欲念的對象;求知意味著使人恢復自然狀態”[5]180-181。自然狀態“就是一種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運動和靜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6]56,亦是亞氏所推崇之狀態。借由喜劇,公民能夠達到自然狀態,恢復到本真的境地。
除求知快感外,喜劇快感與悲劇快感一樣與卡塔西斯相關。《喜劇論綱》指出喜劇“借引起快感與笑來宣泄這些情感”[5]391。與悲劇“通過引發憐憫和恐懼使這些情感得到疏泄(卡塔西斯)”[2]63不同,喜劇通過“宣泄”來消除緊張,達到情緒的平衡。亞里士多德認為“快感的反面是苦惱”[5]178。借助“笑”,觀眾能夠得到情感的釋放。舊喜劇中有“插曲”,歌隊長常于插曲中代表詩人發表政治見解,所攻擊的主要對象為政治權勢人物或社會著名人士。而亞里士多德所處的中期喜劇時期是雅典遭受外敵壓迫和內部動亂時期,人民無法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對政治缺乏關心,導致喜劇較少指涉政治,更多地選用市民生活為內容。因此,在此時期,公民處于動亂之中,面對自身困境,行動力也處于一個較小的時候,喜劇詩人則借助喜劇給經受苦難的人民堅持的勇氣。
俄瑞斯忒斯選擇放棄復仇,逃避了倫理規則的要求。利普斯認為愉悅感是由移情產生的,“這種聯想、類比的方式為的是更好地理解對象,除了使我們回想起自己所經歷的過程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回想起自己發出同樣動作時的意象,以及伴隨這種動作的情感體驗”[7]374。觀看者在觀看喜劇的過程中,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虛擬代入,將“我”放置到喜劇摹擬對象的身上。在現實生存世界,受到多種倫理責任的制約,人常常陷于左右為難的困局之中。脫離倫理道德思考的行為選擇,恰恰是觀眾在日常生活中難以實現的,而喜劇中低行動力的呈現,讓觀眾產生了替代性滿足的快感,并借由此釋放了現實生活中的倫理道德焦慮。
除此之外,重大事情通過簡單的方式得到化解,這種“化解”使得觀眾產生了輕松的快感。亞里士多德提到:“滑稽的事物,或包含謬誤,或其貌不揚,但不會給人造成痛苦或帶來傷害。現成的例子是喜劇演員的面具,它雖然又丑又怪,卻不會讓人看了感到痛苦”[2]58。換言之,喜劇式的快感不包含痛感,這與悲劇所引發的“恐懼和憐憫”不同。相比起悲劇,喜劇的快感是一種輕松的快感。如喜劇版本的俄瑞斯忒斯沒有復仇,巨大的矛盾以簡單的方式進行化解。
喜劇之快感生成還體現在大團圓之結局引發的替代性滿足上。亞里士多德論述悲劇結構時提到,好人和壞人分別受到賞懲的結構“這不是悲劇所提供的快感——此種快感更像是喜劇式的”[2]98。悲劇所呈現的人的有限性,不免讓人懷疑對抗的意義所在。而好人和壞人分別受到獎懲的“大團圓式”結局的呈現,讓人相信善良與正義能夠最終獲得勝利。科普基于亞里士多德的研究對喜劇快感的生成機制提出的“義憤”說中也同樣提到喜劇快感有“在看到惡人遭到應有懲罰后產生的愉悅”[8]113。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會一直實現,但喜劇的表演使得觀眾產生了替代性滿足的快感。
三、喜劇的倫理政治指涉性
亞里士多德并不排斥喜劇,他認為:“快樂是靈魂的習慣”[3]23。亞氏提出:“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3]3。“衡量政治和詩的優劣,標準不一樣”[2]177,雖常被視為亞里士多德區隔藝術和政治倫理思考的證據,但將《詩學》作為完全脫離倫理道德思考的藝術創作指南的觀點并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本意。古希臘以戲劇為媒介進行社會教化,公民在觀看戲劇中培養基本的文化素質,反過來亦為參與城邦政治活動做準備。“模仿有這樣點石成金的神奇力量,而且它的感染力對于知書達理的精英階層和認知能力相當有限的大眾階層一并有效,很大程度上,它已經不失為哲學認知局限的一種補充。”[9]128喜劇作為戲劇技藝的一部分,必然逃不脫對“善”的思考。亞氏對產生快樂的喜劇之討論也必然包含著倫理政治的思考。
前文提到喜劇性的生成,亞里士多德強調的并非是“動作”,而是注重情節的編制,情節又是對行動的摹仿。陳明珠關注到《詩學》第三章中多里斯人對喜劇發明權的宣稱“他們把ποιε?ν[做、制作]稱為δρ?ν[做],而雅典人卻稱之為πρ?ττειν[做,行動]”,從詞義上看,“δρ?ν(做動作)意義上的行動則只強調做,不強調做什么、為什么做”[10]121。實際上亞里士多德對此不置可否,甚至暗含反諷。陳明珠借助瑪高琉斯的注解,認為在《詩學》“通過眾摹仿者作為所有行動者(πρ?ττοντα?)即事功活動者(?νεργο?ντα?)”(1448a23-a24)這句話提示了?νεργο?ντα?一詞作為πρ?ττοντα?的同位語中意義的等同,而?νεργο?ντα?是?ν?ργεια的同源詞,?ν?ργεια的名詞形式正是πρ?ξι?,該詞正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和倫理學語境中十分關鍵的術語,即“行動”。[11]218由此可看出《詩學》語境中的“行動”,實際上也指向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意義上的“行動”,即倫理德性的實踐活動。陳明珠指出,喜劇摹仿的對象“卑俗低劣者”指向的是道德德性意義上的低劣,她引用瑪高琉斯對亞氏的德性作出定義“城邦最微賤的成員也有其要去履行的職責,而德性正是使其得以好好履行其職責的那種東西”[11]217。喜劇人物存在具有其必要性“沒有可笑的事物,嚴肅的事物就不可理解”[12]282。在觀看喜劇的過程中,普通公民能夠對自身的德性實踐產生思考。
亞里士多德認為喜劇比諷刺詩更高級,其原因是喜劇所能表現的普遍性“在喜劇里,這一點已清晰可見:詩人先按可然的原則編制情節,然后任意給人物起些名字,而不再像諷刺詩人那樣寫具體的個人”[2]81。亞里士多德所追求的是對整個社會群體的反思。諷刺、辱罵,更多地指向具體的人和事,在面對更為具體的人和事面前,觀眾作為旁觀者容易產生“旁觀者”心態,將辱罵和諷刺歸納到私人領域。喜劇所展示的這種非具體,能夠擺脫對具體個體的道德批判,敞開到對集體倫理層面的思考。而“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的特性就在他對善惡和是否合乎正義以及其他類似觀念的辨認”[13]8。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至高的善不在于擁有善的狀態,而在于實現行動,具體的行動是人之性格的外顯,也反過來促進性格的形成。喜劇呈現了最低行動力的可能性,觀眾通過“笑”這一否定性姿態對行動力不足和不勇敢的人進行否定。在對行動力不足的人的否定之中,人們認識到行動的重要性,從而實現德性認知與德性實踐的統一。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必須把伴隨著活動的快樂與痛苦看作是品質的表征”[13]39。當公民在觀看喜劇時,伴隨著觀看行為的快樂同樣是公民品質的表征,與公民德性相關。戈爾德希爾指出雅典及其民主制度依賴表演。雅典公民通過觀看戲劇這一公民行為來進行“自我提升”。表演這一公民實踐促進了民主的公共對話,促進了“民主的政治性主體”的構建。同時,公民身份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又反過來促進了個人主體性的形成。文森特·法倫格認為,“雅典人以表演性的方式維系著其民主性的公民身份”[14]4,甚至“雅典的公民身份也可以視為一種表演”[14]4。個人參與公共活動表現自己的公民身份,而共同的政治生活能夠“使人好的、出色的生活實現活動同一般的活動通過某種共同的評價顯示出實質的差別”[15]15。由于廣場場域的特殊性,“笑”更容易傳染。在觀看中,公民為保持自身與周圍公民的一致性,即使個人對喜劇無感,也容易表演出與周圍一致的反應。在觀看喜劇表演中,個體進行自我認知的教育和塑造。喜劇借由“笑”也強化了亞氏所重視的公民教育。通過喜劇,公民能夠看到普遍性的缺陷所在,能夠更好地參與政治生活,承擔自己的政治責任,在行動中促進城邦政治的完善,最終實現至善的“優良生活”。
亞里士多德喜劇理論背后指向其倫理政治的思考,暗藏了他的倫理政治的關切。觀眾在公共場域中,通過“笑”對行動力不足者進行否定,又從喜劇所展示的普遍性看到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在當今許多喜劇中,存在著許多依靠粗鄙的語言和夸張的動作進行逗笑的情況,只讓觀眾停留在生理性的“笑”之上,其實是另外一種悲劇。重返數千年前的現場,思考亞里士多德喜劇理論及其背后的倫理政治性思考,對當代喜劇創作亦有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1]石可.喜劇的倫理邊界[J].電影藝術,2017,(02).
[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卷3[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羅念生.羅念生全集·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6]徐開來.亞里士多德論“自然” [J].社會科學研究,2001,(04).
[7]劉小楓選編.德語美學文選·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8]林琴.“義憤”與“蔑視”——論本·瓊森的喜劇快感觀[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6(02).
[9]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思想史·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陳明珠.“動作”還是“行動” ?——亞里士多德《詩術》的“戲劇性”論述[J].藝術學研究,2022,(04).
[11]陳明珠.亞里士多德悲劇定義的倫理政治意涵[J].浙江學刊,2020,(04).
[12](古希臘)柏拉圖.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朱光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
[1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14](美)文森特·法倫格.古希臘的公民與自我[M].余慧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
[15]廖申白.《尼各馬可倫理學》導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