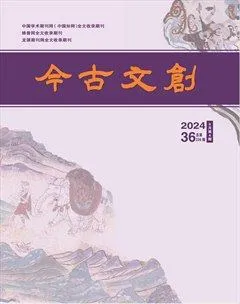張隆溪學術方法研究
【摘要】張隆溪先生以其豐厚的中英文比較文學研究成就享譽海內外,他以跨文化的視角、對待中西方文化的平等態度和對文本的重視進行比較文學的研究,以闡釋學理論為橋梁打通中西方文化的相似之處,在具體的研究中以術語為點、文本為線串聯起中西方文化,在比較文學領域做出了創見性的成果。
【關鍵詞】張隆溪;平等意識;跨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36-003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6.010
張隆溪先生20世紀在北大就讀研究生期間,在《讀書》上發表了十一篇文章為國內讀者介紹了20世紀西方文論,后來這幾篇文章被編輯成《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出版,也由此開啟了張隆溪先生的比較文學研究之路。2016年7月,張隆溪先生當選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迄今為止,張隆溪先生在中西方比較文學方面發表中英文論文專著多部,享譽海內外學界,其學術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分析學習,本文將從人生經歷和跨文化視角,淺析張隆溪先生的學術研究方法。
一、張隆溪人生經歷對其學術道路影響
(一)學習經歷的影響
張隆溪先生自述從小就對中華傳統文化很感興趣,讀了很多歷史、文學等方面的著作,而且還背誦了很多古詩詞,與此同時他對西方文化也非常感興趣。他在偶然間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礎,“我當知青的時候手里只有兩本英文書,一本是希臘羅馬神話,一本是英國文學選讀,從莎士比亞到赫胥黎的十個作家的作品選段。當時我就看這些,你想想,三年的時間只看兩本書,每個字都看得很仔細。”[1]他在《錦里讀書記》中自述“文革”時期的讀書經歷:“山村里沒有電,我只有一盞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每天晚上就著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讀到深夜。”[2]后來張隆溪先生在成都當工人時,偶然有幸結識了歐陽子郡先生,從他那里第一次讀到了莎士比亞全集,還有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不僅如此,張隆溪先生還讀了很多19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依靠這些積累,張隆溪先生考上了北京大學英美文學的碩士研究生。無論是對古典文化的親近還是對西方文學的喜愛都為其日后的比較文學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礎,也可以說正是這一點讓他得到了學貫中西的錢鍾書先生的賞識。
在北大讀研期間,張隆溪先生師從楊周翰教授,同時結識了對其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學者錢鍾書先生。張隆溪先生第一本學術著作《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就是在錢鍾書先生的引薦下完成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這是錢鍾書先生的治學理念,可以說張隆溪先生很好地繼承了這一點。“在我看來,這正是他本人最根本的學術立場,這種立場也是我所深深認同的。這就是我后來之所以長期從事中西文學、文化比較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3]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不僅對古典文化知之甚深,對外文文獻典籍也是信手拈來,這一點也影響了張隆溪先生,在其論文專著中都有所體現,如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的第一篇“管窺蠡測——現代西方文論略覽”中就引用了愛爾蘭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的《詠詩》英文原文,在“諸神的復活——神話與原型批評中”引用席勒《希臘諸神》的德文原文。[4]
1983年,張隆溪先生赴哈佛留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學習的六年,張隆溪先生讀了很多國內讀不到的著作,同很多知名學者進行了學術交流。他曾在耶魯與德里達交流了幾個小時,討論了有關“道與邏各斯”的問題,還曾與伽達默討論闡釋學的問題。在哈佛學習的幾年對他的學術研究有很大影響,他曾在訪談中提到幾位哈佛的老師,比如丹尼爾·艾倫(Daniel Aron)、芭芭娜·魯瓦爾斯基(Barbara Lewalski)和詹姆斯·庫格爾教授(James Kugel),這三位老師的英文文學課程對張隆溪先生的學術研究有很大幫助。
張隆溪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與他的學習經歷是分不開的,可以看出無論是在“文革”期間還是在北大以及哈佛的學習,張隆溪先生始終對中西方文學抱有極大的興趣、平等的態度以及對文學作品的關注,他閱讀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和文學作品,始終堅信中西之間同大于異,以跨文化的開闊視野和闡釋學的理論論述中西方文學相通之處,從中可以看出錢鍾書先生對其影響之深遠。
(二)錢鍾書先生對張隆溪治學的影響
錢鍾書在《管錐編》這本書中論述道:“‘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兩‘道’字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為道白之‘道’,如《詩·墻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語言。古希臘文‘道’(logos)兼‘理’與‘言’兩義,可以相參。”[5]這段論述對張隆溪先生啟發很大,他還以此為靈感,用英文寫下《道與邏各斯》這本專著,希望能夠讓外國學者更加關注中西比較研究,增加中西方比較的可能性。在此書中,他圍繞文學闡釋學展開,深刻地論述了“語言”和“闡釋”之間的關系是如何體現在西方的文學批評傳統和中國古典詩學當中的,這一點也深受錢鍾書先生《管錐編》的影響。《管錐編》是比較早論述有關闡釋學問題的中國典籍,書中對于闡釋學的解釋與應用大大啟發了張隆溪先生。在一篇回憶錢鍾書先生治學方法的文章中,張隆溪先生介紹了錢鍾書先生對闡釋學的真知灼見。錢鍾書先生對中西方異同的比較研究,注重具體事例的運用,認為空泛的理論論證力度不夠。此外,錢鍾書先生還認為文學鑒賞與批評不僅要注重簡潔明了的闡釋,更要注重具體的審美體驗。張隆溪先生認為在這一點上,錢鍾書先生與德國闡釋學名家伽達默達成一致,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伽達默認為文學批評不必也不能以作者的主觀意愿為準則,解釋者完全可以加入自己的“成見”,也就是說以解釋者所獨有的認識水平進行批評。張隆溪先生認為在闡述并論證中西方文化與文學的可比較性時,應該以具體的文學內容舉例。在這方面,張隆溪先生從錢鍾書先生的研究著作中受到很大啟發,比如在《七綴集》中,錢鍾書先生發現《詩可以怨》里“蚌病成珠”這個意象不僅出現在中國古代的詩歌中,在西方詩歌里也有所運用。張隆溪先生的這一發現為錢鍾書先生大量有關闡釋學的論證提供了有力證據,說明在中西方比較研究中,錢鍾書先生的這種在論證時以具體文學實例為支撐的方式可以使得文學內容的理論闡述更具有普遍意義。
總之,錢鍾書先生的治學理念深深影響了張隆溪先生的學術研究方法,無論是對中西文化的平等態度和“求同”思想還是對文學文本的重視,都可見錢鍾書先生對他的啟發。
二、以術語闡釋為基礎的跨文化研究
(一)術語為點、文本為線的串聯
張隆溪先生繼承了錢鍾書先生對中西方文化學術的態度,他始終堅信中西方文化中存在許多相通之處,中國文化文學傳統并非是一個符號化的、西方的對立面和“他者”。他認為西方學者過于夸大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這將間接消除跨文化比較的可能。這一點在其早期著作當中已初見端倪,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介紹結構主義詩學時,為了更好地說明雅各布森的“選擇和組合兩軸”,張隆溪先生舍棄了雅各布森選用的實例,而將目光轉向中國的律詩,用律詩中的“當句對”來解釋雅各布森所說的“對等詞語”,并用杜甫《曲江對酒》中“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一句說明“把類似性添加到鄰接性之上”。這樣一來,對當時讀者來說陌生的西方文論就變得親切明白許多。
在近年來的學術研究中,張隆溪先生常常找出中西方文化類似的地方或相同的術語,并以術語為點串聯中西方文化,以《略論“諷寓”和“比興”》為例,張隆溪先生選取“諷寓(allegory)”和“比興”兩個中西方獨有的術語,并以《圣經》中的《雅歌》和詩經中的作品為支撐,論述闡釋過程中的過度闡釋問題。他發現無論中方還是西方都曾為經典作品做出超出字面意義的解釋,西方存在為維護經典作品的正當性和權威性而做的用諷寓解釋,也就是“用完全不同于經文字面的精神意義來替換和取代引起爭議的字面意義”[6]。而在中國,對《詩經》十五國風的注釋中“也是通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闡釋方法,斷定這些作品都另有寄托,可以起到符合儒家觀念之美刺諷諫的作用”[5]。張隆溪先生并不是想通過對“諷寓”和“比興”的論證來證明中西方文化傳統中存在意義相同的術語可供文化交流使用,他肯定諷寓解釋和美刺諷諫對保護繼承經典作品的意義,但他認為一切闡釋都應該建立在原文原意的基礎上,他反對“這種為了某種宗教、倫理、政治之目的而歪曲、誤讀、誤解作品文意的闡釋”[5],并舉蘇軾“烏臺詩案”為例說明這種過度政治化的闡釋對文人和整個文壇的危害。
張隆溪先生在《“滄海月明珠有淚”:跨文化閱讀的啟示》一文中,舉了一個在宗教中比較常見的比喻,就是把“語言”喻為手指并把“實在”喻為手所指的月亮,二者的聯系比較牽強,但是“以手指月”的比喻主要在于強調宗教的終極目的是“內在精神”而非“外在事物”,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如此,這也說明了東西方宗教具有共通之處。針對這一現象,張隆溪先生闡釋為:“純粹從東方典籍的傳統中來理解這一意象,就會認為以手指月是具有佛教禪宗特色的比喻,而在西方傳統中來理解圣·奧古斯丁使用這一個意象,又會以為那是基督教的獨特比喻。但是,從跨文化閱讀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這兩種看法都顯得太局限而缺乏識力,兩者都好像只看到了手指,而不知道那根手指只是局部而又限度的理解,而輝映在那兩根手指和世間所有手指之上的明月,其映照的范圍都要廣闊得多,會使我們舉頭望遠,看清人類的心智想象可以自由馳騁,認識到人類的創造力無限廣闊。”[7]
(二)平等意識下的跨文化視角
張隆溪先生在美國求學時發現西方的學者將中國文化傳統當作完全相反的他者,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和語言沒有精神性和抽象性,與西方文化存在根本性的差異,這種觀念持續到20世紀,德里達在批評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音主義時仍然將中國的語言作為圖像式而非語音式與西方對立起來,這種偏見體現出歐洲中心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張隆溪先生在美國學術環境里對這種偏見帶來的研究中西方比較文學的障礙有深刻體會,因此發表了很多論著,如《道與邏各斯》就從文學闡釋學的角度開始了對這種偏見的批判。張隆溪先生認為西方對希臘羅馬經典和圣經解釋是闡釋學產生的基礎,而中國對經典具體內容和理論的討論也為闡釋學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二者之間存在溝通的可能,從闡釋學的角度來看,中西方對經典的解釋無疑是跨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從中可以看出張隆溪先生對待中西方文化都持平等的態度,西方學者的偏見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確實為歐洲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然而膨脹的民族主義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二戰后歐洲對民族主義進行了反思,但西方的學者對中國的態度仍然受其影響,張隆溪先生在《文化封閉圈》中批評美國漢學界十分封閉,跟外界幾乎沒有什么交流。張隆溪先生認為要有全球的眼光和視野來研究世界文學,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多進行學術交流,主動地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學和文化。交流的前提就是語言,張隆溪先生很好地繼承了錢鍾書先生學貫中西的特點,在論著中旁征博引,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外國文學都能侃侃而談,掌握多種語言。在掌握語言的基礎上更加廣泛的閱讀,開闊自己的視野,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很可能認為某一個問題是自己的文化傳統所獨有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張隆溪先生出版了很多英文專著和論文,他認為想要在國際學界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至少現在用中文是不行的,用英文的優點就是可以在西方學術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研究跨文化問題時,既要有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的問題意識和獨立見解以及文化平等的心態,又要了解他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從而能夠進行交流和對話。
在張隆溪先生的跨文化研究中,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結合了理論和文學的力量,在闡釋學的背景下搭建起中西方學術交流的橋梁。有學者批評張隆溪先生的英文寫作主要面對的是英語讀者,寫作重點在于討論西方學術中存在的問題,為此在寫作中多為討論中西方比較中的相同之處,希望能夠達到跨文化的理解。但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側重凸顯中國文學獨特的民族特點,在論述中大多探討中西方的不同點,“張隆溪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對這種文化對立的批判,源于他對這種夸大了的差異帶來中西不可理解的焦慮以及跨文化理解的渴望,而不在于對某些結論的探討上面。”[8]
不能否認的是海外漢學研究和國內學者的研究始終存在很大的差異,在海外做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不可能不受當地學術環境的影響,但二者之間的差異正是值得相互交流學習借鑒的地方。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越來越強盛,有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對中國感興趣,正如在海外漢學研究的歷史上有很多因政治原因開始中國研究的學者對中國產生興趣和好感一樣,越是了解某種文化就越明白這種文化的優劣所在,吸收海外漢學的優勢的同時堅守自己文化傳統的視角,正如蔡元培先生做北大校長時的辦學理念“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持有平等開放自信的態度才能真正地做到兼收并蓄。
三、張隆溪治學方法及啟示
張隆溪先生在自己治學的過程中讀了很多書,包括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具有良好的外語水平。他認為做學問讀書就是要多讀、多記。學問只有積累到一定的閱讀量之后才能達到融會貫通。一開始讀書是讀一本一本孤立的書,它們相互之間未必見得有很好的聯系。隨后一個階段讀某一方面的書,這樣能夠集中成一個主題,在進行廣泛的閱讀后,讀過的書就能匯集成知識網絡,進而進行深入的研究。另外可以在研究之外再多看一些東西,也能夠受到很多啟發,不管是什么讀法一定要做筆記。通過廣泛而深入的閱讀,把研究的問題聯系起來,將學問打通。錢鍾書先生曾開玩笑說自己不是學者,是通人。通人首先就是要有歷史的眼光,不僅看到自己的傳統,也要了解其他國家的傳統,這就是打通中西,張隆溪先生在美國教授研究生課程時對學生強調要有歷史的眼光和作品的積累,歷史的眼光能夠幫助了解學術的根源,作品的積累能夠成為理論的支撐,還有就是人文學科的打通,多閱讀藝術、歷史、宗教、哲學等與文學密切聯系的書籍。
張隆溪先生認為對年輕的研究者來講,最重要的是對學術的熱愛與追求。學術研究枯燥而緩慢,需要成年累月的閱讀、做筆記,慢慢去思考。此外,做學術要真誠,對學術傳統的尊重,遵從學術規范和道德,了解前人的成果才能提出自己的新見解,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堅持和努力。他認為東西方的比較研究的歷史沒有很悠久,總體上呈現出一點稚嫩和膚淺,但如果有后輩學者愿意不斷努力,刻苦用功,總會有守得云開見月明的一刻,無論是對東西方的比較還是國內的研究,張隆溪先生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
書寫和敘述,傳遞著一種信念。張隆溪先生在比較文學的領域里辛勤耕耘了三十年,從少到多,從無到有,“綜學在博,取事貴約”,以其學術實踐為后輩研究者指明了廣闊的研究方向,其治學的態度和方法值得人們學習。
參考文獻:
[1]梁建東,張隆溪.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化——與張隆溪教授的訪談[J].學術界,2010,(09):113-119.
[2]張隆溪.“三十年集”系列叢書·一轂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3]梁建東.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與對話——張隆溪教授訪談錄[J].書屋,2010,(04):23-30.
[4]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5]童明.說西-道東:中西比較和解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36-48.
[6]張隆溪.略論“諷寓”和“比興”[J].文藝理論研究,2021,41(01):1-14.
[7]張隆溪.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8]孫華明.超越對立:論張隆溪的跨文化研究[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1(05):98-102.
[9]王炎.跨文化視閾:北美漢學的歷史與現狀——張隆溪教授訪談錄[J].文藝研究,2008,(01):73-79.
[10]蔣洪新.博采中西 積力久入——漫談張隆溪與錢鍾書學問之道[J].東吳學術,2012,(05):60-71.
[11]蔣洪新.戛戛獨造 融通中西——管窺張隆溪先生的中西文化研究[J].中國比較文學,2013,(01):113-122.
[12]張和龍.對學術要有一種愛——張隆溪教授訪談[J].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1,(01):1-21.
作者簡介:
陳鶴,女,漢族,遼寧阜新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唐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