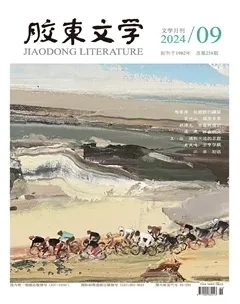在講述中抵達真實
我的大部分時間,或者說生活的軸心,是放在寫作上的。我偶爾會感到困惑:我絞盡腦汁鉆研尋索的東西,是否已經向我展開全貌?虛構的意義何在?文學的內核應該是怎么樣的?諸如此類。我想我還有大把時間可以去搞明白這些問題,或者去搞明白它們究竟是不是問題。畢竟文學沒有嚴格的標準,一切都是模棱兩可的。
小說就是講故事,無非是怎樣講和講什么的區別。用語言構建的故事也好,用文字描述的故事也罷,總歸是在“講述”。“講”是第一位的,故事需要敘述者,需要一張“嘴巴”。在我過去的創作中,我更習慣讓自己充當這個“嘴巴”。但也有例外,比如這篇《香蕉樹漫記》里我借用了別人之口——一位我很尊敬的女性長輩。我們之間有過很多坦誠、直率的交談,加上這個故事本就以她為原型,于是我下定決心依托她的視角來寫,再蔓生一些枝節,寫得更豐富一些。而我自己則充當小說中的傾聽者。這與現實情況相符,只是時空發生轉變。我畢竟要虛構,要使出“搬弄”人物與語言的本事來,以求在平平無奇的結構上,生出一點兒波瀾。
這篇小說的誕生極其偶然。相比有原型的故事,我更喜歡凌空蹈虛,從一個點寫起,然后是一條線、一個面、一個物體,故事從虛無中誕生,于這個世界并沒有明顯的根據。它并不完全脫離現實主義,但總歸要有點兒超現實的元素在,無所拘束,這是寫沒有原型的故事的好處。而當故事有了原型,也就和大地接續了根脈,雖然現實性更加“豐厚”,但也牽絆了我。這篇是例外,也許和那位女性長輩的講述有關,她以小說家的敏銳,精準地抓住了那個核心,也就是我在小說中寫的兩次吃香蕉的情節,我正是被此打動,才寫下這篇小說。我把這兩個情節“搬”進小說,文字與講述完全吻合,這是我對那位女性長輩“講述”的信賴。我一直認為故事的精要部分——極富藝術性的情節段落,一定是在講述中完成的。情緒慢慢疊加,回憶撲面而來,與生人對壘,和亡者為伍,發自肺腑,經由喉嚨,然后化作音符,噴涌出口,成為不可更易的鋼與鐵。相比之下,摳搜、推敲、琢磨出來的東西,就顯得虛浮。這是我寫小說時所遵循的理念。
當然,我的“講述”不一定是故事中人物的“口述”,它也可以是心理活動的展現,或稱之“心述”。正如羅恩·拉什在短篇小說《艱難時世》結尾處所描述的,一切歸于平靜,不再有話語。雅各布試圖睡一個回籠覺,入睡時他還在幻想一個比他所在的地方更糟糕的地方。這就是力量,沉默的力量。但話語消失了嗎?正相反,話語在沒有被“脫口而出”時才最有力量。在這里,講述并未停止,它沉入心臟和靈魂,依然絮絮不休。
在講述中抵達真實人性的幽微一面,是我要追求的。講述只是一種手段、一條路、一架橋,我要經由它到達虛構的彼岸,那是人跡罕至的所在,卻又無時無刻不充斥著人嘈雜的話語。在講述中,黃小玉所牽掛的香蕉樹,以及香蕉樹所代表的南方,已經變成一個概念性的東西。包括張劍武,也包括蟑螂、炎熱、暴雨等,這些東西統攝在“香蕉樹”之下,成為她的矛與盾,用來對抗原生家庭的“壓迫”。黃小玉曾經有很多盟友來幫助她完成這種逃離或反抗。先是寧寧、張劍武,后是那幾棵親手種下的香蕉樹,但根本上是深圳這座城市給了她勇氣和力量。她想要留在這里,這種愿望無比正當,卻難以說出口。因為她還有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主要是對她的母親。在逃離繼父的同時,她也逃離了她的母親。這是她始終緘默,需要將自己與外在事物捆綁在一起的原因。
既然是講述,就要通過人物之口娓娓道來,因而有些東西也無法避免。一是敘述情緒的波蕩,二是人物發自私心的諱言。關于前者,我的情緒是豐沛激昂的,以期在某些關鍵段落能與敘述者的感情相呼應。這也導致小說中出現了很多“情感泛濫”的詞句,它們的表達或許不夠節制,但我想為自己辯白幾句:這樣寫是否更契合敘述者的身份?她畢竟是一位四十九歲罹患癌癥的中年婦女,而非一個二十四歲的小伙子。關于后者,所謂諱言并非難以啟齒,而是沒有說的必要與心思。小說畢竟是在講述,有講述者與傾聽者。考慮到二人的身份以及敘述的時機和地點,有些話是說不出口的。比如主人公十八九歲時的逃離,究竟出于怎樣的動機?她多年未曾回返家鄉,是否真的下定了永不回去的決心?她對繼父是否存有一點兒感激?和張劍武在一起,真的只是因為他曾用摩托車載她去看過一次香蕉樹嗎?她對張劍武有沒有愛?諸如此類的問題。我想我不寫滿,是有好處的。威廉·特雷弗說過,小說的力量在于其隱藏的東西和它所展現的東西一樣多,甚至更多。適當的隱藏,是我近兩年學到的最實用的創作技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