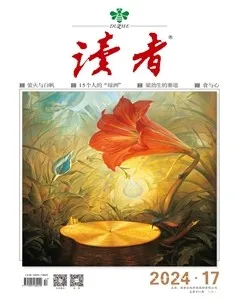“如魚離水”的農村名校生

一個從農村考入名校的孩子會經歷什么?在他的人生出現轉折的4年后或10年后,情況又會是怎樣的呢?
近兩年,農村名校生在互聯網上受到不少關注,類似的問題被反復提及。可公眾的討論大多基于對這個群體的標簽化特征和刻板印象,例如,他們更擅長答題,但缺乏開闊的視野。
在這種偏見之外,“農村名校生”的身份在一個個具體的生命歷程中,到底意味著什么?他們如何體驗和認識自己人生轉折的意義?他們在想什么?他們又有哪些獨特的收獲?
為了找到以上答案,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謝愛磊,結合自身的經驗和反思,專門做了一項長達10年的調查,深度追蹤了上海、廣州、武漢與南京的4所“雙一流”高校里的近2000名學生,并將采訪與研究成果匯成了專著《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態與象牙塔》。
在這些受訪學生中,有家庭年收入兩三萬元、從農村考入一線城市精英學府后依然勤奮讀書的孩子,也有父母務農、進入大學后發現自己幾乎喪失學習興趣并感覺前途迷茫的孩子,還有感覺童年生活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孩子……他們時常在精英大學的環境里感到“失落”與“匱乏”。
類似的經歷,謝愛磊自己也經歷過。他是從安徽農村一步步考出來的名校生。
作為從這條路徑里走出來的極少數幸運兒,如今已是教授的他,在十余年的調查和研究中發現,教育是改變農村孩子命運的重要路徑,但這條路很不容易走。
在謝愛磊看來,外界對于農村名校生擅長應試的偏見,包含一種特別的隱喻。這不僅指在從中學到重點大學的適應過程中,固有的機械式學習訓練與新環境中多元認知之間的錯位和沖突,而且指一種社會流動中稍顯沉重的生存心態和情感代價。
如魚離水
謝愛磊的思考是從自己開始的。
高考那年,謝愛磊是當地省重點中學的文科第一名,按照他的成績可以上全國最頂尖的大學。但在他當時的認知里,因為家境不富裕,認為自己應該去上有學費補貼的師范類院校,于是他填報了華東師范大學。
上海對謝愛磊而言也是另一個世界。他驚訝于學校里的每一寸路面都鋪上了地磚,宿舍比自己家還漂亮。他第一次知道,打羽毛球的場地是可以有球網的。
入學后,謝愛磊花了一段時間去確認“我是誰”。他發現,一些從小地方來的同學,和他一樣,腳上穿的是布鞋,與此同時,從大城市來的同學更習慣穿運動鞋。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謝愛磊感覺,自己過去的認知正在被消解和陌生化。他所熟悉的課余休閑活動,比如在稻田里抓泥鰍,在新的世界里無緣存在。他也觀察著與自己同在一所學校的“別人家的孩子”,他們會彈鋼琴、跳舞,而這些謝愛磊都沒接觸過。他讀的是英語專業,但倫敦與巴黎、莎士比亞和歌劇,這些都離他太遠了。
對于這種現象,謝愛磊化用了一個成語“如魚離水”來解釋:“我們長期在一種文化中長大,離開這片文化水域之前,便如魚兒意識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離開水,陌生感和窒息感就隨之而來。”
具有農村和小鎮背景的孩子,憑借著在學校里不停地刷題來考取更高的分數,以此朝著廣闊的環境和更大的平臺前進,卻在真正抵達那個世界后,發現自己似乎并不擅長游泳。在文化積累、生活習慣、興趣愛好與見識等方面,他們都感受到難以忽視的割裂感與陌生感。
“一個人的童年就是一種社會建構”,父母的認知、文化投資都是完成這種建構的重要條件。譬如定期旅游、參加夏令營、參觀博物館、欣賞音樂會,但它們的效用,要到進入大學后通過與其他同學的對比才能體現出來。
謝愛磊采訪的不少學生向他反映,他們從農村到大學后,有一種“失去坐標”的感覺。課余空閑時間一下子多出了太多,他們找不到地方可去,沒有事情可做。新環境不再看重做題和應試技巧,舊的生存法則與心態忽然失效或失蹤了。
中學與大學之間出現了斷層。成績是他們進入學校的唯一入場券,他們本以為,像人生前十幾年那樣一步步積攢分數,就可以沿著既定的階梯一步步往上走,哪怕流汗也感到踏實。
可等緊握那張浸滿汗水的入場券進去后,他們也許會發現,身邊有不少同儕都手握不止一張入場券。在后者眼前鋪展開來的,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曠野,而非用“一心只讀圣賢書”鋪成的唯一軌道。
謝愛磊借由沃爾夫岡·萊曼的觀點闡述:“社會流動、跨越社會階層通常意味著建立新的自我認同,否定舊的自我,并會因此減少與過去的聯系。”
不過,謝愛磊認為,這種對環境的敏銳覺知,會促使和他一樣的農村孩子更多地追問自我,反躬自問“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而這種適應過程是必要的,這是大學功能的一部分——幫助一個剛成年的孩子適應真實的世界。
做題機器人
謝愛磊反復強調,“農村孩子是依賴考試進入大城市的,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更擅長考試”。“事實恰恰是,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依賴,這部分學生其實更難通過純粹的刷題改變命運。”
10年前,謝愛磊剛開始做調查時,很多從農村來的學生把自己形容為“做題機器人”,“機器人”這個詞語強調的是被迫和持續的狀態。但一句反問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消解這一群體的“優勢”:“別的孩子也是通過考試進入名牌大學的,他們怎么可能在答題上不如我們?”
“所謂的‘更擅長’也許只是一個機遇問題。”謝愛磊說,自己念小學時,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是通過考試升級的,很多小伙伴因為只差一點分數便無法升級。“所以我不覺得我比同輩更聰明,只是多了一點幸運。”
謝愛磊認為,精英家庭的孩子所表現出來的“毫不費力”,背后有著無數看不見的鋪墊和助力。
他察覺到這些年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在變動。比如,在他念書的那個年代,十分強調個人努力。“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就是崇尚用功,只要你用功,哪怕你資質平庸,你也是值得贊頌的,你也可以被大家喜歡。”但如今,社會似乎更強調“松弛感”,一個優秀的人取得成果最好表面上是“毫不費力”的。謝愛磊覺得,這種對“毫不費力”的崇尚,背后更多是一種天賦論,“但天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被社會建構的”。
過去的人生和成長經歷,勢必在一個人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跡,而教育并不是要抹去這些痕跡,更不是要用成功學的標準替代個人價值。真正的教育所追求的,是在保存這些痕跡的同時,讓他們建立起新的自我認同和價值感。
謝愛磊認為,好的教育,“是在孩子走進世界以后,幫助他反觀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所在的世界,讓他能夠從另外的意義上肯定過往”。過去的人生能給予一個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養分,而非成為他實現自我價值的枷鎖,這是教育的終極使命之一。
讓“公平”前置一些
如今,謝愛磊既從事科研工作,也承擔教學任務。他發現,很多學生到了大學,仍然延續著中學的學習和生活模式。比如,他們從來不主動找老師,也不認為老師有義務且能夠解答學生的成長困惑。
“進入高校以后,對這部分學生來講,人生的確定性在于學業領域,不確定性則在于非學業領域。但由于對確定性的部分依賴太多,他們往往不敢邁出第一步,去追求那些不確定的事物。”
但他一再強調,在他的故事版本里,他也看到了改變,沒有誰是一成不變的。例如,隨著來自小鎮和農村的孩子慢慢適應大學生活,他們也會逐漸地參加各種學生活動。他發現他們參加公益類團體活動的頻率,要高于參加學生會這類組織的,“他們對于自己想要什么有一些獨特的思考”。
但對今天不少從小地方出來的學生而言,“如何讀大學”依然是個難題。剛結束高考,放下習題,新的難題就迎面而至,而在大學中的生活、人際關系、社會適應等議題,它們的影響甚至會持續終身。
我們是否可以嘗試在中學與大學之間,有一種過渡性的學習和培訓?謝愛磊期待出現一種模式,譬如中學與高校合作,教學生如何讀大學。如果有這樣一種培訓,“第一步應該是告訴學生,你需要一直思考自己的目標是什么,需要思考大學的學業、生活和這些目標是什么樣的關系,再把大學的學業和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告訴學生”。
“現在很多大學與中學對接,但出發點是品牌推廣,目的是爭搶好生源。”謝愛磊說,“但我們能否從更加公平的角度出發去做一件事?”他感覺到,時代發展到今天,“效率”與“公平”的天平其實應該向后者傾斜。“我們或許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追求效率,但在今天,種種跡象表明,教育公平被放到了很靠前的位置。”
課堂上,謝愛磊說:“你們將來可能成為社會的精英,但要警惕桑德爾所說的‘優績主義’陷阱。我今天所擁有的幸運生活,可能是以另外一個人的曲折經歷為代價的。如果說,在你們的認知地圖里沒有另外一個群體,那么當你們做決策的時候,這些人就會受到影響。”
(晚芝摘自《南風窗》2024年第13期,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