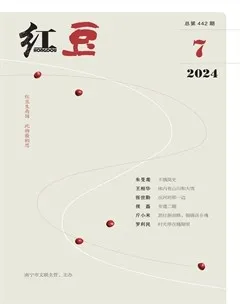豆棚瓜架記
菜花
婺源的菜花其實無甚特色,花田萬畝,多而已,人往客來,眾而已。就像張岱筆下的《西湖七月半》:“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看婺源花也是如此。我輩同道看花的四個人,該歸屬于哪一類?大約是也看花、也看看花之人、也被看花人看之列吧。
從未去過,跑錯了地方,向路邊老奶奶一打聽,才知道婺源菜花最艷處在江嶺,我們?nèi)サ膮s是曉起。曉起就曉起吧,也并不求花多,一萬枝是春色,一枝也是春色。
人生逆旅,多是于陰差陽錯之中尋求片刻的歡欣與安寧,余下的,識味、辨味、知味、嘗味而已,別無其他。
既然奔波四五百公里,來了總得做做看花的樣子。何況春風(fēng)駘蕩,柳色青青,粉墻黛瓦,桃傍籬開,加上寶馬香車,如云似水,妖童冶女,笑啼雜之,婺源的菜花實在是好看的,是很香的,看花的麗人也實在是很好看的,是香的。
我們在花田里作姿擺勢,拍了一張又一張,自以為張張好看,片片精彩,稍一忘形就跌了一跤,半邊褲腿全是黑泥。那泥仍然是香的,是好看的。
遠(yuǎn)游的妙處不在花,不在人,不在野游本身,而在于扯開了塵網(wǎng),掙脫掉樊籬,暫時做得了一個假隱士。
天地何其空闊,人間何其漠漠!我不識人,人也不識我。我無意識人,人也無意識我。可以扮雅士,可以爆粗口,可以長歌當(dāng)哭,可以泣涕雙行,可以往熱鬧中尋小小樂子,可以坐在花田之間兀自寂寞,可以于人海中學(xué)劉姥姥簪花滿頭,可以于野林無人處迎風(fēng)撒尿。我是我,我亦非我,快意何如之!
落腳在草徑盡頭一戶張姓人家的小客棧。運氣實在是太好了,才蓋的新房子,我等竟然是第一批住客,床單、被子、電視機、洗浴器具、茶壺、花布簾子之類全是簇新的。偷著樂。待到打開窗,望見平疇沃野數(shù)十里內(nèi),油菜花在春風(fēng)中如平湖風(fēng)波,起伏搖蕩,馥郁花香一浪接一浪紛涌而入,到底禁不住矜持,狂喜以至手之舞之了。
唯一的遺憾,是這田園小棧的主人比不得舊式名士,小棧也比不得徽派建筑的古雅風(fēng)致。主人太俗,為幾兩紋銀的房價喁喁復(fù)喋喋,掙了不算少的房錢、飯錢、茶錢、酒錢、小吃錢,仍不知足。俗也就罷了,又端著架子,再三聲明他是讀過不少圣賢書的風(fēng)雅人,是某某文化部門退下來的官員。
不管他,只管叉腿擺臂高坐人家軒堂之上,拍出幾張大錢來,把人家的廚娘左支右使繞著鍋臺團團轉(zhuǎn)。“有特色的菜,盡管上來!”酒菜不錯,有色有香有味,自然不算便宜,可也不是特別貴。四個人圍著大大的八仙桌,東西南北方各霸一面,吃菜花嫩蕊,喝婺源紅土燒,學(xué)那綠林好漢,捋袖袒腹,放馬轟飲。
然后趁著酒興與月色,東倒西歪,再去門前花田小徑上胡亂走上一遭,惹一身花粉和月光。我對菜花和月色說:“花兒,月兒,我總算不負(fù)卿。”
忽然想起白日里逛江灣古街,遇見一樹上好的梨花,正打算拍照片,一個拄拐長須老者忽然顫巍巍地殺將過來,像嚴(yán)監(jiān)生再世,固執(zhí)地?fù)u著兩根蒼黑的指頭,啞啞斥曰:“二十塊一張,一張二十塊!”意思是不準(zhǔn)白拍,拍一張照片收二十塊錢。也罷,也罷,梨花勝雪,雪厭梨花,我遠(yuǎn)遠(yuǎn)地打望一眼,總是可以的吧。
吾鄉(xiāng)岳西人家從前也種油菜,家家戶戶都種,春日菜花澄黃,也是滿山滿灣,當(dāng)年無人看花。鄉(xiāng)人中意的只是菜籽,以及菜籽壓榨出來的香油。
現(xiàn)在總算有人看了,可是肯在田地里下力氣的人家不多了,菜花寥落,不成風(fēng)情。好些鄉(xiāng)人似我這般跑老遠(yuǎn)去人家那里看,喝一肚子異鄉(xiāng)的風(fēng)。吾鄉(xiāng)人家還是不要刻意種了吧,黃了菜花,綠了眼睛。
葫蘆
從江西婺源帶回幾只小葫蘆,瑩潤澄黃,盈盈一握,渾樸可喜,甚為寶愛。生平見過的葫蘆也不算少了,似這種袖珍型小葫蘆還是第一次遇見。不知是江西特產(chǎn),還是他鄉(xiāng)方物輾轉(zhuǎn)流浪到那里。
回來后偷閑摩挲那些小葫蘆,搖一搖,聽種子在葫蘆里沙沙作響,心里總是癢癢的,幾次想打開一只倒出種子種在花盆里。私下盤算,假如一根藤上結(jié)一百只,五塊錢一只,可賣得五百大洋;假如種十棵,那將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
到底舍不得,掌中物件玩味久了,就有些通靈的意思了,親手破壞掉總是不忍。某天一個兄弟財迷心竅,趁我不注意,抓起一只就用螺絲刀在葫蘆底部鉆出一個小洞,倒出幾十粒種子。然后和我均分,商定各自回家撒到土里,等到發(fā)芽結(jié)果收獲了,一起去夜市擺攤。
我把種子撒在一只裝有泥土的木盒子里。起先幾天還著意呵護著,后來漸漸疏忽了,終于連盒子都不知去向,種子是否發(fā)芽也就不得而知了。那個兄弟說他的葫蘆種子出了苗,大有開花結(jié)果的希望。人世間的事紛亂如麻,誰有閑心一直惦記著葫蘆種子呢?倒是窗臺上那只被掏空了種子又破了相的葫蘆,像不貞之人一樣,被我冷落,以至于最后全然遺棄了。
其他的幾只,送給孩子一只,桐城文友要去一只,不翼而飛了一只,只剩下作為掛件掛在車子里的兩只,伴著一個笑口常開的小小彌勒佛,晃來蕩去地伴著我的人生逆旅。我一直在等待一個好刀手,給這兩只僅存的葫蘆刻幾個字,一個刻“乾坤”,一個鐫“糊涂”。
每一只葫蘆,不管是大葫蘆還是小葫蘆,也不管是用來吃的還是用來玩的,都是一個乾坤,是一個自我閉鎖又自我完足的世界,所謂“一壺一乾坤”“乾坤一壺收”。葫蘆又像大肚子羅漢,外表圓融而內(nèi)心闊大,恰好又與糊涂諧音,頗有鄭板橋那句著名智語的意味。
然而天下多的是糊涂人,一生大多是一筆糊涂賬,不僅他人不能“難得糊涂”,恐怕連鄭板橋自己也不能把握好糊涂與清醒之間的度吧:作畫,雅極;鬻畫,俗極。鄭板橋以畫為志趣和生計,在雅俗之間擺渡,焉知他不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他在山東濰縣知縣任上,因請賑災(zāi)民忤逆大吏,最后只好卷起鋪蓋回鄉(xiāng),即是明證。不過,鄭板橋畫的竹子確實好看,節(jié)是節(jié),骨是骨,一點兒也不糊涂;他的字確實好看,也如筆下的竹,骨骨節(jié)節(jié),一點兒也不糊涂;他的文章也和字畫一樣,確實好看,骨干疏朗,氣格清雄,也一點兒都不糊涂。一如架子上的青葫蘆,清通脫俗,寶相莊嚴(yán),我尤其喜歡。
“乾坤”與“糊涂”,自勉加自嘲而已。一個人要是真能如葫蘆這般,既肚收乾坤又賦之以糊涂之形,那就是鐵拐李了,不位列仙班,至少也名在林泉。塵世多喧鬧,不宜多談玄,還是說說葫蘆吧。
父母從前是種葫蘆的,一季三五棵,種在屋側(cè)庭前,那是我年少時的事了。種的都是常見的那種大葫蘆,主要用處是制作舀水的葫蘆瓢。
舊時鄉(xiāng)下,家家廚房拐角里都有一口可以兼作磨刀石的粗陶大水缸。半截埋在土里,取其沁涼,當(dāng)然也有接地氣的意思。水缸里漂著一只黃而老的葫蘆瓢,用水時,抓起瓢就舀。鍋臺上也有一兩只,型號略有差別,用處也略有不同。那些葫蘆瓢都是用老透了的秋葫蘆制作的。
我見過父親鋸葫蘆瓢。把收獲的干透的有長相的老葫蘆拿來,用墨斗彈出中分線,然后用鋸子沿線齊整鋸開,掏空內(nèi)瓤就成了瓢。一鋸得二瓢,工藝很簡單,但鋸工要好,否則鋸路歪七歪八,瓢就難看。我也見過母親縫過葫蘆瓢。葫蘆瓢耐用,一只用三五年不成問題,但不小心就會摔出裂縫,漏水,用縫衣針一針一線費力地縫合起來,還可繼續(xù)用上兩三載。鄉(xiāng)下人家的薄產(chǎn),都是這樣一厘一毫一針一線積攢下來的。
嫩葫蘆是一味好菜,尤其是刮了皮做湯,放蛋花蔥葉,味道極鮮美,就面食吃更得味。只是從前父母舍不得吃,家里種的葫蘆,除留下做瓢用的,都趁其鮮嫩摘下來,送到農(nóng)貿(mào)市場當(dāng)菜賣了。
老葫蘆籽的味道也甚佳。我以為在所有的瓜子中,數(shù)葫蘆籽的味道最為上乘,其形色也俱佳。古人形容美人的牙齒,譽之為“齒如瓠犀”,瓠犀也就是瓠瓜的籽。其實葫蘆的籽,無論是色澤之瑩白,還是排列之整飭,都與瓠瓜沒有兩樣。
幾間瓦屋,土而老,一臉歲月,但只要庭前種有一架葫蘆,綠葉層層疊蓋,隨風(fēng)如書頁翻飛,數(shù)十只碧色葫蘆在藤下靜靜低垂,就有風(fēng)雅處士之風(fēng),也讓人想起“靜女其姝”。
蘿卜
在小飯館里吃到一味蘿卜煨豬肉。蘿卜切成半寸厚的墩子,大塊的方肉半精連著半肥,在火鍋里咕嘟嘟煨煮一通后,蘿卜里有了肉味,肉里有了蘿卜味,極合胃口。不覺吞飯三大碗,轆轆饑腸得以安妥,冬日寒苦減了七八分,皺巴巴的眉眼也舒展了許多。于是念起蘿卜的好來。
念起蘿卜來,就自然地想起一首童謠:“蘿卜蘿卜纓子,某某是我孫子;蘿卜蘿卜杪子,我是某某老子。”髫年時期,岳西鄉(xiāng)間流傳著不少小孩子就地取材自創(chuàng)的童謠,如今多已忘記,這一首《蘿卜纓子》卻記得十分清晰。因為有趣而繞口,念得不好,不是自己成了人家的孫子,就是人家成了自己的老子,惹人哄笑。還因為極合用,可以把“某某”換成任何一個人的名字,群起而攻之,翻來覆去地罵,聽起來像唱歌似的。
舊時鄉(xiāng)野之人雖然鄙俗,卻并不流行國罵,稱自己是別人的老子或娘,已經(jīng)是很侮辱人的了。遇到弱的,對方啼號一番也就罷了。若是遇到強狠的,非得干起架來,不打個頭破血流難收兵。
似乎是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末,有人發(fā)明了“蘿卜賽水果”這一說法,而且很風(fēng)行。蘿卜是很有營養(yǎng),富含這酸那素的,但是否賽過水果,畢竟是值得商榷的。吾鄉(xiāng)幾乎不產(chǎn)水果,偶爾能見到寥寥幾樹澀棗和酸梨、數(shù)棵品相和口味都很劣的葡萄,西瓜、蘋果、雪梨、柑橘、香蕉、龍眼、荔枝這些一概沒有。其時街市上也有賣西瓜、蘋果、梨子、橘子的,專供城里的闊人,鄉(xiāng)野之人除非家中來客,或走親訪友,否則無緣無故是不敢問津的。所以有水果吃,乃至吃過水果,對孩童而言都是件頗為榮耀的事。
記得有一年母親咳嗽一個多月,仍然不見好。在醫(yī)生的叮嚀下,才狠心買了三只黃梨,用來燉冰糖黃梨水止咳。梨子放在手提篾籃子里,原本是用包頭巾蓋著的,不料被西北風(fēng)掀起一角,露出里面的奇珍來,于是七八個拖著鼻涕的孩子,嘴角流著涎水,可憐巴巴地跟著母親,從半里外的菜園地一直跟到屋里來。母親無奈,只好一人切一塊比撲克牌厚不了多少的薄片,才將一班饞蟲打發(fā)出去。
蘿卜是有吃的,秋冬的田里地里到處都是,誰要是想吃,無論到哪家田地里都可以隨手拔幾個,用衣襟擦擦泥,蹲在田地邊上啃得滿地蘿卜皮都沒有人過問,更不會索賠。所以我以為,在當(dāng)時第一個說“蘿卜賽水果”這話的人,不是吃厭了水果的人,就是無水果可吃的人。前者略似于“何不食肉糜”的司馬衷,后者則好比是未莊的阿Q。
吾鄉(xiāng)原只有白蘿卜、紅蘿卜,胡蘿卜的引進種植是后來的事。青蘿卜和水果蘿卜至今依然是外運。白蘿卜當(dāng)然有很多品種,最好吃的莫過于那種圓滾滾的土著品種“春不老”,生吃脆而甜,熟吃甜而軟。那種后來引進的吾鄉(xiāng)人稱之為“系馬樁”的蘿卜,長粗滾圓幾可系馬,產(chǎn)量高,但味道畢竟遜色了許多,只適合喂豬。當(dāng)然要秋冬的蘿卜才可口,夏蘿卜類似木頭,無論生食熟食都干澀辛辣得難以下咽。最好吃的則一定是經(jīng)霜過后,蘿卜纓子被凍得蔫頭耷腦,埋在土里的蘿卜卻如雪梨一般,鮮甜又脆爽,咬一口,口舌津津然。
七八歲的時候,寒冬的禮拜天也不得閑,要上山砍柴。我記得有一天正午時分,我和只比我“小一蘿卜皮”的發(fā)小兒國輝,各自背一捆柴趔趄著往家里趕,既渴且餓。恰巧在半山坡上望見一塊蘿卜地,土被凍得蓬松起來,蘿卜有一半露在土面上。于是兩人放下柴捆,就地一屁股坐到地溝里,拔起蘿卜用袖子揩揩泥張嘴就啃。直到啃得地溝里全是白生生的蘿卜皮,半個臉沾滿泥巴和蘿卜碎屑,連打嗝兒都是蘿卜味,才滿意而罷休。那味道今日想來,恰如清人吳其浚在《植物名實圖考》中所言,“瓊瑤一片,嚼如冷雪”,當(dāng)真比水果美妙多了。冬陽下笑嘻嘻相對而坐,舉蘿卜咔嚓大嚼,也成為我和國輝的人生典故,此后相遇,每每提及。
蘿卜是賤物,即使在鄉(xiāng)野也是待客菜中的陪襯。幼稚時村莊里所有人家一樣窮,秋冬餐桌上幾乎餐餐有炒蘿卜、煮蘿卜、煨蘿卜、腌蘿卜。因為連油星子也難以覓到幾點,吃多了,聞到蘿卜的味道就皺眉頭,胃里就泛酸水。但若是在蘿卜里加幾片肉,則另當(dāng)別論,哪怕是加幾塊肥肉片也是好的,可惜父母難得慷慨一回。
祖父生前,吃飯時經(jīng)常說一句話:“肉是好東西,哪怕是干稻草,加兩片肉炒也吃得下去。”大約是出身使然,我至今仍然認(rèn)為,豬肉燒蘿卜是人間大味。
月亮菜
扁豆扁扁彎彎,像初七八的明月,鄉(xiāng)人們因之叫它月亮菜,其本名倒被忽略了。我也這樣叫了許多年,后來查了《植物圖鑒》才知道月亮菜就是扁豆。月亮菜這個名字好,好在比它的本名形象生動,也更富有情調(diào)。
月亮菜和絲瓜、南瓜一樣,都是極好種的。在角角落落里隨便點一棵,施夠肥,從此不用管它,風(fēng)一吹,自會藤藤蔓蔓,攀籬掛壁,牽延無窮盡。花期和結(jié)果期又很長,從夏初到秋末,瓜瓞綿綿,跨度差不多是兩個季節(jié),是懶漢惰婦都能種好的菜蔬。農(nóng)家一年到頭都忙,耘田耕地回來,尤其是早上和中午,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精心烹制菜肴,月亮菜正好幫上了大忙。柴已經(jīng)點燃,鍋已經(jīng)燒熱,主婦不慌不忙走到月亮菜藤架下,摘下一把,掐頭去尾,放在砧板上切絲或切片,推到鍋里爆炒,三兩下就是一碗脆碧清香的好菜。所以在木瓜沖里,家家種月亮菜。
鄉(xiāng)鄰們種月亮菜,多是三兩棵,我的父母卻是用大田搭架子種一大片。夏秋時節(jié),每天下午三四點鐘,他們就拎著籃子去摘菜,盛產(chǎn)期往往要摘到天黑,第二天拿到農(nóng)貿(mào)市場零星散賣。月亮菜剛上市時,能賣到四五塊錢一斤,后來賣到兩塊左右。一季下來,也有幾千塊錢的收入,只是辛苦得很。有二十年了吧,父母一直靠種菜維持生計,父親會種,母親會賣,小城飯店酒樓的采買以及家庭主婦,都喜歡父母種的菜腌的菜。在飯店吃飯,老板娘有時會跟我說:“你是木瓜沖種菜的老儲家的兒子吧?你家的菜好。”我聽了,便覺得欣喜。
自夏天至秋天,飯桌上總有月亮菜。有時與紅辣椒切絲爆炒,夾一筷子擱在飯頭上,紅配綠,看不足,清香若隱若現(xiàn),勾人食欲。有時與青辣椒切成片,炒后清燉,軟糯得很,佐飯頗佳。那燉出來的月亮菜湯,用來煮飯或者泡鍋巴,滋味更是上乘。
月亮菜肯定還有很多種做法,只是不為我所知。母親是個實誠人,做菜不會變花樣,幾十年如一日,做月亮菜不是切絲就是切片,而且必然與辣椒相配,從沒有把月亮菜做出東坡肘子味道的念頭。
懶散如我,更是二十幾年沒有燒過飯,什么菜都不會做。母親燒的菜是地道的山間農(nóng)家風(fēng)味,對我來說,更是家的味道,在家里吃飯,總會吃得飽才肯罷休。
有一年秋天,我去岳西西邊一個叫河圖的鄉(xiāng)鎮(zhèn)公干,長了些見識。在鄉(xiāng)鎮(zhèn)食堂里的餐桌上,擺著三只火鍋,其中一只火鍋名曰“月亮菜煨毛魚”。月亮菜本來是不適宜煨的,因為容易煨爛。而毛魚,在我的認(rèn)知里,更是極忌諱水煮,一沾水就腥得讓人捂鼻子,通常是油炸了拌辣椒粉,或者與青辣椒一起炸了上桌。可是那個地方,偏偏有這道“月亮菜煨毛魚”,而且還是當(dāng)?shù)孛恕Uf實在話,一進食堂門,那腥味就熏得我胃里酸水澎湃。及至坐到桌上,更不敢朝那道名菜下箸。見到當(dāng)?shù)厝顺缘媒蚪蛴形叮胰滩蛔⊥低蛋櫭碱^。
三里不同風(fēng),五里不同俗,我當(dāng)時真是很佩服河圖人這般茹腥嗜爛的勇氣,當(dāng)然,也佩服他們在飲食方面的創(chuàng)新精神。
月亮菜在鄉(xiāng)下隨處可見,城里住火柴盒子的普通人家,自然是沒有地方可種,但人的創(chuàng)新精神無處不在。以前住的房子附近,三樓有一戶人家,某一年就在陽臺上種了一棵,青翠的藤條爬滿了他們家的鐵質(zhì)防盜窗,硬是把只有鄉(xiāng)間才有的“滿架秋風(fēng)扁豆花”的景致,搬到了城里來。
我坐在自己家中,見他們家那滿窗綠藤上,一只只碧瑩瑩的小月亮在陽光或者月色下泛著銀光,很是羨慕。記得我曾專門為那棵月亮菜寫了篇文章,名字叫《一千只月亮掛在藤上》。我還記得冬初的時候,藤蔓已經(jīng)枯萎,還有些干癟的月亮菜莢,大約是留作種子的緣故,沒有摘下來,靜夜里北風(fēng)一吹,菜莢紛紛搖動,齊齊吟唱,有風(fēng)鈴的生動韻致。
【作者簡介】儲勁松,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作品散見于《天涯》《山花》《青年文學(xué)》《紅豆》等刊,著有《在江湖與廟堂之間:貶謫中的宋代文人》《雪夜閑書》《草木樸素》《黑夜筆記》《書魚記:漫談中國志怪小說·野史與其他》等作品多部。
責(zé)任編輯 藍(lán)雅萍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