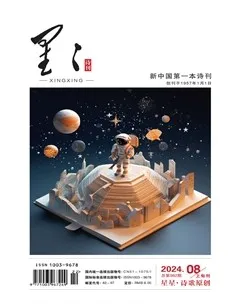大師的肖像(二首)
2024-08-20 00:00:00李東海
星星·詩歌原創 2024年8期
詩人波德萊爾
詩人波德萊爾
走在詩歌的憂巷里
苦悶時,就用耳朵看書
用眼睛去聞巴黎的腐臭
象征和通感
是他手中最得意的家什
像《惡之花》和《巴黎的憂郁》
都是他孤獨憂郁的苦難表征
于是,象征派和整個現代派
都從他的手中涌流而出
波德萊爾無窮燦爛的智慧
非常茂盛地生長在他
寬厚無比的額頭地帶
他把文學和藝術的冥思苦想
沉重地堆放在他那
眼瞼以上,只要他的炯目一閃
那些模糊穩定的語言
及其象征的森林
就會像玉珠一樣
滾落下來
艾略特的時光
——獻給T·S艾略特
走過哈佛
來到巴黎和倫敦
玳瑁眼鏡的艾略特
斯斯文文
艾略特是個有身份的人
羈絆在哲學與詩歌的夢里
被微微安的小手,牽絆得搖搖晃晃
于是,龐德伸過一雙大手
把這窘迫漂亮的男人拉上了河岸
大不列顛的夜空,突然亮起了一道星光
艾略特吟唱《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時候
是優雅的琴師
可是歐洲正在沉淪,龐德正在寫詩
荒原吞噬著歐羅巴的叢林和孩子
玳瑁眼鏡的艾略特
奮筆寫下炸裂的《荒原》
可四月,依然讓春天發臭
讓歐洲在茫茫的荒原
一槍斃命
《四個四重奏》
終于從《金枝》里找到了舊約的圣杯
找到長矛的尖刺
諾頓的莊園,閃爍著永恒的黃金
1948年
艾略特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
神情自若,衣冠楚楚
那天的歐洲,溫暖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