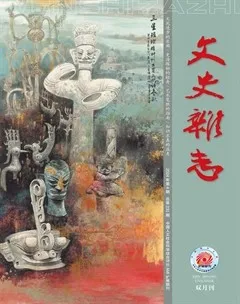呂林版畫創作與川渝畫像磚形式的融合
摘 要:呂林的版畫創作是結合畫像磚藝術形式表現的重要內容。他用“在傳統中找尋藝術”的實踐方式,為川渝版畫發展提供了一條關鍵線索和特殊發展的路徑,是具有民族形式感與時代感的藝術典范。他充分吸收了川渝畫像磚在圖像的構成空間、繪畫造型以及繪畫技法中所包括的平鋪式、分隔式和符號化的繪畫特點,而又有所創新,為川渝版畫的振興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關鍵詞:入蜀;語言互通;符號化
一、入蜀方知畫意濃
著名畫家黃賓虹曾言:“潑墨山前遠近峰,米家難點萬千重。青城坐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畫意濃。”[1]詩句描繪的正是四川成都清麗秀美之象,且重點突出了巴蜀之地濃郁的藝術氛圍。縱觀巴蜀藝術的發展歷程,自五代后蜀時,黃荃父子便首創皇家富貴之氣象,不但活躍了繪畫藝術的氛圍,而且促進巴蜀繪畫的發展。唐朝時期,由于四川地區政局穩定,經濟繁榮,加之地方官員重視繪畫,不僅培養了一批如梁令瓚一樣的本土畫家,還吸引了眾多中原地區的畫家入蜀,如吳道子、張璪、李思訓、盧楞伽等。宋朝及以后,巴蜀美術也一度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各擅其長。在全民族抗戰的8年間,巴蜀美術界更是云集了全國的精英。中國畫壇掀起了一股入蜀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30年里,還有不少畫家相繼入蜀。他們在川渝開創的畫風深深影響著中國美術的格局。
呂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入蜀畫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呂林于1920年出生在山西吉縣。他的藝術生涯起源于1938年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時期,其時便展現出極高的藝術天賦。當時他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從事美術創作,并在學校主辦的《先鋒》雜志上發表了自己第一幅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版畫作品——《敵機轟炸后》。1940年他奔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深造。在這一時期他成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參與者。“延安魯藝”的藝術思想和創作方法造就了呂林早期的藝術探索與繪畫實踐脈絡。1945年至1948年,呂林在晉綏軍區政治部和120師獨一旅戰斗劇社任宣傳干事。在此期間,他不僅編演了大量的文藝宣傳節目,也創作了很多木刻版畫和連環畫。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版畫《馬尸掩體》、木刻連環畫《紀利子》、油畫《巷戰》等。[2]這些作品都具有濃郁的傳統中國風格。他善于運用鮮明的線條和對比色,刻畫出豐富動人的形象。他在作品中注重細節的表現,通過精確的線條和細膩的陰影來刻畫人物的表情和神態,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充滿藝術感染力。這些都體現了他早期的版畫創作方法與藝術思考。
解放戰爭時期,呂林隨軍南下,先后參與創建西北軍政大學美術系和西南人民藝術學院美術系。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長期旅居巴蜀,并擔任西南人民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西南美協副主席。在這期間他開始關注四川地區的畫像磚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對巴蜀藝術逐漸深入的了解下,通過觀察、體悟畫像磚夸張的造型、古拙奇特的風格,又通過系統地研究、拓印和圖像整理,提煉出漢代畫像磚造型藝術形式的特征,并嘗試將川渝畫像磚的形式、語言與中國現代版畫創作相結合,然后運用到版畫藝術的創作中去。他由此逐漸創立出獨特的個人版畫語言,終至達到了個人版畫藝術創作的高峰期。他在川渝地區創作的代表性版畫作品有《桑園》《春》《梨園管理》等。他為中國版畫語言開創出一種非常奇特的繪畫風格。其版畫藝術創作不僅折射出自身的藝術主張,更展現了他的藝術思想的自覺。
實際上最早提出將畫像磚與版畫創作相結合的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致李樺的信中說:“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圖,并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也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3]而呂林是國內第一位將這種觀念付諸實施的藝術家。
二、版畫與畫像磚形式語言的互通
呂林的版畫相比于同時期的版畫具有很多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東西。這使得它區別于同時期普遍性的題材和表現方式,而這個區別最重要的體現在形式語言上。例如,呂林版畫在構圖空間的平鋪直敘化、繪畫造型的分隔化以及繪畫技法的符號化方面特征明顯。形式語言的研究與理論都是為繪畫創作具體實踐來服務的。藝術家直覺地、理性地運用這些理論和手段,將形式構成與繪畫創作相結合,并通過這些形式語言來傳達藝術家的主觀意識和審美理想,會對藝術實踐起到積極作用。[4]基于這個原理,本文采用形式分析來探討呂林版畫創作與川渝畫像磚相契合的內在邏輯。
(一)“平鋪式”形式語言
畫像磚尤為突出的審美在于它的平面性造型特點。畫像磚的構圖往往呈現出平鋪式的平面效果。其畫面內容龐大復雜到幾乎占滿整個空間,但構圖處理卻井然有序,表現出整體協調的效果。石刻藝術家往往把縱深空間都壓縮在一個平面上,達成視覺統一的效果。
受歐洲版畫的影響,中國當代版畫已經繼承了西方透視法則,打破了傳統版畫平面空間的表現形式,畫面逐漸呈現出三維空間表現的趨勢。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版畫創作路徑大多是對歐洲木刻版畫形式語言的吸收,鮮有個人對版畫藝術創作形式進行探索并展開系統的分析。呂林則有意識地認識到,若將漢代畫像磚與當代版畫制作特點相互吸收,并把畫像磚獨有的藝術特點融入到版畫當中,那么版畫的形式語言便突破了常規,達成一種視覺統一的效果。畫像磚是一種正塑型的藝術,而版畫則相反,是對負空間的處理。盡管兩者之間有著天然的差異,但受漢畫像磚石拓片的啟發,呂林在版畫創作上乃有意提升空間與物象交織的層次,使平面性上的立體結構得以凸顯,由此形成的畫面便是浮雕感和拓印平面的結合體。這樣融會而成的新的語言形式,使得畫面更為率真、厚樸,于平常處顯出靈韻。[5]
我們從東漢畫像磚《弋射收獲圖》(圖一)與呂林版畫《春》(圖二)對比可看到,后者呈現的“畫像磚”形式可謂更上一層樓。
(二)“分隔式”形式語言
漢畫像磚的最大藝術特點就是“分隔式”。畫像磚的構圖方式較為獨特,它不同于焦點透視,卻又類似于散點透視的方法。畫像磚中常常用一些景物跨越被分隔的空間,或用疊加、平列的方式來表現深度,每一個被分隔的空間都在進行著相似的活動內容,景物和人物之間在深度上展現的結構清晰,層次分明。從構圖整體性來看,畫面大都呈現為平視或俯視的角度,畫面中雖沒有遵循近大遠小、焦點透視等技法,但作者卻非常在意畫面大小比例和空間距離,因此從整體上看仍不失和諧統一。反觀現當代版畫藝術幾乎都遵循西方繪畫黃金比例的構圖原則,采用焦點透視原理來展現空間感。[6]呂林注意到這種差異性,便將二者的造型特點相結合,創作出富有趣味藝術的版畫造型特征。
呂林的《桑園》(圖三)版畫與南朝畫像磚《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四)是較為典型的兩幅“分隔式”作品,畫面人物風景對稱均衡,簡潔緊湊,且一改畫像磚剪影式的風格。作者給每人精心設計一個恰當的場面,使畫面生動,情調統一。《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中八人席地而坐,人物之間以銀杏、槐樹、青松、垂柳、闊葉竹相隔,完美地體現了對稱美學。畫面每一段單獨分隔出來的空間都有不同的特征,八個人或撫琴嘯歌,或頷首傾聽,或酣暢飲酒,人物性格特征鮮明。樹木分隔出的人物空間既有相似性和重復性,卻又擁有完整獨立的情節。畫面沒有一處視覺中心點,但每一處分隔出來的畫面空間都是視覺主體。整體構圖呈現平視角度,給人以舒展平穩、簡潔明了的形式感。呂林《桑園》借鑒此構圖形式,畫面四組人物以左右樹木相隔,五人以四組的形式上下形成各自獨立的畫面空間。每組人物或跪地拾果,或仰頭采摘,或精修枝葉,或相談甚歡。各種樹木一方面將畫面劃分為不同的單元,另一方面又將人物聯系在一起。從架構上看,由于人物間體態動勢互相呼應,所以仍不失為完整統一的畫面。
二者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以橫向左右分隔的形式描繪,后者以豎向上下分隔的形式展現,但都表現出分隔對稱的形式美學。呂林的《桑園》還一如既往地采取畫像磚中元素重復的形式,沒有強調各異其趣的樣式,彰顯出形式本身的趣味特征。
(三)“符號化”形式語言
呂林對漢代畫像磚學習的形式語言既體現在“平鋪式”和“分隔式”方面,也展現在“符號化”的表達上。“符號化”是畫像磚中最為顯著的藝術特征,意指通過一些簡單的符號或象征性的形式來表達復雜的形體或概念,且符號間具有相似性和重復性。[7]漢畫磚中的符號化形式體現在各時期多方面:如在早期出土漢武帝時期的畫像石中,多以對角線、同心圓等簡單幾何圖形來代表一些葉狀柏樹、建筑的圖像;到了西漢中期,畫像石上開始有人物活動,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裝飾性處理,人物大多表現為剪影式的正側、半側或四分之三側這樣簡單式的符號化處理;東漢中期以后,畫像磚中一些神祇、車馬的形象也趨于符號化,幾乎每一張畫面中出現的形象都是如此表現。這種方式的好處在于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真實再現客觀物體的需求,簡化了形體,體現了人們對抽象的認知,增加了畫面的意趣表現。借鑒畫像磚的“符號化”形式語言,呂林也將其特征融會到自己的版畫創作中。
呂林版畫《梨園管理》充分吸收畫像磚《采蓮圖》的符號化藝術形式,使之不僅在繪畫技法上表現一致,對勞作場景的選擇也顯出經提煉后的同質的抽象表達。兩幅畫面相似的符號化元素有很多。《采蓮圖》中滿池的荷葉都是以簡單、相同且重復的實心圓依次排列展現,包括每三兩荷葉間戲水的天鵝以及遠處起伏連綿的山巒形象都是符號化的體現,每座山峰都以較為抽象簡練且均勻的線面一筆概括。雖然這種符號化的處理方式會略顯固化,但是作者安排了一抹剪影駕著一葉采蓮舟蕩漾在湖光山色間,仿若有婉轉悠長的歌聲回蕩在耳畔,留人以無限遐想。湖面小舟打破了畫面的整體布局,使畫面既有變化,又不失協調勻稱。以同樣表現方式創作的《梨園管理》,畫中樹干、枝葉以點線面重復的符號化形式共同呈現,人物也是接近剪影化的平面處理,無表情處理,無細節裝飾,但卻絲毫不減弱畫面的敘事性和情節性。樹葉和人物相互交錯掩映,環境與人物排列組合看起來既錯綜復雜又整齊有序。畫面雖無復雜的場景描繪,卻營造出一種熱烈而宏大的秋收場面。其整體搭配的橘紅色調,又平添一種喜慶的氛圍。
符號化的語言形式通過簡約、幾何化的手法表現出來,可能使觀者第一眼看不出畫的是什么,但正是如此,才會給作品平添一層意境。呂林的符號化手法以較少的線條和形象刻畫來表達豐富的故事情感,不但豐富了當代版畫的藝術表現力,表現了中國傳統藝術對形象的生動詮釋力,而且對后來的藝術創作和審美意識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呂林將畫像磚的藝術語言充分地融合和表現在現代版畫創作之中,這正如藝術家王林所講:“以滿幅布局的平面構成,單體符號化形象的多次重復,整體結構的飽滿生動,把繪畫形式的獨立性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呂林作品的超前性是顯而易見的,幾乎是20年前(即在20世紀60年代),呂林就創作了這樣以形式美為歸旨的作品。”[8]
三、小結
呂林所呈現的將現代版畫藝術與傳統漢畫藝術的文化碰撞及結合,不僅是中國版畫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和創新,還促進了藝術的現代化、本土化與民族化。長期以來,學界對中國現代版畫藝術的認知與定義,基本歸結于20世紀30年代初以魯迅為旗手而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但僅將新興木刻運動或“一八藝社”作為源起,來洞悉中國現代版畫的發展歷程,并不夠準確。這里的原因乃在于忽略了版畫的本土發展淵源和民族化、本土化歷程中對民間文藝和傳統文化的吸收與轉換。呂林注意到了這一弊端。他用“在傳統中找尋藝術”的實踐方式,為川渝版畫發展提供了一條關鍵線索和特殊發展的路徑。事實證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并非是“新瓶裝舊酒”,而是具有民族形式感與時代感的藝術創新。
呂林先生的版畫在革命中鍛煉成長。他將自己的藝術文脈與巴蜀獨有的繪畫融會貫通,通過創作實踐的形式為中國版畫與畫像磚藝術的創新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途徑,為20世紀巴蜀畫壇的變革與振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呂林將個人的藝術生命完全融入到20世紀巴蜀畫壇變革的嶄新格局中。
注釋:
[1]黃賓虹:《黃賓虹詩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頁。
[2]參見寧佳:《方寸之間 見微知著——呂林的“拓印版畫”》,《美術》2022年第12期。
[3]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頁。
[4]參見辛華泉:《空間構成》,黑龍江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頁。
[5]參見張道一:《畫像石鑒賞》,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頁。
[6]參見王茹:《版畫藝術的空間感及表現》,《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8期。
[7]參見許德民:《中國抽象藝術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頁。
[8]李維佳:《當代綜合版畫形式語言表現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1—14頁。
作者:云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2021級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