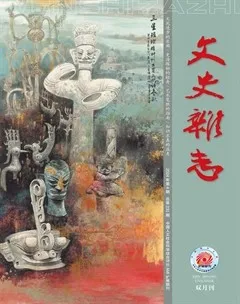李冰父子戲考述
摘 要:自蜀守李冰帶領巴蜀人民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以來,深受福澤的巴蜀民眾在兩千多年里創造了李冰父子文化,并通過民間故事戲表達對治水者的感激與敬意。扎根于民眾的李冰父子戲儼然成為還原李冰父子文化流變的珍貴史料。面對科技文明對原生鄉土文化的挑戰,鼓勵傳統李冰父子戲與現代科技視聽藝術結合,有利于為巴蜀李冰父子文化存續與復興提供科技能量。
關鍵詞:李冰;李二郎;巴蜀文化;戲劇
兩千多年前,蜀守李冰帶領巴蜀人民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巴山蜀水一改飽受澇患之景,從此“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1]。深受福澤的蜀人惋惜李冰功高無子,在民間傳說中為他創造了兒子“李二郎”。隨之產生的李冰父子文化,經過千年歷史激流淘洗,不僅毫未褪色,而且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民間故事傳播、民俗祭祀活動的延伸以及歷代文人志士的抒寫感懷,擁有了日益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從而成為巴蜀水文化及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巴蜀民眾在喜聞樂見的民間戲劇中留存著對治水者的感激與敬意。至今,都江堰二王廟仍保留著正對二郎神大殿的戲樓和農歷六月二十四二郎神生日舉辦廟會、演戲娛神的風俗。在重視傳統文化和歷史名人精神延續的今天,從李冰父子戲角度回溯李冰父子故事,對發掘和發揚李冰父子文化,有著積極意義。
一、李冰史料及傳說考述
對李冰開鑿離堆、修筑都江堰的最早記載,來自西漢司馬遷《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百姓饗其利。”[2]東漢班固《漢書·溝洫志》基本承襲《河渠書》相關語句。東晉蜀人常璩所撰《華陽國志》在李冰“壅江作堋”[3],“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4]等現實舉措之外,記載了李冰“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5]的祭江活動,顯露出治水過程中的巫術祭祀身影。李冰又“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作三石人”,“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6],頗具神異色彩。而李冰鑿崖激怒水神,“操刀入水中與神斗”[7]的情節,則彰顯出不懼神威的反抗精神。《水經注》引東漢應劭《風俗通》所記李冰與江神的戰斗,增添了“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8]的故事背景,與先秦蜀地巫風相呼應。“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斗于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斗大亟,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9]這里出現了李冰以白綬為記、化牛斗江神的傳說,且江神之死是李冰與官屬協力完成,神異色彩之下記錄了李冰帶領民眾開鑿離堆的史實;蜀人以“冰兒”稱呼健壯者,充分彰顯對李冰的推重。李冰逐漸從功績卓越的現實生活中的蜀守,演化成不懼犧牲、身強體健、帶領百姓挑戰惡神的異人,并不斷神化。六朝古籍《蜀記》中出現了李冰升仙的傳說:“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10]今巴蜀民間亦有《李冰巡江升天》傳說。唐代盧求《成都記》直言“冰非常人也”[11],他以石犀鎮壓的對象變為了“毒蛟”,持刀入水戰斗的對象也變為“江之龍”。《太平廣記》卷二九一李冰條曰:“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為龍,復與龍斗于灌口,猶以白練為志,水遂漂下……唯西蜀無害。”[12]時移世易,唐代傳說中的李冰可神魄化龍斗龍,仍掛著秦時化牛為記的白練,護佑西蜀之心一如既往。史料與傳說中李冰“祭神者—斗神者—弒神者—新神”的蛻變過程,反映出李冰形象在巴蜀人民心中經典化的歷史。
二、“戲神”灌口二郎
及至宋代,李冰之子二郎開始出現于正史之外的記錄與傳說中。據高承《事物紀原》所云,元豐年間百姓即于都城汴梁之西立灌口二郎神祠,并認為此神是李冰之子。北宋趙抃《古今集記》中治水傳說已演化為“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壓水精,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13]。張商英《元祐初建三郎廟記》云:“李冰去水患,廟食于蜀之離堆,而其子二郎以靈化顯圣。”[14]從《朱子語類》《夷堅丙志》有關灌口二郎的敘述可知,宋時灌口二郎屢顯靈怪。此后,灌口二郎獲歷代統治者加封而迅速崛起,李冰治水的史實逐漸讓步于李冰父子共同治水的傳說。巴蜀民間現存《李冰父子鑿離堆》《二郎擒孽龍》《二郎擔山趕太陽》等傳說中,李冰父子即便同時出現,故事中解決問題的主角也多為二郎。人們把從前傳說中李冰的強健體魄、過人膽識、超凡神力,賦予了更年輕、更具生命活力的新神祇——李二郎。
《東京夢華錄》詳細描繪了北宋汴梁萬勝門外神保觀二郎生日廟會的盛況,反映出人們對灌口二郎生日的重視:“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為繁盛……作樂迎引至廟,于殿前露臺上設樂棚、教坊,鈞容直作樂,更互雜劇舞旋……自早呈拽百戲,至夕而罷。”[15]由此管窺,二郎生辰六月二十四日演戲娛神的傳統可上溯至北宋,當時即包括雜劇、歌舞、百戲等豐富娛樂活動,可見二郎信仰在北宋民間的普及程度之高。南宋洪邁《夷堅志·夷堅支丁卷第六·永康太守》記載了蜀人在灌口神生日“醵迎盡敬”的情況:“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字王,置監廟官視五岳,蜀人事之甚謹……當神之生日,郡人醵迎盡敬,官僚有位,下逮吏民,無不瞻謁。”[16]在宋代商品經濟繁榮的背景之下,作為集驅疫除災、鎮宅作福、游戲風流于一體的神祇,二郎十分符合市民階層的美好生活祈盼與精神娛樂需求。
明代湯顯祖《遣張仙畫乃作灌口像》詩云:“青城梓浪不同時,水次郎君是別姿。萬里橋西左丞相,何知卻是李冰兒。”[17]這說明為湯氏所認可的灌口神即李冰之子二郎。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祖師廟記》中肯定了西川灌口神美姿容與好游戲的特點:“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為人美好,以游戲而得道,流此教于人間”[18]。可知,灌口二郎乃因“游戲得道”而被尊為戲神。廟會酬神演戲往往針對具體神祇擇演劇目,李冰父子既是備受尊崇的川主中的兩位,二郎又演化為游戲得道的戲神,川主會酬神演《二郎降孽龍》等戲以及二王廟廟會例行演戲,也就不足為奇了。據幼年居住于二王廟旁的當地老人回憶,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二王廟廟會不僅劇目豐富,還會請一尊栩栩如生、頭頸可活動的二郎神像出巡。至今,都江堰二王廟廟會的場面依然繁盛可觀。
三、李冰父子戲及當代文藝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19],“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后世戲劇之萌芽”[20]。中國戲劇可追溯至先秦與祭祀巫術相關的歌舞表演,而李冰父子戲的發源,亦與祭祀活動相關。《太平廣記》所引唐代盧求《成都記》再現了李冰化牛斗江神場景的春冬“斗牛之戲”,與民間李冰化牛傳說相對應,是目前最早的有關李冰治水戲的記載。王圻《稗史匯編》認為此戲或源自秦時;今學界普遍認可此戲出現時間早,至晚也在漢晉之時。在興修水利、改造不利自然條件的過程中,“能知天文地理”[21]的李冰躬身篤行,帶領巴蜀民眾克服了以江神為代表的殘酷自然之力。因此,在巫風盛行的戰國時期,李冰和他的治水事跡被賦予了神話色彩,并迅速進入早期戲劇的文化記憶,在春冬設斗牛之戲祭祀李冰的傳統中延續下來。
斗牛戲中李冰的神性,亦為李二郎所繼承。據宋代張唐英《蜀梼杌》所記“十五年……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斗之象”[22],以及清人陳鳣《續唐書·后蜀世家》中“教坊優人作灌口神墜二龍之象”[23],唐末五代時,孟昶宮廷表演中已有故事情節穩定的《灌口神隊》之戲。此戲演灌口李二郎收伏孽龍事,且演出后天降雨雹、岷江大漲,頗顯神異,可惜劇本未見傳世。《教坊記》所錄唐曲曲名有《二郎神》,《蜀梼杌校箋》認為此曲即演李冰父子與水神戰斗之事,但無傳世文本佐證。不過現存巴蜀儺戲《二郎降孽龍》中可見類似情節。李冰父子與江神或孽龍搏斗的超凡力量和庇佑百姓的道德神性,使他們被尊為“川主”。此后,在祭祀川主的民間小戲中,偶爾可見他們的身影。
封建社會,百姓往往雜糅傳說、附會史實以造神,故而從李冰治水的歷史與傳說中衍生出神化的灌口李二郎。后來,經過歷代統治者的介入與官方認可,宗教因素的滲透及后世戲曲、小說的影響,“灌口二郎”的名號逐漸在區域文化交流之中被遷移給趙昱和楊戩。“二郎”名號歸屬問題對李冰父子戲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戲中主角身份的雜糅。今存元本雜劇《灌口二郎斬健蛟》《二郎神醉射天魔鏡》中的趙昱于嘉州斬蛟,自述“奉天符牒玉帝敕,加吾神為灌江口二郎之位清源妙道真君”[24],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圣》中的主角同樣是趙昱,與李冰父子無涉。現存巴蜀儺戲《二郎降孽龍》《二郎掃蕩》,雖似李二郎治水傳說,但主角均為楊戩。
廣元射箭提陽戲“天戲”《出二郎》,充分體現了民間對二郎身份認知的多元混雜狀態。演員首先唱著“打馬灌州請二郎”[25],被請出的二郎神自述“母是上界神仙女,父是下界楊善人”[26],分明屬于楊戩身世;但“封吾灌州鎖孽龍”[27]等臺詞,卻對應巴蜀民間傳說“李二郎鎖孽龍”事。劇本接著串聯多個民間傳說,幾乎都與李二郎有關。二郎不忍見百姓受烈日暴曬之苦,以黃泥彈子打碎十一對日月,“只留一對鎮乾坤”[28],化用后羿射日典故。面對玉帝對他身世的詢問,二郎直言“我是灌州李二郎”[29],復歸于李冰次子身份。玉帝賞賜鮮桃美酒,二郎醉酒誤時,“急時擔山趕太陽”[30],又與蜀地傳說“李二郎擔山趕日”呼應。土地告狀孽龍作亂,二郎大顯神威,“萬丈深洞鎖孽龍”[31],符合“李二郎擒孽龍”傳說情節,末尾他更是自稱“灌州青天李二郎”[32]。在保留降龍治水、擔山趕日、使用彈弓等李二郎元素的同時,這位“祈陽作福是慈像,降龍伏虎顯兇神”[33]的神祇又被賦予了“鎮宅掃當”[34],驅除“瘟癀濕氣,兇神惡煞”[35]的廣大神通。射箭提陽戲里的二郎,雖然融合了楊戩的部分內涵,但主體仍植根于巴蜀與李冰父子相關的民間傳說。劇中二郎身世的雜糅,是文化傳播交流過程中一代一代民間藝人創作、傳承留下的歷史痕跡。民間戲劇是地域文化的秘史,李冰父子戲儼然成為還原李冰父子文化流變的珍貴史料。
現存古代戲曲中,清人楊潮觀所作《灌口二郎初顯圣》雜劇明確描繪了李冰及子李二郎斬蛟治水故事,收于《吟風閣雜劇》三十二種之中。劇敘蜀郡守之子李二郎趁父親李冰率眾開鑿離堆,架鷹牽犬到山前打圍,忽聞父親鑿壞蛟龍窟穴,與龍婆母子在江邊廝殺,急往救護。二郎以鐵彈丸、細犬制伏龍婆,放神鷹、丟黃金索擒獲龍子;又揮劍插杵、離堆平水,使河水蓄瀉有方;最后鎖龍婆于離堆下約勒江波,裝小蛟于寶瓶口內守定水門,蓋伏龍觀供江神血食。劇中龍婆母子變化人身與李冰廝殺,龍角掛碧綃,李冰頭盔上掛紅綃的設定,無疑承襲了李冰化牛斗江神、以白練為記的遺風。劇情中串聯玉壘山、離堆、寶瓶口、伏龍觀等都江堰實地,充滿地域傳奇色彩。時任邛州知州的楊潮觀在劇中安排李冰戰敗以襯托李二郎的神力不凡,將《華陽國志·蜀志》中李冰“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36]的情節挪移給李二郎,不吝筆墨地描繪他截戰孽龍時深諳戰術、勇武機敏的英雄形象,但又在開篇展現他偷去圍獵、游戲人間的少年心性,似乎在這個血肉豐滿的少年英雄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意志。
如上文所述,李冰父子戲及巴蜀傳說中的二郎不同于以往年高德劭、沉穩持重、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一位豐姿俊秀、披堅執銳、智勇雙全的翩翩少年郎。他既擁有悲憫蒼生之心和護佑蒼生之力,又保留著貪玩好耍的少年心性,會因醉酒誤時而擔山趕日,會趁父親出門而偷偷打獵。誕生于巴蜀百姓對李冰美好祝愿中的李二郎,被賦予了鮮活的人性。他既源于百姓,也就天然親近百姓。
在當代川劇中,李冰父子戲得到創新與延續。1983年5月,溫江地區川劇團在中共四川省委“振興川劇”口號的呼吁下,創演了新編歷史劇《李冰》并參加省振興川劇第一屆調演,飽受好評。《成都舞臺》1989年第2期刊載了川劇《孽龍》劇本,敘伏龍潭底金色大仙貪慕青城山白云仙姑,偷放孽龍搶之,孽龍水漫川西;李二郎巡游歸來,大戰孽龍并將其重鎮潭底,平息水患。在二郎降龍治水的主線之外,與青城山道教文化結合,增加了白云仙姑與張陵之侄張生的愛情線,以及金色大仙私放孽龍卻被之奴役的反轉,劇情曲折而富新意。
當代李冰父子文藝還將觸角伸向電影、電視領域,不斷推出富有創造性、創新性的作品。1983年12月上映的電影《李冰》擁有莊嚴沉重的歷史感和悲壯古樸的悲劇性,講述一心為民的能吏李冰,在饑荒、洪水等天災和權貴阻撓等人禍中,帶領百姓治理水患,最終以家破人亡為代價換來蜀地百姓幸福生活的故事。影片借王綴之口道破祭祀江神是無益的封建迷信,并提出科學合理的治水方法。影片中李冰讓二郎假扮江神新娘,揭露“江神”實為作威作福的華陽侯之子烈龍,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特色。2015年播出的電視劇《李冰傳奇》從治水線、政治線和身世線對李冰故事進行了藝術想象,2021年的紀錄片《蜀守冰》以客觀的立場對李冰歷史形象進行了還原。它們都是李冰文化依托影視載體、走出巴蜀的新意表達。文學作品方面。
2019年,四川作家凸凹出版了第一部描寫李冰的長篇歷史小說《湯湯水命:秦蜀郡守李冰》;此后又創作了李冰長詩《水房子》,通過文學想象追憶并歌頌李冰。2020年出版的馮廣宏先生的《李冰傳》歷考前史,征引翔實,從歷史背景、個人檔案、治水事業等方面為讀者還原了李冰的真實形象。
近年來,都江堰文化與旅游業不斷推出大型情景劇《道解都江堰》、皮影戲《李冰治水》等扎根歷史與本土文化的文藝作品,探索李冰父子文化與當代旅游效益有機轉化的路徑。
結語
縱觀前代李冰父子戲,大部分情節與降龍治水有關,融入李冰父子的各種傳說,任戲中主角與具體情節嬗變,終歸離不開巴蜀水文化的基本思維與敘事。從現存李冰父子戲劇本中,我們能感受到巴蜀民眾對治水者造福后世的功績的認可和對其品格能力的尊崇。
在視聽文明大放異彩的新時代,面對科技文明對原生鄉土文化的挑戰,我們應尋求李冰父子文化與時代的同頻共振,在新媒體與古老傳統之間建立聯系。鼓勵傳統李冰父子戲與現代科技視聽藝術結合,有利于豐富李冰父子文化的載體與傳播方式,為巴蜀李冰父子文化存續與復興提供科技能量。
注釋:
[1][3][4][5][6][7][21][36](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卷三,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202頁,第202頁,第207頁,第201頁,第202頁,第207頁,第201頁,第202頁。
[2](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07頁。
[8][9](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三十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67頁,第767頁。
[10][11][12][13]王文pL4ZlXV2/3KSQgnFUm3oXz9vNY9bMFH3ZmPnJxreQgM=才、王炎編著《蜀志類鈔》,巴蜀書社2010年版,第140頁,第155頁,第160頁,第184頁。
[1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一百二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頁。
[15](宋)孟元老撰,王云五主編《東京夢華錄》,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55—156頁。
[16](宋)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夷堅支丁卷第六》,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017—1018頁。
[17][18]徐朔方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03頁,第1128頁。
[19][20]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第1頁,第3頁。
[22]王文才、王炎校箋《蜀梼杌校箋》,巴蜀書社1999年版,第388頁。
[23](清)陳鳣:《續唐書》,齊魯書社2000年版,第231頁。
[24]隋樹森編《元曲選外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61頁。
[25][26][27][28][29][30][31][32][33][34][35]杜建華等編校《中國儺戲劇本集成:巴蜀儺戲》,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5—76頁。
基金項目: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曲海總目提要》新編”(18ZDA256)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2022級中國古代文學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