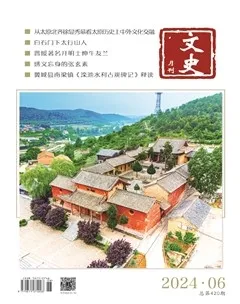孫嘉淦的理學思想與履宦事功
牛寨中

孫嘉淦(1683—1753),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城關人,三十一歲中進士,歷河東鹽政、順天府尹、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在其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雖頻遭顛蹶而旋即進用,休致返里后,又被乾隆皇帝召返,教授諸皇子,位列相位。他畢生以其突出政績和敢于犯顏直諫而蜚聲朝野。山西學者郭象升評價“嘉淦初為直臣,后出將入相,功業赫奕,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實以嘉淦為第一人也”。
師拜朱張 精研理學
明末至清中晚期,興縣共取進士二十三名,其中孫氏一族就有十三名。最為耀眼的是孫嘉淦兄弟四人,除長兄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外,其余三人均讀書成碩彥,考取進士,是清代晉西北名門望族的典范。
“一門三進士”,孫嘉淦最為顯赫。孫嘉淦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萬壽恩科”中進士,他入翰林院后專心論纂文史,沒有機會受到重用和顯示其政治才能。日久,已不滿足于此類職責,便游于朱軾、張伯行門下,研求理學。朱張二人不僅是康熙、雍正兩朝重臣,且是理學的研學者和實踐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西發生旱災,欽命朱軾到山西發放賑災糧款,恰逢孫嘉淦此時因母丁艱在籍守制,受邀至太原,與朱軾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往。
孫嘉淦在研求理學中,認為“大賢推孝悌之道,而得為仁之本焉。蓋人能孝悌,則不仁之事遠而仁道生矣。故為仁以孝悌為本也。”“君子之為仁于天下者,將使天下有治而無亂也。”在孫嘉淦的理學思想中,孝道是仁義中信的基礎和出發點,進一步引申為對君主的“誠敬”。認為不孝者,絕談不到忠誠和敬信。正是如此,他不顧個人安危,多次冒死犯顏直諫,表現出其對君主的忠誠。
犯顏極諫 直不隱晦
康熙帝晚年因儲位之爭,發生了紛繁復雜的“奪嫡”之戰。孫嘉淦雖在翰林院任七品編修之職,也耳聞雍正即位“弒兄”“屠弟”的一系列事件,對新皇不念手足之為,十分不滿,而朝中大臣們都敢怒不敢言,民間亦謠言四起。孫嘉淦愿冒天下之大不韙,奮筆疾書三言:一曰“親骨肉”,勸皇上不要兄弟相殘,以免天下人恥笑,百姓膽寒;二曰“罷西師”,與葛爾丹停戰改和,減少士卒傷亡,調兵轉餉;三曰“停捐納”,減免黎民繁重的稅賦,讓百姓休養生息。爾后,將奏折交給翰林院掌院學士鄂爾泰,托其呈上。
孫嘉淦的三言,可以說每一條都違背了當下的圣意。雍正御覽孫嘉淦的折子后,將其甩給大臣們看,并點著鄂爾泰的名說:“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站列班中的吏部尚書朱軾,看到孫嘉淦此折子,嘆后生可畏,便出列開導說:“皇上,此生誠狂,然臣竊服其膽。”雍正亦轉怒為喜,笑曰:“朕亦服其膽。”孫嘉淦一生以忠清鯁亮著稱于官林,每次奏劾,直不隱晦。雍正帝曾對九卿說:“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汝等當以為法。”
雍正十年(1732年),頒旨要從國子監教習人員中選拔一批外放官員,孫嘉淦掌國子監祭酒,知道那里有不少期滿的教習人員可以外放。于是,他與九卿挑選其中的六名,待早朝時向雍正逐一匯報這些人的情況,提出任免建議。他剛稟告完畢,果親王便出班陳奏:“皇上,孫嘉淦所言,顯然是欺罔,此六個教習,如同圣人一樣,沒有一點毛病?”
雍正問孫嘉淦:“依爾所言,此六個教習都可外放?”孫嘉淦道:“宋鎬、方叢仁等六人,作教習與臣一起共事,未發現他們有不端之處,且臣與九卿核察無異,可外放。”
雍正說:“朕聞此方叢仁人品不端,把情況搞清楚再議敘。”孫嘉淦脫口道:“臣對他了如指掌,不需再考核。”皇上聽了不悅:“爾敢保舉他嗎?”孫嘉淦耿直地說:“臣愿保”。
“憲皇帝不用,公爭益堅。”上擲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果親王呵之曰:“孫嘉淦,汝太狂妄,敢擅動御筆耶!”孫嘉淦“方悟,捧筆叩頭。”“上大怒,反縛置獄,擬斬。”幾天后,皇上怒氣漸消,已而大學士朱軾曰:“孫嘉淦大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皇上亦言:“從寬免其治罪,著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公出獄,不抵家。逕趨庫所”,徑自去銀庫效力,一干就是兩年。
一次,果親王帶著幾個侍從,“突至庫視公。”要看看孫嘉淦被貶后的表現。到了銀庫,出乎果親王意料的是,“公方持衡,傴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待果親王檢查過所收銀兩和賬冊,兩相對照,賬物相符,絲毫不差。“王大奇之,即為轉奏,堪以重任”。雍正知孫嘉淦不愛錢,便啟用他為山西河東鹽政。
乾隆元年(1736年),孫嘉淦由河東特召返京,遷吏部侍郎,又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其時,新皇初政,群臣俯首,宮娥簇擁,其中不乏阿諛奉承之人。孫嘉淦憂心新皇被此風所染。于是,在乾隆即位幾個月后,便上了一道奏折《三習一弊疏》。疏折近兩千字,提出“三習一弊”,即耳習、目習、心習。疏言中指出:皇帝聽慣頌揚之詞后,就會“喜諛而惡直”,見慣了順從趨媚之人后,就會“喜柔而惡剛”,習慣了自以為是的思考方式后,就會“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就是“喜小人而厭君子也”。孫嘉淦勸諫乾隆帝要力除“三習一弊”,做到君心居正;要虛懷若谷,不要唯我獨尊;要有自知之明,并非無所不通;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遠小人,近君子”。
《三習一弊疏》不僅使孫嘉淦成為直言諫諍的名臣,其言也被后世諸皇帝當作座右銘,以此警示自己。清曾國藩在其《鳴原堂論》云:“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帝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抄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為本朝奏議第一。”
精研六經 著述甚豐
孫嘉淦任直隸總督時,于保定督府寫下“居官八約”匾:“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于無名,事止于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短短42個字,字字珠璣,句句經典,概括了其為官做人的基本原則,可以說是顯古法之精要,育后人以勵志。
孫嘉淦一生勤學,精研六經,著述甚豐,僅流傳下來的理學著述就有百萬余言,所述又不拘泥于前人成說,多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僅理學經解類就有《南華通》七卷,《春秋義》十五卷,《詩經補注》二十卷,《易經解》十卷。其中《詩經補注》和《周易述義》由乾隆皇帝親自裁定,書名分別冠以《御纂詩義折中》《御纂周易述義》。《南華通》是孫嘉淦解釋莊子《南華》的一本書。因莊子文中詞組成篇而無系統性、流變性,非常難讀,人們認為“南華之文天下之至奇也,來不知所自來,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倏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歸。”孫嘉淦伏案深耕,將《南華》之文一一作了注釋,對后人研究莊子起了拋磚引玉之效,實乃佳作。

孫嘉淦畢生研究《周易》頗有心得。乾隆十八年(1753年)初,皇上命他從事易傳爻象,他用近一年時間寫出了《周易述義》十卷,即將告竣之時,瘡病復發,不久與世長辭。乾隆接到孫嘉淦長子孝愉進呈的遺本后,對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皇帝珍惜孫嘉淦未完之《周易述義》,命內閣重臣傅恒、來保等人統領,組織二十人續編、謄錄、提調、校對,終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竣工,乾隆又親自作序,付梓此書,并收入《四庫全書》。
孫嘉淦還有一些對理學的講解著述,如《春秋義》等。他晚年認為自己于《春秋》本旨未能盡悉,自覺其失,“誤解圣賢,”以訛傳訛,旋毀其版。所幸時任山西巡撫劉于義有一采進本,得以保存,現收藏于山西省圖書館繕本部。可見他的治學態度嚴謹且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