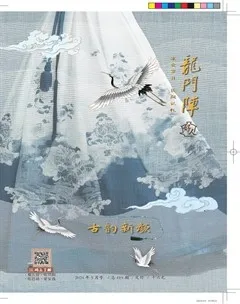重操舊業的剃頭匠
吳建
他仍舊像以前那樣認認真真,一絲不茍,理完了,他還仔仔細細地修剪著。
大年初五,是迎財神爺的日子。一大早,巷口就響起了“噼噼啪啪”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一打聽,原來是陳二虎的剃頭鋪又開業了。
陳二虎原來是我們這里有名的剃頭匠,個兒高高的,身材健碩。叫他“剃頭匠”并非對他不恭,也并不是他不配“理發師”“美發師”“發型師”這些“高雅”的稱謂,而是他樂意這種稱呼。“老李,來剃頭的啊,請坐。”“二胖,頭發又長了啊。等這兩個人剪好了,我幫你剃頭。”聽聽,陳二虎平時就是這么招呼前來理發的人。久而久之,人們都喊他“剃頭匠”,最多尊稱他為“剃頭師傅”。他在弄堂口理發已有二十多年了,附近居民都認識他。他的“頂上功夫”有口皆碑,連鎮上的書記、鎮長都是他的常客。算起來,我們這個小鎮的理發店、美發廳大大小小也有十幾家,但比他理發技術高超的還真是寥若晨星。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和悅,服務周到,理發剃須剪鼻毛掏耳朵全套“一條龍”,價格公道,童叟無欺。男人來洗個頭、挖個耳朵,女人來剪個劉海,他說這些都是舉手之勞不收錢,老年人來剃個光頭,假如不刮胡須的話,他僅收半價,對那些不便前來的顧客還提供上門服務。住在巷尾的李老頭是個孤寡老人,癱在病床上幾年了,陳二虎為他義務理發十八年,直到其去世,沒收過一分錢。正因為如此,陳二虎的生意非常紅火,我和家人的頭發都到陳二虎那里去理。有一次我要參加一個重大活動,主辦方安排我上臺發言,想想頭發也長了,就特意去陳二虎那兒理發。他聽說了我的來意,理得格外認真、細致,幾乎花了以往替我理發的雙倍時間。完了捧著我的頭對著鏡子看了又看,發現兩鬢還有幾絲白發,又拿起剪子小心翼翼地修掉。最后還給我噴了發膠固定發型。他說:“一般我不給客人噴發膠,這個東西氣味刺鼻,用久了對頭發也有傷害。但年輕人喜歡,他們說要噴我就給他們噴。當然你偶爾噴一次沒關系的。”看著鏡子里的我頭發理得漂漂亮亮,胡須刮得干干凈凈,整個人顯得莊重多了,真有點氣宇軒昂的派頭。我很滿意,就多給了他點錢,可他怎么也不要,還說:做生意就是要規規矩矩,不就是多花了點工夫嗎,哪能多收錢?
十多年前,陳二虎的生意開始冷清。年輕人都不愿意找陳二虎剃頭。一則陳二虎跟不上時尚,男人理的大多還是“小平頭”; 女的理的不是齊耳短發,就是過肩長直發。二則他不會染發,這可是致命弱點,別說青年人,就是許多老人都時興染發,白頭發染成黑頭發,黑頭發染成黃頭發、紅頭發……問他為啥不學染發,他說他有氣管炎,不能聞那些化學氣味。漸漸地,他的剃頭生意就淡下來了。那些崇拜他的人都對他敬而遠之了,許多老主顧也不來了,有時一天難得有幾個人光顧。后來,有一位常來他店里理發的賣豬老板邀他入伙。于是,他關了店門,買了一輛四輪小貨車,去販賣小豬。
陳二虎不愧為“二虎”,塊頭大,有一股虎勁,而且腦子活絡,跟在賣豬老板后面沒多長時間就掌握了販小豬的竅門,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不過,他沒有學會(或許不想學)那些坑人的本領,比如短斤少兩啊,給小豬強行灌水啊,等等,依舊和理發時一樣講究誠信,以質論價,從不乘人之危壓價,所以周圍十村八里的養豬戶都愿意把小豬賣給他。那個時候販賣小豬的老板都發了大財,有人問陳二虎收入怎樣,他狡黠地嘿嘿笑笑,半晌才說:“比剃頭強多了。”
前兩年,由于不少地區經常遭遇豬瘟,養豬戶蒙受重大損失,大多數農戶不再養豬了,販賣小豬的人收入斷崖式下降,很多販豬老板金盆洗手。陳二虎想想自己年紀大了,兒女們都成家立業了,沒必要再打拼了,于是也洗手不干了。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況且也沒有退休金。今年初他與租房老板商議,租下原來的理發店,重操舊業,拿起了理發剪。此后,我每次經過巷口,總要朝陳二虎的店鋪里張望一下,如果有人在理發,我就感到高興;如果沒有人,心里就感到缺少什么似的。
我對理發從來不講究,更不在乎什么發型,只要理得干凈就行。可我到那些美發廳、金發廊去理發,他們對我這個單理發不做造型、“油水”不大的人,總是愛理不理。有一次,我到一家理發店理發,女服務員非常熱心地給我推薦這樣那樣的發型,我說無所謂,又讓我辦會員卡,我沒辦,她就馬馬虎虎幫我理了一通。回家一照鏡子,好丑啊,弄得我被人嘲笑了好幾天。以后不到頭發太長了絕不理發。現在見陳二虎的店又開張了,摸摸自己的頭發確實長了。周日的下午,我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去陳二虎的剃頭鋪理發。
來到剃頭鋪,陳二虎正戴著口罩在給一個小孩剃發,沙發椅子上還坐著三四個人。陳二虎看到我,忙熱情地招呼我坐下。我打量了一下這小小的剃頭鋪,還是一如既往的整潔,四面雪白的墻壁上沒有蜘蛛網,屋頂沒有灰塵,地面上僅有少許頭發。我坐下來,耐心地看著他理發。他仍舊像以前那樣認認真真,一絲不茍,理完了,他還仔仔細細地修剪著。有個小伙子等得不耐煩了:“一個小屁孩的頭發有必要這么費勁去剪嗎?你能不能快點啊,我還有事呢。”陳二虎微笑著說:“人家來我這里剃頭是信任我,不管大人小孩我一視同仁,都不能草率了事,請您再耐心等一會兒,我幫他理好了就是你。”天快黑了,終于輪到了我,陳二虎歉疚地說:“讓你久等了!”說罷,他開了日光燈,給我圍上白圍布,脖子上箍了毛巾,先幫我用熱水洗頭。我打趣地問他:“你還記得我嗎?”“記得,記得,你是吳老師。”我真佩服他的記性,“這么多年了,你還沒忘啊!歇了多年沒理發,現在還順手么?”他一邊理發一邊說:“你別擔心,我保證會幫你理好發的。這些年來,其實我并沒有荒廢理發的手藝,只要有空,我就幫我的家人和親友理發。”我善意提醒他:“現在新冠病毒還在零星傳播,你可要注意啦。”“這你就完全放心了。在我這里理發,每人各一條毛巾,不合用。每剪完一人,理發剪、剃須刀都要用消毒濕巾擦拭。每天晚上,當天用的毛巾、白圍布全部用次氯酸浸泡消毒。對別人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沒想到陳二虎雖然是個大老粗,做事還這么細心嚴謹,考慮周全。理完發,我問他多少錢,他說十元,我驚愕:“十元?現在理個發都漲到三十元了。”他笑笑說:“剃發就是個功夫活,哪能瞎收錢!不管別人漲不漲,反正我就收這么多。”付完錢,我說:“這么晚了,你也該下班回家了。”他笑笑說:“前巷子里王大娘病重了,他的兒子今天在家,早上來約我給他娘理發,我這就去他家。”
我走出店門,他也收拾好理發工具出來了。鎖好門,他跟我說了聲“慢走!”就快步向前走去。那身影,在明亮的路燈下,是如此高大,如此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