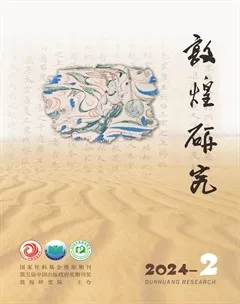回鶻王室兒童供養人及其服飾研究
陳菊霞 劉宏梅



內容摘要:本文對敦煌石窟和新疆石窟中的回鶻王室兒童的排列規律、身份及其服飾特征做了全面考察,總結出三個主要特點:一、回鶻兒童多排列于父母供養像的前面,絕大多數作回首狀,以此與身后的父母形成呼應關系;二、除幼童外,回鶻兒童的頭冠和服飾基本與父母保持一致,男童類同父親,女童類同母親;三、回鶻兒童多額前梳劉海,耳前留一綹頭發。
關鍵詞:回鶻;兒童;供養人;服飾
中圖分類號:K879.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2-0051-10
A Study on the Clothing Worn by Royal Uighur Children in
Cave Paintings
Abstract:By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identities, and clothing of the children of the Uighur royal family painted in artworks at both Dunhuang and Xinjiang cav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hese illustrations: (1)The Uighur children are often arranged in front of their parents, and many children are looking backward towards their elders, which form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2)Except for the toddlers, the headwear and costumes of the children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ir parents: the boys are adorned similarly to their fathers, while the girls are like their mothers. (3)Many of the Uighur children have bangs over their foreheads and a strand of hair in front of their ears.
Keywords: Uighur; children; donor; clothing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8世紀中葉至9世紀上半葉,回鶻曾一度稱霸漠北。然而,至9世紀30年代末,回鶻汗國連年疾疫,且大雪成災。同時,王室內部爭權奪利而相互傾軋。這使回鶻國力日益衰弱。至開成五年(840),回鶻汗國被黠戛斯攻滅,其部眾被迫遷移。其中向西遷移的有三支,一支遷至今蔥嶺以西,與原隸屬于回鶻的葛邏祿部落合并,之后建立喀喇汗王朝;一支投奔至吐蕃統治下的河西走廊,與當地的回鶻部落合并,建立甘州回鶻政權;另一支行至天山南北,逐漸與當地的回鶻部落結合,形成以高昌和北庭為中心的高昌回鶻王國[1-2]。
西遷后的回鶻人原本信奉摩尼教,但受遷居地的影響,逐漸改信佛教。所以在新疆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西大寺和七個星等佛教石窟和寺院中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回鶻供養人。另外,因歸義軍節度使曹氏家族與甘州回鶻王室聯姻,且敦煌在11世紀中后期曾建立沙州回鶻政權,這使敦煌石窟也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回鶻供養人畫像。本文將對敦煌石窟和新疆石窟中的回鶻王室兒童供養人及其服飾加以重點考察和研究。
一 甘州回鶻
9世紀末10世紀初,張氏歸義軍政權在內憂外患中走入“絕境”,已無力支撐政權。敦煌世家大族經過重新“洗牌”,將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的外孫婿曹議金推為節度使。曹議金上臺后不負眾望,對內籠絡僧俗官吏,維護社會安定;對外積極加強與中原王朝和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的交往。針對東邊日益強大的甘州回鶻,曹議金采取聯姻方式密切雙方關系,他不僅自己娶甘州回鶻可汗的女兒為妻,還將女兒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由此,在曹氏家族及其姻親營建的家窟中,我們多看到著回鶻裝的供養人,其中既有曹議金回鶻夫人的供養人像,也有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的曹議金女兒及其子女的供養人像。下面我們重點對這一時期莫高窟第100、454窟中的二身回鶻兒童供養人加以考察。
1. 莫高窟第100窟的回鶻小公主
莫高窟第100窟營建于曹元德任歸義軍節度使時期,即935—940年間。據賀世哲先生研究,該窟的窟主是曹議金的回鶻夫人李氏,而實際主持修窟的人是曹元德[3]。該窟甬道北壁繪制一組女供養人畫像,其中第二身是位女童(圖1),她雙手捧花盤,面向主室虔誠供養。她的前方有一綠色榜題框,題名曰:“□天公主是甘州可汗……”[4]。這則題名保存得不完整,我們還需結合她前后的女供養人題名來考察她的身份。女童的前后的兩身女供養人均著回鶻裝,題名分別是:
第一身女供養人:
……郡……人汧……圣天可汗的子隴西李氏一心供養。
第三身女供養人:
女甘州回鶻國可汗天公主一心供養。[4]49
第一身是曹議金的回鶻夫人;第三身是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的曹議金女兒[3]223。從這三身女供養人的排列順序和題名來看,女童當是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的曹議金之女的女兒,其題名“□天公主是甘州可汗……”之缺失的第一個字當是“孫”字。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這位女童位列母親的前方,這并非反常現象。依照新疆和敦煌的回鶻供養人排列規律,回鶻人習慣將子女繪制于父母的前方。而漢族則不同,往往將子女繪制于父母之后。
這位女童梳著整齊的劉海,頂發用寬綢帶扎束。這條綢帶很長,上面飾有綠色四葉花紋,分二股一直垂至腰部,末端剪為三角形。束發之上佩戴桃形冠。此桃形冠原本有紋飾,但因其顏料層出現“脫皮”現象而不能辨識,但從其前后兩身供養人即曹議金回鶻夫人和她母親回鶻公主頭戴桃形鳳冠來判斷,女童很可能戴的也是桃形鳳冠。
女童的面部已漫漶,看不清五官線條,但滿臉所貼綠色面靨卻清晰可見。如眉心和酒窩處用錢寶圓,眉尾上方、兩頰和鬢間裝飾花葉形,這完全符合“滿面縱橫花靨”之描述[5]。女童佩戴上大下小的雙環耳珰;身穿圓領窄袖缺胯長袍,袍衣為紅色,略顯寬松,長及腳踝處,上面飾滿綠色的小團花;腳部雖漫漶,但大致能看出穿尖頭白鞋。
2. 莫高窟第454窟中的回鶻小王子
莫高窟第454窟本是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深的功德窟,大體營建于940—942年間[6],30余年后其子曹延恭又出任歸義軍節度使,他組織家族力量重修了此窟。此窟的供養人主要分布在甬道和主室東部區域。我們認為現存甬道的供養人是曹延恭夫婦重繪的,而主室東部的供養人則基本是曹元深始建時的原作(部分供養人的臉部線條后人重描過),不過,曹延恭夫婦在重修此窟時以他們夫婦的名義重新改寫了供養人的題名[7]。
第454窟東壁門北側南起第四身供養人為男童形象。由于這位男童位處兩身回鶻裝女供養人之間,他的題名已漫漶,郭俊葉結合第100、61窟的回鶻供養人排列規律推定他的身份,是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的曹議金女兒所生之子[8]。也就是說,男童是甘州回鶻可汗之子。
這位甘州回鶻小王子的面部和頭冠已漫漶不清,服飾較為清晰。他身穿深色窄袖缺胯長袍,袍衣飾滿較大的四葉花形圖案,腰系寬帶,右側懸掛兩件細條狀的蹀躞物。
上述莫高窟第100窟的女童和第454窟的男童都是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的曹議金女兒所生的子女。關于曹議金女兒所嫁之可汗有阿咄欲[9]、仁裕[10,11]、仁美[12]、景瓊[13]等多種說法,本文認同仁美說。由此認為莫高窟第100、454窟中的兩位回鶻兒童就是仁美可汗的子女。
二 沙州回鶻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圍繞沙州回鶻這一專題展開了深入討論。目前基本認定在歸義軍政權滅亡之后和西夏有效統治敦煌之前曾存在一個沙州回鶻時期。然而,關于這個政權,以森安孝夫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是依附于西州回鶻的政權[14-16],而以李正宇和楊富學先生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是獨立的回鶻政權[17][11]272-299。以上兩種觀點,我們贊同后一種。同時,也認同馮培紅將沙州回鶻統治時間大致定在1030—1067年之間[18]。
1. 莫高窟第409窟中的回鶻小王子和小公主
莫高窟第409窟是整體重修的一個洞窟。關于這次整體重修的年代,形成西夏說和回鶻說兩種觀點①。近年來,松井太在第409窟東壁門南的國王像的榜題框中發現兩行回鶻文題記,分別是:
針對這一新發現,學界又展開新一輪的討論。松井太依據新辨識出的回鶻文題記再次肯定了森安孝夫先生所提出的關于第409窟東壁門南所繪國王為高昌回鶻王的觀點[21],并具體稱作高昌回鶻王阿廝蘭汗(獅子王)[19]。劉永增先生也據此分析了第409窟的重修時間,認為“莫高窟第409窟東壁南北兩側的回鶻供養像是西州回鶻阿廝蘭汗及其王妃,該窟重修應在11世紀之初的北宋末年”[16]8。與此同時,學界也出現不同看法。如任懷晟通過討論第409窟國王像的題記、妝容和服飾得出這身國王像為西夏皇帝像之結論[22]。隨后,楊富學先生針對以上研究成果做了積極回應。首先,他駁析了由史金波先生和任懷晟所提出的第409窟國王為西夏王之觀點。其次,他再次論證了第409窟的國王不是西州回鶻可汗而是沙州回鶻可汗[23]。綜觀以上看法,我們贊同楊富學先生的觀點,即第409窟繪制的是沙州回鶻可汗和其王妃的供養人畫像。
(1)回鶻王子。第409窟東壁門南回鶻可汗前下方的一身男童像頗引人注意(圖2)。他身材矮小,還不及可汗的腰部,有學者稱其為“回鶻王子”[24,25]。這位手持盛放寶瓶和寶珠供盤的小王子頭戴與可汗類同的尖頂高冠,由于漫漶,已不能辨識其具體結構和紋飾,但從遺存的下圓上尖的高冠外輪廓來看,他們戴的當是尖頂花瓣形冠。
王子身穿圓領窄袖缺胯長袍,腰束窄帶,上掛蹀躞諸事。王子袍衣的顏色與其父袍衣的顏色一致,原本應該是紅色,現氧化為黑色。袍衣在腰部左側開衩,露出綠色里子。腳穿白色尖頭靴子。
(2)回鶻公主。第409窟東壁門北側繪制2身回鶻王妃供養人像。南起第1身王妃的前下方繪制1身女童,從其身高和樣貌來看,似為2—3歲的孩童,她當是回鶻王妃的女兒。這位女童的姿態充滿動感,她高高舉起右臂,并回首望向右手緊握的花枝。女童的面部五官和發式已模糊,僅能看出戴著葉形耳珰。由于女童僅遺存上半身,尚不能明斷其服飾,但從其肩部垂下的兩條寬帶判斷,可能穿的是背帶褲。
2. 莫高窟第148窟中的回鶻公主
莫高窟第148窟是盛唐時期由以李大賓為代表的敦煌李氏家族營建的一個大型涅槃窟。在張氏歸義軍時期,李明振作為李大賓的重孫又組織李氏家族重修家窟。至沙州回鶻時期,又在甬道南北壁、主室東壁下方以及南北兩壁龕下重繪供養人①。
第148窟的甬道南北壁分別繪制回鶻可汗禮佛圖和回鶻王妃禮佛圖。不知何時,有人在甬道東端加砌窟門,致使回鶻可汗禮佛圖和回鶻王妃禮佛圖的東端被掩蓋。就人物畫像來說,甬道北壁的回鶻王妃禮佛圖僅能看到王妃右側一小部分身體和其前方站立的二身女童畫像(圖3)。
這兩位女童當是回鶻王妃的女兒[25]218,即回鶻小公主。她們手拿花枝,并排站立在方毯上。西側的公主較東側的略矮一頭,其年齡應該小一些。兩位公主的面部出現氧化和漫漶現象,五官不甚清晰。她們額前梳著整齊的短劉海,耳前各留一綹頭發,頂發用綢帶束起。此綢帶在腰部打花結,一直垂至腳踝部。兩位公主的綢帶顏色有明顯的差異,東側的為紅色,西側的為白色。兩位公主的束髻上都套冠。從冠的輪廓來看,無疑是桃形冠,裝飾紋樣已漫漶,僅冠的底座殘留金箔。
兩位回鶻小公主都穿寬松的窄袖長袍,袍裾曳地,對襟、上臂、臀部有聯珠紋裝飾的橫線。兩位公主的長袍也有相異之處。如一是領式不同,西側的公主為圓領,而東側的公主為弧形大翻領;二是長袍的顏色不同,西側公主穿的是紅袍,而東側公主穿的是藍袍。
3. 莫高窟第237窟中的回鶻王子
莫高窟第237窟甬道南北兩壁分別繪制回鶻可汗和二位回鶻王妃的供養人像。甬道南壁回鶻可汗的前方有一身童子像,其形象漫漶嚴重,幾乎看不清冠飾、面容和服飾。從隱約可見的上尖下圓的頭冠形態判斷,他戴的應該是與身后回鶻可汗類同的尖頂冠。這身童子的身高還不到可汗的腰部,當為回鶻小王子。
4. 西千佛洞第16窟中的回鶻王子和公主
西千佛洞第16窟始建于晚唐,五代、宋、沙州回鶻和民國時期曾重修。現存甬道和主室的壁畫主要是沙州回鶻時期重繪的[26]。
(1)回鶻王子。西千佛洞第16窟南壁門西側繪制兩身立姿供養人像,東起第一身是位比丘,畫像高大;第二身供養人身高略低,從其形象判斷,大概是十五歲左右的男童(圖4)。這位男童的面部已氧化為黑色,仔細觀察,仍能在其豐圓的臉部辨識出五官,眼睛細長、眉毛短粗、嘴唇厚小。男童的額前有整齊的短劉海,頭戴尖頂花瓣形冠,紅色冠帶繞耳后系于頦下。頭冠結構和裝飾紋樣雖然較清晰,從勾勒的卷云紋樣來看,還是略顯簡單和隨意,缺乏精細之感。
男童身穿橘色圓領窄袖缺胯長袍,袍衣飾滿小團花圖案;腰束革帶,鞓上有橢圓形的帶銙,并懸掛著大概是刀子、礪石、火石袋、針筒等蹀躞物品[27];腳穿尖頭白色靴子。
這位男童手持長莖花枝,面向甬道而立,而甬道南北兩壁繪制的是回鶻可汗與回鶻王妃的供養人像。我們注意到,這位男童的頭冠和服飾樣式與甬道西壁的回鶻可汗的幾乎一樣,僅是袍衣的裝飾圖案不同,可汗的是團龍圖案,而男童是小團花圖案。從男童的朝向位置和服飾特征來看,謝靜稱其為“回鶻王子”[25]210當無疑義。換言之,這位男童當是甬道西壁回鶻可汗之子。
(2)回鶻公主。西千佛洞第16窟甬道西壁主要繪制回鶻可汗及侍從像。在可汗的左前方還有兩身形象較小的回鶻女童像。她們雙手握花枝,并排站立。由于畫面漫漶,她們手握的花枝幾乎看不清線條和顏色。更甚者,她們的面部和頭冠也已漫漶,不僅看不清五官,也看不出頭冠的線條和紋飾。有幸的是,頭冠的外輪廓還殘存墨點,大體能看出是桃形,這說明兩位女童戴的應是桃形冠。
兩位女童所穿衣服樣式與莫高窟第148窟甬道北壁的兩位回鶻小公主完全相近,即窄袖對襟長袍,袍裾曳地,對襟、上臂、臀部有聯珠紋裝飾的橫線。兩位公主的袍衣均為紅色,領部漫漶已看不出是圓領或翻領。
第16窟甬道東壁繪制兩身回鶻王妃供養人像。在北起第一身王妃的右前方有兩身呈前后站姿的女童供養人。女童的形象嚴重漫漶,仍能大體看出她們等高且服飾相同。身高約及王妃的腰部,頭冠呈上尖下圓的桃形。如果考慮第一身王妃頭戴桃形鳳冠,那么,兩位女童戴桃形鳳冠的可能性較大。女童的面部已漫漶不清,能看出穿的是窄袖回鶻袍衣。這兩位女童的位置和服飾特征表明,她們當是兩位王妃的女兒。一窟之中繪出回鶻可汗五位未成子女的現象實不多見。
上述莫高窟第409、148、237窟和西千佛洞第16窟都有回鶻可汗和家人的供養人像,他們的題名幾乎都漫漶不清,致使無法判定這四窟中的回鶻可汗身份。不過,史書有關于這一時期“沙州鎮國王子”和“沙州北亭可汗”之記載,又據李正宇先生推斷,他們可能是同一人[17]。由此,有學者推測這四窟中的回鶻可汗當有“沙州北亭可汗”[28],可暫備一說。
三 龜茲回鶻
庫木吐喇第79窟中的回鶻王子
第79窟方向不正,《庫木吐喇石窟內容總錄》記錄坐東向西[29]。該窟西壁(前壁)門北側下部繪制五身供養人像(圖5),均面南而跪①。我們在《唐與回鶻和親的歷史紀念:庫木吐喇第79窟新探》一文中對這五身供養人的身份做了考證,認為自南起的四身成年供養人分別是昭禮可汗、昭禮可汗之妻頡里思力公主、昭禮可汗親兄、昭禮可汗之妻頡里公主(太和公主)。昭禮可汗的前方有一童子,他雙手合十,回首反顧,當是昭禮可汗和頡里思力公主所生之子[30]。
這位童子身穿紅色圓領窄袖長袍,腰部束帶。他的頭部現已漫漶不清,但《新疆庫木吐拉石窟新發現的幾處洞窟》記其“束冠”[31],《印度到中國新疆的佛教藝術》記其“束冠,黑發垂肩”[32]。或許他與其父昭禮可汗一樣,戴的是尖頂花瓣形冠。
第79窟佛壇東壁(正壁)繪有七身供養人(圖6),居中童子面北而跪。南北兩側供養人相對而立,南側一身比丘和男女供養人各一身,北側三身比丘。我們對這七身供養人的身份以及與第79窟重修之關系做過討論,認為南側的兩身世俗供養人是昭禮可汗亡故的父母騰里可汗和咸安公主,居中的男童是昭禮可汗之子[30]。這里再補充說明一點,從這位男童的身高來看,大概是三四歲,而經我們論證認為佛壇東壁的供養人繪制于昭禮可汗繼位之初,即長慶四年(824)或不久[30],但騰里可汗和咸安公主于元和三年(808)就已相繼去世,所以,這位童子只能是騰里可汗之孫,即昭禮可汗之子。當然,他與前述西壁門北側的第一身童子應不是同一人,因為他身形略矮,當是弟弟。
這位男童頭戴翻檐白色小氈帽,額前有劉海,發辮垂后,身穿圓領窄袖團花長袍。有幸的是,他的漢文題名清晰可讀,題曰:“童子搜阿迦”[33]。
四 高昌回鶻
1. 柏孜克里克第22窟中的回鶻王子
柏孜克里克第22窟為縱券頂長方形窟。勒柯克將該窟的營建年代斷在9—12世紀[34];賈應逸先生判定在公元11世紀中葉至12世紀[35]。
勒柯克在《新疆佛教藝術》中刊布了柏孜克里克第22窟(勒柯克編為10號窟)一組兩張供養人像圖版,并將左側的圖版編為a,將右側的圖版編為b。b圖是一位雙手合十站立的供養人(圖7),勒柯克推測是15歲左右的男童,其題名回鶻文書寫,勒柯克轉寫為“t(a)ngrikan oyul qurt qa tigin t(a)nagrimt(a)ngidam korki bu arur”[34]227,254。這位男童臉部豐圓,額前有劉海,頭頂束發,上戴尖頂花瓣形冠,冠帶系于頦下,腦后散發垂至肩部;身穿圓領窄袖缺胯長袍,腰部系軟帶,在腹部置又出一個半弧形軟帶,從而形成雙帶狀。腰帶的兩側佩掛小刀、錐形物、磨刀石、袋子、手巾等蹀躞七事。男童腳穿白色靴子,靴底踩著垂直條帶。
這位男童和a圖中呈跪姿的成年男供養人都繪在后墻佛像基座的右側,成年男供養人在上方,男童在下方。這位男童的頭冠、長袍樣式與其上方的成年男大體相同,只是長袍的裝飾圖案略異。男童的長袍為素色,而成年男紅色長袍上飾眾多黃色圓形圖案。如果從這兩身供養人的分布位置和服飾特征來看,男童當是這位成年男供養人之子。這位成年男供養人也有回鶻文榜題,勒柯克轉寫為“bu birtam adgu inalol”[34]225。勒柯克據此稱他們為“回鶻貴族供養人”[34]226。賈應逸先生據柏孜克里克第22窟門壁左側繪有國王的供養人像,就將該窟的供養人稱為“王室成員”[32]448-449。馬振林說回鶻文榜題顯示,他們分別是回鶻王者和回鶻王子[36]。
2. 柏孜克里克第27窟中的回鶻小公主
柏孜克里克第27窟為縱券頂長方形窟,正壁有佛臺基,兩側壁各有三個佛臺座。該窟改建于公元11世紀中葉到12世紀[35]430-431。勒柯克在《新疆佛教藝術》中亦刊布了該窟(勒柯克編為17號窟)一組兩張供養人圖版,他將左側的圖版編為a,將右側的圖版編為b[34]255。b圖中共有三身女供養人,她們分布在后壁佛臺座左下壁[36]37。第一身供養人身材矮小,乃女童,雙手籠于袖內,面向基座的主尊禮敬(圖8)。她的題名以回鶻文書寫在她的前上方,勒柯克轉寫為“il tigin qiz tarim”[34]227,譯為漢文是“伊爾特勤幼女像”[24]445。第二、三身均為成年女供養人,她們當是伊爾特勤之妻,其中一位當是女童的親生母親。伊爾特勤幼女用綢帶束發,此綢帶長及小腿部,且在腰部打成美麗的蝴蝶結。束發之上戴金黃色桃形冠,上面用紅線勾畫火焰紋樣[36]37。女童的冠式與其身后的二位女性供養人的冠式完全相同,僅在發式上有所區別。伊爾特勤幼女梳中分,將額前發分左右自耳前垂至肩部;而其身后的二位成年女供養人則梳蝴蝶狀的博鬢,上飾云氣紋。幼女佩桃形耳飾。
伊爾特勤幼女的服飾與其身后的兩位女供養人完全一致,為橘色翻領窄袖長袍,領子上繡著卷草祥云圖案[36]37,膝蓋處有襕線。
與上述三身女供養人相對的,即后壁佛臺座右下壁也有兩身女供養人,她們的頭冠與服飾幾乎與后壁佛臺座左下壁的二身成年女供養人相同。而在佛臺座正壁的前壁有一身回鶻男性供養人,他頭戴花瓣式尖頂冠,身穿橘色圓領團花長袍,他應該就是伊爾特勤,即女童的父親。從供養人的布局來看,伊爾特勤應該是窟主。也就是說,后壁佛臺座的正壁、左右壁繪制的是伊爾特勤與其妻女像。回鶻可汗的子弟稱作“特勤”,伊爾特勤及其家人屬回鶻王室成員。
綜上所述,本文對莫高窟第100、454、409、148、237窟和西千佛洞第16窟,以及庫木吐喇第79窟和柏孜克里克第22、27窟中的回鶻王室兒童的排列規律、身份及其服飾特征做了全面考察,總結出五個主要特點:
第一,回鶻兒童大多排列于父母前面,偶有排列在祖父母前面,如果有引導僧,則排在引導僧的前面;第二,絕大多數回鶻兒童作回首狀,以此與身后的父母或祖父母形成呼應關系;第三,除幼童外,回鶻兒童的頭冠和服飾基本與其父母一致,遵循男童類同父親、女童類同母親的習俗;第四,回鶻男童額前常梳劉海,耳前留一綹頭發;第五,本文所考察的回鶻王室兒童,其形象看似矮小,但作為王子和公主,他們一旦成年,則非富即貴。王子會出將入相,甚至個別王子會成為可汗,公主則出嫁豪門。
參考文獻:
[1]楊富學. 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6,7.
[2]林幹. 突厥與回紇史[M].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80-203.
[3]賀世哲. 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M]//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3.
[4]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49.
[5]御定全唐詩[M]//永瑢,紀昀.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1冊. 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663.
[6]馬德. 曹氏三大窟營建的社會背景[J]. 敦煌研究,1991(1):23.
[7]陳菊霞,王平先. 莫高窟第454窟營建年代與窟主申論[J]. 敦煌研究,2022(1):82-86.
[8]郭俊葉. 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69-75.
[9]榮新江. 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27.
[10]孫修身. 五代時期甘州回鶻可汗世系考[J]. 敦煌研究,1990(3):44.
[11]楊富學. 回鶻與敦煌[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205.
[12]王艷明. 瓜州曹氏與甘州回鶻的兩次和親始末——兼論甘州回鶻可汗世系[J]. 敦煌研究, 2003(1):74-75.
[13]陸慶夫. 甘州回鶻可汗世次辨析[J]. 敦煌學輯刊,1995(2):38.
[14]森安孝夫.沙州ウイグル集團と西ウイグル王國[C]//內陸アジア史研究(15). 東京:中央ユーラシァ學研究會,2000:21-36.
[15]松井太,著,白玉冬,譯. 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回鶻語題記[C]//西域——中亞語文學研究:2012年中央民族大學主辦西域——中亞語學術研討會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13-214.
[16]劉永增. 敦煌“西夏石窟”的年代問題[J]. 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3):4-14.
[17]李正宇. 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國[C]//敦煌研究院. 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史地語文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163.
[18]馮培紅. 敦煌的歸義軍時代[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453.
[19]松井太. 敦煌諸石窟語題記銘文關劄記(二)[J]. 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學編)第32期,2014:27-44.
[20]松井太,著,劉宏梅,譯. 敦煌石窟中回鶻文題記劄記(二)[J]. 吐魯番學研究,2019(1):118.
[21]Moriyasu Takao,“The West Uighur Kingdom and Tun-huang around the 10-11th Centuries,”in Berlin-Br-
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ichie und Abhandlungen,Academie Verlag,Berlin,2000:340.
[22]任懷晟. 敦煌莫高窟409窟、237窟男供養人像考[J].敦煌學輯刊,2019(3):91-96.
[23]楊富學.莫高窟第409窟的營建時代與民族屬性——兼評西夏說與西州回鶻說[J]. 美術大觀,2022(2):42-
46.
[24]賈應逸. 莫高窟第409窟與高昌回鶻供養人像比較研究[M]//新疆佛教壁畫的歷史學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35.
[25]謝靜. 敦煌石窟中的少數民族服飾研究[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6:209.
[26]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內容總錄[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01.
[27]原田淑人,著,常任俠,等譯. 中國服裝史研究[M]. 合肥:黃山書社,1983:116.
[28]劉人銘. 敦煌石窟回鶻王像身份屬性再思考[J]. 中國美術研究,2021(2):21-222.
[29]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 庫木吐喇石窟內容總錄[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53.
[30]陳菊霞,馬丹陽. 唐與回鶻和親的歷史紀念:庫木吐喇第79窟新探. 待刊.
[31]梁志祥,丁明夷. 新疆庫木吐拉石窟新發現的幾處洞窟[M]//張國領,裴孝曾. 龜茲文化研究(三).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728.
[32]賈應逸,祁小山. 印度到中國新疆的佛教藝術[M].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332.
[33]馬世長. 庫木吐喇的漢風洞窟[M]//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13.
[34]阿爾伯特·馮·勒柯克,著,管平,巫新華,譯. 新疆佛教藝術:第3卷·壁畫(一)[M]. 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225.
[35]賈應逸. 柏孜克里克石窟初探[M]//新疆佛教壁畫的歷史學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31-
432.
[36]馬振林. 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回鶻時期供養人圖像研究[D]. 新疆藝術學院,2020: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