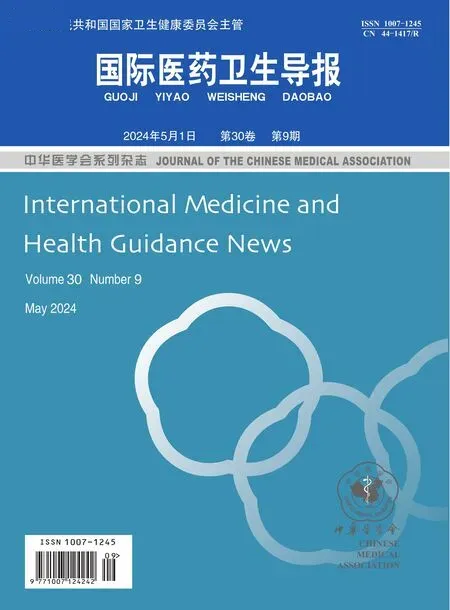暈痛針聯合前庭康復訓練對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的影響
杜青 顧寶東 徐棟 王英超 趙曉慧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腦病科,連云港 000;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檢驗科,連云港 000
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PPPD)是一種新定義的以非旋轉性眩暈和/或不穩感為表現的慢性前庭功能障礙疾病[1]。主動或被動運動及復雜視覺刺激、直立姿勢等均可導致該疾病癥狀加重,當下更多考慮的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功能性疾病。目前,臨床上多數采用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類或五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類藥物、心理治療、前庭康復訓練療法(VRT)、認知行為治療等。然而,相關藥物會產生消化道癥狀、睡眠障礙、焦慮、抑郁、頭痛、性功能減退等不良反應,甚至可能涉及嚴重的藥物成癮問題,從而導致不良反應大于治療效果。基于對相關藥物不良反應的擔憂,更多患者愿意選擇補充和替代醫學進行干預治療,故中西醫結合治療優勢顯現。中醫針灸治療該病在國內已有報道,但仍較為匱乏[2]。本研究分析暈痛針聯合前庭康復訓練對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療效及對情感障礙的影響,以期為臨床實踐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1.一般資料
選取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收治的90例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進行隨機對照試驗,依照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45例。對照組男17例、女28例,年齡31~73(62.82±9.86)歲,合并癥:高脂血癥19例、2型糖尿病11例、高血壓30例。觀察組男12例、女33例,年齡38~79(62.64±9.40)歲,合并癥:高脂血癥17例、2型糖尿病10例、高血壓34例。納入標準:⑴西醫診斷符合2017年巴拉尼協會提出的PPPD診斷標準[1];⑵中醫符合《實用中醫內科學》中眩暈病診斷標準[3];⑶年齡18~80歲;⑷患者及其家屬知情且簽署同意書;⑸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⑴孕產婦女; ⑵合并嚴重心腦血管、肝、腎、造血系統等疾病者;⑶曾發生過嚴重的暈針情況;⑷不能準時復診,或配合回訪患者。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經南京中醫藥大學連云港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倫理審批號:2022倫理審查(KY)-36]。
2.方法
兩組患者入院后均不停用對相應基礎病的常規藥物治療。⑴對照組予以前庭康復訓練治療,具體方法為:根據視覺、本體覺及前庭覺分別進行視覺追蹤、掃視、頭畫圈、轉頭時注視、趾踵直線行走、原地轉體、靜態平衡訓練、行走練習等[4],可以參考“眩暈小助手APP”。前幾次由專職人員指導患者完成訓練,掌握要領后,可在家中由家人陪同或自行完成,具體治療應根據患者自身情況選擇增加動作,循序漸進治療,每日訓練2次,訓練時間為20 min/次,7 d為1個療程,每個療程的最后1 d休息。⑵觀察組在前庭康復訓練基礎上加入暈痛針治療。選取主穴位:四神針(百會前后左右旁開1.5寸)、雙側太陽穴、印堂穴。如氣血虛者,加三陰交、足三里;腎虛者,加太溪、氣海;痰濁者,加豐隆、中脘;肝郁者,加天柱、大椎;血瘀者,加血海、風池;肝陽上亢者,加太沖、內關。操作方法:使用75%乙醇溶液對針刺穴位皮膚表面消毒,選用0.25 mm×40.00 mm一次性針灸針進行針刺,采用平補平瀉法,得氣后留針30 min出針。主穴的具體操作方法:四神針針刺方向均指向百會穴,沿頭皮平刺0.8~1寸;太陽穴需直刺0.8~1.0寸,此穴的針感非常重要,以向目上或眼內放散者為佳;印堂穴采用提捏穴位局部皮膚,沿皮從上垂直向下平刺達鼻根部位,進針0.3~0.5寸。其他輔穴可參照《針灸學》[5]常規操作。每日針刺1次,7 d為1個療程,每個療程的最后1 d休息。兩組患者均治療4個療程。
3.觀察指標
⑴評價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患者眩暈癥狀嚴重程度,采用眩暈殘障程度評定量表(DHI)[6]。該量表可以計算4個指標:DHI總分及軀體、情緒、功能3個指數,總分100分,評分越高說明患者眩暈程度越重。⑵臨床療效評價采用DHI指數判定,療效指數=[(治療前評分-治療后評分)/治療前評分]×100.0%,痊愈:療效指數≥75%;顯效:75%>療效指數≥50%;好轉:50%>療效指數≥25%;無效:療效指數<25%。⑶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焦慮、抑郁狀態進行評分,采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7]、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7],≥7分則可能存在焦慮、抑郁,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焦慮、抑郁狀態越嚴重;⑷兩組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睡眠質量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8]評分進行評價,總分21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情況越差。⑸治療期間不良反應:包括暈針、惡心嘔吐、皮下淤血、肌肉疼痛等。
4.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6.0軟件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表示,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兩組患者治療前后DHI總分、軀體、情緒、功能評分比較(表1)
表1 兩組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的DHI總分、軀體、情緒、功能評分比較(分,±s)

表1 兩組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的DHI總分、軀體、情緒、功能評分比較(分,±s)
注:對照組采用前庭康復訓練治療,觀察組在前庭康復訓練基礎上加入暈痛針治療;DHI為眩暈殘障程度評定量表;與同組治療前比較,aP<0.05
組別例數DHI總分治療前治療28 d后軀體治療前治療28 d后情緒治療前治療28 d后功能治療前治療28 d后對照組觀察組t值P值45 45 69.96±6.00 69.47±6.60 0.368 0.714 33.02±10.54a 24.22±11.08a 3.860<0.001 18.62±3.04 19.16±2.61 0.893 0.374 8.67±3.19a 6.98±3.32a 2.462 0.016 25.87±2.15 25.29±3.20 1.007 0.317 11.51±3.22a 8.27±4.08a 4.182<0.001 25.91±2.00 24.93±2.75 1.93 0.057 12.40±4.42a 8.71±4.07a 4.120<0.001
治療前,兩組患者DHI總分及軀體、情緒、功能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28 d后,兩組患者DHI總分及軀體、情緒、功能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且觀察組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2.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表2)

表2 兩組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臨床療效比較[例(%)]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2.873,P=0.005)。
3.兩組患者治療前后HAMA、HAMD及PSQI評分比較(表3)
表3 兩組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的HAMA、HAMD及PSQI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持續性姿勢-感知性頭暈患者治療前及治療28 d后的HAMA、HAMD及PSQI評分比較(分,±s)
注:對照組采用前庭康復訓練治療,觀察組在前庭康復訓練基礎上加入暈痛針治療;HAMA為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D為漢密爾頓抑郁量表,PSQI為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與同組治療前比較,aP<0.05
組別例數HAMA評分治療前治療28 d后HAMD評分治療前治療28 d后PSQI評分治療前治療28 d后對照組觀察組t值P值45 45 27.80±4.54 27.60±5.44 0.189 0.85 15.24±4.35a 10.00±5.59a 4.963<0.001 25.96±4.72 25.64±5.50 0.288 0.774 15.96±4.92a 10.20±6.33a 4.820<0.001 14.93±2.57 14.58±3.19 0.582 0.562 10.11±2.70a 6.31±2.98a 6.339<0.001
治療前,兩組患者HAMA、HAMD及PSQI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治療28 d后,兩組患者HAMA、HAMD及PSQI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且觀察組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4.兩組患者不良反應比較
觀察組有2例針刺出血導致瘀斑、1例輕度暈針、1例惡心不適、1例頸部肌肉酸痛;對照組有2例惡心不適、2例頸部肌肉酸痛。觀察組不良反應發生率為11.11%(5/45),與對照組的8.89%(4/45)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37,P=0.711)。
討論
目前尚無PPPD確定的流行性病學數據,主要通過慢性主觀性頭暈、恐懼性姿勢性眩暈以及急性前庭疾病后慢性頭暈患者的統計資料來估計其發病率[9]。國內研究發現PPPD患者多集中于41~60歲人群中,并以女性為多,內向型人格特征及神經質可能是PPPD的危險因素[10]。與健康人群相比,低內向型、高神經質性格及較為嚴重的焦慮更易體現在PPPD患者身上[1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PPPD在臨床上與前庭性偏頭痛(VM)存在共病問題,不僅在臨床表現上,而且在發病機制上也有重疊[12]。PPPD發病過程中有可能出現VM癥狀,同樣在VM發作后也可能出現PPPD的臨床表現,這可能與相關的神經遞質在PPPD和VM的病理生理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13-15]。而腦干聽覺誘發電位檢測有助于VM的早期臨床診斷[16]。VRT作為一項以運動作為基礎的康復訓練計劃,主要對前庭系統障礙導致頭暈/眩暈的患者采取以運動訓練為主的綜合措施,使機體已受損的前庭功能得以修正,提升機體代償能力,消除癥狀,避免復發[17-18]。隨著VRT理論和實踐的不斷完善,業內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用于治療前庭疾病,包括周圍性和中樞性[19]。通過頭、眼和軀體一系列運動促進前庭中樞代償是VRT的核心理論,使凝視改善,平衡功能得以增強[20]。VRT的優勢在于,操作簡便、耗時短、患者可以自主練習,但要改善前庭功能卻需要一定訓練療程。中醫治療頭暈類疾病歷史悠久,尤其是針灸方法能快速緩解頭暈癥狀,提升患者治療信心。
依據中醫學理論,PPPD可歸“眩暈”范疇,眩暈有“風眩”“頭眩”“眩冒”等別稱,可分為兩種不同病證。眩者,即視物不清、旋轉感,甚至眼前發黑;暈者,即頭昏沉、倦怠、不穩感。兩者可同時發展,也可僅出現某一種癥狀,而PPPD的核心癥狀更貼近后者。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對眩暈的記載。追溯《素問》,對其致病臟腑的描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靈樞》中記載:“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是對其具體癥狀的描述。中藥湯劑在治療“眩暈”方面有諸多經典方劑,但出于辨證問題,很難固定方劑,從而難以實現標準化治療。針灸歷史早于湯藥,在治療“眩暈”疾病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在先人的傳承基礎上后人不斷發揚創新,精簡穴位,在治療“眩暈”方面可達立竿見影之效。《通玄指要賦》提及“頭暈目眩,首覓于風池,其次為百會”,闡述治療眩暈可針刺風池穴、百會穴。頭部取穴可起到安定神志、解郁調神的作用,且取穴范圍包含小腦所對應平衡區,可以針對糾正前庭功能障礙、共濟失調而達到改善頭暈的目的[21]。譚璐璐等[22]采用小醒腦針刺法聯合度洛西汀治療PPPD,可以調和肝膽和氣血,通過針刺作用于“神”,提神醒腦,達到治療PPPD的目的。金婧[23]采用依托大腦皮層功能定位理論創立的方氏頭針結合VRT治療PPPD,可緩解患者頭暈癥狀,改善患者生活質量、睡眠效率、認知程度等諸多問題。由此可見,頭部取穴是治療PPPD的關鍵點。
暈痛針為靳瑞教授所創的一種獨特針刺療法,收納在柴鐵劬所編著的《靳三針臨癥配穴法》[24]一書中。其取穴之精且常能針到病除,它既代表嶺南針灸學派,也是一種成功的臨床針灸模式,以暈痛針為主穴,在臨床治療頭暈類疾病療效極佳[25]。暈痛針選取穴位為四神針、雙側太陽穴及印堂穴,其中四神針以百會為中心取穴,在百會前后左右旁開1.5寸,腦部的投影區較四神聰范圍更廣,針刺療效更強,具有提神醒腦、提升陽氣、升清降濁之功效,是治療眩暈頭痛的要穴[26-27]。而四神針行針方向是關鍵,四根針均向百會穴方向平刺,刺激能較集中,相當于強化刺激百會穴。雖然取穴為四神針,實則強化百會穴。也有研究采用火針點刺百會穴治療慢性主觀性眩暈,取百會壓灸治療頸椎疾病,這些方式均有強化百會穴而達到良好臨床療效的目的[28-29]。印堂為經外奇穴,首見《黃帝內經》:“厥者,眉間也”,當時有定位而無穴名。正式確立印堂穴的名稱及功效出自《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書中描述:“印堂,在兩眉間宛宛中。”并有“頭風嘔吐眼昏花,穴在神庭刺不差,子女驚風皆可治,印堂刺入艾來加”的記載。現代印堂穴的主治病癥遠廣于古代,尤其是在神志病、情志病方面,如失眠、抑郁癥、焦慮癥、精神分裂癥、神經衰落等,而PPPD又多伴有情感障礙、睡眠紊亂。通調督脈和調神為印堂穴兩個重要的中醫機理[30]。針刺印堂穴是通過調節腦中元神,而對全身的神起到調節作用。《律書》言:“神使氣,氣就形”,調神所以能固形,則能形與神俱。太陽穴也屬經外奇穴,《銀海精微》曰:“太陽穴,在外眥五分是”,位于足少陽經與手少陽經相交處,具有開竅醒腦、清利頭目等功效。以上穴位合用,可達升清降濁、開竅醒神、益髓止暈作用。臨床治療PPPD患者采用以上三穴操作可取良效,而在血虛、腎虛、痰濁、肝郁、血瘀、肝陽上亢等證型時配用相應輔助穴位,可更好改善其兼癥,如頭痛、腰酸、身重、面赤、心煩等。
本研究中,兩組患者治療后DHI總分、軀體、情緒、功能、HAMA、HAMD、PSQI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且觀察組均低于對照組,療效優于對照組(均P<0.05)。暈痛針治療PPPD,能在較短時間內改善頭暈癥狀及社會適應能力,從而提高患者對治療的信心,建立良好醫患關系,保證治療完整度[24,31]。基于以上針刺治療可能存在即時療效的考慮,故聯合VRT治療。VRT優勢在于患者學會后可在家自行操作,在有一定依從性的前提下能使患者更好完成VRT治療。此外,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相當,因為針刺部位為頭部,而頭皮部位毛細血管豐富,故易導致針刺后出血,甚至因拔針后按壓不規范、按壓時間不足等導致頭皮血腫事件發生,所以對施針者有較高要求。進行前庭康復訓練時,醫生應明確告訴患者在訓練時可能會發生不良反應或特殊情況,如眩暈、嘔吐、肌肉酸痛等,但是堅持訓練一段時間后癥狀會逐漸減輕,并且PPPD臨床癥狀也獲得改善,讓患者身心處于放松狀態[32]。
綜上所述,對于PPPD患者在常規VRT治療的同時配合暈痛針治療,可有效減輕患者頭暈癥狀,同時改善患者情感及睡眠障礙,提高患者生活質量。該法安全可靠,值得臨床推廣。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杜青:設計試驗方案,實施研究,撰寫論文;顧寶東:統計分析;徐棟、王英超:收集病案,采集相關數據,隨訪工作;趙曉慧:分析/解釋數據,對文章的知識內容作批評性審閱,支持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