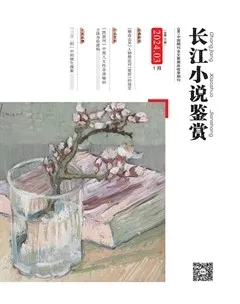寺山修司作品《死者田園祭》中的凝視機制分析
劉艾琳
[摘? 要] 二戰后在日本“松竹新浪潮”中涌現出一批講述反思歷史,回望鄉土,尋根戰后新生代身份特點為敘事主題的導演,其中寺山修司以其奇幻的美學風格以及特殊的成長經歷創作了五部長片。半自傳體影片《死者田園祭》基于拉康的鏡像理論通過不同時空同一主體相遇的設置,以“自我凝視”為切口在套層結構中形成了獨特自我詮釋的方式和策略。戰爭原罪和鄉土創傷籠罩于戰后一代導演們的影像中,寺山修司的影片在戰后的人文領域起到“調節劑”的作用,帶領觀眾以解剖自我的方式直面反思歷史。
[關鍵詞] 寺山修司? 《死者田園祭》? 凝視? 鏡像理論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3-0108-04
寺山修司是日本電影“松竹新浪潮”的代表導演之一。在《死者田園祭》中,寺山修司使用了非線性的套層結構將時空并置轉換,以成年主人公拍攝的自傳電影為鏡像,映射出阿新的童年經歷并進行成年視角的凝視反思。拉康認為“凝視”是“主體對他自己的分裂所產生的興趣與那規定了這一興趣的東西,即一個獲得特許的對象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對象出自于某種原初的分裂,出自于某種真實的逼近而造成的。”在拉康的理論中“凝視”處于主體、可見對象與他者的三元關系之中,在影片中分別對應成年阿新、童年阿新以及戰后的鄉土三方面。寺山修司在影片中投入的凝視介入并沒有消滅主體,而是讓主體在欲望的功能中能夠進一步維持自己的存在,通過自我解構的方式意圖實現一種自我和解。
一、真我之鏡:日本近現代西化與本位精神內核對撞的他者凝視
影片選取鐘表作為重要的意象符號,象征其不容變動的本位文化,當鐘表停滯,人們從夢境中轉醒,卻意外發現現代化進程轟然而至,在快速的變革下人們來不及反應,只得抱著古老的鐘在恐懼下手足無措地等待。陰暗逼仄的房間內身著傳統服飾,面色灰暗的母親慌忙制止了鄰居西裝男人試圖打開鐘表檢查內部結構的舉動,寺山修司在影片敘事的最前端就交代了要表達的宏大主題,掛鐘象征著以母親為代表的傳統日本精神內核,而西裝男人則意味著二戰期間近現代西化過程對日本傳統文化的沖擊,傳統婦人所能接受的限度被表達得十分明晰,絕不允許現行社會的細化過程觸及到日本的本位文化,寧愿放任已經崩潰的鐘表不再運行。在后續的劇情中,男孩阿新不止一次向母親提出自己想要一塊手表以及割包皮的欲求都被母親勒令制止,并通過榻榻米下的視覺通道監視阿新的行為。家庭中父親身份的缺失以及母親非正常的占有欲使得這一母子關系發生扭曲。手表則象征著日本戰后新生代對于西化過程不同于傳統一代的看法,他們試圖在文化沖擊下找到一條日本發展的新道路,漠視反對已然存在的公共準則,如同孤苦伶仃的精神囚徒被束縛在無法表達自我的壓抑環境中,卻急切渴望看到成果,然而這樣的變革道路在當時日本的歷史環境下必然會處處碰壁。
鏡頭跟隨阿新來到鄰居家,西裝男人的妻子是一個身著和服在躺椅上休憩的少婦,身邊擺著作為西洋工藝品的留聲機。少婦相較于阿新母親而言,對日本的細化過程接觸的程度更深,是日本第二代傳統內核的代表,在其身上體現著近代日本傳統文化在表象層面的妥協與嘗試。當夜晚降臨,西裝男人對少婦表達出渴望欲求時卻在熟睡的妻子身邊發現了一把尖銳的鐮刀,窗外偷窺的老嫗露出欣喜的神情,少婦被丈夫的動作吵醒,男人變得慌亂開始顧左右而言他,老嫗又表現出十分憎惡的神色。在影片中,西裝男人所代表的是純粹西化這一概念,而通過這一情節,少婦的身份則進一步被明晰,第二代日本傳統精神內核的表現層面已與西化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與接受,但依然無法觸及其本位文化,這在影片里具現為少婦愿意與西裝男人同榻而臥,但絕不與其同枕而眠。這種處理是對現實場景的荒誕戲劇化變形,鏡頭與鏡頭承接之間沒有很強的邏輯因果關系,人物此時也沒有發生對話,觀眾的期待視野卻被進一步的情節擊打得支離破碎。
作為一部自傳體性質的電影,寺山修司選擇了自己的家鄉日本東北部青森縣作為《死者田園祭》的故事發生地,作家松永伍一曾形容:“青森擁有南方沒有的清冷詭秘,這里擁有恐怖的民族文化之根。”背著祭壇的小販在亂石堆間叫賣,男孩走進這片荒誕,隨著紅衣半裸女子的引領走過一片荒蕪之地,阿新郁郁而歸。隨后躺在家中休息時,一抹蒙面殘影注視著阿新一言不發,又轉瞬即逝。這種“注視”有其特殊含義,其父作為生前的軍國主義代表者,以亡人的身份凝視著戰后新生代的迷惘,試圖通過扶乩還魂的方式對新生代進行規訓。在戰爭的影響下,日本的傳統武士道精神已在西化的沖擊下發生本質性的扭曲與變形,象征著“制定規則的人”對日本傳統精神內核異化開始反思。
二、偽我之鏡:“存人欲,滅天理”白日夢中的對象凝視
寺山修司的電影情節荒誕不經,淺層人物的視覺顛覆不足以表達他的意圖,他將日常生活環境抽離出人們的邏輯之外,變得冷漠異常。運用大量的超現實主義手法,精心塑造了自己的作者風格。在背著祭壇的小販走過的海灘邊,靜靜矗立著一個衣柜,天空中升起一只紅日,太陽呈現在鏡頭中像是一支變色的藍底日章旗,傳統的價值體系已經像太陽一樣籠罩著這里,試圖將人們包圍在這片窒息之中,以期遠離時代的變革沖擊。軍國主義的暴力與破壞摧毀了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人們在沖擊的夾縫中產生懷疑,艱難求生。影片運用變形夸張的人物形象作為隱喻表達了寺山修司對待鄉土的明晰態度。男孩如同歌舞伎的臉龐意味著一切都是成年時代對過往的粉飾,極度肥胖的馬戲團女人需要男人來充氣滿足性欲,一眾黑衣獨眼的使徒在影片中毫無規律地出現意味著那套已然變味的價值體系陰魂不散地捆綁著鄉土本身。這些符號借用藝術形式模仿流動的天馬行空的夢境,在給觀眾提供“制造驚奇”可能性的同時增強了影片的魔幻色彩,制造出含混性的破壞性結構,召喚著觀眾與其一同重新建構起邏輯框架。
影片中彌漫著“存人欲,滅天理”的規矩桎梏,在寺山修司的敘事中,價值體系自身都已成為畸形的產物。影片中眾多的黑衣獨眼使徒在屋外無情地注視著紅衣女人草衣生產,新生兒身上的胎記被視為不祥之兆,在神婆絮絮叨叨的預言下大家紛嚷著要將剛出生的“不詳的”孩子置于死地。福柯提出過“圓形監獄”中有著“全景敞視”的結構,監控者處于被權力控制的注視之中,體現為一種規訓權力的機制。電影中的草衣正是在這種“全景敞視”中崩潰,走投無路只好親手將孩子投入河中送予河神。阿新也在返家的路途中遇到多年后歸來的草衣,被其輕佻地奪走了童貞,得到了象征成年的手表,一場糟糕的性體驗徹底打破了少年懵懂的性覺醒,在另一個強主體的壓制下完成了成人儀式。在當時的環境中,軍國主義賦予了變形的規矩落地生根的機遇以及至高無上的權威,規矩長時間的約束又造成了人們主動或被迫的適應,釀成了一幕幕荒誕的悲劇。
混亂的規矩桎梏為當時的戰后新生代建立了一種無意識的心理結構范式,“無意識不是給定時間內意識之外的東西,而是因為壓抑而與意識分離,以致不經歪曲就不能進入意識感覺系統中的內容”。拉康認為,無意識是能指對主題所產生的影響,被壓抑的部分就是能指以無意識的形式回歸。在影片中體現為導演以電影這種白日夢形式在無意識中美化了自己當年的一系列性懵懂事件。阿新在接收到心上人的心意后與她約在深夜逃離這里去到新世界。然而,當成年阿新在自己真實地回望之后,向觀眾呈現了真實的情節,少婦在離開之前同男孩講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年少時父親應征入伍生死未明,母親罹患中風苦守薄田,很快便撒手人寰,自己則投奔親戚寄人籬下。待男孩歸來時少婦已與舊時情人殉情在荒野之上。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伊德用白日夢來概括藝術創作活動。他認為創作同做夢一樣是無意識的欲望在想象中的滿足,而藝術家則善于將潛意識欲望改頭換面,將自我分成若干部分的自我,來實現自我本能欲望的代替性滿足。至此,目睹了兩人殉情的阿新從白日夢中抽身而出,褪去了少年的那部分自我幻想,對鄉土再無半點迷戀。
三、鏡像結構的破碎與重構:進入套層結構后的主體凝視
當拍攝進入瓶頸后導演獨自一人在東京街頭漫無目的地散步,對于自己的自傳影片他產生一種迷失感,不僅是迷失在城市中,也迷失在內心深處。拉康在鏡像理論中利用幼兒觀看鏡中的自我影像來闡明“想象秩序”這一概念,幼兒在凝視中接受了鏡子中的虛假整體自我觀念,完善了自我認同。在想象秩序中,主體在消解自我、凝視自我的過程中建構自己,以期“放逐自己是為了找出身處何在”。當敘述結束時,在話語之下被遮蔽的、被壓抑的言語還沒有被言說,在這種困擾中寺山修司選擇通過歷史敘述的文本抵達過去來實現個體認知。此時,個體的回望被認為主要是由劇烈的“生活不連續性”經歷而導致的,“它以現實不滿為直接驅動,以尋求自我的統一連續為矢的,它是現代人為彌補生活的不連續性而自行采取的一種自我防御手段”[1]。阿新在作品創作瓶頸期完成了一次自我解構,打破了想象秩序進而向觀眾呈現了自己破碎又不連貫的童年經歷。
套層結構敘事是電影敘事的重要手法。“所謂敘事的層級控制及敘事作品對敘事層建構之操控,進而言之,即作品中的敘事層對作品整體建構之影響及不同敘事層之間的交互作用。”[2]寺山修司對打破敘事層級關系進行重構有一種癡迷,在這部影片中再次構架了獨特的敘事層級架構,以人物為核心,構建每層敘事的獨立性。“從縱向來說,外敘事層通常對內敘事層具有涵括顛覆能力,即使當外敘事層的篇幅遠遠小于內敘事層時。”《死者田園祭》中的外層敘事存在于影片的后半部分,時長占比非常小,但仍然能對內敘事層的情節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影片由四條線索所構成:童年阿新與母親的抗爭、寡婦被迫對女兒的殺害、依靠充氣以滿足性欲的女人自食其果以及成年阿新最后站出理清真實的故事脈絡。《死者田園祭》拋開傳統電影的敘述方式,打亂常規的心性邏輯,整體呈現“第三層—第二層—第一層的敘事進程,在后面揭示前面所述的是戲中戲影片的內容”“但《死者田園祭》中最開始的講述是假的,即敘述者的敘述不可靠”。這種敘事帶給觀眾一定的疏離效果,模糊了代際關系,從而在一眾二戰反思的影片中產生嶄新認知。幾條情節線以男孩童年成長時間的正向流動和導演在成年角度的回望為時空轉換基礎,在導演走進套層結構之后,錯亂的情節開始有跡可循,草蛇灰線的來龍去脈以及前后因果逐漸明晰。在男孩成功與少婦攜手私奔時,鏡頭驀然拉開告知觀眾方才的影像是導演的電影情節,成年的阿新將自己的見聞投射于屏幕之上,觀眾與劇中人一起凝視著他的成長經歷。后現代理論家們認為“凝視并不僅僅是感知的一種機制,而是一種最為基本的結構。凝視成為主體與文化秩序產生聯系的方式,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他成為了主體性賴以建構其自身的一種機制。”[3]只是他自己也已走入記憶的迷宮之中,陷入“博爾赫斯式的困惑”,置身于時空的迷宮中,難以準確界定存在的本質。新宿市區中阿新帶著紛亂的思緒向家的方向走去,孤立的公寓門前,他見到一個身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這是成年阿新與童年阿新的第一次相遇,他察覺到在自己的記憶中鄉土與人物都被重塑,又將自己懵懂的性覺醒進行了粉飾,于是導演進入自己電影的套層結構與兒時的男孩一同赴約,然而自己與隔壁婦人情投意合的私奔僅存在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夜晚掙扎著掙脫了母親的束縛,卻只見到少婦與舊情人私會,隨后又目睹二人在荒野上殉情。正如巴爾曾指出:“鑒于敘述者與被敘述者兩個層次之間的等級關系,敘述者的一個否定詞就能改變被述故事的整個意義。”[4]
寺山修司在與石子順造的談話中闡述道:“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母親兼任著父親的身份,也是在父親缺席的時代唯一與我們自身對立的他者。因此,我們必須從俄狄浦斯情結轉向到俄瑞斯忒斯情結,所以在我看來,母親能成為一種中心主題,毋寧說是歷史本身的需求。”這恰好可以解釋影片的情節矛盾——弒母與戀母二者的不停轉換。男孩與成年后的導演在田野里下棋聊天,他們都困惑于自身被決定的命運,導演向男孩提出自己想要“弒母”的欲望,或許擺脫這種束縛,可以從根本上扭轉人生的軌跡,不至于被陰暗的童年經歷所困擾。導演不見男孩歸來于是親身回到兒時的屋子,母親熱情地呼喚他落座準備飯食。他突然意識到哪怕僅是他自己電影中的橋段,哪怕他帶著武器,都無法實現對生母的屠戮,母親已和鄉土一起塑造了他的成長經歷,這是再也無法篡改的。所以,導演進入套層結構后的“凝視”表面上看指向的是經過粉飾的過去,實際上是面向現在和未來的“記憶”改造,“通過將現在的主觀情緒投射于過去的‘記憶之物,來塑造未來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走向”。寺山修司認為,日本社會的母親已被功能化,不再是實體而成,為了一種幻象。由于其實體的“缺席”和“不在場”才能具有活力[5]。回歸這一行為是主體在外界動蕩中尋求穩定與依靠的方式。他承認了人類原始的本能,認為孩子對母親的眷戀是難以避免的。
導演阿新坐下來同年輕的母親一起吃了一頓家常飯,此時室內的墻壁倒下,身后是繁華的新宿街頭,那些記憶里或真實或虛構的人出現在他們身邊,或揮手告別,或消失在湍急的人潮中。男孩的成長史與宏大的歷史反思在此刻相遇,幕布坍塌消解了主題的嚴肅性,各層敘事者達成了和解。“這作品是借用一個青年的自傳形式虛構而成的,為了從歷史的詛咒解放出來,我們首先必須從記憶中覓回自由。這部電影乃通過修正記憶的嘗試去追求青年自身的身份所在的位置。”[6]寺山修司在進行完整的敘事之后打破了第四堵墻,消除了屏幕的桎梏,將觀眾的反思一并放置于影片的結構當中,運用特殊的敘事實驗手段書寫一段少年時代的挽歌,完成了一場近乎完美的影像裝置。
四、結語
寺山修司是一位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自我解剖與詮釋的導演,他的影片善用反復出現的意象和特殊的童年經歷闡述日本戰后的傷痛主題,將鏡頭對準自己進行凝視,在詭譎未知的影像中體現出尖銳性和顛覆性。《死者田園祭》的創作是寺山的一次“逼近自我身份的苦澀追求”,他以自我白日夢為鏡像映射出未曾發生的經歷,在自我凝視的過程中又將其親自打碎,用奇幻化的視覺呈現完成鏡中自我的涂畫書寫。
參考文獻
[1] 趙靜蓉.在傳統失落的世界里重返家園——論現代性視域下的懷舊情結[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04).
[2] 楊鵬鑫.電影敘事的九種層級關系及層控問題[J].當代電影,2023(02).
[3] Patrick Fuery and Nick Mansfield. Cultural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J].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 楊鵬鑫.電影敘事的九種層級關系及層控問題[J].當代電影,2023(02).
[5] 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M].第11版.焦雄屏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
[6] 侯克明主編.多維視野:當代日本電影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