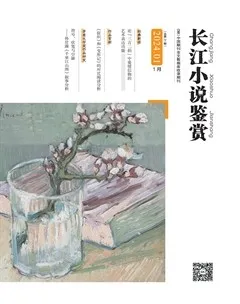《殺手》對話中的隱性沖突
胡斯淇
[摘? 要] 《殺手》充分體現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全篇多由人物對話組成,人物基于自身所處的認知環境發聲從而使得這個表面簡短平靜的殺人故事處處有留白。本文將基于小說對話,結合作品創作的現實背景信息,針對人物對話在故事背景、人物關系、情節主題上存在的隱含意義進行分析,挖掘隱藏在人物對話中的多重現實沖突。
[關鍵詞] 《殺手》? 對話? 現實沖突
[中圖分類號] I106?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1-0052-05
《殺手》講述了兩個殺手來到亨利餐館,挾持店內三人意圖暗殺拳擊手,因拳擊手遲遲未至選擇先行離開,在殺手離去后,服務員尼克去告知安德瑞森此事,但拳擊手坐以待斃的態度讓尼克感到恐懼,尼克最終選擇離開小鎮。小說充分體現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人物對話占據小說主要篇幅,表面上看,作者好似一個隱身的局外人,僅僅只對事件進行記錄,但在人物看似波瀾不驚的對話下卻是作者對多重現實沖突的隱性呈現。
一、對話中隱匿的現實暴力沖突
讀者隨著“亨利餐室的門開了,兩個人走進來”[1]直接進入文本,作者提供一個故事能自由展開的場所后就隱身于文本,讓小說中的人物來演繹。這場暗殺的背景信息被作者以一種模糊甚至是空白的狀態呈現,但“文學作品的意義未定性與意義空白,決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作品的缺陷,相反是作品產生效果的根本出發點”[2]。背景信息的留白并不等于故事基柱的殘缺,反而促使讀者從閱讀之初就隨著人物對話的展開去多角度解讀文本的隱含背景,挖掘作者對現實暴力沖突的隱性呈現。
作者通過人物對話交代了山峰小鎮上的亨利餐室和赫希寄宿舍是故事發生的兩個地點,余下的背景信息皆被隱去,若非喬治在故事結尾說了一句“他一定是在芝加哥卷進了什么事”,讀者很難將故事背景與現實中的芝加哥聯系起來,海明威也曾說過他在小說中將整個芝加哥都省略了[3]。結合《殺手》的創作時間和作者此前在芝加哥的生活經歷,讀者不難推斷出山峰小鎮是作者用以影射20世紀初的芝加哥的一個縮影。海明威將暗殺安排在這個背景模糊的亨利餐室中,又特意在故事快結束時提及拳擊手是在芝加哥惹上的麻煩,實際上是借小說前文中地點背景信息的留白來著意突出芝加哥這個現實地點。因為20世紀初的芝加哥是一座犯罪之都,各種暴力事件都在這座城市出現,小說的暗殺矛頭指向了處在暴力中的芝加哥。
人物對話中暗藏了芝加哥在20世紀初出現的“酒”沖突。小說有一段關于“酒”的簡短對話,艾爾兩次問“anything to drink”,兩個drink前為正體,后為斜體,作者故意為之卻并未向讀者闡明緣由,促使讀者關注兩個drink所指的差異,艾爾口中drink一直指向烈性酒,喬治的第一次回答將drink指向店里的啤酒、佐餐酒、姜汁水,這才產生了艾爾第二次帶有強調性的追問;喬治的回答無法判斷他是否真的誤解了艾爾之意,還是因殺手是外來者所以拒絕提供烈性酒。小說并未談及為何酒成為人們對話中的隱晦話題,讀者只有從故事創作的時間切入才能得知此時美國正實行禁酒令,所以艾爾才隱晦地用drink代替了酒。但艾爾為何會在一個標明餐室的地方問酒,這說明亨利餐室很可能私下售賣烈性酒,不在場的亨利也許是去暗中經營私酒業務,而當時私酒業最繁榮的地方就是芝加哥,小說的背景空白在與現實的聯系中被進一步充實。禁酒令的出現與一戰后美國財政壓力變大、酒業受壓,以及美國新教徒保守派的禁酒宣傳等因素密切相關,支持者認為禁酒會提高人的道德水平、減少暴力事件,但事與愿違,禁酒令反倒促使走私盛行,起初只是愛酒的美國人因為禁酒令會去被稱為Speakeasy的地下酒吧或私自釀酒。隨著私酒業利潤變大,黑幫從保護地下酒吧轉向發展私酒業務,從走私、釀造到售賣,形成了完整的私酒產業鏈,不同黑幫團體間為了賺取豐厚的利潤而不斷擴張勢力范圍,由此產生了許多惡性暴力事件。芝加哥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也與黑幫勾結,甚至當時芝加哥市長也是被稱作“芝加哥地下市長”的黑幫大佬卡彭推舉上臺,社會上黑白勢力交雜,槍支、爆炸、殺人等沖突事件反倒因禁酒令的頒行變得更加頻發。小說中有關drink的對話看似是人物的隨意交流,實質是作者在借對話中drink所指和能指的豐富性影射美國禁酒令所暗含的暴力沖突。所以后文中麥克斯對喬治說的那句“你應該多看看電影,像你這樣的聰明小子,看看電影有好處”[1]并不突兀,只有帶有暴力色彩的或是涉及黑幫沖突的電影才會讓殺手作出積極評價,麥克斯的話也說明暗殺走進屏幕實質上就是社會暴力以另一種形式合法化,且殺手從言語中流露出對身份的認同和驕傲,無疑都佐證了暴力頻發的現實社會。因而麥克斯說的那句“This is a hot town”不僅可解讀為麥克斯用hot形容小鎮天氣炎熱,更大可能則是暗示了小鎮即將發生的暗殺危機,作者暗示這個小鎮或未明說的芝加哥是暴力沖突頻發之地。
小說的地理背景信息由模糊走向清晰,并且模糊程度越深,越能使讀者在后文關注到芝加哥——這個現實的地點,對這次暗殺事件描述得越平靜,越是充滿了對現實暴力的諷刺,作者將所處社會中的現實暴力沖突通過背景的空白隱晦地傳達給了讀者,引導讀者從小說中虛擬的殺人沖突走向現實中的暴力社會,去感受暴力沖突后無法消散的創傷氛圍。
二、對話中隱匿的人際關系沖突
《殺手》中人物多是基于自己所處的認知環境發出聲音,人物因個體性格和社會身份的差異在對話中產生多重人際關系沖突,讀者唯有隱身于文本進入不同人物的視角才能探析到對話中的隱含信息。
在亨利餐室內,兩個殺手和喬治三人間因實力懸殊在對話上呈現出強弱善惡的對立沖突。首先,殺手多用命令式語句操控著喬治三人的動作,如“Tell him to come in/Go on back to the kitchen,
nigger/Listen...Stand a little further along the bar”[4];其次,他們缺少禮貌用語,點餐時直接說“give me chicken croquettes/give me bacon and eggs”[4],還在對話中多次使用一些俚語和侮辱性話語,如殺手知道喬治和尼克名字后仍喚其“bright boy”,結合語境這更像是一種上位者對下位者的調笑和嘲諷,而不是禮貌的夸贊,他們用“the nigger”代指廚師是最直觀地對弱者的言語侮辱,他們的言語中充滿了傲慢無禮和野蠻粗俗,流氓式的話語“the hell you were/what the hell/why the hell”[4]已然是其口頭語。在對話中殺手壟斷了長句,言語的數量也明顯高于喬治三人,這些語言特點既說明了殺手霸道、狡猾、兇狠,也很符合殺手的身份。喬治三人的話語則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喬治在察覺到殺手的身份后在對話中多用一些帶有附和性的回答或是一些重復性詢問,小說里喬治目睹殺手要挾尼克和塞姆進廚房后開始選擇沉默,“麥克斯說,眼睛盯著鏡子‘你干嗎不說話?……‘我不愿說。……喬治一句話也不說”[1],都說明喬治在通過減少發言來自保,更不用說尼克和廚師在餐室中幾乎是被動失聲。殺手是這個餐館的外來者,但因為其力量強于喬治三人,便在餐館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喬治三人在行動和言語上都受到限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殺手和喬治三人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立沖突。
人物對話中還隱含了種族沖突。艾爾讓喬治叫廚師出來的那段對話中:“‘誰在廚房里?‘那個黑人。‘什么意思,那個黑人?‘做菜的黑人。‘叫他進來。‘那么要對他干什么?‘沒什么。動動腦子嘛,聰明小子,我們會對黑人干什么?”[1]在原文中喬治的回答是“the nigger/the nigger that cooks”[4],為何喬治先強調廚師的黑人身份,后文喬治喚廚師出來時稱呼了廚師的名字“塞姆”,這是他和廚師即將同處一個空間時做出的表面上的尊重,而之前廚師在另一個空間時,喬治對他的稱呼和對其黑人身份的強調無疑說明即使是在這場暗殺事件中,同為弱勢的一方彼此間也存在社會種族的高低之分。而殺手對黑人的態度更加惡劣,艾爾和喬治都明確知道黑人的社會地位,所以當喬治明確地問艾爾他會對這個黑人廚師做什么時,艾爾的回答則是帶有誤導性地默認了喬治的認知,即他大概率會去傷害塞姆,而且艾爾一直對塞姆使用“nigger”這個極具侮辱性的稱呼。所以通過喬治和殺手對黑人的稱呼可以看出,在某種程度上,兩個殺手、喬治、尼克四人成了一個團體,他們同塞姆變成了對立關系,社會地位最底端的塞姆同時受到來自強者的壓迫和種族霸凌,由此可知種族沖突并非單純發生在小說中,而是在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在所謂人人平等的口號面前,白人牢牢掌握話語權,黑人長期遭受種族霸凌。小說中的對話片段影射了美國現實社會中弱者被動陷入暴力沖突之中并喪失話語權和生命權的現實。
人物間隱形的價值觀念沖突亦借由對話的空白表現出來。通過對話,讀者可以看出麥克斯性格沖動,話多且缺少警惕,與喬治交流時甚至主動說出暗殺的動機和目標;艾爾則嚴謹審慎且經驗豐富,言行上具有很強的計劃性和目的性,其敏感狡猾和心狠手辣較麥克斯更勝一籌。暗殺失敗后,“‘走吧,艾爾,麥克斯說。‘這兩個聰明小子跟黑人怎么辦?‘他們沒問題。‘你以為沒問題?……艾爾說:‘干得拖泥帶水。你話說得太多。”[1]艾爾提問的弦外之音是為避免消息泄露意圖滅口,但麥克斯拒絕了他的提議,艾爾譴責麥克斯做事拖泥帶水的話語暴露出兩人在對待無辜生命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同為殺手,艾爾比麥克斯更冷酷無情。而喬治等三人雖同為弱勢的一方,彼此間也存在價值沖突。在殺手走后,喬治對尼克和塞姆說了殺手的目標是安德瑞森,廚師的反應是不斷強調自己與其無關,并勸尼克裝聾作啞別插手這件事,由此暴露出他的膽小怕事。喬治則是矛盾的,喬治應對殺手的鎮定自如說明他對當時社會的游戲規則有一定的了解,也明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他知道殺手的危險性仍支持尼克的選擇,說明他有“利他”的一面,同時,當他與殺手產生直接利害關系時他會機智地與其周旋,而當他察覺自己危險解除時他會因畏懼暴力選擇成為一個“利己”的局外人,所以他作為第一個知情人卻將殺手的暗殺目標轉述給尼克和廚師,支持尼克也是基于尼克的話語順勢而為,言語間處處透露出其圓滑世故的性格特征。而尼克還保有少年的單純與正直,他和安德瑞森不熟,但對暴力的排斥讓他選擇立刻去告知拳擊手,三人在“利己”或“利他”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無論是在兩個殺手之間,還是喬治等三人之間,個體性格的差異和外在社會因素促使他們在“利己”“利他”之間做出了不同的價值選擇,無形中形成了多重價值沖突。
海明威在冷靜客觀的描述中從不過度渲染和表現人物形象,但通過人物的聲音讀者卻能感知文本中隱匿的多重人際關系沖突,海明威對人性復雜面的了解也由此可見。
三、對話中隱匿的虛實沖突
小說對話是有限的,對話中的未言明之處使得小說情節上虛實結合,促使讀者從文學文本的表層敘述去多角度探析作者在小說背后隱藏的對人性善惡、生死存亡等現實沖突的思考。
表面上看,故事就是從五點二十分開始,但實際上,這個時間元素從開始便是不確定的。“‘那是正餐,喬治解釋。‘六點鐘才供應。‘現在五點。‘鐘上是五點二十分,第二個人說。‘這鐘快二十分。”[1]墻上的鐘是否真的壞了,如果壞了為何無人修理,如果沒壞,那么喬治告知艾爾時間快了二十分鐘是出于何種目的,是因為擔心未能供應餐食招來禍端,還是為了保護或掩藏什么?隨后喬治說安德瑞森日常來亨利餐室的時間是六點,這是不是真的?殺手后來看見時間晚了選擇再等待十分鐘、五分鐘,他們是不是也意識到喬治所說時間是假的?故事發生地亨利餐室也存在很多空白,從亨利餐館這個名字可以推想這個餐館的老板叫亨利,但是縱觀整部小說,亨利始終是缺席的,那么亨利與打理餐室的喬治是什么關系?亨利的不在場是不是與殺手找到亨利餐室間有著某種密切的關聯?無獨有偶,安德瑞森租住的是赫西太太的公寓,但赫西太太也缺席了文本,出場的貝爾太太與赫西太太間又有什么關聯?時間的不可靠、相似的人物缺席和人物關系的模糊讓故事呈現出模糊性,而這種不確定最終指向的是那個充滿荒誕的現實社會。
海明威創作《殺手》時,戰后的美國雖然在經濟上出現了短暫的繁榮,但社會繁榮背后失業率攀升、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變大、暴力事件等社會問題頻發,不少人仍沉迷在物欲享受之中,人們精神空虛,陷入道德墮落的困境。而海明威對世界走向荒誕和人性走向罪惡是持批判態度的,《殺手》中殺手形象的矛盾性就是最好的例證,海明威在最后描寫殺手離場時形容他倆“像一對演雜耍的搭檔”,使得這對本應是兇殘狠辣的殺手形象在結尾突然具有諷刺的喜劇感,這句旁白是作者在對殺手的暴力身份作出隱晦地批判。而喬治那脆弱的關懷,黑人廚師表面的好意提醒無疑折射出現實社會中人的冷漠麻木和卑微虛無,通過這些人物精神上的“虛無”,讀者能想象到作者所處社會的荒誕。
迷惘一代的出現正是基于上述罪惡、荒誕、空虛的社會環境,作者作為迷惘一代的代表性作家,其創作的《殺手》從模糊和空白開始,最終也是以一種留白狀態結束,這種留白恰好對應了現實中迷惘的人生狀態。故事的開頭是“亨利餐室的門開了,兩個人走進來”[1]。殺手為了殺拳擊手而來,但他們的殺人動機卻是空白且荒誕的,空白是因為殺手是替人殺人,那個真實的殺人動機只有故事中的安德瑞森或是雇傭殺手的人知曉,但讀者受限于敘述視角無法得知,這個故事的出發點就是模糊、荒誕的,所以殺手來到這個小鎮后表現出一種混亂、茫然的感覺,他們在餐廳里隨意交談,拿餐廳的員工消遣取樂,甚至還暴露殺人目標,其言行更像是在等待過程中隨意打發時間,將整個暗殺過程變成了一次消磨時間的無意義行動,既不符合殺手的身份,也完全沒有考慮行動失敗所帶來的危險,他們對自己的行動意義和殺手身份的存在意義完全不在乎,生命的寶貴性也早已被他們忽略。被殺者安德瑞森也是如此,當尼克告訴安德瑞森有人要殺他,并勸他去報警,他卻冷淡地拒絕了,他放棄自救的情節也給讀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間,為什么安德瑞森作為拳擊手卻如此消極?而他被人追殺的原因也不是小說中“我得罪了人”可以一筆帶過的,但這種消極的態度和那兩位殺手對暗殺任務的隨意態度卻有著不謀而合之處。由此,作者更像是借這次事件來反映迷惘社會中人們的空虛、無聊和荒謬,人們都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接受了被現實、暴力、罪惡所捆綁的命運,也無力去思考如何解決當下的困境。行動的成功與否,生存境遇的好或壞,生命價值的可有可無都歸于空白和虛無之中,小說留存的情節空白仿佛是對迷惘一代精神空虛、悲觀茫然人生態度的暗合。
海明威并沒有真正提供解決這種迷惘人生的方法,所以小說也是以空白狀態結束。結尾處尼克決心離開這個鎮子,尼克說:“我準備離開這個城市;他明知道自己要被殺,還在屋里等死,一想到這個我就難受。媽的,太可怕了。”[1]尼克的形象相較于其他人無疑是更為飽滿的,開始時尼克單純、善良、熱心,會因為自己大難不死而激動,也會因正義感去通知拳擊手,但在目睹拳擊手的消極等死后他開始對這種被動等死的狀態感到恐懼,他最后的選擇便是作者給讀者留下的最大空白:尼克的選擇可被解讀為是一種區別于他人麻木度日的勇士行為,他因為受到心靈震撼而促使他要逃離這個環境。如果尼克選擇留下,那么類似的事情仍會發生,看慣了別人麻木的生活,不管他是保持初心還是變得與他人一樣都會是一種痛苦和折磨,所以尼克的選擇可以被解讀為暗合了海明威一貫主張的硬漢精神,是對“生”的一種積極追尋,他的離開正是對這個冷漠麻木且喪失生命力的小鎮的反抗。但是這種選擇還留下了另一種解讀,即尼克的離開是一種逃避的選擇,因為經歷的這次事件已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圍,安德瑞森作為拳擊手在暴力面前尚且無能為力,彌漫著暴力氛圍的社會又該如何逃離?安德瑞森的消極態度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的離開是毫無意義的,他也是迷惘的,可以想象,他離開后很大可能只是不斷改變居住地,然后到了某一天,就像拳擊手拒絕尼克建議時說的“這樣跑來跑去,我跑夠了”[1]。尼克最終也會困于一隅,望著自己面前的“墻”,消極地結束自己的一生,尼克的生存意義最終仍是空白的、虛無的,他不過是重蹈無數個迷惘之人的覆轍。所以小說最后的結局其實是空白的,當這種空白被解讀的時候,一種關于人生的積極與消極、充實與虛無、生與死的沖突就呈現在讀者面前。
《殺手》中沒有完整連貫的故事情節,人物對話也存在信息省略,正是這種空白和省略映射出作者對社會現實荒誕、人們精神迷惘、正義缺失、生命虛無等問題的思考,小說主題意義的未定性得以讓讀者重新審視人生的意義。
四、結語
海明威深刻揭示出現實社會中陰暗的一面。但是在他的小說中現實社會里的暴力沖突、人與人之間的強弱沖突、種族沖突等都被隱藏起來,代之以客觀平常的人物對話將故事呈現在讀者眼前。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使得對《殺手》對話空白中的價值解讀并不局限于對現實沖突的影射上,文本中人物對話的空白并非空洞和虛無,反而給讀者留下更大的思考空間。
參考文獻
[1] 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說全集[M].陳良廷,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2] 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3] 董衡巽.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4] Hemingway E M.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責任編輯 羅? 芳)